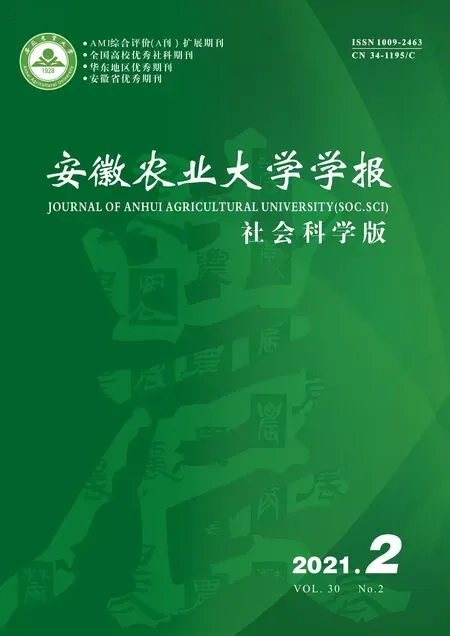“花腔”式叙述中无法探寻的真相
——利己主义视角下的人性思考
王启俊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2)
《花腔》是李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写了红色知识分子葛任悲剧性的一生,展现了一群知识分子在特定年代的心路历程。小说通过各类“花腔式”的叙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残酷和无奈,直面人性的自私与邪恶,直面善恶时的生死抉择。小说主体部分为三位叙述者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关于葛任生死情节的叙述。他们对葛任死于大荒山的有关细节陈述,令人真假难辨,而对葛任的出生至二里岗战斗之前的叙述却显得异常清晰,这种“花腔”着实令人困惑和诧异。
一、“花腔”之声的本意
“花腔”一词在小说中有两种解释。一是西方的舶来品,“花腔是一种带有装饰音的咏叹调”,与本土的文化经典《二月里来》形成了二元对峙;二是民族的、民间的用词,“耍花腔”,指言不由衷,“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不管是带有装饰音的咏叹调还是巧言令色的“耍花腔”,都是对原本声音或语言的一种掩饰或矫饰。因为腔调不够纯正,作者在小说中也借领导之口给出了自己的态度,“但领导说了,美国人来后,最好还是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的《二月里来》”,《二月里来》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声音,至于花腔则上不了台面。
在小说中,花腔所体现的不仅指利己主义趋势下人性趋于虚伪和丑恶;同时,花腔也是人性好坏的分割点、聚焦点。 “耍”与“不耍”“花腔”就在善恶一念之间,耍花腔的经历着人性善恶考验;花腔更是混淆视听的方式,即便是小说中三个主人公都一再强调其所述属实,但仍然难以避免怀疑;花腔是真与假的搅拌器,或最终将人们的认知引向歧途,而这也正是它的存在方式。“人格担保仅仅是一种道德担保,而道德并非解决一切的良药”。
如文中所述的主人公葛任的岳父胡安,倾尽家财投身革命事业,伪造假币扰乱国民党经济社会秩序,对国统区的金融稳定产生了破坏作用,但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的革命者,在一场演出后中枪身亡。其死因解释有三种:被国民党派人击毙、被共产党内部肃清、现场群众太入戏失手将其打死。没有人去为他的死正名,没有人提及其为革命所做的贡献,更没有人为他记载和追忆,他的一生就这样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各类角色花腔节奏鼓动下,在人性和时间的双重作用下,真相本身已渐行渐远,真假难辨。
文中两条叙事线索也诠释了花腔的性质。一条是主线,即医生白圣韬、人犯赵耀庆(阿庆)以及著名法学家范继槐的叙述,他们的叙事有时间、地点、听众、记录者、录音等,客观性、关联性、真实性似乎无懈可击,但三者的叙述之间存在诸多互相矛盾之处,只能姑且认为这是在耍花腔,或者就可以认定他们确实在耍花腔;另一条是副线,即革命者葛任还活在世上的唯一亲人“我”的追踪探寻,通过引文的方式对前面三位叙述者的明显的遗漏、悖谬做出了必要的补充和梳理。将“我”的叙述直接植入小说文本中,似乎也在表明揭示历史的真相不是作家的唯一任务。“花腔”的本意还在于引导“个人”去揭穿“花腔式”叙述制造出来的假象,并在“花腔”的迷雾中进行真相探险。正如米兰·昆德拉说:“如果一个作家认为某种历史情景是一种有关人类世界新鲜的和有揭示性的可能性,他就会想如其所是地进行描写。但就小说的价值而言,忠实于历史的真实仍然是次要的事情。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先知,而是存在的探险家。”
二、“花腔式”叙述者视角下的人性主题表达
时间可以淡化历史的真实,但无法促使人性的根本改变。分析李洱先生至今创作的作品,无论长篇还是短篇,他试图在叙事中展现生活和人性真相。通过对文本的建构以及叙事形式的多变,将人性乃至知识分子的人性特点传递给读者。小说通过叙述者的叙事话语,展现更深层次的语义,在这样一种叙述结构里,作者围绕“人性”一词,构成自己话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人性主题进行探讨。在某种程度上说,人性是有其自私利己的一面的,在自私一面的支配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利己主义者。
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三位叙述者根据他们的回忆来完成的,不再是昨日重现,而是基于现实的重建。“我们的回忆本身,就有重建过去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回忆总是立足于现在的需要才产生的”。三位叙述者围绕葛任死亡情节的叙述,更像是魔术师的指挥棒,变幻莫测,似乎每个表现者都极力证明他所呈现的就是事实本身。但实际上,小说通过“我”的搜寻各种资料,并加以印证推敲,发现“事实”却是被掩盖的,真相仍扑朔迷离。“虽然三人的话语类型各具特性,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把握人物性格的能力和对时代语境变迁的敏锐捕捉,但当把它们联系起来,构成了多元对话形态时,读者往往又会陷入了这样一种花腔式的话语中不能自拔,找不到关于葛任的真实历史,只能在迷雾重重的话语中感悟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
(一) “避实就虚”的无奈
在白圣韬的叙述话语中,无时不透露出一些知识分子人性中欠缺的一面,知识分子的困境往往在于过度维护所谓的尊严和形象,从而容易在判断选择上做出避实就虚的矫饰。
白圣韬以医生为职业,最终成为革命的叛变者。1943年抗战时期,他被国民党中将范继槐由白陂镇押解至香港,途中向范继槐转述葛任的死因。由于白圣韬特殊的身份和承担着处决葛任的任务,当他面对范继槐时,自知如果将所有的秘密和盘说出,事后延安方面定会对其加以追究;若他一点秘密都不透露,就没办法逃脱范继槐的控制。当时的处境决定了白圣韬的叙述必然虚与委蛇。他把自己叙述成不畏艰难一定要把葛任救出来的铁骨铮铮的硬汉形象:“倘若能用我的死换来葛任的名节,换来我丈人和儿子的平安,那我白某人的死不也是重于泰山吗?”他的叙述掩盖了真相,在是否执行上级命令的犹豫之中和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之下,只求自保而无暇顾及其他人,无意真正去营救葛任。
(二)“明哲保身”的怯懦
在特殊年代,知识分子开口说话时,多会表现出犹豫不决的状态,他们往往沉思默想,明哲保身。赵耀庆是潜入军统的地下党员,是葛任家中仆人的孩子,葛家资助其读书求学,曾与葛任情同手足。他的叙述是在劳改农场中进行的。赵耀庆叙述的时间是在1970年的“文革”时期,处境并不比白圣韬自由,加之当时“劳改犯”的身份,他的叙述只能避重就轻,否则,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命丧黄泉。他在叙述时察言观色,谄媚不堪。为了麻痹审讯者和使叙述更加趋于合理性,他需要不断地征求审讯者的意见:“还是从头讲起?嗐!那还用说,向毛主席保证,俺的每句话都是实话。葛任早就说过,阿庆同志是个老实人。”“俺就这样讲,行吗?好,那俺就接着讲。”同时,阿庆还运用获取香烟、酒菜等方式及无厘头的语言扰乱审讯者的判断,在叙述营救葛任的情节中,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向白圣韬,以致说白圣韬背叛了党,迟迟不肯营救葛任并带他离开。他的叙述诿过于人,缺乏担当,掩盖了他本人不积极营救葛任的真相。此人蒙昧无知,见风使舵,参加革命的出发点也只是获得实质性的利益,是田汗(精于权术的“革命家”)手中的一枚棋子。
(三)权威粉饰的虚伪
在作品中“众生喧哗”的状态下,花腔般的叙述为叙述者提供了广阔的话语场。在这个场域中人性的善恶最需要探寻的就是知识分子中某类人的虚饰。范继槐的叙述以“OK,彼此彼此”开始,讲述的背景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个人物形象展现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想开口说话时候的心理状态,却又发出虚伪又饶舌的腔调,需要对其说话的初衷进行破译。与前两位叙述者不尽相同,他的身份显赫,曾是国民党军统的中将,现在德高望重,是国家级的政协委员。他是葛任之死的亲历者,更是实施者,是他设计让葛任死到日本人(石井)的手中。因其现在“法学泰斗”的身份,出于严谨或者是为了爱惜自己的羽毛,以及为了以后的传记,他不动神色地对历史事实进行修饰,并将自己包装成绝对权威的形象。他深知胡适说过的“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话,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敢说别人知道的都是一鳞半爪。白圣韬死了,赵耀庆死了,冰莹死了,田汗也死了,有关的人都死了,就留下了我老范。我若咬紧牙关不吭声,这段历史就随我进八宝山了。”这样一个“泰斗”式的人物,他的叙述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唯一性,就像卡尔所说:“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程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他的所说正是小说中的“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可是他的叙事又时不时地透露出自傲的情绪。正因为他的叙述具有唯一性,其叙述的情节到底有多少可信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把营救葛任的想法寄希望于杨凤良和阿庆,但他们却都没有付诸行动,这直接导致葛任的牺牲。即使这样,也被范继槐粉饰为是为了“成全”葛任,是对葛任的终极的“爱”。
(四)叙述碎片整合后的人性归位
三位叙述者的叙述,就像葛任的代号“O”,自圆其说形成闭环,可是由于时间久远等原因,当我们把三者进行比照的时候,就会发现诸多荒谬之处。因为“人们只在过去的时间中认识现实。人们不认识它在现在时刻,它正在经过的时刻的那种状况。然而现在时刻与它的回忆并不相像。回忆不是对遗忘的否定,回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小说中另外一个叙述者“我”发现了其中诸多疏漏之处,这是代表着其他众多亲历者发出的声音。
电力营销主要指的是在电力市场中,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基础,对电力产品以及相应的服务进行销售从而提升电力企业社会满意度的一种营销方式。在具体的营销过程中会是用到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等处理方式,从而进一步确保用户用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电力营销的实际应用中,需要对企业内部的服务进行科学评估和处理。
这里的“我”整理出了叙述的碎片,就作品中“我们怎么说”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人性本性善恶的探索。在解决这一难题的基础上,“我”是一个人物,但又不仅仅是一个具象的人,不仅是揭露真相、探究人性的代表,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复杂的特定的时代中能否做到独立自处和保有尊严的发问者和探究者。
作者在卷首语中这样写道:“我只是收集了这些引文,顺便对其中过于明显的遗漏、悖谬做出了必要的补充和梳理而已。”我只是一个呈现者。正是通过这种补充叙述的方式来对正文部分进行印证或者辩驳,以增加情节的真实感、丰富感以及历史感。当通过“我”的视角来剥离三个叙述者所耍的“花腔”时,我们看到了利己与自私的真相,以及特定历史背景下“个人”坚守人格独立向善的艰难。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葛任所代表的“个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对生存法则“挑战”时的艰难。葛任最终被吞没在“残酷斗争”的汪洋之中,他用自己的牺牲,实现了“个人”的价值追求。
三、真相无法探寻的原因
小说“花腔式”叙述者视角下的人性主题表达,一方面展现了对葛任之死无法探明的真相,另一方面也揭露出那个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小说叙述的重点不在于阐述事实真相的一般规律和应当遵循的常识,也不产生关于事实真相的正确推导,而是通过叙述葛任的生死情节的细枝末节,提出关于探寻真相的问题,体现出深刻的觉醒意识和追求意识。关于历史的“真相”,小说运用大量的细节营造出事件的真实氛围,扑朔迷离的多重讲述文本让读者产生一种信息的不确定感与陌生化的阅读效果,使读者与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甄别历史,去探究作品深层的意蕴。作者李洱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我们对真相的探寻,明晰人性趋利避害之恶和特定历史环境下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人格的艰难。为什么真相难以探寻?究其原因,主要是个人选择以及时代的主导影响。
(一)利己主义的选择
“小说的真正敌人,不是近代的哲学和科学,而是现代之前的宗教——道德伦理的生活教条:区分善恶和对生活道德明晰性的要求”。善恶抉择之艰难,是小说中三个叙述者的暗含情感。在生与死的革命斗争面前,不管是曾经的战友、玩伴、同学,都将接受着善恶的“二选一”的抉择。黎鸣曾在他的《问人性》一书中指出,人性偏向善的可能性为百分之十,偏向恶的可能性为百分之九十——占绝对的优势。罪恶充斥的时空,引导人们不得不滑向罪恶的深渊。善良是需要生长环境的,是需要仁者爱人的大环境才可以生存的,否则,羸弱的善良是无法直面邪恶的,最终将被邪恶无情吞噬。鲁迅曾在《狂人日记》中描述了一个人吃人的时代,一个易子而食的时代,小说《花腔》中也通过不同的语境提到了“易子而食”,这不就是对那个时代的隐喻吗?在那样一个吃人的时代,对真、善、美的坚定似乎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经不起风吹雨打。
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他们有着知识分子本来具有的人文情怀和追求真理的特质,另一方面他们在各种切身利益诱惑下,也存在着质疑、彷徨、拷问、失落等精神焦虑。在面临种种选择的情况下,精神与本性产生冲突,焦虑和矛盾致使他们人性中的利己主义占据主导位置。对葛任则坚定地判处他“死刑”,判处的依据是葛任必须死,这是为了他的名节,也是为了他好,为了对他的爱。这一判断有悖于道德,但是却“合理”地存在了。正如刘小枫所说:“一般来说,邪恶之所以会滋生,是因为人们总会在某个阶段发现自己没有能力行善。邪恶的原因是挫折感。无论人的改变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外面也不可能对人为什么会无力行善做出结论,因为理由太多了,有成百上千种不同的理由!”
(二)“莫比乌斯环”式的时代困境
作者笔下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一些新式教育,但并没有彻底改变传统小农思想的劣根性。他们虽然有内心坚守与人格独立,却同时也存在着软弱和妥协。面临着生死名利的抉择,一方面他们曾引以为傲的仁善教育在那样一个时代就显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却又无路可走。萨特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行动,在一系列选择和行动中展现自己的本质。”确实,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知识分子探寻出路的“自由性”变得极为突出,尤其是在面临动荡的环境、言论无法自由、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从利己主义出发做出恶的选择。从本质来看,知识分子这样的抉择,让他们从“不合时宜”变为圆滑世故,是他们与现实世界宣布对抗的一种方式,也是其独立人格向现实的无奈妥协。这种恶的选择,像拓扑学结构“莫比乌斯环”一样循环往复,无法消除。
这一群知识分子内心清楚,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环境里,人的善良或是直言或将给自己带来祸患。比如邱爱华的死以及白圣韬被打成“托派”,都说明人的真、善、美被控制隐藏,成了不可祈求的东西。白圣韬前往白陂镇的路上,看到一个穿短褂的老人,拎着棍子追打一个女人;在德兴镇的酒店中,掌柜杀了一个盐商,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后来还将盐商的骆驼做成了骆驼肉砖。这些恶行都无形中影响着白圣韬,让他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做出选择,在“范继槐到达之前,葛任的病体虽然虚弱,但骑马转移应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对葛任判处了“死刑”。
所有导致葛任之死的刽子手们演绎了一场以“爱”之名的把戏,他们出于“爱”都一心希望放走葛任,但又不约而同做出“恶”的选择。时代环境影响下的这种“罪恶”不仅令人恐惧,而且比真、善、美更具有传染性。丑恶一旦被传递,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白圣韬受到了“罪恶”的传染,没有营救葛任;赵耀庆因为受到白圣韬的影响,不愿营救葛任;范继槐受到了前面几个人的影响,认为没有必要救葛任。整个情节就像是一个“莫比乌斯环”式死扣,如葛任的代号“O”,根本没有办法将其解开一样。知识分子在利己主义和从众心理驱动下,心甘情愿做出“恶”的选择并传递和循环,拒绝找出人性的“生门”来自我救赎。
四、利己主义引导下的人性思考
在整部小说中,我们不难从飘忽不定的叙述中嗅到利己主义的刺鼻味道,这种味道的载体就是“花腔”,就是小说的主题。在这种“花腔式”的叙述中,小说主人公葛任如沧海一粟,根本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哪怕是这个“个人”曾经救过“刽子手”的命。范继槐曾说过,在长征之前,葛任害怕范继槐被清洗,曾劝其离开,让其逃过一劫。但是即便如此,也难唤醒范继槐这类人心性中向善的一面。作者的意图也是想通过叙述者们“花腔式”叙述呈现出来的众生相,对人性进行鞭笞,进而唤起我们对历史、权威、伦理制度的反思与质疑。李洱说:“在我写作《花腔》的最后一段的时候,我特意提到了‘爱’这个字眼。由于意识形态的积弊,‘爱’这个最纯朴的字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许多人那里, 变得含混和暧昧了,它变成了借口,变成了花腔。可以说, 我写作《花腔》的一个重要动机, 就是对各种意识形态上的积弊进行清理和辨析。”“意识形态上的积弊”,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封建文化遗毒中的阴谋思想体系。
小说主人公葛任原名叫葛尚仁,即“崇尚仁义”,是“利他”的体现;后改名“葛任”,音同“个人”,则隐喻利己和利他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个人”具有深刻的辩证象征意味,个人是决定利己还是利他的关键性因素,是坚持德心仁厚的底线,还是坠入邪恶的深渊,都取决于个人的决断。小说情节也是通过对主人公葛任死亡情节的叙述,揭示利己与利他的转化脉络。在面对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会对“活着本身”产生一种奢求,人会自然而然从利己主义视角下突破善恶的底线,人类的亲情、友情、知识、良心都会被生存的欲望所取代。
三个叙述者的时空设定呈一条纵向的直线,在谈论葛任之死上几乎没有交叉点。他们对葛任之死情节的描述也透露了一个隐含的信息:人总是趋利避害的,他们释放出的“烟雾弹”,既迷惑他人,又麻醉自己,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叙述。这样的叙述与其说是追忆葛任,还不如说是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他们在有意识刻意扭曲或杜撰事实,对真相争相避讳,残忍地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
利己主义主线在“花腔式”的叙述中得到演绎和发挥。那么葛任代表的无数的“个人”为什么不反抗,而选择从容就义呢?正如作者李洱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时所说:“所有作家都是弱者,是因为他理解别人,他理解别人为什么欺负他,他能看到对方的合理性,他事先接受了这种合理性,这并不表明他没有态度。”所以,葛任虽然愿意接受死亡,但他也向范继槐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作者以小说中“我”的身份写了“尾声”,深化了利己主义视角下善恶选择的意义。尾声中说,《逸经》《民众日报》《申埠报》《边区战斗报》刊登的都是关于葛任的信息,都是对葛任光荣战死的颂扬,这象征着人性的归位。但这种人性的归位仅仅存在于这几张报纸的宣传文字之中,似乎又微弱了些。在小说的最后,白凌(白圣韬的后代)追问川井(杀害葛任的日本人)为什么没有把葛任死于大荒山的消息传播开去,虽然没有得到川井的答复,但是也足以象征着人们对于真相的执着追求,象征着对于小说中“花腔式”叙述的事实的怀疑与挑战,和敢于同利己主义作斗争的精神。而最后范继槐在其中的插话,打断了白凌和川井的谈话,似乎有意为之,用一句“花腔式”的模棱之语,将真相再一次予以掩盖。这或许象征着利己主义的恶源不会自动消失,依然会在社会中滋生、传染,会继续和利他主义的善的“个人”展开较量。人们对真相的探寻不会一帆风顺,人性的归位将成为漫漫长路,甚至是一个闭合的循环过程。就像葛任的代号“O”,利己与利他将相互转化,谁也战胜不了谁,但你我必须有清晰的态度,坚持“个人”的良善,战胜自己的一己私欲。
确实,自古以来就有人从利己主义角度出发展开对人性善恶的辩驳,这是一个古老的学术问题。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而“性善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就是“仁”。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利己和利他是属于矛盾的一体两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相互之间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个人是这一组矛盾的统一体,又兼具利己和利他的双重价值追求,在面对不同的环境和时代背景时,会做出不同的人性抉择。
小说《花腔》的出版距今已有段时间,直到《应物兄》的出版,更多人都认为其彻底超越了《花腔》的深度和厚度。反观李洱作品的创作发展,《花腔》在其作品特色中总是回避不开的重要文本。其中大量的“李洱”元素,即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探究,对于当下知识分子的本性思考是不可复制和模仿的。无论是作者的长篇还是短篇小说,他都在试图通过叙述来找寻生活真相。《花腔》中更是通过知识分子“饶舌”的叙述,探究喧嚣时代下知识分子在利己主义占上风的前提下,究竟能否坚持本心的灵魂拷问。文本中的主人公在用着自己说服自己的理由,编织利己主义的谎言。他们一面享受着独语的狂欢,一面自我纠结和权衡,最后做出分裂人格的人性抉择。
小说的故事设置,二十世纪初期,小说的出版是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但对知识分子人性的思考却可以辐射当下,启发当下知识分子对人性善恶的思索。在“花腔”的话语场中,真伪辨别永远不会停止,善恶选择也不会明确结果。对人性的思考,一直都是人性探究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