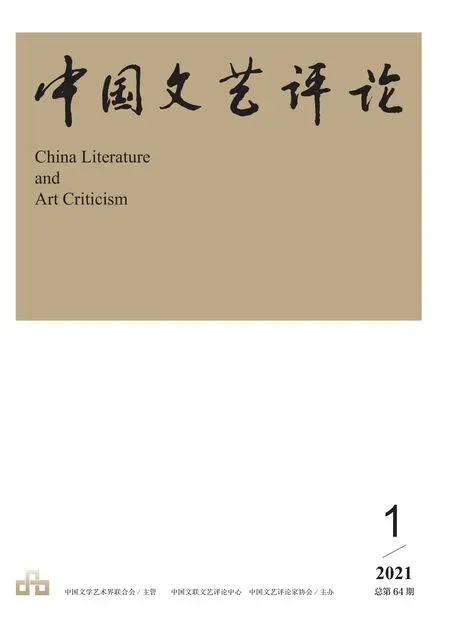“意境”范畴的现代阐释尝试
——从20世纪中叶的系列论争谈起
简圣宇
如何推动古典审美范畴的现代阐释乃至现代转型,是中国学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重要命题。特别是在强调对传统文化资源开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当下语境下,我们需要理解所谓“创新才能激活美学传统的当代意义”,既重视承接中华美学的优秀传统,以传统资源为凭依,又积极面向未来,从而构建能够回应当下理论和实践诉求的中国当代美学。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段时间,若干学者针对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之一的“意境”展开过系列论争。这次小型论争最早是由青年李泽厚发表《“意境”杂谈》一文引起,他试图用当时的话语资源和观念表述来对“意境”范畴进行重新表述。时隔数年之后,由蔡仪《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一文引发的对“典型”范畴的学术热议又让此文重获关注。学者程至的发表文章《关于意境》,对李泽厚用“典型”范畴来阐释“意境”范畴导致的问题提出批评。尔后青年李醒尘和叶朗又针对程至的“空间境象”等问题撰写《意境与艺术美——与程至的同志商榷》一文参与争鸣,认为程至的所坚持的旧意境范畴已经不能反映当代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和现实斗争的内容,其内涵必须加以扩容。
该论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者们推动古典审美范畴现代转型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当时精神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他们思想探索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已属不易。这次论争产生了相应的后续影响,如李泽厚和叶朗成熟期的核心思想在这次争论中初见端倪。李泽厚后面提倡“积淀说”即是对自己青年时期所推崇的“典型”等理论的自我反思。而叶朗日后选择以“意象”而非“意境”作为自己美学的基本范畴,也是由此意识到意象是意境生发的结构基础,而意境则是意象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展,故而理论基点必须落实在“意象”这种基始性范畴而非“意境”这种延伸性范畴之上。参与20世纪中期这次就“意境”范畴展开论争的几位学者都为了在美学领域应答时代需要而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区别只是在于探索的路径各有差异。他们在这次论争中形成的思路、见解,以及后来由此衍生出的自我批判和反思,不但对他们各自的学术生涯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当代美学史产生了延伸性影响。
一、援引域外资源:李泽厚对传统“意境”范畴的现代阐释尝试
李泽厚1959年对传统“意境”范畴所作的现代阐释尝试,代表了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研究路径:试图站在域外理论的立场,援引域外理论来重新阐释中国古典美学。他以更具现代话语色彩的“典型”来阐释“意境”,本意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传统范畴的现代阐释工作,但结果却是混淆了两个范畴之间的本质差别,没能真正初步实现传统美学的现代阐释和现代转型。这种以域外理论阐释中国经验的学术路径,没能谨慎看待两者背后所依据的知识结构和观念体系的差异性,很容易带偏当代中国美学的建设方向。
李泽厚结合自己所提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说,认为艺术是“把美的深广的客观社会性和它的生动的具体形象性二方面集中提炼到了最高度的和谐统一”,而诸如“意境”“典型环境”“典型性格”之类美学范畴则是这种艺术的和谐统一的审美呈现。他由此提出“诗、画(特别是抒情诗、风景画)中的‘意境’,与小说戏剧中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是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这两个概念并且还是相互渗透,可以交换的概念”。又阐释说:“正如小说戏剧也有意境一样,诗画里也可以出现典型性格典型环境”,“他们的不同主要是由艺术部门特色的不同造成,其本质内容却是相同的:他们同是典型化具体表现的领域,同样不是生活形象简单的摄制,同样不是主观情感单纯的抒发;他们所把握和反映的是社会现象中集中概括提炼了的某种本质的深远的真实。在这种深远的生活真实里,艺术家主观的爱憎理想也就融在其中。”
由于一开始就认定欧洲的“典型”能跟中国“意境”无缝对接,所以李泽厚试图推进“意境”范畴的现代阐释和现代转型时,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浓重的“强制阐释”色彩:预设前提地造好一个理念框架,然后把“意境”范畴塞进这个框架当中来加以阐释。不是依据“意境”范畴原本的脉络来推动其在当代语境中的转型,而是“六经注我”式地把“意境”范畴拆散在自己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说”框架中加以重组,也就未能以恰当的角度吸收域外理论,并且将之与本土传统理论恰当对接乃至融合,而是颇为生硬地将“意境”范畴与“典型”这一域外范畴“缝合”在一起。其实“意境”范畴经过长期的演化已经具有丰富复杂的思想内涵,而“典型”则是内涵容量相对有限的小范畴,以作为小范畴的后者来阐释作为大范畴的“意境”,等于是要把大象装进皮箱里。这一过程必然会造成为了达到把“意境”范畴塞进预设框架的目的而将它原本的丰富性削弱、简化到一定程度,结果不是在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和更广范围里阐释“意境”,而是将它局限在某个更小的框架中,乃至用某个时髦的现代理念来强制阐释和曲解原本的范畴内涵。
青年李泽厚这篇《“意境”杂谈》有受当时国内理论界深受苏联文艺话语影响的显著时代特征。他提出,“意境”中的“真实”,“首先‘必求境实’”,即,“要求形象必须基本上特别是外部的造型上忠于生活中的原型,符合于近似于生活的本来面目”。又云,“艺术作品的力量是它能够最深刻的反映出真实的生活的客观。”“艺术是客观生活的反映,艺术家主观情绪的抒发,也正是为了更深刻地反映。”他由此下定义称:“所以美客观的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艺术美只是生活美的集中的反映。”而且他在此文批判朱光潜理论时又补充了两点:第一,“艺术的意境只能是生活境界的反映”;第二,“艺术的意境是经由艺术家艰苦劳作的典型化的结果”。
实际上,他这一系列论述和定义暴露出此时其学术视野和理解方面的缺陷。虽然当时学界普遍以苏联反映论为尊,但苏联反映论也有其局限性。“意境”范畴有其与欧洲理论不同的学理脉络,“反映论”所强调的“客观”“真实”“生活的本来面目”等单一维度的内容,恰好偏离了中国“意境”范畴最为核心的理念。“意境”范畴跟“境生象外”理念密切相关,可谓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是对现实时空的一种拓展”。这些创生性境界存在的背后,是洋溢于天地之间、统摄一切的“生命气韵”。这种对“生生不息”的追求,表现出的是一种内在于中华文化的辩证思维和审美趣味,显然不是苏联文艺那些单一维度的、哲学化、抽象化、略显呆板的话语所能涵盖的。我们在推动传统范畴的现代阐释和现代转型时,不能孤立地将诸如“意境”之类古典范畴从其生长的传统文化生态中突兀地剥离出来,搅拌上各种现代文艺术语和观念,批量制作成一个个看似新潮、实则芜杂的“新范畴”。这类“新范畴”的外表光鲜亮丽,但既经不起当时的学理推敲,也耐不住接下来的时间考验。这种“创新”如果是一种探索路上的实验性尝试,倒也具有学术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但如果纯是为了“成一家之言”则无必要。毕竟,只有真正体悟传统美学理念的博大精深之处,实现对传统资源的深度整合,才能真正构建起参与国际对话的中国当代美学。
尽管如此,彼时青年李泽厚的初步尝试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意境”范畴发展到明清时期时已经陷入明显的内卷化危机,其发展长时间停滞,文人们一味追求远尘脱俗的飘渺高远境界,结果与社会现实脱节,倾向于严重“内卷”的不及物美学。如叶燮《原诗》所言:“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至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旨归在可解与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就概念而言,更多的是玄谈。此论述诗意有余,但学理性匮乏。诸如此类的玄之又玄的阐述显然无法适应当代社会的要求。李泽厚在《“意境”杂谈》中格外强调将审美活动嵌入现实生活感受的重要性,为此他还提出“生活境界”的说法,认为艺术家不但要从理论信念上而且还必须“从感情上具体地来把握和理解生活”,追求一种“真正切身的把握体验”。而“生活境界”不仅是中国传统“意境”理论所缺乏的,同时也是欧洲形而上学美学最为缺乏的。当代美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转向,其中就包含着对形而上学美学那种“理论凌驾于生活”的傲慢态度的批判。而且,青年李泽厚之所以尝试改造“意境”范畴,乃是因为注意到古典范畴已经难以直接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故而他此举也属于一种推动古典范畴现代转型的先知先觉行为。虽然路径有失误,但其理念值得一书。正所谓,对特定时期的审美形态进行考察时,需要联系这一时段内的社会形态。因为审美形态虽不会对社会形态亦步亦趋,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重要关联,社会形态的变化或迟或早地会在审美形态上表现出来。学者们试图在他们所在的当代语境下重新整理、阐释古典审美范畴,继而构建现代美学体系,正是希望构建出能够适应当代社会形态变化的新的审美形态。
二、探索中国美学话语:程至的对“意境”内涵的现代阐释
程至的撰写《关于意境》对李泽厚现代阐释尝试进行批评,既是对其具体论点的批评,也是对以其为代表的具有相对普遍性的这种以域外理论强制阐释中国传统理论路径的批评。他表达的是一种构想:希望借助现代学术语言和思维,且依循中国传统审美意识的脉络,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美学的路径,以现代美学学科的专业精神为传统范畴注入现代活力。
他对李泽厚《“意境”杂谈》的立论进行驳斥,提出:“阎立本的《列帝图》虽然神形兼备,有它的典型性,可是历来一般只评论它画面传神,没有说它意境很美。”又补充说:“诗画的意境,更不是主题思想的代名词,不能认为凡是有意义的作品,就有意境。”他这番话包含了两个关键意思:其一,“典型”与“意境”存在重合之处,但两者是不同的范畴。其二,不能用作为文化政治范畴的“思想性”作为衡量“意境”的核心标准,因为两者各有不同的侧重点。这都是李泽厚《“意境”杂谈》中的关键性硬伤。
借鉴域外理论,其过程始终是一种所谓“引进与抵抗”的博弈。“典型”概念背后是强调明确性、经典性、模范性的欧洲古典主义的思维模式,而推崇悠远、缥缈、空灵的“意境”,则表现出的恰恰是中华传统美学那种侧重“模糊判别”和“动态转换”的对立相生思维。且“典型”强调的是从现象的一般性之中萃取本质的普遍性,秉承了本质主义那种追求超越时间的确定性、典范性和普遍性的思维逻辑。而“意境”所推崇的是“生生不息”的持续生成性,虽然作为集结审美共识的自然意象群都一样,都是“枯藤老树昏鸦”“夕阳西下”,但主体不一样,情境不一样,其所基于具体机缘而生发出的意境也有所差异。大家都是离乡在外,同读这首诗,同样缘发意境,难道能说谁缘发出的意境更典型,更接近本质?毕竟无论是本质还是典型,都不是意境追求的核心,“意境”关注的是“刹那永恒”的审美情思的“妙悟”,领悟和欣赏宇宙生命的节奏和律动,在情景交融之中生发“象外之象”。这种“妙悟”是生成性的,不需要特定的典型范式(如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等)作为衡量依据,亦无须体现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换言之,“意境”不是要归纳出作为最终完成形态的典型性,而恰恰是要挖掘出各种未完成的潜在可能性,故而青年李泽厚试图整合两者的努力从一开始在方向上就错了。更重要的是,“意境”在中国语境下并非仅显现为一个知识学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因为它作为“美善合一”的复合观念,同时也展现出一种以文艺空间来安顿灵魂、寄托精神的中国人的生命体验方式,是理念和实践的统一体。正所谓“中国古人在探寻生命本原和宇宙奥秘的过程中,常以一种涤除玄览、空明圆融的‘空灵’心境作为主体在终极信仰中安身立命的精神场域,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来建构中国式的理论体系和阐释价值”,这就跟欧洲理论框架中的“典型”概念在观念体系上产生了重大区别。
对“意境”的现代阐释,程至的使用了“空间境象”这个更明晰而具有现代内涵的概念。这样的“空间境象”,有时(比如绘画)能够直接表现出来,有时(比如文学)则需要借助想象、联想而构造出来。他谈到:“当人们感受到一幅画或一首诗有意境时,便会在眼前呈现出一片清新的,或宁静的,或开朗的,或萧疏的,或壮丽的等等的空间,仿佛自己亲临于大自然之中一样。可以说意境的特点主要是依借空间境象来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并且他还给“空间境象”设定了一个结构的核心:“情趣”,认为必须是满含“情趣”的“空间境象”,才能产生意境。他以《山居秋暝》为例,提出这首诗之所以有意境,归功于诗人“巧妙的有机的表现了自然景物的动态,从而寓于一种情趣”。他阐释说:“诗中的恬静太空之间,隐隐约约显出了丁点的动态和声响,非仅生动地描绘了新雨后山林中溢水的清新景象,而且也能使整个空间益发显得幽静。由于静中有了少许的动态,便能吸引人们心灵的起伏,使人老是觉得有寻思捉摸的地方,于是这首诗既有空间的境象,又有意境的情趣。”他的阐述颇具诗意,但其缺失在于,虽创造了“空间境象”概念,同时为其构建了作为核心的“情趣”概念,却没有围绕着这一系列概念给予确切、凝练的定义,而是以这个概念所展现的具体样态来加以描述,虽然形象生动但却缺少学科化所需要的规范性。或许他认为“空间境象”四个字就已经明确阐释了概念本身的内涵,即创造一个特定空间,并且在此场域范围内构造出饱含审美情感内涵的场景。
需要指出的是,程至的始终未能从社会性、历史性的维度审视“意境”。传统“意境”理论正是因为缺乏这些维度而始终停留在狭窄的领域,而李泽厚赋予“意境”社会性内涵也恰恰是为了突破这种传统的桎梏。“意境”在程至的眼里只是“情景交融”的单个场景,仿佛是个超时间的、与社会实践变迁无关的存在。但实际上,意境是多层叠加的复数空间,既有现实的、具体的、此在的“情景交融”空间,也有超越性的、自由的、彼岸式的其他审美空间,必须以历史辩证的目光来加以审视。作为主体的人可以在“身”“情”“思”“梦”等多重空间之间切换,而如此在诸多审美空间中畅游,才是一种真正的中华审美的“游”和“逸”的态度,真正实现了“象外之象”的审美超越。
而且他藉由“空间境象”所阐释的“意境”,乃是一种被狭隘化了的创作论的“意境”。依照他的定义:“意境的表现,虽然和作者整个思想意识有密切的关系,但它不是抽象的‘立意’,不是单纯的把思想加在境象里,而是通过感性的、具体的形象来表现。可以说意境的产生是一种复杂、严密、巧妙的构思和表现的过程。”虽然他在这段定义中也试图矫正自己侧重于创作主体的偏向,强调需要“通过感性的、具体的形象来表现”,但他始终把“意境的产生”视为创作者的“构思和表现的过程”。然而意境的产生是一种创作者和接受者在主体间性意义上的递进生成过程,不仅包含创作,而且还包含欣赏这种新的意义和情感构建活动。比如王维借助诗歌创造出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空间境象”,这只是意境生成的第一步,仍需要阅读这首诗歌的接受者借助自身的阅历、情思、体悟等去充填这个“空间境象”的结构,赋予其审美情感的内涵,从而在自己的意向性结构中呈现出这一充满情趣的境界,这样才能包含“意境”的整个递进生成过程。
程至的也没能以统一的整体话语来阐释“意境”,而是将“空间境象”“情趣”和“意境”三者视为相对零散分离的范畴。按照他的阐释,“空间境象”与“情趣”之间不是融合互嵌的关系,而是若即若离的组合选项关系,只有具有“情趣”的“空间境象”才有可能进而呈现出“意境”。这就意味着在他的理论框架中,还存在着一些缺乏“情趣”的“空间境象”,而这种“空间境象”是不能呈现出“意境”的。他这种分类法看似遵循了西方学术强调细化分类的要求,实则架屋迭床,结构过于繁复,不符合中国审美强调“大道至简”的习惯,也未能达到现代美学强调凝练明晰的要求。并且,由诸多文本意象构成的“空间境象”,并非一种纯客观存在,而是审美主体经过审美对话之后在自己的意向性结构中呈现出来的“心象”,这样的“心象”必然带着审美主体的“情趣”,两者本就是一体的,所以并无必要刻意将“空间境象”与“情趣”设置为组合选项关系。
诚然,彼时学者所能凭依的域外理论资源较为有限,在该时段所能接触到的域外文论主要都是经由苏联传入的文艺理论,以及少许西方古典文艺理论,至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以及现象学美学、空间美学之类则多暂付阙如。在“资产阶级文艺”和“唯心主义”标签的禁忌担忧之下,理论研究多自我设限,仿佛越是多谈“客观存在”就越显得自己很“唯物”,结果始终在认识论而非存在论的层面里,以带着浓重的思辨哲学色彩的抽象、乏味的哲学话语来阐释本该鲜活灵动、自由超越的审美内容。程至的的“空间境象”论虽然缺陷甚多,但在当时的语境中,能够如此强调鲜活感性的审美内容已值得嘉许。
程至的对“意境”的现代阐释距离突破传统藩篱已经只差几步,比如他可以进一步尝试将“境象”的生发,具体分解为在特定文化语境下“创造、接受、升华”这一系列过程。他更应该立足于存在论的层面,从内在视觉的角度思考“境象”,而不是将“境象”仅仅作为阐释“意境”的基本架构。他的学术遗憾就在于,始终没有在思想观念上冲破彼时认识论、心理学、主体性三个层面的局限,虽已接近将自身理论提升到存在论、空间意识、主体间性的高度,可最终却还是回到既有的话语窠臼之中。
三、适应当代语境:李醒尘、叶朗对“意境”内涵的扩容尝试
青年李醒尘、叶朗撰写《意境与艺术美——与程至的同志商榷》一文参加研讨,目的就是试图解答“意境”传统内涵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适用范围和阐释的有效性问题。其核心论点在于强调学界不能固守传统“意境”定义,而应依据现实需要对其内涵进行扩容,使之能够回应当代审美实践的需求。探讨“意境”内涵不可停留在美学史的知识型追溯层面,而需将其置于本时段构建当代中国美学实践的视野之中,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推动古典审美范畴的现代阐释乃至现代转型。
回顾“意境”在中国传统美学史上的习惯性用法,其适用范围有相应限定,即只能在“虚静”的状态下发生。很显然,程至的所提倡的“意境”,仍然采用中国传统美学的提法,这也正是李、叶两人试图打破的旧有适用范围。《意境与艺术美——与程至的同志商榷》一开篇就谈到:“意境是我国传统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构成艺术美的不可缺少的要素。意境不仅反映着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国民族的美感特殊性,同时也因为它与艺术反映现实并反作用于现实的本质相联系,因而包含着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性内容。”正是基于这种思维,李、叶两人批评了程至的所谈的“意境只是某种艺术作品的意境,而不是所有艺术作品中共同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一观念。在李、叶两人看来,程至的限制了“意境”的适用范围,而美学范畴必须跟时代需求保持同步,而非固守原有的阐释框架。他们提出,并非只有“以表现空间为主的山水自然景物为主”才产生意境,实际上“以表现时间中人物性格、神态、动作、情节或故事为主”同样可以产生意境。李、叶两人尝试以意境“包含着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性内容”为切入口,将那些非“虚静”的“有意之境”也纳入“意境”范畴。如果将传统的“意境”称为“虚静意境”的话,那么李、叶强调的“意境”就是加入“激烈意境”之后的“新意境”。
尽管如此,李、叶此文在理论建构方面仍显得较弱,更多的还是提出具体观点。他们认为应当超越程至的所推崇的旧式“意境”范畴,构建符合新的时代语境的新“意境”范畴。他们提出,历史已经前进,时代已是新的了,但程至的依旧固执地在“意境”和“描写人物性格、人们活动斗争的艺术”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按照程至的的逻辑就会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有意境的作品就不能以描写人物性格人物斗争为主,以描写人物性格、人物斗争为主的作品,就不可能有意境”。这样一来,产生的负面效果就是,文艺家“在创造意境时,就会放弃深入表现社会生活的重大主题,以及直接反映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努力”,而“在描写人物性格人物斗争的作品中,就会放弃创造意境的努力,从而使这部分重要作品失去引人的魅力,失去广大的欣赏者”。所以李、叶认为,除了“静穆、淡泊的‘空间境象’”可以构成意境之外,“热烈、飞动的人物斗争”同样可以构成意境。李、叶给出的结论是,程至的由于忽视“社会生活的前进运动”和“时代的差别”,导致他将已经是过去式的“古人心目中的意境”作为后世在具体创作时不可逾越的界限,片面理解“意境”的适用范围,等于是“把历史的某一阶段所出现的艺术特点当做是一切历史阶段都必须遵循的普遍法则”。
这种对意境适用范围的学术分歧,表面上只是李、叶与程至的之间对于具体术语的争议,但该个案背后显现的,乃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在进行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学界皆知传统理论必须“再语境化”以回应当代需要的道理,也明白推动古典理论现代转型的重要性,但具体到究竟应当如何实施,则很容易陷入困惑之中。即,我们在继承和发展这些已经具有一定的约定俗成的意义、内涵和适用范围的传统范畴时,究竟是应该进行“大幅度翻新”,还是对这些传统范畴“修旧如旧”?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两难选择,必须在所谓有效阐释和无效阐释之间博弈。
一方面,如果选择进行大幅度“翻新”,虽然符合了跟随时代发展的要求,但同时也会导致整个范畴“面目全非”。比如本文所谈的青年李泽厚用“典型论”阐释“意境”范畴,虽然还带着“意境”两个字,但实与中国传统“意境”定义相背离。即便是青年李醒尘、叶朗这样相对温和地尝试对“意境”内涵进行扩容,同样也会出现在一定幅度上偏离约定俗成的“意境”内涵的问题。毕竟传统的“意境”是一种建立在以“虚静”为前提的古典静观理念之上的范畴,如果把热烈的斗争、叙事性情节、人物性格和动作神态等内容也加入其中,那么这样的“新意境”显然已经逾越了“意境”在历史上约定俗成的界限,如果改变后又不加说明地直接加以运用,就很容易造成概念混乱、语境错置、随意阐释等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假若只是对这些传统范畴“修旧如旧”,尽量依循传统的脉络,不做特别大的改造,特别是颠覆性改造,那么很有可能跳不出古人的窠臼,到头来只能是对这些传统范畴术语做“注释性阐释”,而无法对它们进行真正的现代阐释和现代转型。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这次由李泽厚等学者参与的系列论争,其历史遗憾就在于未能真正处理好这两方面之间的平衡问题。以今日视域观之,其实在他们二元对立的两难选择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并行而不相悖的“双轨路径”,即让旧的范畴仍保持传统的样态,同时再基于该范畴的理念精华而另外创造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范畴,从而让新、旧范畴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理论谱系。比如李、叶强调要考虑把“热烈、飞动的人物斗争”纳入“新意境”范畴的想法并无不妥,但完全可以在不改变传统“意境”内涵的情况下,基于其基本要素去创造出新的术语名词,如“情境”。这样一来,传统的基于虚静的“意境”和李、叶所提倡的作为激烈、动态的“有意之境”的“情境”,就可以共同构成新的意境理论谱系。这样既没有破坏“意境”本身在传统美学中的脉络,也能以作为现代范畴的“情境”来填补传统缺失的阐释动态的部分。
结语
推动“意境”范畴的现代阐释和现代转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外部环境变化之后的时代需要,也是中国传统理论自我革新的内在需要。当代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探索,包含着如何在世界学术界“确立自己的位置”的探索过程。而随着时代语境的演进迁移,各种新的文艺类型、文化现象和具体文本的不断涌现,文化观念和文化生态也在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使得既往的传统理论无法恒久地用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形态来及时、有效、全面地阐释新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学者们与时俱进地以新的理念、理论、范畴来回应新的理论诉求,以便匹配时代的深刻变化、把握时代的发展趋势,使传统理论获得长青的生命力,在当下语境中具备阐释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