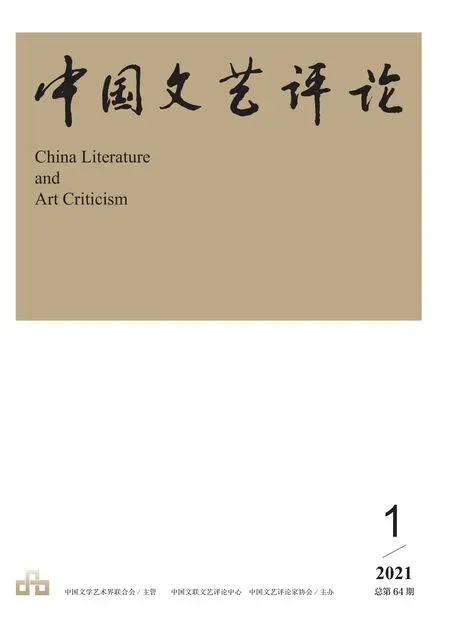笔法与功法
——梅兰芳绘画之“笔法”和表演之“功法”的融通
顾春芳
中国画的笔墨之美集中体现在笔法,京剧表演的美学集中体现在功法。绘画之“笔法”和表演之“功法”与其说是技巧层面的问题,不如说是美学层面的问题。
刘熙载《书概》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又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这里强调的是中国美学中艺术与心灵的关系。中国画的笔墨既是形式,也是内容,更有着精神性的内在构成,笔墨背后的精神性并不是脱离形式的,而是寓于形式本身的。在我看来,中国绘画的“笔法”和戏曲表演的“功法”有着相通的精神性结构。在中国美学的视野中,表演的要义和笔墨的要义在美学的最高追求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戏曲表演中的程式和功法也不仅仅是形式,同时也是文化结构和意义结构,是可以被不同的艺术家赋予精神内涵的意义结构。正是基于内在的文化结构和意义结构,戏曲表演艺术才能在法格的基础上不断开宗立派,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在世界文化史和艺术史上才能独树一帜。
梅兰芳在京剧表演艺术上博采众长、终得大成,在书画艺术方面也是转益多师、自成一家。他本人对于京剧、昆曲、书画、诗文无不精通,研究梅兰芳及其艺术,不能不关注其各种技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不关注其艺术中包含的中国古典美学精神。俞振飞先生这样评价梅兰芳的表演艺术:
他的艺术,以博大精深而著称,我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出其特点来。我十分欣赏他在舞台上那雍容华贵的品貌和仪态,欣赏他那“婉若游龙,翩若惊鸿”的舞姿。他的风格典雅大方,秾纤得中,体现着一种典型的古典美。这种美贯彻在他的整个演出中。
为了实现这样的艺术追求,梅兰芳转益多师,除了向其他流派行当学习,还大胆取法其他的艺术样式。梅兰芳擅长书画,他从书画艺术中体悟并汲取中国艺术精神,并把它注入到了戏曲舞台表演艺术中去。绘画的“笔法”和表演的“功法”之间有何关系,这种关系在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中是如何融通的,梅兰芳又是如何兼容并蓄的,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不二法门:戏曲和绘画的相通
黄庭坚说“取古书细看,令入神”,梅兰芳深知读画和撷萃的道理,就梅兰芳本人收藏的历代书画来看,出自名家之笔的多达百位,清代以前的名家如金农、改琦、梅清、蒋予检、陈铣等人的作品,近现代的名家名士如汪蔼士、王梦白、陈师曾、陈半丁、胡佩衡、于非闇、溥心畬等人的作品。这些名家也间接地成为了梅兰芳在绘画艺术上的师友,而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黄宾虹等人的书画则是梅兰芳书画收藏的核心部分。
梅兰芳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练习书画,甚至有心收藏历代名画呢?在梅兰芳的时代或者梅兰芳之前的时代,演员除本技之外还要学习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是梨园中普遍的风气。正所谓“笔墨之道,本乎性情”,艺人大多懂得决定艺术境界之高低在于艺术之“道”,正是“道”决定了从艺者从技术层面不断向内在人格修养、人格精神作永无止境的自我完善,这个过程既是艺术的磨砺和提升,个体生命的修为和完满,也是艺术在美学意义上的最终旨归。无论是“笔法”还是“功法”,对中国艺术而言,都源于一种内在的精神性追求,正是这种精神性追求,才能通过舞台表演艺术向世人展示一种生命状态的精致和高贵。
首先,中国戏曲和绘画有着相通的艺术精神。梅兰芳在《舞台艺术四十年》“从绘画谈到《天女散花》”一章中,专门论述了绘画和表演的关系。梅兰芳认为绘画艺术的布局结构、虚实处理和意境的产生密切相关,这一点和表演艺术是相通的。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和父亲都擅长笔墨,也有不少珍藏的画稿和画谱,他一有空就把家中珍藏的画稿和画谱找出来加以临摹,为的是揣摩和体会绘画的用墨调色、布局章法如何化用在舞台表演中。沈宗骞说:“学画者必须临摹旧迹,犹学文者之必揣摩传作,能于精神意象之间,如我意之所欲出,方为学之有获。”在梅兰芳看来,“布局、下笔、用墨、调色的道理,指的虽是绘画,但对戏曲演员来讲也很有启发”。他在遍览历代名人书画后,特别指出:
我感到色彩的调和,布局的完密,对于戏曲艺术有生息相通的地方;因为中国戏剧在服装、道具、化装、表演上综合起来可以说是一幅活动的彩墨画。
从历史上看,戏曲人物的扮相,很多都取法绘画人物的妆容和神采。梅兰芳曾说学习绘画对他自己的化妆术的提高有直接帮助,他说:“因为绘画时,首先要注意敷色深浅浓淡,眉样、眼角是否传神。久而久之,就提高了美的欣赏观念。一直到现在,我在化妆上还在不断改进,就是从这些方面得到启发的。”时装新戏《天女散花》的形象中海棠髻、白色古装袄裙、浅色花纹钩边、小珠子穿成的小云肩以及五色珠子穿成的小腰裙、胸前的“五色缨络”、肩窝左右的风带,就是根据北魏菩萨的造像设计的。《奔月》《葬花》两出戏的服装和扮相也同样脱胎于绘画的形象。设计穆桂英的发型和头饰,也曾经在古画中得到灵感,穆桂英的古装头在保留贴片子的前提下,发髻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式,用什么发式代替后面的“线尾子”,梅兰芳参照的就是古代画作。舞台上一切装饰,包括图案设计、色调调配、线条组织都是为表演艺术服务的,都需要有绘画的审美意识。舞台意象的审美创造过程不仅在于造型样式、角色形象、语言艺术、视觉画面、灯光色彩、音乐音响等各个不同门类艺术的综合性呈现,它最终要完成的是依据审美的直觉,融合各类艺术和舞台时空构作的方法,继而创造出充满本质力量和精神品格的意象世界和美感境界。
梅兰芳认为观画必须观一流的画,唯有一流画作方能真气弥漫、意味无穷。他说:“凡是名家作品,他总是能够从一千人千变万化的神情姿态中,在顷刻间抓住那最鲜明的一刹那,收入笔端。”为此,他走访考察了云岗、龙门、敦煌等文化遗址,对中国古代的绘画和雕塑保持着格外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北魏雕塑、龙门石刻,无论是造型、敷彩、刀法、部位、线条、比例,还是衣纹甚至莲台样式,他都力求从中深究艺术的奥理。他认为晋祠塑像群和故宫博物院所藏《虢国夫人游春图》手卷上的女官非常相似,工匠把宫里太监特有的鞠躬惟谨的神气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出来,也把宫女“闺中少女不知愁”的姿态刻画了出来。他评价晋祠塑像群“宋塑像群,体态轻盈,一颦一笑,似诉生平”,他说:“这些立体的雕塑可以看四面,比平面的绘画对我们更有启发,甚至可以把她们的塑形直接运用到身段舞姿中去。”
梅兰芳温柔敦厚、谦虚好学,他本人曾经拜王梦白、汪蔼士、齐白石、陈师曾等大家学画。特别是在王梦白的指点下,梅兰芳的绘画进步很快,关于戏曲和绘画相通的体会也就更深了,他说:
王梦白先生讲的揣摩别人的布局、下笔、用墨、调色的道理,指的虽是绘画,但对戏曲演员来讲也很有启发。
梅兰芳的《奔月》《葬花》《天女散花》等艺术形象的创造,就脱胎于绘画中的艺术形象。尤其是《天女散花》这出戏,其灵感来自于他偶尔在朋友家看到的一幅《散花图》。为了深入揣摩画中天女的飘逸和轻灵,他还特意向友人借回了这幅画,以便日夜观察体会。为了寻觅和呈现画中天女舞动绸带的飘逸劲儿,他还参考了古代的木刻、石刻、雕塑、敦煌的飞天形象,最终在心里培植出了“散花天女”意象,成就了一出经典剧目。
艺术是心灵世界的显现,梅兰芳的舞台意象是一种心灵化的呈现,故事、画面、形式和内容对他而言,都是一种心灵世界的显现。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需具备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的深厚修养。中国历代绘画和画论中包含着戏曲可以借鉴的形式与意蕴的资源。梅兰芳洞察了“笔法”和“功法”的内在精神的相通,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情景相生、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洒脱,俯仰天地、性灵超越的自由,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觉解,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传统绘画艺术的基本造型法则等,均可为戏曲取法。
技臻于道:由技入道的艺术境界
石涛在《大涤子题画诗跋》中说:“书画非小道,世人形似耳。出笔混沌开,入拙聪明死。理尽法无尽,法尽理生矣。理法本无传,古人不得已。吾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董逌在《广川画跋》中说:“由一艺已往,甚至有合于道者,此古之所谓进乎技也。”说的是艺道的相互关系,阐明了由技入道的艺术境界。过去有人认为京剧的本体是行当程式、四功五法,如果仅仅这样认为,就容易陷入程式万能和技术至上主义,而忽略京剧内在的精神性构成。程式如果没有人的精神性的追求和承载,没有人的精神赋予他光照,它就是一种技术手段,而脱离了审美追求、精神意蕴的技术是一种无聊的杂耍。如果没有这种至高的审美追求和精神追求,任何艺术都只能退化成一般的大众文化,娱乐文化,而不能上升到人类精神层面和审美层面的高度。
学习戏曲和绘画,有以苦练成就,有以顿悟成功,但无论如何必须从最基本的功法学起。书画的基本功当从画稿和画谱着手,书法的基本功必要真草隶篆一一临过,荆浩曾说:“学者初入艰难,必要先知体用之理,方有规矩。”郑燮说:“必极工而后能写意,非不工而遂能写意也。”龚贤《柴丈画说》提到:“笔要中锋为第一,惟中锋乃可以学大家,若偏锋且不能见重于当代,况传后乎?”这里涉及的都是笔墨书画的基本功问题。梅兰芳从长期的戏曲基本功训练中体悟出表演艺术之道,故而对笔墨书画的基本功训练也备加重视。
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提到自己幼年练功,教师在一张长板凳上放一块方砖,必须踩着跷站在这块砖上,一站就是一炷香的时间。起初站不稳,经常摔下来,时间长了腰腿就有了劲,功夫练到了就可以站得很稳。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冬天必须踩着跷在冰地上练习打把子,跑圆场,经受无数次摔打,唯其如此,才能长功夫。他说:“踩着跷在冰上跑惯,不踩跷到了台上,就觉得轻松容易,凡事必须先难后易,方能苦尽甘来。”先难后易,苦尽甘来,是习艺的规律。练习书法要写烂多少笔头,用完多少墨汁才能有所长进,笔墨和戏曲基本功的训练是完全一样的。这种严苛的基本功训练,往往要从童年就开始,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但梅兰芳说:“今天,我已经是近六十岁的人,还能够演‘醉酒’、‘穆柯寨’、‘虹霓关’一类的刀马旦的戏,就不能不想到当年教师对我严格执行这种基本训练的好处。”特别是对于旦角,小小年纪就要学习跷功,但练习跷功不一定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脚下有根。梅兰芳认为幼年练习跷功,对旦角演员的腰腿功夫是有益处的。
表演功法的演习和进步是循序渐进的。梅兰芳本人自幼从皮黄青衣入手学习戏曲表演,然后陆续学习昆曲里的正旦、闺门旦、贴旦,皮黄里的刀马旦、花旦等旦角的各种类型。和书法一样,起初要临摹各种字体和字帖,苏、黄、米、蔡,各有各的路数和妙处,只有长期练习和琢磨各种字体的内在韵味,辨明各家的法度胸臆,才能在日后自然而然创化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在这个转益多师的过程中,还能充分发现自己的特点。梅兰芳就在各种旦角类型的学习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特色,他说:“我跟祖父不同之点是我不演花旦的玩笑戏,我祖父不常演刀马旦的武工戏。这里面的原因,是他的体格太胖,不能在武工上发展;我的性格,自己感觉到不适宜于表演玩笑、泼辣一派的戏。”
除了旦角各部的研习,梅兰芳的表演功法中还有武工一项。他的武工大部分由茹莱卿先生教授。茹先生的教学要求就是“小五套”和“把子功”这样一类的基本功,戏曲表演非以此入门不可,学会了这些,再学别的套子就容易了。然后再学“快枪”和“对枪”,这是日后台上表演最常用的技艺。梅兰芳《虹霓关》里的东方氏、《穆柯寨》里的穆桂英都有对打戏,频繁使用“快枪”和“对枪”,后来又演习“对剑”,为的是掌握在舞台上使用短兵器,《木兰从军》《霸王别姬》都有类似的技艺展示,而这些艺术形象的完成全仰赖幼年时的基本功。
除了手上的功夫训练,还要不断练习脚上的功夫。梅兰芳回忆当年打把子训练,脚上还要有三种训练方法,一是武旦一行用的踩跷打把子,二是刀马旦一行用的穿着彩鞋或是薄底靴打把子,三是武生行用的穿着厚底靴打把子,可以想见梅兰芳为此付出的艰辛和汗水。此外,戏曲表演功法训练中,还有胳膊、腰、腿的系统训练。“耗山膀”“下腰”“压腿”是日常功课,还有虎跳、拿顶、扳腿、踢腿、吊腿等。
关于戏曲功法的根本,梅兰芳认为是戏曲的“音韵规律和身段谱”,他以余叔岩为例总结说:
叔岩的学习方法,虽然是多种多样,但归纳鉴别的本领很大。他向一个人学习时,专心致志,涓滴不遗,必定把对方的全副本领学到手,然后拆开来仔细研究,哪些是最好的,哪些是一般的,哪些是要不得的,哪些好东西用到自己身上不合适,要变化运用。这如同一座大仓库,装满了货色,经过选择加工,分成若干组,以备随时取用。而最重要的是要通晓音韵规律,基本身段谱,这如同电灯的总电门一样,掌握了开关,才能普照整个库房,取来的货物自然得心应手,准确合用。
正是源于对戏曲以“音韵”和“身段”为核心的基本功法的体悟,梅兰芳非常重视昆曲艺术。梅兰芳之前的时代,学习京剧表演的时候,讲究的戏班子同时教授昆曲的表演。梅兰芳回忆自己的先祖都非常重视昆曲,他说:“我家从先祖起,都讲究唱昆曲。尤其是先伯,会的曲子更多。所以我从小在家里就耳濡目染,也喜欢哼几句。”梅兰芳11岁登台,串演的就是昆曲。然而,在梅兰芳时代,昆曲已经全面衰落,台上除了几个武戏之外,很少看到昆曲了,北京仅有乔蕙兰、陈德霖、李寿峰、李寿山、郭春山、曹心泉等几位擅长昆曲的老先生,各个戏班子也只有很少几出武戏演的是昆曲。梅兰芳还曾跟着乔蕙兰老先生学会了三十几出昆曲。梅兰芳学昆曲,屠星之老先生就建议他到苏州请老师来拍曲子,后来梅兰芳还特意从苏州请来了谢昆泉,并特意把他留在家中随时拍曲子、吹笛子。在梅兰芳看来,昆曲的身段是历经数代艺术家,耗费了许多心血的实践总结,凝结着极为重要的智慧和价值,他说:“经过后几代的艺人们的逐步加以改善,才留下来这许多的艺术精华。这对于京剧演员,实在是有绝大借镜的价值的。”
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的表演体系在世界文化史和艺术史上,是异常独特的一种艺术形态,它之所以独特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包含在“功法”的形式之中的美学的、精神性的意义结构。所以,就绘画的笔墨或者京剧表演的功法而言,其精神性内涵的意义结构不可被消解,不可被漠视,不可被浅薄化,更不能被淡忘和丢弃,必须要传承下去。这个意义体系如果丢失了,这种艺术形态就面临灭绝的危机,就一定传不下去。
气韵生动:意在笔先与传神写照
中国美学注重“气”,到了六朝出现了“气韵”的范畴,谢赫论画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而“气韵生动”乃六法之核心。画功注重传神写照,画法推崇气韵生动。传神写照,气韵生动,同样也是舞台表演艺术所要追求的境界。气韵生动体现的是活泼泼的生命感,是中国艺术追求的审美境界,也是艺术家的生命合于天地自然节奏的至高境界。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
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
梅兰芳对于张彦远所说的书法艺术中的“一笔而成,气脉相通,隔行不断”“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自然是深谙于心,有所领悟,他才能够将画论中的笔法准确地转用在对谭、杨二人元气淋漓、余韵不尽的评价之中,而他自己的表演也潜移默化地思慕并持之以恒地追求这样的境界。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说:
在我心目中的谭鑫培、杨小楼的艺术境界,我自己没有适当的话来说,我借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面的话,我觉得更恰当些。他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驱电疾,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谭、杨二位的戏确实到了这个份儿……
最能体现梅兰芳“气韵生动”的表演就是《霸王别姬》中的“舞剑”。这一段“舞剑”虞姬从上场门出来,右手压着剑诀,左手抱剑,在“长锤”的节奏中缓慢步出。从亮相、揉胸、弹泪到拉山膀望向帐内一气呵成。接着是圆场,环手向右转身到台中心,二六过门亮相后,走小圆场到大边,右手一环向右转身在台中心亮相,再唱“劝君王……”一段。到了《夜深沉》,从舞剑前的开势,然后云手上步到台口,从“小边”台口走直线到“大边”台口,再从“大边”台口走斜线到台中,再从台中走至台口,这个过程中完成“怀中抱月”“左右插花”“涮剑”“栽剑”“云手”“十字蹲身”“剑花”“探海”“鹞子翻身”“大刀花”等身段动作……整个舞剑的过程好像以舞台空间为纸,完成了一幅元气淋漓、尽显灵性的行书长卷。石涛说:“作书画者,无论老手后学,先以气胜得之者,精神灿烂,出之纸上。”这段《霸王别姬》就是精神灿烂,出于纸上。唐代书法家张旭看到公孙大娘舞剑而悟出草书,表演的境界与书画的境界是相通的,一切艺术的境界也是相通的。不管是梅兰芳自己,还是他对谭、杨二人的评价,都体现了“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
要做到气韵生动,需要意在笔先。张彦远说:“夫运思挥毫,自以为画,则愈失于画矣。运思挥毫,意不在于画,故得于画矣。”梅兰芳与齐白石交往密切,齐白石常说自己的画法得力于青藤、石涛、吴昌硕,梅兰芳评价齐白石的作品“疏密繁简、无不合宜,章法奇妙,意在笔先”。他曾回忆与自己交游频繁的绘画名家,在作画的时候虽然各有各的习惯,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意在笔先。有的人在落笔前会拿起笔来在嘴里大嚼一番,接着就在碟里舔颜色,或在洗子里涮几下,梅兰芳说:“当他们在嚼了又涮的时候,是正在对着白纸聚精会神,想章法,打腹稿。这和演员在出台之前,先试试嗓音,或者活动活动身体的道理是差不多的。”
梅兰芳处理舞台上的“贵妃醉酒”也把握了“意存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1935年,梅兰芳访苏时表演的“贵妃醉酒”让苏联专家赞叹不已,他们认为喝醉酒的人真实的情形是呕吐不止,令人厌恶,而舞台上贵妃的醉态非但不让人讨厌,还让人觉得美,觉得为她的伤感而心碎。这就是中国戏曲的“传神”,舞蹈身段传达出的是人物生命的活力和内心的苦闷。梅兰芳说:“这出‘醉酒’,顾名思义,就晓得‘醉’是全剧的关键。但是必须演得恰如其分,不能过火。要顾到这是宫廷里一个贵妇人感到生活上单调苦闷,想拿酒来解愁,她那种醉态,并不等于荡妇淫娃的借酒发疯。这样才能掌握住整个剧情,成为一出美妙的古典歌舞剧……每一个戏曲工作者,对于他所扮演的人物,都应该深深地琢磨体验到这剧中人的性格与身份,加以细密的分析,从内心里表达出来,同时观摩他人的优点,要从大处着眼,撷取菁华,不可拘于一腔一调、一举一动的但求形似,而忽略了艺术上灵活运用的意义。”
唯有气韵生动,才能传神写照。齐白石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艺术的真实不在于表面的模仿,而在于内在精神的传达。如何做到似与不似之间的传神,是一切艺术最难企及的境地,这种境界是绘画和戏曲共同的审美追求。无论绘画还是戏曲,如何模仿前人,如何传承技艺?梅兰芳指出有些人模仿“活曹操”黄润甫,居然去模仿他晚年掉了牙齿后的口风,这是本末倒置了。他认为学习黄润甫要学习他并不僵化地模仿前人塑造的“曹操”,没有把曹操处理成肤浅浮躁的莽夫,他的勾脸、唱腔、做工表情都结合了自身特点,应该学习的是黄润甫“气派中蕴含妩媚”的传神的人物塑造。
梅兰芳认为,从表面上看,《青石山》里的关平扮相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杨小楼的关平就有“一副天神气概”,配合着【四边静】牌子的身段,真有“破壁飞去的意境”,“从神态气度中给人一种对神的幻想”。杨小楼之所以能够把天神的神态、气度,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梅兰芳看来主要原因是杨小楼有意识地吸收了唐宋名画里天王及八部天龙像,不简单追求“形似”,而是追求“神似”和“气韵”。 梅兰芳自己在处理《生死恨》中韩玉娘《夜诉》那一场的表演时,完全是从一幅旧画《寒灯课子图》的意境中感悟出来的,而《天女散花》中天女凌空飞翔姿态的处理也是从绘画和雕塑中直接吸收借鉴而来的,这种借鉴和吸收注重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
此外,对于绘画而言要达到气韵生动,需注意墨色浓淡,对表演而言也要留意虚实关系。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认为:“须用虚实。虚实者,各段中用笔之详略也。有详处必要有略处,虚实互用。疏则不深邃,密则不风韵。但审虚实,以意取之,画自奇矣。”如何处理好虚实既是美学的问题,也有利于演员自身的保护。劳则伤音,逸则败气,如何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既是功法也是学问。余叔岩就非常注意唱腔的虚实处理,梅兰芳剧团的李春林回忆说:“叔岩的嗓子,高音用‘立音’,膛音用本嗓,真假音参用,衔接无痕,非有极大本领,不能圆转如意”。
对于绘画中的梅兰芳和表演中的梅兰芳而言,两种不同艺术的审美表达可谓异源同流,二者都体现着中国传统美学的精神光照。画功注重传神写照,画法推崇气韵生动为第一,传神写照、气韵生动,同样也是舞台表演艺术所要追求的境界,这种境界的获得在梅兰芳那里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梅兰芳说:
中国画里那种虚与实、简与繁、疏与密的关系和戏曲舞台的构图是有密切联系的,这是我们民族对美的一种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正因为这样,我们从事戏曲工作的人钻研绘画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变换气质,从画中去吸取养料,运用到戏曲舞台艺术中去。
贵在融通:文戏武唱和武戏文唱
梅兰芳的墨梅文弱中见刚劲,正如他的唱腔和做工平淡中显精彩,平和中见深邃。倘若将梅兰芳的绘画艺术所呈现的美学风格进一步同他的舞台表演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绘画和表演一样,不求偏锋,不走险崎,体现了中和典雅之美。这种典雅中正、中道仁和的内在气质既是他的人格境界也是他的艺术境界,更是梅兰芳艺术的精神气韵和生命格调的彰显。
过去有学者认为杨小楼是“武戏文唱”,而梅兰芳是“文戏武唱”。两位艺术大师都能够博采众长、融汇百家、取长补短,兼容并包,不断推升舞台表演的境界。这种不同行当的融通,犹如米氏父子的画中有行草的意趣,也类似绘画中不同派别的兼容,书法中碑帖的相融,书法和绘画的融通,也就是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所说的:“能集前古各家之长,而自成一种风度,且不失名贵卷轴之气者,大雅也”。
杨小楼是“武戏文唱”的典范,他的大家风范体现在不满足于单纯的武戏外部技术呈现,而是追求人物塑造的生命姿态和精神气质,所以他注重表演和生活内容、历史情境和思想内容的结合,而不仅仅满足于卖弄武工。梅兰芳是“文戏武唱”的典范,他的《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兼具文武之道。《天女散花》作为一出正旦的戏,要表现天女的御风而行,传统的水袖功不能完全达到这样的效果,于是梅兰芳改用了“风带”。抖风带难度很大,用到的是“三倒手”“鹞子翻身”“跨虎”等武戏身段,唯其如此才能表现天女轻盈凌空的翔姿。《贵妃醉酒》是地道的文戏,但是表现贵妃的“醉”却要用到“卧鱼”“下腰”等武戏的身段。醉酒的三次“卧鱼”跟着三次“衔盃”,靠的是武工的腰腿功夫,这就是为什么《贵妃醉酒》可以入刀马一工的原因。梅兰芳还将曹操的身段融入了《贵妃醉酒》,他说:“我在入座时有一个小身段,就是用手扶住桌子,把身子略略往上一抬。这个身段,别人都不这样做,我是从唱花脸的黄润甫先生那儿学来的。我常看他演《阳平关》的曹操,出场念完大引子,在进帐的时候,走到桌边,总把身子往上一抬……杨贵妃能学曹操的身段,我不说,恐怕不会有人猜得着吧。”还比如,梅兰芳偏爱《宇宙锋》,这是一出青衣应工戏,但赵女的舞蹈和身段如果没有武工的底子,是根本表现不出来的。
梅兰芳的“文戏武唱”,追求的是“遒者柔而不弱,劲者刚亦不脆”。大艺术家不会死抱程式行当,程式行当在不同的人物和剧情中可以有无限的创化和妙用。正如方薰所言:“功夫到处,格法同归。妙悟通时,工拙一致。”京剧表演的基本功训练是必要的,必需“学透”,唯有“学透”才能“创化”。倪云林寥寥数笔,就能“尽取南北宗之精华而遗其糟粕”,梅兰芳同样善于尽取各派之长,为我所用。学习功法不能荒腔走板,但是最后一定要善于创化,就像书法家将苏黄米蔡、草情篆意一一临过,最后才能创化出属于自己的风格。
这种融通和创化正是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美学特点。比如二本《虹霓关》的丫环,原本是一个正派角色,可以憨态可掬,但不可油滑轻浮。如果专工花旦的角色来唱,容易流于轻佻冶荡,就表现不出这个形象的特质。因梅兰芳学过《假期》《拷红》《春香闹学》这一类大丫环戏,他在演二本《虹霓关》的时候,就自然而然融入这些丫环戏的风格和色彩。梅兰芳说:“别瞧这短短两刻钟的戏,我在当年倒的确能拿它来叫座的。”
不同行当之间的融通,在梅兰芳这里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最终是为塑造人物,实现他典雅中正的美学追求。就《贵妃醉酒》而言,如果处理不当,杨贵妃这个人物便容易落入香艳。这出戏重在做工表情,很多演员都在“醉”态上做过了头。而梅兰芳塑造的杨贵妃在幽怨之余,从初醉到微醉,从微醉到沉醉,注意区分“醉”的层次的变化,逐渐展现出人物精神上的空虚和苦闷,从而深刻地表现了杨贵妃的心灵世界。特别是梅兰芳对于杨贵妃“醉步”的刻画,他说:“要把重心放在脚尖,才能显得身轻、脚浮。但是也要做的适可而止,如果脑袋乱晃、身体乱摇,观众看了反而讨厌。因为我们表演的是剧中的女子在台上的醉态,万不能忽略了‘美’的条件的。”他认为:“演员在台上,不单是唱腔有板,身段台步,无形中也有一定的尺寸。”关于如何把握《贵妃醉酒》和《游园惊梦》两出戏的分寸,梅兰芳说越演越懂得“冲淡”。他说:“我历年演唱的‘醉酒’就对这一方面,陆续加以冲淡”,“我现在唱‘惊梦’的身段,如果对照从前的话,是减掉的地方比较少,冲淡的地方比较多。”
梅兰芳不仅自觉地在不同行当,文戏和武工之间加以融通,也十分注重艺术和自然的融通,与生活的融通。黄庭坚曾有言:“余寓居开元寺之怡偲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黄庭坚写草书,从江山景致中获得灵感,梅兰芳认为绘画和表演也要善于观察和提炼生活。画家画花鸟鱼虫,人情世态必须要观察生活,演员要塑造各种形象更要观察生活。在《贵妃醉酒》中,前人表演一般有三次卧鱼的身段,没有嗅花的表现。过去戏班子老师怎么教,学生就怎么演。梅兰芳也说自己莫名其妙地做了很多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做三个卧鱼动作。有一次他在香港小住,见房前草地中开了不少花,忍不住俯下身子去闻,这时旁边一位朋友说他的动作像卧鱼的身段。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将贵妃的三次卧鱼改成了嗅花,这种创新就来自他对于生活真实的敏感,将生活真实融入艺术的真实。他好像改了身段,但其实不是肤浅地改,而是提升了原有身段的意味和内涵。他在谈到昆曲身段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
昆曲的身段,是用它来解释唱词。南北的演员,对于身段的步位,都是差不离的,做法就各有巧妙不同了。只要做得好看,合乎曲文,恰到好处,不犯“过与不及”的两种毛病,又不违背剧中人的身份,够得上这几种条件的,就全是好演员。不一定说是大家要做得一模一样才算对的。有些身段,本来可以活用。
此外,梅兰芳还注重表演和其他艺术的融通,“诗画合一”就是梅兰芳的自觉追求。《历代名画记》引陆机的话说:“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苏东坡题摩诘画《蓝田烟雨图》也曾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与画的融合,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美学传统。在戏剧中表现画境,目的是要诗画相通,使表演的画面诗意盎然。在强调“情之追求”的抒情品格的同时,又能借景写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达到诗画合一的境界。诗画合一是中国诗词和书画艺术的根本精神,诗画合一也是梅兰芳艺术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性追求,他的天女散花、洛神、杨贵妃无不与中国的水墨书画意境相通。
戏曲和绘画一样,都面临继承传统、发展创造的问题。梅兰芳的艺术修养最终指向的是不断提升舞台表演艺术。他善于从绘画艺术中吸收创化,他善于把绘画艺术转化为戏曲舞台的意象世界。梅兰芳的表演与中国绘画所体现出的古典美学精神是高度一致的。明人胡应麟《诗薮》把诗人分为大家与名家,说大家是“具范兼镕”,名家是“偏精独诣”,梅先生正是一位能把旦角行当的多种艺术风格、表演的多种技巧熔于一炉的具范兼镕的大家,而他的理论见解大多来自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综合修养。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在对最高的精神和美学旨趣的守望与实现中,与中国画的笔墨追求殊途同归,而正是借助中国画的笔墨功夫,梅兰芳更深地体悟并汲取了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精神,并把它注入到了戏曲舞台表演艺术中去。
绘画之“笔法”和表演之“功法”本质上是美学的问题。梅兰芳说:“戏曲演员,当扎扮好了,走到舞台上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普通的人,而变成一件‘艺术品’了,和画家收入笔端的形象是有同等价值的。画家和演员表现一个同类题材,虽然手段不同,却能给人一种‘异曲同工’的效果。”中国美学格外注重艺术在心灵层面的表达,一切艺术的形式和内容都是艺术家心灵世界的显现。借由艺术的创造,以艺术作品为载体,艺术家活泼泼的生命状态和内在灵性从有限的肉身中超越出来,向世人展现一种更为永恒的精神性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观看伟大的作品时,常常感到艺术家的性灵和精神宛然在前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通过艺术的创造,艺术家的精神超越肉身和有限,趋近无限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