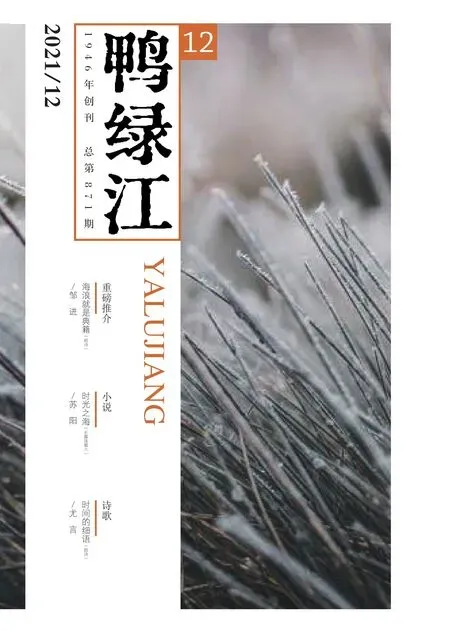张翎《余震》中小登的伤痛形象塑造之缺陷
吴盈莹
张翎是北美华文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创作,至今已有多部优秀作品诞生,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在小说《余震》中,作品想要传达的主题是在伤难过后,不是每个人都能重新站起来,也有人被苦难打倒永不能重新站立。作者近乎完美地塑造了处在心灵创伤中难以治愈的小登这一角色。前人对其的研究大多是在分析小登形象的生动饱满,少有人分析这一人物设定的欠妥之处。而本文旨在分析在张翎小说《余震》中作家“为伤痛而伤痛”的主观意图造成了小登这一伤痛人物在形象塑造上的缺陷。
一、“伤痛”诞生的不可逆
伤痛诞生于“不可逆”的作家意图。在构思《余震》时,作家张翎是偶然读到《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书中对劫后余生的孩子,用“成了企业的技术骨干”“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来概括。张翎固执地认为不应一笔带过一个人的伤痛,“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因此在回到加拿大后,她萌生了对《余震》的构思。她收集了有关唐山大地震的资料,看见了那些被称为孤儿的孩子。她想要在作品中书写那些受难者无法言语的创伤,“帮”他们诉说伤痛。同时她也清晰地勾勒出自己想要展现的不是地震带来的伤痛,而是心灵的余震,因此诞生了主人公小登这一人物形象——一个经历过伤痛且无法治愈的人。“她决定让小登成为灾难中那个被遗弃者”。
作家以伤痛之名让小登被迫承担起抒发伤痛的责任。可以说,作家是为了写伤痛,所以才创造出一个典型的伤痛人物。作为创作的主体,作家要表现悲剧,那么她笔下的人物就不能幸福。因此,她最原始的使命就是承担作家附加于她的伤痛,被动地任作家安排,并不能做出任何反抗。
二、“伤痛”塑造得不合理
在小说中,作家对伤痛形象的塑造主要是体现在小登身上。利用唐山大地震这一灾难背景,通过让一位母亲在地震中选择救弟弟而不救姐姐这一情节,让小登成为在身体与心灵上都受到伤害的人。接着又在后文通过“养母去世”“养父骚扰”“丈夫离婚”等一系列事件加深主人公的心灵创伤,从而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塑造出一个近乎完美的“伤痛人”。
1.人物符号化
对小登的形象塑造实则是将人物进行符号化处理,人物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真实可感的人,而是作者抒发伤痛的符号。
当母亲做出选择时,小登就应该死去,但她没有。采访中张翎也说:“这个叫王小登的女人若死在1976年7月28日,她就会定格在一个单纯快乐渴望上学的七岁女孩形象上。可是,她却活了下来。”作者没有让她死亡或失忆,而是让她清醒且痛苦地继续活着,这是作家为她营造的第一层伤痛。到新家庭后,作者也没想让她过安稳的生活,而是让养母离开她,养父侵犯她,造成她心灵的第二层伤痛。在一系列事件后她产生了对身边人强烈的控制欲,但也因此让身边的人都一步步离开她,女儿离家出走,丈夫无可奈何地选择离婚,面对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无力感在她的心灵上形成了第三层伤痛。
童年、青年、中年,她始终活在源源不断的痛苦之中,但这些痛苦实则是作者为了表现伤痛而特意为她设置的情节,让她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书写伤痛的符号。
2.人物机械化
作者对小登在灾区醒来后的描述也是不合理的。“女孩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撕扯着身上的书包带”“书包带很结实,女孩就弯下腰来咬”“布带断了,女孩将书包团在手里,像扔皮球一样狠命地扔了出去”“女孩蹒蹒跚跚地走了一会儿,又停了下来,回头看她走过的那条路”。表面上确实传达出小登对母亲的仇恨以及与原生家庭的决裂。但实际上这一系列举动是经过加工处理后较为理性的思维方式,既不符合人类面对突发困境的应激反应,也不符合孩童原始本能的宣泄。按照一个未经历过生死的7岁孩子的本能反应,由于地震的冲击加上没被选择的委屈,醒来后首先应该是放声大哭,再产生出强烈的困惑和愤怒情绪,而不是做出一系列冷静的情节化处理。就如在电影《唐山大地震》采访中,小演员在述说这段表演经历时,也是委屈地大哭,并且疑惑地问“妈妈为什么不救我”。
能够看出作家在描写主人公的伤痛时,刻意想要营造出女童在面对亲人抛弃时的极度痛苦。她弱化了处于7岁年龄阶段孩童应有的情绪,转而放大其心灵的疼痛,使读者能够体会到强烈的痛感。但这彻底背离了一个年幼孩子的真实心理特征,使人物在作者的操控下进行机械化的伤痛传达。
三、“伤痛”表达得不深入
作者在表现小登的心灵创伤时并没有深入小登这一人物的内心去剖析其伤痛的根本,而是借助一次次新的伤害来加重其内心的余震,从而掩盖住无法深入地对最初心灵地震的刻画,最后以“因为实在太疼了”为由,扔给自己一片“止痛药”,强行让小登回到了最初的地方和生母见面,让小登自己推开了“心里紧闭的窗”,化解了自己的伤痛。
整个情节的刻画都向读者诉说着“疼”字,但这种疼不过是表面上的疼,是小登这一人物符号所传达给读者的痛感,小登内心真实的痛其实并没有被深入刻画。这是因为作者并不了解幸存者们的真实经历,只能通过新闻采访及各种碎片化资料来组装人物,文章中“小登的记忆也是在这里被生生切断,成为一片空白”也体现出因距离之远,所以作者无法对地震的过程及人物的心理展开详细描述,只能以空白填补。她在采访中也说“我也曾为那些数字伤痛过,可那却是山高海远的伤痛,并无切肤的感觉”。
因为不了解,所以她无法进入小登的内心,不能对小登的内在痛苦进行深刻描绘,只能借助一层层外因,为小登定制一系列伤痛情节,从形式上加深小登的痛。
结束语
总的来说,小登的伤痛形象塑造存在缺陷,作家张翎将多个残忍的外因全部附加在小登身上从而形成了对伤痛的刻画,使小登变成被表述的抽象符号,成了“伤痛下的失语者”。能够看出作家张翎站在第三文化空间里,审视的空间变得更加理性和犀利,但同时也使得她与第一文化空间产生了较大距离,失去了和当今中国社会最鲜活扎实的事物接触的机会,从而让她“在距离产生的优势与缺陷中挣扎”。
注释:
①张翎.浴火,却不是凤凰——《余震》创作谈[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02):70。
②同上。
③罗屿.《唐山大地震》:32年后的影像余震[J].小康,2010(08):39-41。
④张翎.浴火,却不是凤凰——《余震》创作谈[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02):70。
⑤罗屿.《唐山大地震》:32年后的影像余震[J].小康. 2010(08):39-41。
⑥刘雪明.小说是疼痛 电影是疗伤[N]. 乌鲁木齐晚报 . 2010-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