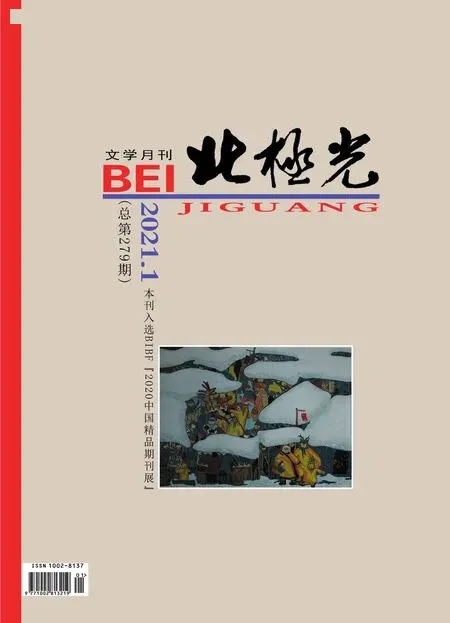火柴映像
火柴也称洋火,我小时候这种东西很常见,现在却不常见了。今年初冬时节我和几个朋友去饭店吃饭,我又一次见到了久违的火柴,餐桌上我们点了一道压锅土豆片,土豆片放在干锅里,锅下面放了一块酒精块,服务员一起端上来两道菜,由于腾不出来手,就让我帮忙点酒精块,我拿起盘子边的火柴盒,取出火柴稍微用力逆茬划,只听见“刺啦”一声,火柴点着了,我赶紧用点燃的火柴点燃酒精块,就在火柴点燃的那一瞬间,许多童年划火柴的记忆浮现在眼前。
我的家乡在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我出生在加格达奇区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我经常用火柴点炉子,我烧火烧得很好,奶奶做饭时都让我帮忙烧火,奶奶和面、炒菜,我就在灶坑旁看着添柴火,时间久了,奶奶觉得我烧火烧得还不错,就让我单独去给爸爸烧炕,爸爸很忙,印象最深的是一到冬天,爸爸都要上山区干活儿,年复一年的干活儿,而且是早出晚归,那时我还没有听说过羽绒服,我们穿的棉袄、棉裤都是奶奶用棉花做出来的,奶奶还会给我们做手套,奶奶做的手套只能分出大拇指,剩下的四个手指都在同一个洞里,我们也叫手闷子。
冬天,天黑得早,我要在爸爸没回来之前把灶坑和炉子点上,然后在那看着多烧几灶,我点火烧炕的功夫是我爷爷教我的,先放一根粗一点的木柴,顺着灶坑放,我习惯放在左边,在炉灰上放几个小树枝,准备好两块桦树皮,然后再找一根木柴斜着放在那根粗木柴上,大约成35度角,最重要的的就是划火柴,火柴划的时候要逆茬,不能太慢还要稍微用点力,能看见一丝光亮,听见“刺啦”一声,火柴就点着了,不过火柴很快就会燃尽熄灭,得赶快点着桦树皮,把桦树皮放在小树枝上,然后在那根斜着的木柴上再填一些小树枝,斜木柴的作用就是在桦树皮和填进去的木柴之间留一点空隙,这样桦树皮上的火苗不会被填进去的木柴压灭,等到火着起来了再放稍细点的木柴,火苗烧得很旺时就可以放粗木柴了,要让火一直烧,至少也得烧个四五灶,等到爸爸回来的时候,炕是热乎的,爸爸回家就可以暖暖地睡一觉,第二天爸爸还要上山干活儿,爸爸每天干活儿回来的时候,帽子上满是呼吸时凝的雪霜,裤脚里、棉袜口、手套口都是雪,雪被体温化成了小雪块。爸爸每次回家摘身上的雪块都要好半天,有时也让我帮他弄,我就用扫炕的笤帚帮他拍打,许是觉得我力气小,拍几下爸爸就自己拿过笤帚拍打身上的雪。
我喜欢春暖花开,一到春天就开始种木耳椴了,那些年种地只能维持温饱,要说挣钱就靠种木耳椴了,虽然钱不装我兜里,但我也高兴,更何况我一个小孩要钱也没处花,春天种的木耳椴如果雨水充足当年秋天就等收获秋木耳,第一茬秋木耳产量不高,木耳偏小,但质地偏厚、口感劲道,所以秋木耳的价格要比普通木耳价格高。木耳椴最高产的时候就是第二年和第三年,最多的时候十几根木耳椴就能摘一筐鲜木耳,鲜木耳装在麻袋里,但不装满,都是半袋一个,这样装在中间的木耳也不会被压坏,攒多了就开车送回家,晾晒在木耳筛子上,爸爸把木耳倒在筛子上,隔不远,一小堆,木耳都倒出来之后爸爸就又去采摘木耳了,我负责把木耳堆摊开,再把木耳里的草叶、树皮、草籽挑出来,整个夏天我们几乎天天都在采摘木耳,晾木耳,隔三差五就会有商贩来收购干木耳,我们家的木耳质量好,还干净,价格卖得也好,从我开始关注价格开始,我记得最初是十八块元一斤,后来价格慢慢涨起来了,二十元一斤、二十三元一斤、二十八元一斤等等,干木耳一大丝袋子也就十五到十八斤一袋,不过听说村里别人家一丝袋子能装到三十斤,爸爸还特意看过他们家的袋子,和我家的一样大啊,后来奶奶从别处听说了木耳压秤的方法,就是在木耳半干的时候,把白糖融化到水里,用给地里喷药那种喷壶把白糖水喷到木耳上,爷爷听说后坚决不同意在我们家的木耳上喷白糖水,爸爸也说这种方法不长久,时间久了没有商贩愿意收购我们家的木耳了。就这样年复一年,第一年的木耳椴也变成了好多年的了,第四年或第五年的木耳椴产量就很低了,都不够采摘的人工钱,所以就会被立起来,节省空间,可以在原来的地方摆放新的木耳椴,被立起来没有草遮挡,风吹日晒,木耳椴就风干了,只能烧火做饭了。其实,家家都不愿意用木耳椴烧火,椴里残留的木耳菌会洒落的到处都是,所以来不及烧火的木耳椴就立在草甸子里了。我家院子外面就是一条土道,土道的对面就是草甸子,里面立着一堆堆年久的木耳椴,像一堆堆木房子。
每年秋天,护林员都会烧防火隔离带,所谓的防火隔离带就是在草甸子里先把干草烧出一条道,万一真的发生火灾,因为之前防火隔离带而失去可燃物,使火情不至于失去控制。我记不清楚是哪一年的秋天,只记得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我最小的叔叔因为爬房顶,从上面掉下来摔伤了,家里大人都带着他去医院了,就留下我和妹妹在家,大约过了中午,我们在屋里玩,听到外面有“呼呼”的声音,好奇的我们马上从屋里出来,看见眼前的一幕,愣住了,火,是大火,很高,像一面火砌的墙,而且是会走的“墙”,“呼呼”地向我们家走来,那时候的我可没有任何火灾逃生的概念,火在朝我走来,我也朝它走去,我想靠近一点,看清楚,火怎么会这么高,它在走向我的同时也在向左右两边走去,感觉它越来越大,稍微向它靠近几步都会觉得呼呼声震耳朵,而且脸颊发热,身上穿的衣服也发烫,它甚至带来一股风,好像要把我和它拉近,我还是看不清楚它是怎么来的,但它已经非常靠近我家院子外的那条土道了,我觉得它比三四个我还要高,我猜它会轻而易举的跳过院障子,好像要把我和妹妹抓走,妹妹问我怎么了?我回答她:我也不知道,我大声的告诉她,努力让我的声音大过“呼呼”声。那现在怎么办?妹妹又问,我指了指那面“火墙”,回屋里吧,不然会被它抓走,我和妹妹跑回屋,把门插上,坐在炕上不敢去看外面,不知道是害怕了,还是真的困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竟然睡着了。醒来时迷迷糊糊听到爸爸在叫我,问我有没有出过屋、有没有害怕?同时也听不到屋外面的“呼呼”声了,我问爸爸那面“火墙”怎么来的,爸爸说是护林员在烧防火带,突然风改变了方向,火就朝这我们家的方向烧过来了,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屋看到原来的草甸子都变得黢黑,有几个地方还有一堆堆黑色像土包,那里原本立着的就是一堆堆风干的木耳椴,大火过后就只是稍微高一点的土包了,听爸爸说,那场火不光烧了风干的木耳椴,就连我们家在内的几户村民摆在附近当年的木耳椴也被烧了一部分,我记得后来我还听爸爸说过赔偿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赔偿我就不清楚了。后来就听大人们说开始“封山”了,不允许村里人上山砍木耳椴了,连烧火的木柴都不许砍了,有“自作聪明”的人,偷偷上山砍木柴被抓住,最后不但交了罚款,人还被关了几个月。
从那场大火以后我就就很少划火柴了,村子里没有中学,我的中学是在加格达奇读的,上中学后几乎没有烧过木柴。现在偶尔也会回到村里,村里的干柴垛都没有了,也都不种木耳椴了,就连院子的障子也没有了,原来的院障子都是从山上砍得小树,用几年风干了就得换一茬,现在大家连小树都不砍了,风干的障子也是夏天种地烧炕的时候引火用了,村里的泥土房都参与了棚户区改造,村民们都在加格达奇分到了楼房,不像以前在村里单独取暖,现在楼房集体取暖,一冬的取暖费也就相当于自己烧一个月的煤钱,既省钱又节约煤炭资源。
现在我的爸爸在加格达奇找了一份工作,交着五险,还能兼顾种着自己家的土地,种大豆还可以领着国家的直补和大豆补贴。国家提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近几年全国也有许多地方因为改善生态环境而兴起旅游业,拉动居民增收,我们大兴安岭以前生态环境就很好,为国家的发展出过许多木材,停止砍伐之后,我们大兴安岭的环境更好了,我们的樟子松、蓝莓、红豆等等也都有了各自的价值,未来我们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好,我真心地希望更多的人能来我们大兴安岭,看看我们的山山水水,还可以为家人带回去我们的蓝莓、红豆、松子、榛子、蘑菇等山特产品,我们这里夏有“绿水青山”,冬有“冰天雪地”,还可以一路向北,一路寻北。
而我记忆中的那根火柴也已映像成茫茫林海。
——以桦树皮画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