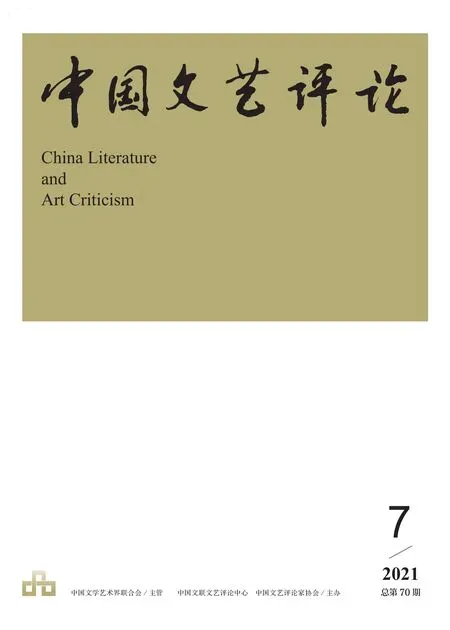典型建构论:从艺术形象到文化符号
李 震 李牧泽
众所周知,关于典型理论的讨论,在西方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则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才从西方引进的,至今也已有百年历史。今天,在典型理论百年之际,重新讨论“典型”这个话题,其意义似乎应该不仅仅是引经据典地回顾前人对“典型”的论述,或者梳理典型理论在中国走过的百年学术史(这项工作早在叶纪彬先生的《中西典型理论述评》,以及饶芃子、王一川等学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著述中就基本上完成了),更重要的是应该在百年来新的文艺实践基础上,结合当下的历史时空、文化语境和媒介环境,去发现并拓展典型理论新的认识空间和学术视野,从而催生更多新时代的典型形象。基于此,笔者尝试提出拓展典型理论的一点思路,姑且称之为“典型建构论”,并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典型的诞生:从原创到建构
以笔者陋见,从西方引进的典型学说,基本上是在哲学和美学视域内对某个特定时空中、某部特定文艺作品塑造的某个特定人物形象,在艺术构成方式和美学意义上的一种分析与概括。无论是偏重共性的类型说,还是偏重个性的特征说,或是个性与共性统一说,乃至黑格尔的“这一个”、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别林斯基的“熟悉的陌生人”等精妙概括,都是建立在对某个作品中的某个人物形象的分析基础上的,概莫能外。而在愈加丰富的文艺实践中,一个典型形象的诞生及其意义,却往往不是在某个作家艺术家的某部作品中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漫长的建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其构成方式和意义也不仅仅是哲学的或者美学的,更应该是文化的。
笔者认为,典型形象的诞生,或者说典型的创造,是一个从原创出发,不断延伸、不断积累的建构过程。现有的典型理论所观照的只是典型创造的原创环节,是典型建构的起点和出发点。笔者完全认同个性与共性统一说和黑格尔的“这一个”、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别林斯基的“熟悉的陌生人”等学说。但我们对一个艺术形象的典型性的认知,仅仅建立在塑造它的那位艺术家所处的特定时空、特定艺术形式和特定媒介之中是远远不够的,其意义仅仅限于美学和艺术的层面也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一个艺术形象无论是其个性还是共性仅仅属于其所处的时代和区域,而不具备时空超越性,不能成为特定时空中的一种文化符号,就很难说它具有多高的典型性和文化价值。
事实上,我们目前所认同的典型形象,基本上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过长期跨时代、跨区域、跨媒介、跨文体、跨艺术门类的再创造,与理论家、批评家们的阐释与再阐释,以及社会公众的文化习俗、审美习惯、想象力和公众舆论共同建构出来的。这一建构过程从理论上讲应该是没有终点的,但在客观上有一个可以被人们认同的结果和目标,那就是,当一个具有典型性的艺术形象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建构,被约定俗成为一个为公众所共识、共用、共享的文化符号的时候,才可以真正被视为典型。
人类艺术史已经创造出了数不尽的艺术形象,但真正成为典型的并不多。因为可以被称为典型的是那些被人们在口头或书面表达中不断重复的、被文化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比如,欧洲人把虚伪的人叫“答尔丢夫”,忧郁而优柔寡断的人叫“哈姆雷特”,沉溺于幻想之中而不切实际的人叫“堂吉诃德”;中国人把粗莽之人叫“猛张飞”或“黑旋风”,女汉子称为“母夜叉”或“孙二娘”,巾帼英雄称为“花木兰”,多愁善感的女子称为“林妹妹”,神通广大、翻云覆雨的人称为“孙猴子”,神机妙算的人称为“诸葛亮”,信仰坚定、意志刚强的女性称为“江姐”,心胸狭窄的人描述为“武大郎开店”,等等。这些活在人们口头上或笔墨中的人物,大多不是来自历史或现实,而是来自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都是在作家艺术家原创的基础上,经年累月,被人们建构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的。这种由艺术形象上升为文化符号的过程,就是笔者所说的典型建构。
典型建构是人类艺术创造被纳入人类文化总体进程的重要环节之一。文化有数百种定义,但不管哪一种定义,有一点是明确的:文化是特定民族、特定时代,人们按照共同遵循的生产、生活秩序与规则,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的总和。人们从事创造活动的领域分门别类,但各个领域的创造,只有成为人们共同遵循的生产、生活秩序与规则的一部分,才有可能被纳入创造成果的总和,也就是说才有可能被称之为文化。所有领域的创造行为,诸如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等,概莫能外。在科技领域,从事科学技术的人不计其数,成果也多如牛毛,但真正能够被纳入人类文化总体进程的,却只有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极少数科学家,文学艺术领域同样如此。那么,在文学艺术创造的艺术形象中,能够被纳入全人类,或者至少是特定民族、特定时代的文化总体进程的人物形象,自然也是凤毛麟角。也只有这部分艺术形象,才能真正被称为典型。而那些只在一时一地产生过某方面影响,但很快被历史所遗忘的艺术形象,只能被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
如果按照上述理解确立的标准来认定“典型”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典型不是某个作家艺术家一次性创造完成的,而是被长期建构出来的;第二,典型是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所有艺术形象中,最终被建构为一定范围的人们约定俗成,并共识、共用、共享的文化符号;第三,作为文化符号的艺术形象,被人们共识、共用、共享的时空范围越大,其典型性就越强,其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
二、典型建构的内在因素及其建构逻辑
一个艺术形象要被建构为一种文化符号需要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且在理论上讲,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其复杂性,除了对原创艺术形象的典型性的认知与把握外,还关乎一系列复杂的内在因素、建构逻辑和建构主体。这里笔者就其中的核心因素及建构逻辑作初步分析。
1.典型建构中的时代因素
任何一个艺术形象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会留有其赖以产生的时代的印记。时代因素应该是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核心因素。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典型建构论的意义上,一个艺术形象一旦诞生,就开始经历时代的流变,就必然要与不同时代的新的时代因素不断相遇,并受到新的时代因素的冲刷与重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因素也是典型建构过程中的核心因素。
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典型建构的过程,是艺术形象不断被其遭遇的新的时代因素重塑的历史。花木兰是南北朝时期的乐府长诗《木兰辞》中塑造的替父从军、战功显赫的女英雄形象。尽管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没有典型理论,但花木兰的确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环境中诞生的典型人物。如果我们站在典型建构论的角度来看,《木兰辞》中的花木兰只是一个尚待完成的、具有一定典型性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的典型建构过程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直到今天仍未结束。《木兰辞》所处的那个需要“替父从军”的时代的各种因素,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花木兰的艺术形象却在这一千五百多年中,经历了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舞台剧、影视剧、动画片的建构与再建构、复活与再复活的过程,成为家喻户晓的、标志着中华民族巾帼英雄的文化符号。
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类似花木兰这样的艺术形象,在与不同时代相遇时,会与新的时代因素构成怎样的关系?这一关系决定着一个艺术形象能否成为不同时代的人所共识、共用、共享的文化符号。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时代因素,包括所面临的问题、所形成的时代精神和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以及由此提出的时代的必然要求。一个艺术形象如果不能顺应、满足这种要求,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在这个时代被忽略或者被遗忘,反之,则会被建构为更具典型性的艺术形象。这种关系会衍生出艺术形象与时代因素之间复杂的排列组合:有的艺术形象与时代因素的关系是顺应型的,有的则是逆反型的,有的是部分顺应、部分逆反型的,有的则在这个时代是顺应型的、而在另一个时代却是逆反型的,如此等等。而任何一个时代对既有典型形象的建构逻辑,都是要力求光大顺应型的一面,抑制或改造逆反型的一面,最终以此去回应和满足彼时所处时代的必然要求。还是以花木兰为例,《木兰辞》和古代文人为其撰写的碑文、民间为其建造的庙宇等,都将花木兰建构为一个“忠孝”“勇武”的巾帼英雄,而在现代的各种舞台剧、国产影视剧中,其作为女性有着强于男性的“勇武”的一面,与现代中国所需的保家卫国的革命精神、战斗精神相融合,形成了与时代精神相顺应的关系。而“忠孝”的一面则因带有某些封建意识而被改造为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
一个真正有魅力的艺术形象,是凭借其不断被建构的典型性去超越不同时代的。同时,不同的时代因素又在不断地丰富、扩展、刷新其典型性的魅力。不断更新的时代因素与具有魅力的艺术形象,就是如此循环往复地重组出不断更新的典型意义,直至将其建构为一个时代所共识、共用、共享的文化符号,然后再去迎接下一个时代的到来。
2.典型建构中的民族因素
民族因素,包括特定民族的文化性格、文化习俗、文化心理以及文化价值观,是所有典型形象生成的重要根源,更是典型建构过程中与时代因素同等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民族因素与时代因素一样,应该是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具有典型性的艺术形象都是从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生长出来的。然而,如果从典型建构论来看,一个艺术形象一旦诞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都有对其进一步建构的权力和可能性。事实上,这样的建构行为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中国,一直都在进行中。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在《赵氏孤儿大报仇》中原创的艺术形象赵氏孤儿,先后被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意大利歌剧作家塔斯塔齐奥、德国诗人歌德建构为欧洲版的“赵氏孤儿”,一个来自中国战国时期的历史人物被容纳了欧洲人的爱恨情仇。一个中国元代公主“图兰朵”的艺术形象,经由阿拉伯人的《一千零一夜》、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以及意大利剧作家卡洛•戈齐、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和弗兰科•阿尔法诺的不断建构,成为一个驰名中外的中国文化符号。2009年,“图兰朵”这一国际知名的中国文化符号,又经中国导演张艺谋的改编,由意大利“图兰朵”拉法艾拉•安吉丽缇和中国“卡拉夫”戴玉强联合主演,回到了中国,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首演。
当然,不同民族因素在典型建构中是一种异常复杂的现象。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的差异,会给这种建构行为带来诸多变数。可以确定的是,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家在建构异域民族的艺术形象时,都必然会从本民族的文化性格、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出发。如法国人伏尔泰改编的“赵氏孤儿”形象,不仅将作为中国人的赵氏孤儿改编为作为他者形象的“中国孤儿”,还要给这个中国的复仇者形象强加上法式的浪漫爱情。
这种从本民族因素出发的典型建构行为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常常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一种是建构,一种则是解构。二者的分水岭便是建构主体的价值观。如果一个艺术形象在被异域民族进行典型建构的过程中,被加入了建构主体所属民族的某些文化元素和文化心理,应该属于正常情况,只要不改变原创艺术形象所标志的原民族文化价值观,就是正常的典型建构行为;相反,如果改变了原创艺术形象所标志的原民族文化价值观,便会成为一种解构行为。这种解构行为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美国影像艺术家杜撰出来的中国艺术形象。譬如,在中国深受人们喜爱的、具有反抗意识和叛逆精神的美猴王孙悟空形象,在美国却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破坏分子形象,完全篡改了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在中国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忠孝”“勇武”的巾帼英雄,又被现代艺术家们赋予了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的花木兰形象及与其相关的中国文化元素,在迪士尼大片《花木兰》中被“他者化”为一种供人玩赏的娱乐元素,并被装进了一个鹰人合体的“女巫”所代表的女权主义价值观之中。这些都属于彻底的解构行为。
异域建构主体携带着异域民族文化因素的介入,尽管使典型建构行为变得复杂而不确定,但不可否认,异域民族因素具有丰富、拓展和传播原创艺术形象的典型性的作用。这里只强调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家,在建构异域民族的艺术形象时,必须尊重这个艺术形象所代表的民族及其文化价值观。
3.典型建构的媒介逻辑
在典型建构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媒介。因为典型建构的实际过程,大多是由跨媒介叙事和跨媒介传播构成的。
跨媒介叙事和跨媒介传播能够借助不同媒介的特异性能、叙事功能和传播效能,有效扩大或强化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如1987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用真切的视听语言强化了小说《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一系列艺术形象,不仅没有改变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基本性格,而且使其典型性特征更加鲜明、逼真。特别是1987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的《枉凝眉》《葬花吟》等一组歌曲,更加凸显了小说《红楼梦》中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让人们在声音中感受到了比在文字中更加透彻的穿透力,更加动人心魄。总体而言,20世纪末中国对“四大名著”的电视剧改编,用视听媒介的特异性能和叙事方式,有效强化了“四大名著”中的一组组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并通过大众传播特有的渠道和规模,使其比在原著中更加深入人心,可以被视为目前最成功的跨媒介叙事与跨媒介传播,也可以被视为目前最成功的典型建构行为。
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特异性能,也就具有不同的叙事功能和方式。而不同的艺术形象也是各具姿态、各具魅力、各有各的典型意义的。因此,媒介因素介入典型建构,必然会遵循与艺术形象双向选择的逻辑。即特定媒介的特异性能与特定艺术形象的独特魅力之间的双向选择。1964年,空政歌舞团将小说《红岩》中有关江姐的故事改编为歌剧《江姐》,就是这样一种选择的结果。编剧阎肃和作曲羊鸣对这种选择的理由作出过详细说明。他们认为,小说《红岩》中只有“江姐”这个形象最适合用歌剧去表现。因为“江姐”是个女人,而且是个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中途丈夫又被敌人杀害,头颅被挂在城楼上示众,年幼的孩子又不能在自己身边的女人。这个身高只有一米四几的女人,革命意志却异常坚定,在如此孤苦的情况下还要坚持与敌人斗争,在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受各种酷刑却坚贞不屈。女人本来就是情感的化身,而江姐的孤苦与坚强又使她成为一位具有巨大情感含量的女人。同时,歌剧是唱出来的,因而是一种比其他艺术需要更大、更集中的情感因素的艺术。这是由歌剧的媒介(声音与剧场/舞台)决定的。歌唱需要情感的强度,而剧场/舞台需要情感表现的集中度。因而江姐便成为小说《红岩》中最适合成为歌剧主角的人物形象。
无论是“四大名著”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红岩》中的江姐形象,经由不同媒介的建构后,都比在原著中更加鲜明,更加真实可感,更加具有典型性。事实上,这些人物形象都是通过视听媒介从读书人的想象中走向公众视野的。而且这些人物的典型性,不管是个性特征,还是共性意义,都得到了有效的强化。虽然有人因痴迷于原著,无论如何改编都要叫骂,但这显然是由于他们忽视了不同媒介的特异性能及其叙事功能。
因此,特定媒介在介入艺术形象的典型建构时,建构主体必须遵守一个基本逻辑,那就是:既要尊重原著,又要尊重媒介。
三、典型建构的途径与方式
一般来说,典型建构的主体不仅仅有不同门类的文艺家,还应该包括理论家、批评家、媒体/自媒体工作者、社会公众等。因此,典型建构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本文择其要者简述之。
1.跨文类、跨文体书写
典型建构意义上的跨文类书写与跨文体书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跨文类书写是指文学文体之外的其他各文类对特定艺术形象的书写,包括史书、论著、方志、碑文、家谱、日记、书信等;跨文体书写是指文学中不同文体对特定艺术形象的书写,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
不同文类的书写参与典型建构的对象多侧重于非虚构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者有历史或现实原型的人物形象。譬如“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许多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在小说成书前后的各种史书、论著、方志等文类中有大量记述。还比如前述的花木兰,不仅在历代史料中多有记载,被认为是花木兰故里的河南商丘市虞城县还建有“木兰祠”,且留有祠碑两座,均对花木兰其人有记述。此外,《河南通志》《商丘县志》中也都有关于花木兰的记述。这些记述对文学文本中所讲述人物的原型,从体貌特征、家世、履历、功绩、个性等进行了程度不等的记载。尽管这些记载的内容有的来自史料,有的来自民间传说,但这种来自非文学文本的记载,会给人们以“合法”的真实感。其与文学文本形成的互文关系,有助于人们对这些人物的认识与理解,从而成为这些人物形象典型建构的合理组成部分。
跨文体书写对典型建构的作用则更加直接,多表现为诗歌、剧本对小说或叙事体诗歌中人物的再书写。由于同为文学作品,跨文体书写并不拘泥于非虚构人物形象。此类情形多不胜举,如果还以花木兰为例的话,那么历代诗人咏颂花木兰者已有很多,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戏题木兰花》、杜牧的《题木兰庙》都对花木兰有独到的书写。至于剧本中的花木兰形象,在明清以来的几百年间,包括舞台剧、影视剧、动画剧的剧本多不胜数,仅新中国成立以来排演过花木兰的剧种就有豫剧、京剧、秦腔、越剧、汉剧、昆曲、评剧、黄梅戏等二十多种,特别是由常香玉主演的豫剧《花木兰》更是成为爱国主义经典剧目。
跨文类、跨文体书写对典型建构的作用显而易见,无需赘述。需要强调的是不同文类、不同文体的书写对典型建构的不同意义。一般来说,不同文类的书写多为对历史或现实中有原型的人物形象的记载,对人们认识和理解该形象赖以产生的典型环境,以及该形象的真实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不同文体的书写则根据不同文体的不同特性对典型建构具有不同的意义。譬如诗歌是高度抽象、概括、凝练的文体,更多地侧重提炼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舞台剧本是为舞台艺术准备的文学台本,与小说相比,其人物形象和环境的典型化过程更为集中、浓缩;影视剧本是为影视艺术准备的文学台本,由于影视是要演的,是用来看的,所以必须突出人物和环境的画面、细节和动作,这样会使人物形象比在小说或叙事体诗歌中更加直观、真切。那么仅从文学的意义上说,一个艺术形象如果经历了多种文类、多种文体的书写、建构,其典型性自然要比在单一作品中更加丰富、更具魅力。
2.跨媒介叙事与跨媒介传播
尽管跨媒介叙事是在数字媒介高度发达以来的2003年才被作为一种基于协同创作和集体智慧的内容创意理念和文化活动而提出来的,但跨媒介叙事行为一直都存在。特别是语言/文字媒介与剧场/舞台媒介、影像/视听媒介的跨媒介叙事早已十分普遍,且为典型建构作出了巨大贡献。跨媒介叙事作为一种协同创作,在典型建构中通过不同媒介的特异性能形成的特有的叙事效果,聚合并扩展着艺术形象的典型性。随着数字媒介迅猛发展,跨媒介叙事将更加丰富、更加普遍、更加具有对典型性的聚合力和扩展力。
跨媒介传播作为跨媒介叙事产生的传播效应,通过不同媒介的融合与协作,从不同的传播渠道和传播范围,将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扩散到不同的受众群体。在典型建构的意义上,跨媒介传播不仅发挥了不同媒介对典型的建构功能,而且还将不同媒介的庞大受众群变成了典型的建构者、分享者、传播者,从而从根本上终结了典型创造只是个别文艺家的专属权的历史。
跨媒介叙事与跨媒介传播作为同一行为的两种不同效应和两个不同的考察视角,为典型建构打开了辽阔的视野和多样化的方式。同一个或同一组人物形象通过跨媒介叙事和跨媒介传播,其典型意义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自1993年出版后,不仅吹响了“陕军东征”的号角,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更重要的是创造了跨媒介叙事和跨媒介传播的奇观,由此也成为典型建构的一个范例。《白鹿原》作为一部以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小说,推出了一组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从2000年起,《白鹿原》的这批人物形象开始在各种媒介中绽放。姿态各异的白嘉轩、鹿子霖、鹿黑娃、田小娥开始进入公众视野。首先是李小超的大型陶塑《白鹿原》系列作品推出了雕塑版的白鹿原人物群像,紧接着是西安市秦腔一团的秦腔《白鹿原》,由孟冰改编、林兆华导演的北京人艺版话剧《白鹿原》,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西安外事学院版话剧《白鹿原》,首都师范大学的舞剧《白鹿原》,李志武的连环画《白鹿原》,王全安的电影《白鹿原》,光中影视的电视连续剧《白鹿原》,等等。这些不同媒介的《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绝大部分能够在尊重小说原著中人物的性格逻辑和文化品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媒介的特异性能和叙事方式,按照人物原有的性格逻辑进行扩展和延伸,使人物的某些个性特征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彰显。在这些不同媒介的人物塑造中,最为成功的是电视连续剧《白鹿原》。该剧充分发挥了视听媒介的特异性能和叙事手段,将小说中人物个性、文化心理的许多过于概括、过于抽象,或者一笔带过的部分,置于充满动作、细节和冲突的故事情节之中,让人们直观、生动、强烈地感受到这些被语言文字定性了的个性和心理特征。譬如电视剧对白嘉轩死了六个老婆后,娶第七个老婆仙草的桥段的设计,既按照电视的媒介逻辑增加了故事曲折的戏剧性、传奇性,又比原著更加凸显了白嘉轩“仁义”的品质和仙草的个性特征;再譬如该剧对交农号令放三响铳子这一桥段的设计,在小说中只是简要说了交农事件以三响铳子为号令,而在电视剧中则被视听化为白嘉轩与鹿子霖之间的一场斗智斗勇,竟至两人扭打在地上,结果是在鹿子霖的老父亲鹿泰恒抢过铳子后不小心被自己正在抽的老旱烟给点着了,这样第三响铳子才被如约放响,这就是电视剧的做法。电视剧所依仗的视听媒介,就是要能够让人看、让人听的。可以说电视剧《白鹿原》在将语言/文字媒介所能够达到的想象力,用视听媒介真实地展现在了观众眼前,而且人物的性格逻辑和文化特征不仅没有被改变,反而被强化了,可以说既尊重了原著的本义,又尊重了媒介的特性。
在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今天,跨媒介叙事与跨媒介传播正在成为典型建构最重要的途径和方式,许多具有典型性的艺术形象必将会在日趋智能化的数字媒介的强大叙事功能和传播效能中获得新生,成为更加被广泛共识、共用和共享的文化符号。
3.作为建构主体的理论家、批评家和社会公众
长期以来,典型形象的创造一直被视为文艺家个人的事。而在典型建构论的意义上,典型建构的主体不仅包括了更多的作家艺术家、更多的媒介经营者,而且还应该包括理论家、批评家和社会公众。
理论家、批评家应该是典型建构的重要参与者,而且途径很直接。一般来说,理论家、批评家是从两个途径参与典型建构的。
一是已有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成果对作家艺术家塑造人物形象的影响。但凡有一定品位的作家艺术家,都会自觉阅读一些与自己的创作思路相关的文艺理论批评论著。这些论著中的一些观点、理念、思想会对作家艺术家的人物塑造形成直接影响。小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生前曾多次通过书面或口头披露过他在写《白鹿原》之前的阅读情况。他直言,写作《白鹿原》的很多思路和人物塑造的方法来自他的阅读,其中包括对理论批评论著的阅读。其他的作家艺术家大致也有同样经历。这样,理论家、批评家的观点、理念和思想自然会在作家艺术家的阅读过程中潜在地参与到典型形象的建构之中。
二是一代又一代的理论家、批评家对某些已经具备典型性的艺术形象的不断阐释与再阐释。与不同文类、不同文体、不同媒介对已有艺术形象典型性的丰富和扩展一样,理论家、批评家对已有艺术形象典型性的论述、阐释,会对典型意义的发现、认知和扩展,具有直接的作用。事实上,宝、黛的典型意义固然来自《红楼梦》这部作品,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脂砚斋、胡适、俞平伯、李希凡等各个历史时期的红学家、批评家发掘和阐释出来的。而这些来自理论家、批评家的论述与阐释,会直接影响这些艺术形象典型性的再建构。譬如20世纪80年代,央视组织拍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时候,特意邀请了一批红学家对所有演职人员进行了专业的讲解和培训。可以说,1987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之所以成功建构了小说《红楼梦》中的一批典型人物,理论家、批评家们功不可没。因此,理论家、批评家可以说是典型建构主体之一。
社会公众对典型建构的作用是潜在的,而且似乎从来未被人们承认过。然而,这是一个很大的盲区。社会公众的文化习俗、审美习惯、对艺术形象的想象力及其形成的口碑效应、舆论效应,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作家艺术家的典型创造。
社会公众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场,也是一个审美场,还是一个舆论场。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社会公众对艺术形象会形成比较稳定的审美倾向,而且会诉诸舆论和口碑的影响力。“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等语言中所蕴含的巨大想象力,会以某种隐形的方式发挥其潜在的影响力。作家艺术家作为社会公众,不可能不受此影响。无论是在一个艺术形象诞生之前的原创中,还是诞生之后的建构与再建构之中,这种影响力会一直弥散在作家艺术家和媒介的周围,潜在地决定着这个艺术形象的初创、建构和成为一个文化符号的方向与路径。
所以说,理论家、批评家和社会公众,既是典型建构的参与者,也是典型形象的欣赏者,更是艺术形象被建构为一种文化符号之后的共用者和共享者,是当然的建构主体。
四、典型建构论的当下意义
本文所谈论的典型建构问题,特别是典型由艺术形象到文化符号的建构因素、逻辑和路径的一些思路,试图去拓展人们对“典型”及“典型理论”的现有认识,虽难免存在粗疏之处,但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极具当下意义的话题。
1.典型建构论与开放的现实主义
从西方到百年来的中国,传统典型理论都是围绕某个特定的艺术形象及其个性特征和普遍意义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展开的。经典理论家们,特别是黑格尔、恩格斯、别林斯基等对典型的论述,为人们认识典型的本质,为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典型建构论是在充分认同这些经典论述的基础上,将典型形象的创造置于不断流变的、动态的时空场域中,将典型创造的考察视角从单个作家艺术家的一次性行为,扩展为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不同作家艺术家、不同媒介,乃至理论家、批评家和社会公众的协同行为;将典型创造的意义从单纯的文艺和美学层面,扩展到文化建构层面。如果能够在这样的视域中来认识典型形象的话,那么,典型创造就已经不再是某个作家艺术家的专属权,而是由更多的人、更多的媒介参与的协同行为,是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艺术形象的传承与发展。尽管典型形象在建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命运,大部分变得更加丰富和丰满了,也有一部分本来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形象却受到了损害,有的甚至被恶搞、被解构了。但承认这一建构过程,不仅完全符合各类典型形象发展的实际(我们目前认识的典型形象几乎不存在没经过这样的建构过程的),而且对当下和今后的典型形象创造,以及人们对典型形象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典型理论与现实主义精神和方法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现实主义文艺无论是目标,还是过程、方法,都是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尽管文学艺术史上对现实主义有过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如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革命现实主义,乃至魔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等,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直是现实主义文艺的基本原则和目标。然而,如果人们能够在此基础上,从典型建构论的意义上来认识现实主义的话,曾经有人大声疾呼过的现实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广阔起来。因为,建构论意义上的“典型环境”已经不限于原创作家艺术家所描述的彼时彼地的典型环境,而是融合了不同时代因素和不同区域的民族因素的、不断流变的和复合的典型环境。在这种流变的、复合的典型环境中生成的典型人物及其“个性”“共性”,经由不同文类、不同文体、不同媒介,以及不同文艺家、理论家、批评家、社会公众的协同建构,已经具有了某些跨时空的意义,“个性”会更加彰显,“共性”会更加具有跨时空的普遍性。这样的“个性”与“共性”构成的“典型人物”,必将使现实主义不仅成为一条更加“广阔的道路”,而且会成为一条完全开放的道路。在这条开放的现实主义道路上,也将不再是单个作家艺术家踽踽独行,而是操持着不同艺术、不同媒介、不同观点、不同想象力的人们结伴而行,协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典型形象,并一批又一批地将这些形象推入文化软实力提升、民族文化建构的总体进程,凝聚成群星璀璨的文化符号。
2.自觉发掘、建构已有艺术形象的典型性
三千多年持续不断的文学艺术史,让中国文化中潜藏着世界上最丰富、最绚丽多姿的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大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性。但由于经历了太久的历史风尘,很多艺术形象早已无人问津,只有极少数的艺术形象进入了当代人的典型建构视野。这批潜藏在历史烟云中的巨量的艺术形象,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华所在,理应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当代文艺创作最大的IP资源库。所以如果能够让作家艺术家、专家学者自觉地协同发掘这部分资源,并用以当代文艺创作和典型建构,将会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提出典型建构论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提醒人们重视这部分潜藏在历史烟云中的艺术形象的价值与意义,并发挥其在当下文艺创作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的作用。因此,本文期望典型建构论能够唤起当今的作家艺术家、理论家、批评家和各类媒介运营者,以及广大社会公众自觉加入到对已有艺术形象典型性的深度发掘和重新建构中来,并由此创造出具有新的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
当然,典型建构行为一直都在进行中,但大多属于自发的艺术创作、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有的甚至属于商业运作行为。建构者并不完全具备自觉的典型建构意识。从数量和规模上来说,目前的典型建构行为的参与者还属于少数专业人士,还需要更多有能力投入典型建构的人士加入进来,大量的媒介手段还没有真正动员起来去投入典型建构行为。从建构方式和建构目标来看,更多的建构者并不明确该如何发掘具有典型性的艺术形象,更不明确如何将这些艺术形象提升到文化建构的总体进程中来,成为人们共识、共用和共享的文化符号。因此,本文讨论这一话题的意义,也在于提高人们参与典型建构的自觉意识。
黑格尔曾经说过:“历史的事物只有在属于我们自己民族时,或者只有在我们可以把现在看成是过去事物的结果,而所表现的人物或事迹在这些过去事物的连锁中,形成主要一环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事物才是属于我们的。单是同属于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这种简单的关系还不够使它们属于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在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的相关,它们才是属于我们的。”同理,今天的作家艺术家要想真正复活那些消散在历史烟云中的艺术形象,只有把现在的艺术创造看成过往那些艺术形象的结果,并使其与今天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关联在一起,才有可能真正拥有那些过往的艺术形象,才有可能完成对其典型性的重新建构。
可以期望,如果有更多有能力、有条件从事典型建构的人士和媒介,自觉地投入到发掘、建构已有的艺术形象中来,让潜藏在三千多年中国文艺史上繁多的具有典型性的艺术形象,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复活,那么,该会是一次何等壮观的文艺复兴!
3.自觉创造新时代的典型形象
今天,典型创造和典型建构又遇到了新的时代因素和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全面崛起进入了关键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文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物质到精神,正在发生着急速的转型与巨变。因此,中国文艺领域不仅迫切需要,而且完全可能孕育出一批新时代的典型形象。
然而,目前中国文艺发展的现状离时代的要求还存在不小的距离。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
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
这些问题尽管已受到文化管理部门的一再管控和社会公众的普遍抵制,但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而且几乎每一条都与典型建构的方式和质量有关。的确,今天的中国文艺界各类文艺作品产量巨大,但许多作品令人记住的却是满天飞的明星、天价的片酬,却塑造不出几个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的形象。甚至一些已经具备某种程度的典型性的艺术形象,被改编或翻拍进了“神剧”“狗血剧”之中,严重糟践了原创艺术形象的典型性;许多新生的艺术形象由于缺乏时代精神内涵和民族文化根基而昙花一现;许多艺术创作和生产并不是在创造艺术,而是在创造利润;无心建构典型形象,而是在建构自己的商业帝国。
这或许正是我们今天重新讨论典型理论的意义所在,也正是本文提出典型建构论的实际价值所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
的确,典型,无论在原创意义上,还是在建构意义上,都是艺术创造的品格和质量的标志;都是对作家艺术家以及所有典型建构主体的思想水平、艺术素质、媒介素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至高要求;都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艺术良知和艺术理想的严格检验。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典型建构论,除了尝试拓展人们对典型及典型理论的认识等学术目的外,还试图呼唤更多有可能参与典型建构的人士和媒介,自觉地去重新建构已有的具备一定典型性的艺术形象,让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艺术形象随着时空跨越而不断复活,不断获得新生;更重要的是期望文艺界聚集可能的文学艺术资源,自觉地去创造新时代的典型形象,从而促进新时代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