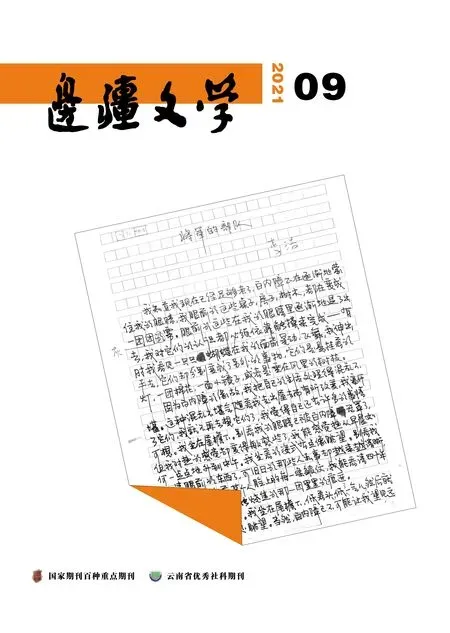百年党史上云南的三大文化名人 散文
晓雪(白族)
学习百年党史,我常常想起云南的三大文化名人:狂飙诗人柯仲平、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和人民音乐家聂耳。
一
柯仲平(1902—1964)是我国新文学史上一位成就卓著、影响广泛的杰出诗人。他对中国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对中国文艺的大众化作出过开创性的重要贡献,他在延安的一系列文艺活动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关怀、热情鼓励和高度评价。他崇高的品德、豪放的性格和爽朗的笑声,他烈火般熊熊燃烧、瀑布般飞腾直泻、大河般汹涌澎湃的激情和洪钟惊雷般震天动地、撼人心魄的诗歌朗诵,他数十年如一日为党为人民的忘我工作、艺术活动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而且也值得后辈后人永远怀念和崇敬。
他出生于云南省广南县,在家乡读完高小后考上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在校时曾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并组织参与了游行、示威、登台演讲、砸日本洋行等爱国学生的活动,17 岁时就在学校创作并登台演出了话剧《劳工神圣》,18 岁发表第一首短诗《白马与宝剑》,并与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秘密成立了大同社,学习北京、上海传来的进步书刊。1924年,考入国立北平政法大学法律系,同年10月24日,写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抒情诗《海夜歌声》,这一年,他22 岁。1925年,他认识了鲁迅先生,就常拿着诗稿到鲁迅家请教。据《鲁迅日记》载,从1925年6月5日到1926年2月23日,半年多的时间,他与鲁迅交往,就达八次之多。常常是交谈几句之后,柯仲平就拿出诗稿,嗓门又高又亮地大声朗诵起来,有时站到凳子上去朗诵,使鲁迅母亲周老太太担心“这个头发都吊在脸上的人”“怕要同大先生打起来”。朗诵完后,他跳下凳子,走到鲁迅跟前,恭敬地弯着腰:“先生,请指教。”每次听柯仲平“大声呐喊”之后,鲁迅都提意见,鼓励他,还把他《伟大是“能死”》等诗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刊物《语丝》和《莽原》上。
1928年冬,柯仲平以大革命时代为背景,创作了反映工农武装斗争的诗剧《风火山》,喊出了“被压迫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建立世界劳动政权”的呼声,诗剧出版三个月后就被查禁。1930年3月,经潘汉年 、陈为人介绍,柯仲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的《红旗报》记者,后来又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和上海总工会纠察部秘书。由于他的诗歌、剧本和论文“宣传赤化”,他在1926年8月、1929年冬天和1930年12月曾三次被捕,在监狱里经受了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还高声朗诵自己的诗《走上断头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上刀山,下火海,也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被组织和朋友们又一次千方百计营救出来后,他于1935年夏天到日本留学,在东京一家私人汽车学校学习,准备将来开坦克杀敌。在日本学习期间,他还同徐克、刘御等云南籍留日学生组织成立了“理践社”,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柯仲平8月便秘密回到武汉,在董必武同志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由于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柯仲平于1937年11月来到延安。
到了延安,柯仲平如鱼得水,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在毛泽东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他出任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副主任(主任是吴玉章),一方面很快成立了“战歌社”,自任社长,与诗人田间、林山、邵子南、高敏夫、史轮等共同发起延安街头诗运动,发表《街头诗运动宣言》,大力推动边区的诗歌创作大众化,另一方面积极筹备并很快组建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自任团长,请马健翎、张季纯任剧务主任,请刘白羽、柳青、方纪、草明等担任教员,迅速组织创作和演出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作品。他本人,既写短小的抒情诗、街头诗,还写长篇叙事诗,仅在1938年,4月份推出一部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12月又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叙事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前者被誉为“是陕甘宁边区最早出现的用诗的语言歌颂工农的长篇佳作”,后者则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用长诗来表现工人斗争生活的作品”。两部长诗都用朴素、清新、平易、亲切的语言来抒写工农兵在抗日战争中的感人故事和英雄形象,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1938年夏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边区印刷厂举办周末文艺晚会,柯仲平最后一个登台朗诵他的新作《边区自卫军》。他声若洪钟,热情奔放,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也坐在观众席上,听得很认真,同观众一起给他鼓掌。朗诵了一半,他感到时间太晚,便弯腰问前排的毛主席:“主席,我看算了,时间不早了。”主席回头看看后面还坐满了听众,便把手一挥说:“朗诵下去!”朗诵完后,毛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很好!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民歌风的。怎么样?稿子让我拿回去看看,可以吗?”柯仲平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当然可以,只是改得太乱,不好看。要么我重抄一遍再送来。”毛主席说:“不必了,先睹为快。”第二天,毛主席就派人把稿子送回来,只改了一个字,并在上面批了“此诗很好,赶快发表。毛泽东”几个大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41、42 两期,破例连载了两千多行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1940年,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由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老诗人肖三说:“延安诗歌运动最初和最有力的发起人要算柯仲平同志,他是朗诵诗放头炮的呐喊人。”柯仲平不但在诗歌创作、诗歌朗诵、诗歌普及和诗歌活动的组织方面在延安做了大量工作,起着引领带头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办和领导的边区民众剧团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创作和演出戏曲现代戏,在抗战八年中走遍边区190 多个市镇乡村,演出达1475 场,观众达260 余万人次,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毛主席曾专门把他和马健翎等人请到枣园一叙,赞扬他们的创作和演出“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大众化的道路。”称他们是“边区文艺的先驱,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播到哪里。”林默涵在《柯仲平与民众剧团》(见1992年11月7日《文艺报》)中说,毛主席在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找来了许多位作家交谈,征求大家的意见,可见毛主席的思想、观点,是从群众中来的。经过综合、提炼、形成科学的理论,反过来又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柯仲平同志和民众剧团的艺术实践,也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
1949年7月,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柯仲平当选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当时只有两位副主席,另一位是丁玲。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任西北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西北文联主席、西北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席等职,在做好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还写了许多好诗,出版了《从延安到北京》等多部诗集。1962年12月,他花多年心血创作的歌颂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的一部长诗却被康生之流诬陷为“反党长诗”,受到错误批判。1964年10月20日,柯仲平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不幸倒下去世。
1979年9月20日,陕西省委在西安举行柯仲平骨灰安放仪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1985年元月五日,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纪念著名诗人柯仲平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习仲勋、贺敬之、张光年等出席。习仲勋在讲话中号召大家“要向柯仲平同志学习”,说他是“一个把一生献给中国革命事业的著名诗人,是一辈子和人民血肉相连、与人民休戚与共的文艺战士。”柯老的爱人王琳在台上朗读了因病未能出席的王震同志的一封信,说“柯仲平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位革命的大诗人,人民的大诗人”。
二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2月3日生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下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他的父亲李曰垓1903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是一个有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有为青年,在仰光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于推翻满清的革命斗争,参加了昆明的“重九”起义,任护国第一军秘书长,起义胜利后任云南都督府军政部次长。他学贯中西,见多识广,写文章才思敏捷、文采飞扬,被章太炎称为“滇中一支笔”。艾思奇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卧室里挂着父亲写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条幅,幼年读私塾时就能背诵先秦诸子的许多文章。11 岁后进入公立国民小学读四年级,除课堂学习外,还在晚间、假日和课余时间向家庭教师学英语、向父亲学古文,并与父亲聊天,少年的心灵里开始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父亲对孩子们的教育很开明也很科学,强调学习的自觉性。他多次说过:“学业的上进,单靠课堂讲授是不行的,要养成博览群书的习惯,要靠自己发奋努力,多读多想,才能成为有学问、有能力、有创造精神的人才。”
1923年,因父亲受到唐继尧的排挤,全家被迫移居香港,艾思奇考入教会学校岭南分校读书。学校的主课是《圣经》、国文和英文。艾思奇的国文和英文在全班数一数二,只是对《圣经》不感兴趣,有时甚至同讲授《圣经》的校长发生争论。有一次,当校长讲到《圣经》里的“箴言”:“当人打你的右脸时,你应该再让他打你的左脸”,艾思奇立即站起来愤慨地说:“我坚决反对《圣经》中的这些话!我们不是奴隶,挨了打,就应该勇敢地反抗还击,我们不能这样忍受屈辱。我们中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不敢反抗的结果!”不容置疑的《圣经》居然受到一个十三岁少年的挑战和亵渎,气得校长大怒:“这是对上帝的冒犯,主将降罪于你!”说完就拍着桌子宣布下课。
1925年,艾思奇回昆明考入省立第一中学读插班二年级。省立一中是云南学生运动的策源地之一,1919年就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并创办了宣传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刊物《滇潮》,后来又成立了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艾思奇积极参加学校的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和学生会文艺部的负责人,并担任《滇潮》的编委,经常在《滇潮》发表反帝反封建的短论和杂文。他还担任省一中义务夜校的训导主任兼教员,利用课余时间搞义务教育,学生大多是工人、学徒和贫苦人家的失学子弟。
艾思奇的社会活动引起当局的注意,把他列入“学生领袖”的抓捕名单。他得知消息后,装扮成一位英国牧师的家庭教师,于1926年随同牧师持化名护照离开云南,到苏州找到父亲。1927年春天,他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负责人、他的云南同乡张天放、寸树声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学习小组。为了更好地阅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在日本期间整天闭门不出,先是苦攻日语,后是学习德语,仅用了一年时间,就能阅读日译本的马克思著作和德国古典哲学,也能通读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
1928年春,因在日本生活艰苦,劳累过度,他患了胃病,回昆明养病两年。这两年时间,他边养病,边比较系统地阅读从日本带回来的英、日、德几种文字版本的马列著作,积极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还以 “店小二”“三本森”等笔名,发表了许多杂文、短论、译文,针砭时弊,鼓吹革命,宣传新思想、新哲学、新文化,在读者中很有影响。
1930年初,艾思奇再度来到日本,考入福岗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他一方面刻苦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同时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时中共东京支部每周在神田组织一次中国青年会的学习会,他每次都从遥远的福岗赶去参加,从不缺席。经过多年的学习与思考,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逐渐坚定,他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总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终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开朗,才找到了对宇宙和社会的发生、发展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解释。”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艾思奇和一批爱国的留日学生表示强烈抗议,愤然弃学回国。1932年初,他先在上海一家日本研究所靠翻译谋生,后又到泉漳中学任理化教员。在学校教书期间,他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并开始以“思奇”“李东明”等笔名在《中华月报》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1933年6月,他第一次以艾思奇的笔名在《正路》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不久又发表了《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两篇文章都思想敏锐、见解独到、文采飞扬,显示出扎实的哲学功底和出众的文字表达能力,在哲学界引起注意。
1934年6月,艾思奇到李公朴先生任馆长的“《申报》流通图书馆指导部”,负责做“读书问答”的工作。11月,“读书问答”栏目从《申报》独立出来,正式改成《读书生活》半月刊,半月刊中的《哲学讲话》和《科学讲话》两个栏目的组稿、审稿和定稿主要由艾思奇承担。艾思奇早有打破哲学的神秘感,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和大学讲台上解放出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人民大众手中的锐利武器的想法,便自己带头写《哲学讲话》,第一篇的题目就叫《哲学并不神秘》。他用平易亲切的谈话形式,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大家熟悉的生动故事,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连续在《读书生活》半月刊发表了二十四篇,1935年11月结集出版,书名就叫《哲学讲话》,先出了两版,大受读者欢迎,很快卖光。国民党宣传机构下令禁止印刷发行。后来改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1936年不到五个月就出了四版,到1948年全国一共出了三十二版。早在1935年,李公朴先生就说过:“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的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1935年10月,艾思奇由周扬、周立波作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除了编著、翻译外,还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他与老舍、郑振铎、李公朴、郁达夫等联合署名发表了《我们对文化运动的意见》。1936年,他发起并组织成立了秘密的新哲学研究会。他还先后出版了《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如何研究哲学》《哲学与生活》等著作,并有一批科学小品发表。1937年,他参加了上海著作人协会,与郭沫若、茅盾、朱自清、郁达夫等署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宣言》。
1937年9月,周扬、艾思奇、李初梨、何干之等一批上海的文化人来到延安,受到热烈欢迎。土墙上贴出了“欢迎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到延安来”的标语。他们到达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就来看望,还给每个人斟茶、递烟。见到艾思奇,毛主席很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你好啊,艾思奇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几遍了,最近还有什么新的著作吗?”艾思奇说:“半年前出了一本《哲学与生活》。”毛主席谦虚地说:“能否借我拜读呀?读完一定完璧归艾!”
不久,毛主席读了《哲学与生活》后,还给艾思奇同志写了一封信:“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
毛主席那么忙,怎能让他来看望呢?艾思奇主动联系,一天晚饭后到毛主席住的窑洞去拜望。45 岁的领袖同27 岁的青年哲学家朋友式的亲切交谈,谈中国,谈世界,谈哲学,谈抗日战争,一直谈到深夜。毛主席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和广博知识,特别是他谈每一个问题都善于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思想方法和独到见解,给艾思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到延安后,艾思奇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主任教员、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任、中宣部哲学小组的指导员、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综合性理论刊物《中国文化》主编、《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等。他主编的《中国文化》在1940年的创刊号上就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发表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他按毛主席指示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之一。他编写的哲学基本教材在《中国文化》上连载。在延安时期,他在做好繁忙的行政组织工作、教好哲学课的同时,还写了大量继续研究哲学、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出版了《科学历史观教程》《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等著作,翻译了《海涅诗选》,为在延安掀起学习哲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为一位有广泛影响的哲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主要还是从事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五十年代初,他应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社会发展史讲座》,出版了专著《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发表了一批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文章,如《评关于社会发展史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对唯心论》等等。他统筹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提纲》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自然辩证法著作。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我国第一本较为系统地论述马克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特别难得的是,在许多人都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年代,他能冷静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地先在《中州评论》上发表《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的文章,指出“破除迷信一定要立科学”,“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接着又在1959年初的《红旗》上发表《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强调指出:“群众力量的发挥总有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的。”“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群众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表现出他作为一个真正马克主义者的坚定立场和卓越胆识。
1959年底,艾思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66年3月22日,艾思奇在北京病故,终年56 岁。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庄严而隆重,灵堂前放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悼念他的四个大花圈,朱德委员长还亲笔写了一条横幅:
艾思奇同志永垂不朽!
三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号子义(又作紫艺)。父亲聂鸿仪是个中医,他四岁那年就病逝了。母亲彭寂宽,是一个勤劳贤惠而又爱讲民间故事、会唱许多民歌的傣族妇女。聂耳从小受到母亲的启蒙,喜欢听民歌,爱听滇剧清唱,爱看花灯表演,还常常到郊外去听农民“对歌”。他的记忆力特别好,白天听了别人唱的调子,晚上能原原本本唱给家人听,十岁时他已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弹三弦,成为小学校“学生音乐团”的主要骨干,除演奏乐器外,他还担任指挥。
1927年秋,聂耳考入全省唯一的公费学校省立第一师范高级部外文组,除搞好课堂学习外,他对音乐、戏剧、文学、美术、体育都有兴趣,成为学校业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云南已成立了中共云南省特委和共青团省委,省师是党团组织秘密活动的重要据点。聂耳开始读到一些进步书刊和马列主义的著作。1928年秋,聂耳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耳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各种活动,被列入军警到处抓捕的黑名单。得知消息后,聂耳便先离开学校躲起来,于1930年7月顶替他三哥到上海“云丰申庄”当伙计。
在云丰申庄不到一年时间,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做好分内工作的同时,坚持学英文、日文、练习口琴、二胡和小提琴。1931年4月,他考入明月歌剧社当乐队练习生,经过半年多的刻苦练习,他小提琴演奏技巧迅速提高,很快成为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他参加歌剧社的各种演出,受到欢迎。但1931年7月12日离开家乡到上海刚满一年的时候,他却在日记中反省自己:“在这一年中,我的生活虽有小小的变迁,但仍不如我计划中的一年应有的进步。”他感到自己只忙于练小提琴,提高业务水平,而没有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火热斗争中去。他开始思考“怎样去做革命音乐”的问题。1932年4月,他认识了比他多大十四岁的诗人、戏剧家田汉,两人看法一致,交谈甚欢,成为知己朋友。不久,他在《电影艺术》上发表《中国歌舞短论》,批评明月歌剧社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仍然为歌舞而歌舞,演出香艳肉感的节目,提出音乐舞蹈应当为人民大众服务。他说:“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
这年8月,聂耳主动退出明月歌剧社,来到北平。在这里,他结识了于伶、宋之的等左翼文化战士,加入北平剧联,参与左翼戏剧音乐的创作演出活动,由田汉介绍,接触了党组织,还多次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钻入了一个低级的社会”,收集北方民族民间音乐素材,体验城市贫民的生活。11月,聂耳重返上海,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从此,主要从事群众歌曲和电影音乐的创作,进入了他音乐生涯的新阶段。
1933年初,聂耳在田汉家中认识了夏衍。2月发起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夏衍、聂耳分任协会文学部、组织部秘书。不久,经过组织考察,由田汉、赵铭彝作介绍人,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联华一厂的一个摄影棚内秘密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监誓人就是夏衍。
1933年夏,聂耳为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电影《母性之光》创作了他的第一首电影插曲《开矿歌》,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他的创作灵感如泉涌、如井喷,从写《开矿歌》到在日本遇难这两年的时间里,他成功地创作了四十多首广受欢迎、充满激情、反映时代精神和人民心声的优秀歌曲,从《开矿歌》《卖报歌》、为话剧《饥饿线》写的《饥寒交迫之歌》,到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的《码头工人歌》《打砖歌》《打桩歌》《苦力歌》,从党直接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桃花劫》的主题歌《毕业歌》到为电影《大路》创作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从为电影《新女性》创作的《新女性》组歌到他改编灌制成唱片的民间器乐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等等,都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在1934年底写的述评《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中,聂耳除继续对脱离群众的音乐痛加声讨外,还充分肯定了左翼电影音乐自《渔光曲》以来新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尤以《大路歌》《开路先锋歌》的刚健新颖、雄烈悲壮为难得,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应该是一九三四年中国音乐不可多得的出产”。
聂耳在群众中的影响,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和仇恨,准备逮捕他。党组织为了保护他,并考虑他渴望得到进一步深造的要求,决定让他取道日本,去苏联或欧洲其他国家学习。1935年2月,田汉在被捕前匆匆写下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聂耳看了歌词,立即“抡”下了作曲的任务。他从夏衍处拿到电影剧本和最后改定的歌词后,连续几天反复推敲、修改、试唱,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在钢琴上弹奏,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他还同导演许幸之反复商量,征求意见。许幸之听了初稿后问他:“你是不是受到《国际歌》和《马赛曲》的影响?”他自信地回答:“是受到一些影响,但要争取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最后,《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是聂耳1935年4月18日带到日本后,又改了几遍才从东京寄回上海的。5月9日,任光组织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袁牧之、金山、顾梦鹤、施超等七人,第一次在百代公司录音棚内录下了这首今天已举世闻名的《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心声,唱出了中国抗日救亡的时代最强音,唱出了中华民族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会昂首挺胸、奋勇前进的伟大民族精神。
聂耳寄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最后修改稿后,开始了对日本音乐的观摩、考察和研究。6月2日,他在东京中华青年会举行的第五次艺术聚餐会上作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报告,还演唱了他创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7月17日,他与友人去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竟被无情的海浪夺去了年轻的生命。那时,他才23 岁。他的骨灰和遗物,由他的好友张天虚、郑子平送回上海,后来安葬在风景如画的昆明西山,可以遥望五百里滇池。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原地重建了聂耳墓。郭沫若题写碑文,称他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称他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我国现在的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壮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