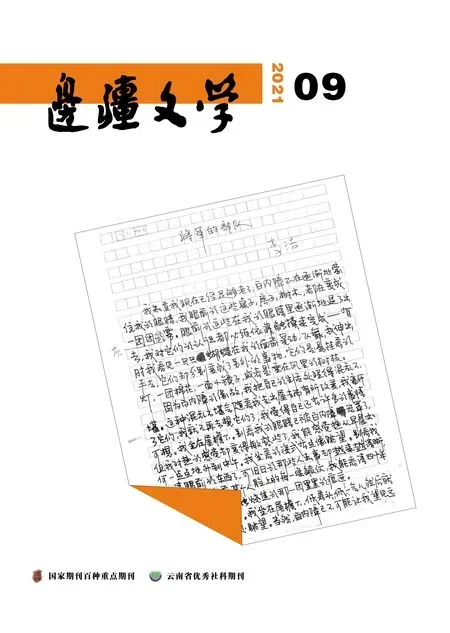养父是一个传说 短篇小说
段平(回族)
部队撤编了。
我这个年龄比较尴尬,三十五岁的正营,留下来上升的空间很小,走吧,又正值盛年,心有不甘。妻子说,地方上,三十五是报考公务员的年龄上限,人家都可以从头再来,你为什么不行?
妻子的意思很明确,让我转业。不是部队撤编,人家还不一定让你走。妻子在电话里强调。
柳政委是我入伍时的指导员,现在是善后办主任。柳政委说,你妻子是对的,三十五岁,你还年轻,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再来。这样吧,我给你两个月时间,回去联系工作。不过,这两个月也不白给,你还得继续寻找熊烈。部队撤编,娘家没有了,如果还是找不到,恐怕今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熊烈是我们师的一位老英雄,但从朝鲜回来,就跟部队失去了联系。十年前,师里编写战史,早已退休的老师长提供过一条线索,熊烈当年因为伤势太重,送回国内治疗,伤愈后,听说转业到了北大荒的一个农场。部队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寻找熊烈,一方面是老师长从北大荒一位战友那里得知,熊烈还活着(还在朝鲜,团里就替他开过追悼会了);另一方面,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熊烈担任排长的3 营8 连3排全体战死,打扫战场时,只知道3 排共击毁英军“百人队长”重型坦克八辆,歼敌近百名,但战斗的具体过程,却无从知晓。十年前的那次军改,部队师改旅,上级要求编写师史,因为没人了解这场惨烈的战斗,师史的编撰工作一时卡住了。我那会儿是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奉命到省城干休所向老师长求助。老师长第一次提到了北大荒,并当着我的面,拨通了那位老战友的电话。但接电话的是那位老战友的妻子,对方告诉他,一星期前,她的丈夫就去世了。
老师长拿着电话看了半天,许久才放下说,不要紧,老战友虽然去世了,但他留下了一条重要线索——熊老英雄的籍贯两面寺。
都说无巧不成书,但这事也太巧了,我就出生在两面寺,两面寺的一座军营里。于是,寻找熊老英雄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我头上。
实际上,过去的十年中,我几乎没有一天放弃过寻找。
这么说,并非我的境界有多高,责任心有多强,而是十年前的那次寻找,虽然无疾而终,但我本人却意外地收获了爱情。
这事说来有点话长。
十年前那个冬天,回到两面寺,按照组织程序,我首先找到了人武部和民政局。但熊烈入伍和转业都没有通过当地人武部,所以那里查不到他的任何记录。同样的道理,民政局也没有。熊烈1948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云南直到1950年的2月,全境才宣告解放,人武部查不到他的信息,实属正常。
在民政局,接待我的人叫小五——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多年以后,我问她,当年那么热情那么认真是不是另有所图?二十五岁的上尉,加上刚刚换发、带资历章和姓名牌的07 式军服,的确很吸引眼球。但每次招来的都是一顿白眼。
两面寺虽然只是一个镇,但因为就在城边上,名气很大。又因为是国家级经开区所在地,人口众多,常住和暂住人口加起来有30 多万,比云南许多县的总人口还多。
小五是经开区民政局优抚科的科长,一开始我还以为她姓武,武科长武科长的叫了半天,才知道“小五”是个昵称,她在家里排行老五。
民政局查不到,小五索性把我带回了家。
路上她才告诉我,她父亲是两面寺文化站的老站长,人民公社时期做过民政助理。她父亲脑子里装的档案,比经开区档案馆还多。
到了小五家,我一面叫“武站长”,一面敬了支“大重九”。“武站长”眯着眼看了看牌子才说,我不姓武,我姓文(后来我才知道,小五叫文苑)。我一愣,这是怎么回事?小五这才解释,她在家里排行老五,小五是她的乳名,这个乳名从小学一直叫到大学,最后又叫到了单位。
听完我的来意,文站长断然道,两面寺没有这个人。我做了二十年的民政助理,两面寺复转退伍军人的档案都装在我的脑子里。我说,常住人口没有,那么暂住人口呢?文站长问我,你说的这个熊烈,大概是哪一年到的两面寺?我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文站长说,那就更不可能了。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的户籍管理非常严格,人们自行从户籍所在地到非户籍所在地,叫盲流,或黑人黑户,属于非法行为。绝对没有这种可能。
想了想,我又说,我记得,两面寺有个熊官屯,一半的村民都姓熊,熊烈会不会是熊官屯的?
文站长说,我就是熊官屯的,如果真有你说的这个人,我还不知道?
我的刨根问底,显然已经让文站长很不高兴了。小五在一旁拼命地向我眨巴眼,我知道,再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自找没趣了。但我还是决定,亲自跑一趟熊官屯。
来的时候,我们科长语重心长地交代,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找到熊老英雄,既是对本部队,也是对英雄和他的亲属负责。希望你不虚此行。一席话,说得我热血沸腾,跃跃欲试。
吸取文站长的教训,这一次我没找官方(村委会),而是让小五带着我直接去找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尤其是当过兵的老人。这一招果然奏效了,一位老大爷说,你们找对人了,我儿子就叫熊烈。我一听不对呀,这位老大爷看上去顶多七十,他儿子充其量也就四十来岁,而我们要找的老英雄,已经七十出头了。老师长说过,熊烈跟他同龄,老师长退休都快二十年了。
离开村里的老人,小五问我,这位熊老英雄有没有家室?我摇了摇头说,没有,肯定没有。我们在师医院查到了一份病历,因为伤势太重,熊烈的脾脏和双侧睾丸都被摘除了。这份病历和组织科保留的档案,是熊老英雄留给部队的唯一的文字记录。但那份档案太简单了,只有入伍和提拔为排长的时间,还不到半页纸。而眼前的小五又是个女孩子,我没法将病历上的内容和盘托出。
没想到,小五听了后说,这样反倒简单了,没有家室,只要在全村的孤寡老人中排查就行了(孤寡老人也归民政系统管)。
由于排查范围大大缩小,进度很快。全村排查下来一共只有五位,但年龄与熊烈相符的,只有一位叫熊三的老人。据村干部介绍,熊三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回到熊官屯的,因为初通文墨,早年还担任过生产队的会计。
姓名虽然不对,但回乡的时间对上了。熊三?也许跟小五一样,也是个乳名?
我们向村干部提出,想见一见这位叫熊三的老人。但村干部说,要见他,恐怕得到三月底了。我奇怪地问,为什么,他出门啦?村干部看了小五一眼,什么都没说。
小五拉了拉我说,走吧,路上我再给你解释。
回去的路上,小五边开车边说,这人肯定是个老上访户。每年的二三月是各级政府召开两会的时间,为了避免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当地政府都会把这些特定人群控制起来。
我大吃一惊,你是说抓起来了?
小五一笑,不是简单的抓起来,他们又没有违法犯罪。是把他们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地点,好吃好喝伺候起来,等两会结束,再送他们回来。
我说,那我们就去这个特定的地点,现在就去!
但小五说,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特定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其次,人家根本不会让我们见熊三。
我说,那怎么办?三月底我肯定等不了。
小五说,你走了,还有我呢。他一回来,我马上去找他。
因此,返回部队后,我与小五开始了长达两年的电话和书信往来。
归队前,我又一次去了我未来的老泰山家。
一见面,未来的老泰山就说,你们说的那个熊三肯定不是你要找的人。这人是个有名的刺头,而且还当过国民党兵——国民党兵?我们部队早年就是由起义滇军改编的。虽说是起义部队,但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坚守汉江之仗,比著名的“万岁军”打得还好(当时,我们与“万岁军”并肩作战),全军伤亡过半,但阵地寸土未丢。战后,军长流着泪告诉彭总,通过这一仗,我们终于能在兄弟部队面前抬起头来了。彭总说,为什么?就因为你们是起义部队?你错了,我彭德怀也是从国民党那边过来的。万岁军有一个就行了,不可能再有第二个。最后彭总说,只要我彭德怀在任一天,你们的番号永不撤销。等苏式装备一到,第一家就给你们换装。永不撤销番号,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也是万岁军。
我连连追问,熊三是哪一年当的国民党兵?
文站长说,听老一辈人说,是抗战胜利前夕抓的丁。当时才十五岁。
年龄也对上了,入朝那年,熊烈刚好二十岁。
但文站长却反复强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熊三是个著名的上访户,他要是个英雄,为什么不去落实自己的政策和待遇?
我又是一惊,你是说熊三上访,不是为了他自己?
文站长说,是的,最初是帮民办教师,帮民办教师落实政策待遇。后来又是帮失地农民,他要是为了自己,早就送劳教判刑了。但每次都是替别人出头,法官也拿他没办法。
接下来文站长又说,这人我太了解了,他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为了赈灾自救,新来的省委书记下令扩大自留地。当时从县里,到公社和大队都有些犹豫观望,担心犯路线错误。但熊三二话不说,拉着生产队长,当天夜里就给社员分了地。他当时是生产队的会计。但到了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他又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为此,还主动辞去了会计一职。公开说,要分你们分,我是不会参与的。当时就有人问他,同样是分地,二十年前,数你最积极,为什么二十年后,你又不干了?他告诉人家,二十年前是为了救命,救急,是非常时期。如今是朗朗乾坤,青平世界。再说了,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大二公,本来就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分田到户,不是倒退,不是让那么多革命先烈的血白流了吗?
这样的人,会是英雄?
说实话,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我确实答不上来。改革开放之初,我还没出生呢。
不过,这反倒让我下定了决心,归队之前,一定要见一见这位熊三。但最后,我还是失望而归,有关部门婉拒了我的请求。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对不起,你是现役军官,这种时候见他,只会助长他的嚣张气焰。
归队不久,我就接到了小五的电话,她说,她见到熊三了。但熊三矢口否认去过朝鲜,更不是什么战斗英雄。你们一定是找错人了。不过,她在电话里安慰我,让我别着急,她会继续找下去。我在电话那边一再表示感谢。她说谢什么,这本来就是她的工作。她是优抚科长,如果两面寺真的藏着一位老英雄,那是她的失职。
没办法,师的战史只能像上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样,写到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最先插到英军29 旅皇家重坦克营前面,对战斗胜利起到关键作用的3 营8 连3 排时,只能笼统地一笔带过,没有任何感人的故事和人物。老师长说过,部队用炸药包、爆破筒等最原始的装备,一口气干掉了英军29 旅皇家重坦克营三十一辆“百人队长”坦克,志司一开始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措辞严厉地表示,谎报战果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毕竟,“百人队长”重达51 吨,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后来,兵团专门派人到现场拍摄了照片,志司这才放下心来。但第一个穿插到位,炸毁八辆“百人队长”堵死英军逃路的8 连3 排,除排长熊烈无一生还,可以想见战斗之惨烈。兵团和军里派人找到熊烈时,他已经在师医院昏迷了五天五夜,至于还能不能醒来,大夫说,只能看他的运气了。从医学的角度讲,他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所以,部队才替他开了追悼会。
那以后又过了两年,小五在电话里告诉我,熊三有一位养子。这么重要的情况,村干部和小五的父亲都没有提到。我立刻向旅政治部柳主任我的老领导做了汇报。柳主任想了想说,好吧,不行你回去一趟,时间不等人啊,熊烈快八十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那时已经下部队担任副教导员了,柳主任说,基层不同于机关,你只能用你的探亲假了。我说行啊,但如果我结婚,你得多给我几天婚假。柳主任瞪大眼睛看着我,你跟谁结婚?我说我跟谁结并不重要,你也不用管。到时候,你只管给我婚假就行了。
回到两面寺,我连家都没回,就让小五带着我去找熊三的养子。
熊三的养子叫熊俊,一看就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
熊俊告诉我们,关于养父,他什么都不知道,早在八年前,他就跟养父分开单过了。我问熊俊,你养父大概是什么时候收养你的?他说是灾荒年生,家里孩子太多,实在养不活,生下地就把他扔到马路边上,看能不能碰到一位好心人。熊俊看上去四十出头,他说的灾荒年生,应该指的是三年自然灾害。
我想问熊俊,他的养父显然是一位好心人,为什么养父老了,他倒要分开单过了?
但小五用眼神阻止了我。
回去的路上,小五才说,熊三的确是一位不可理喻的老人。大约七八年前,两面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经开区,开始大量征用土地。许多农户闻讯买来大批树苗,连夜在自家的田间地角房前屋后种树,因为征地赔偿中的林地,是按树的棵数计算的。熊俊也跟大伙一样,一夜之间种下了五百多棵树苗,但第二天却被养父一棵不剩地拔了个精光。熊俊一怒之下,另立门户,与养父分开单过。
听她这么一说,我越发想见一见这位不可理喻的老人了。但小五说,你来得不是时候,又要开两会了。我说,你们现在还敢随随便便关人?小五连忙否认,没有没有,组织他们外出旅游了。经开区出钱雇了一辆大轿车,计划拉他们沿国境线转上一圈。云南与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四千多公里,这一圈转下来,怎么也得一个多月。
我肯定待不了一个多月,结婚不过是异想天开,小五大眼睛,双眼皮,人长得仙姿玉貌,人家会跟我结婚?
归队后,小五依然跟从前一样,一如既往地给我打电话、写信。当然,电话和信里说的最多的还是熊三。她说,熊三身体大不如前,很少替人上访了。她问过信访局,人家已经把他的名字从老上访户名单中勾掉了。这样持续了两年多,我跟小五终于变成了一家人,按小五的话说,这叫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结婚后,每次探家,我们都要去一趟熊官屯,去看一看熊三。八十多岁的熊三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他连回家的路都常常找不到了,难怪信访局勾掉了他的名字。不过,他的养子熊俊还不错,自从养父患上老年痴呆,他又搬回来照顾养父了。
我们每年都要去熊官屯,起初是我跟小五,小五成了我妻子后,是夫妻两人,再后来有了女儿,变成了一家三口。有一次,熊俊悄悄跟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但你们最好别来了,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也许只是一个传说,你们永远也找不到了。
本来还有一个办法——让老师长出面认一认,但一年前,老师长就因病去世了。
这一次,虽然柳政委(从前的柳主任,我的老领导)慷慨地给了我两个月的假期,但主要是给我联系转业单位的。找到熊烈几乎是不可能了,就像熊三的养子说的那样,也许,他就是一个传说。
话是这么说,但到家第二天,妻子小五还是给熊俊打了一个电话。谁知熊俊在电话里说,养父失踪了,已经失踪一天一夜了。妻子在电话里问他,要不要我们帮忙?熊俊说不用不用,村里的人正在四处帮他寻找。
午饭的时候,已退休多年的岳父文站长说,两面寺自古有个习惯,人老了,不中用了,为了不拖累儿女,都会趁着还能走动,选择离家出走。小五的爷爷当年就是背着一筐鸡蛋(声称赶集),离开了两面寺,从此一去不复返。
见我一头雾水,岳父又进一步解释,两面寺是明代屯兵云南的第一站。当时的云南还是蛮荒之地,危机四伏,除了西汉末年,诸葛亮南征,汉族几乎从未猎足。诗和远方,说起来好听,但谁知道远方是什么,是生?是死?是野兽的血盆大口,还是蛮夷暗中布下的滚石擂木?为了把生的机会留给那些更年轻的人,上了年纪的都会自告奋勇充当探险者的角色,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传统,一种习惯。虽然后来两面寺屯兵第一站的功能逐渐消失,但这种传统或习惯,却无形中保留下来了。
我不由大惊失色,我是从城镇入伍的,虽然出生在两面寺的一座军营,但并不了解两面寺的过往和岳父口中的习俗。莫非,熊三也是有意选择了离家出走?妻子安慰我说,不可能。熊三患上了老年痴呆,他不是离家出走,而是很可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刚吃完午饭,我的搭档装甲营营长杜勇就心急火燎地打来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在家啊,前天刚到,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连连道,好好好,在家就好,老兄,你赶快来一趟马过河,部队开进途中出了点问题,你是当地人,处理起来可能顺利一些。
马过河离两面寺不到五十公里,我连忙钻进妻子的SUV,驱车直奔马过河。
这次军改,旅部机关虽然撤销了,但部队没撤,而是转隶另外一个战区。探家前,我就听说,部队可能过一段就要开拔了,但没想到那么快。
等我赶到马过河才知道,杜勇带了几台车打前站,大部队并未开拔。
杜勇的车队途经马过河时,一辆地方上的车把路边一位老人撞倒了。车队有一名随队军医,杜勇马上下令停车救人。结果却被地方那辆车的司机赖上了,声称自己是为了避让军车,才撞倒了老人。我到的时候,问题已经解决了。在我之前赶到的交警,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怒斥地方司机,信不信我送你上军事法庭?胆敢阻拦军车,你有几个脑袋?同时让杜勇他们快走,事故交由他们处理,跟部队无关。
杜勇把我叫过来,其实是为了被撞的老人。
原来,老人被撞后,当时还没咽气,随队军医下车抢救时,发现老人外套里面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50 式军服。
我的第一反应是被撞老人一定是熊三,不,是老英雄熊烈!
果然,我又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
这张面孔,比我见到的任何一次都更为安详,就像在熟睡之中,又像是卸下了某种重负。
杜勇把老人身上破旧的外套换掉了,换成了从自己身上脱下来的07 式冬季作训服。杜勇虽然比我晚五年入伍,关于熊烈老英雄知道的比我少(毕竟,我找了他整整十年),但还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什么。
我赶到后,军医拉开作训服拉链,露出了里面的50 式军服和军服左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
毫无疑问就是他了,熊烈,我们的老英雄。
我掏出手机向柳政委报告,政委命令,你和杜勇的车队原地待命,我马上赶过来。
熊烈的葬礼非常隆重,极尽哀荣。当地党政军主要领导几乎全部参加了葬礼。我岳父今年七十了,他说,在两面寺,他还从没见过如此隆重的葬礼。
葬礼结束后,在熊烈的家里,我问他的养子熊俊,难道你从没见过养父出走时穿的那身军服?
他说见过,不但见过,他还偷偷地穿过,结果被养父狠狠揍了一顿。那一年他十三岁,也是十三年来养父第一次揍他。
说完,熊俊从床底下拖出一只陈旧的咸菜坛子,依次从坛子里掏出了养父的转业证立功证残废证,以及十几枚纪念章和勋章,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西南战役和抗美援朝纪念章,也有特等功和一、二等功奖章。其中,最珍贵的一枚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授予的“朝鲜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我找了他十年,你知道吗?
熊俊说,我知道,但父亲不许我说。十三岁那年,父亲第一次揍我时就告诉我,他没脸穿那身军装,他是排长,全排三十多个兄弟都牺牲了,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我就更没有资格了。
所以你才说,你的养父是一个传说?
是的,父亲离开北大荒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那儿知道他的人太多了。
我想,熊烈之所以在最后时刻换上了那身军装,显而易见,他已经做好了某种准备——准备去见长眠于地下的那三十多位兄弟了。当然,还有两面寺,还有岳父口中两面寺那种敢为人先的习惯。
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或者还能说什么。
处理完熊烈的后事,我跟柳政委说,我不想转业了,我想跟杜勇的车队去打前站。
政委同意了。
在留队与转业的问题上,我跟小五断断续续争论了好多年了,但这一次,她破天荒地什么也没说。
出发那天清晨,小五带着女儿丫丫来为我们送行。
入冬了,尽管是在四季如春的两面寺,但依然能感到晨风拂过脸面的阵阵凉意。丫丫的小脸蛋白里透红,是冻的。我想,只要像她这样的孩子每天都能坐在安静的课堂里,当一辈子兵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