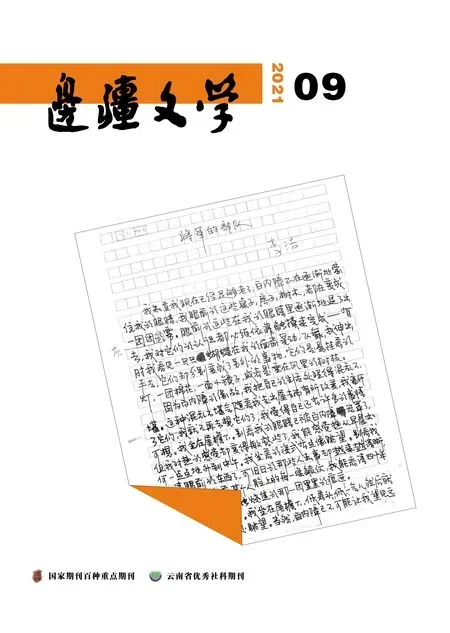万物生 短篇小说
雷霖遥
太阳软绵绵地跌落进院子里,屋前的梨树上,春困还未过去的知了有气无力。树下,王九群正歪在躺椅上打瞌睡,手里还抓着一把未嗑完的瓜子。
“大嫂,那车已经爬上垭口,就快开进大院坝了!”柳芬粗犷的声音子弹一样打进王九群的耳朵。
“这些背时的,电话不打一个,搞突然袭击。”王九群愣了愣,从躺椅上撑起身来,手里的瓜子撒了一地。
“不扯这些没用的,快点,一会儿遭发现了。”眨眼间,柳芬已经走到跟前,一边将院坝里的背篼、锄头、肥料快速捡起往苕坑里扔,拿起扫把哗哗扫地,一边催促还站在一旁发愣的王九群。
柳芬是王九群婆家的兄弟媳妇,两人住在同一间堂屋的两侧。在这同一屋檐下,她俩为了谁生儿子谁生姑娘比过,为了柴米油盐鸡毛蒜皮吵过,为了祖宗留下来的山林土地争过,红脸白眼地过了几十年,在丈夫相继去世后,两人就好得一根裤腰带都要换着拴,吵架也是嘴炮一致对外。
见柳芬已麻利地将院坝收拾干净,王九群赶紧脱下垫着厚厚一层泥的鞋子,哐哐往石阶上砸。泥是早上刚踩上去的,还未干透。王九群手都震麻了,泥依旧死死抱着鞋底。
“刚扫干净,你不要又砸得到处都是。”柳芬一把将王九群手里的鞋子抓过来,反手扔进苕坑,然后转身小跑进屋里,提出一双全身铺满灰的皮鞋。王九群半蹲着,后脚跟刚塞进鞋里,苕坑都还没来得及盖上,一个瘦瘦长长的影子就出现在碎石路的转角。
“奶奶,你最爱的孙子,我,回来啦。”人还未出现,声音已经扑了过来。
“是你崽儿!”王九群和柳芬同时舒了一口气。
“学校放假了吗?不对啊,还没到暑假啊。”两个“啊”字,道出了王九群的惊喜和困惑,本以为又是儿子张国林来查岗,没想到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读书的孙子张星回来了。
王九群双手拉着张星,目光像探照灯一样笼罩住他,长高了,长壮了,也晒黑了。
张星是王九群一手带大的孙子,今年已经22岁,上大四了。以前站着还没有板凳高的张星,转眼已经比王九群高出大半个身子了,从天天在眼前打转,到后来只有寒暑假才能看见。
“快毕业了,回来实习,离报道还有几天,就先回来陪陪你。”张星抽出被奶奶紧紧握住的双手,手臂环绕在奶奶的肩膀上,整个人像玩偶一样挂在奶奶身上,却没有让她承受一点点重量,而是将奶奶整个抱在怀里。
“咦,愣大个人了,还黏奶奶,臊皮。”柳芬的话从王九群和张星间的缝隙挤进去,硬生生将王九群身上的这个“大型挂件”扯下来了。
“幺奶奶也在啊,我都没注意。”
“你娃儿,一回来就满眼都是你奶奶,哪里还装得下我这个幺奶奶哦。”柳芬嘴上一点都不饶人,但从看见张星开始,上扬的嘴角就没掉下来过。
“大中午的,肯定没吃东西,我去给你煮面。”王九群收回一直放在张星身上的眼睛,一边给柳芬使眼色,一边往厨房走去,张星也跟在她身后。
祖孙俩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后,柳芬才蹑手蹑脚地扯过苕坑的盖子,轻轻地盖上,然后回到堂屋的另一侧。
张星将背包放进大屋,屋子和张星小时候一样,东西堆得杂,但一点不乱,所有物件都没有变新,也没有变得更旧。时光就像一块琥珀,将这一切凝固了。
“奶奶,厨房怎么变小了?”
“哪里变小了?是你变大了。”
王九群打开电磁炉放上锅,从碗柜里取出一个大瓷罐,挖出两勺猪油沿锅壁化开。身旁的柴火灶台早就没用了,摆满了瓶瓶罐罐,从盐巴味精到八角大料,一应俱全。
王九群拿出其中一个罐子,随手抓出一把茶叶扔进冒着白烟的锅里。茶叶一碰滚烫的猪油便迅速张开,又迅速卷曲,除了颜色变深外,几乎看不出和刚扔进去时有什么区别。但王九群却知道,煮了一辈子的茶叶面,什么时候加水,什么时候放面,什么时候倒鸡蛋,什么时候出锅,已经成了她身体的条件反射。
面出锅了,张星和爸爸,和爷爷,和村子里所有的男人一样,端着一个大碗,蹲在门口。面条从碗里滑到他嘴里,只发出“哧溜”一声,只是他一点也不老练,被烫得张着嘴直吸冷气。
“是好久没得吃面,吹都不晓得吹了。”王九群拍拍张星的背,扯扯他的耳朵,“慢点儿,怕呛着。”
张星冲着王九群一笑,笑容却因为正在边吸气,边嚼面,显得格外滑稽。
看着蹲在眼前的张星,王九群好像看见一窝包谷,刚才还是一棵苗儿,见风就长,眨眼工夫,就抽穗挂帽了。该是耍起媳妇儿了吧?那闺女像包谷一样乖,肯定的。王九群唉一声,眼眶就湿了。
从小,张星就是整个村子里最能来事儿的孩子,不仅自己皮,还当娃儿王,带着全村的孩子一起皮。几乎天天都有人上门告状。为此,张星没少被王九群揍,但是越打,小兔崽子越来劲。现在立在厨房门后已经快生锈的叉腊肉的铁棍,就是王九群揍他的武器。那时候,全村时不时都能听见张星的哭叫声和王九群的吼骂声,从门前一晃而过。
有时被打痛了,张星就会在心里暗想,打吧打吧,等你老了走不动了,我就搬一张椅子坐在你对面,和你打嘴巴仗,我不跑,你也不追,看谁耗得过谁。
吃完面,张星哪儿都没去,和王九群一起,坐在梨树下。
这棵梨树是张星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种的。从他记事起,每年,这棵树都能结好几筐梨,够他从夏天吃到秋天。直到有一年,爷爷腰上别着斧头,从树梢开始,将树剃得只剩一根光秃秃的树干。
此后好些年没能吃到梨的张星很不理解,长得枝繁叶茂的树,剃它干什么。最近这几年,梨树又慢慢长回了从前的样子,甚至,枝叶比以前更茂密,果子比以前更甜。
抬头看着头上已经挂满果的梨树,张星开始想念那个站在树枝上挥动着斧头的老头。
“奶奶,我感觉有人在想我们。”
“想个屁,就顾着各人到那边儿潇洒去了。”王九群说,“不想他,我们乖乖儿过,各过各的。”
“真的奶奶,我感觉有人在想梨。”
“稀罕他想。”王九群恨了孙子一眼,“我欠他的哟,要是你爷爷投生成一窝包谷,怕是又要飞花挂帽儿了。”
不知不觉间,太阳挂在远山。
“奶奶,你脸红了,像个……小姑娘。”“乱说。”王九群恨了孙子一眼,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果然有点儿烫手。她偷偷呡了呡嘴,偷偷看看那正要落山的太阳。一支阳光刚好打在她脸上,变成了粉红色,阳光在脸上晃荡,像包谷刚抽出的穗儿。
“奶奶,你真的好漂亮哦。真的像个……新姑娘。”“乱说。”王九群拍了孙子一巴掌,扭过脸,最后一朵阳光涂抹在王九群的头上,那满脑袋花白的头发,像一个红盖头。
王九群低下了头,低下了眉,低下了目光。她想起了那天,也是太阳正在落山的时候,一个穷得盖头都没有一块的小姑娘,低着头低着眉低着目光,走进了这棵梨树的影子里,正当她羞得满脸通红的时候,最后那一朵阳光,给她添了一块红盖头。
天色暗成淡蓝色,远处群山如黛,炊烟熏红了晚霞,村子里的灯光点点亮起,住得最远的那户人家,一团橘黄色忽明忽暗,就像草丛里的萤火虫。王九群呆呆地看着远方。月光漫过树梢,清洗整个院子,院子好像被藏进了月色里,盖着天,披着云,安静又温柔……
“我要到梨树影子下面去。”王九群说,“这月光晃眼睛。”张星把奶奶连同躺椅,一把端进了梨树的怀里去。
第二天,村子里的鸡都还未鸣叫,蝴蝶已满院扑腾。房梁下的苕坑旁,王九群正蹲着身子,双手扶着楼梯的顶部,轻声叮嘱正一步一步往下爬的柳芬:“慢点,踩稳再下。”
她们想趁张星还没醒,赶紧把昨天扔进去的工具掏出来。
“背篼,锄头,肥料……还有哪样?”柳芬站在坑里,仰着头比划。
“狗记性!还有我的鞋,我的鞋!”王九群俯下身子轻轻吐出几个字。
将装满工具的背篼从苕坑里背出来时,王九群和柳芬满头大汗,也不知道是累的,还是怕被张星发现慌的。
“快,藏起来。”虽说张星不是儿子儿媳,但王九群还是不敢让这些东西出现在他眼前,看见了万一给他爸妈打电话的时候说露馅儿了,就白费了。
一切收拾完,王九群拍拍衣服准备出门。
“奶奶你去哪里?”还没走出自家院坝,身后就传来张星的声音。
“起这么早?面给你留在碗柜里的,自己热。”看着从来不睡到日晒三竿不起床的张星,王九群愣了一下。
“睡不着了,你要出去吗?我也要去。”张星抓了两把鸡窝一样的头发。
“我就随便逛逛,去看看你姑婆们在干什么,你在家把脸洗了,东西吃了我就回来了。”张星打乱了王九群的计划,她只好胡乱编了一个去处。
“不洗了,反正也还不饿,我陪你去。”
一开始是王九群要出门,最后,王九群是被张星拖着走的。
村子的清晨,就像一颗微凉的薄荷糖,各家各户墙下都开着花,看家狗懒洋洋地坐在门槛边,偶尔叫几声。老路旧瓦,绿树白墙,各条小巷里缓缓流淌的,都是张星的年少时光。
“哎哟,星星回来了!好久不见,又长高了。”
“爸妈没有一起回来呀?毕业了没?”
“带媳妇儿回来没有啊?”
“吃东西没得?想吃哪样?”
一路上,每路过一户人家,张星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好像都带着奶香味。以前,张星不爱听,觉得他们的问题就是废话接着废话,无穷无尽。直到奶奶狠狠拍上一板,他才皱着眉张开嘴,拖着一串“嗯……嗯……啊……啊……”
现在挨家挨户走过,张星都要爷爷奶奶大伯二姑地叫个遍,都要嬉皮笑脸或一本正经地摆上一通。惊得王九群都怀疑眼前这个张星,被掉过包了,不是她的孙子。
太阳还未露脸王九群和张星就出的门,一袋烟就能走完的村子,太阳都爬上屋顶了,他们才回到自家的院子。出去时饿着肚子的张星,回来时已经打着饱嗝撑到要搭着王九群才能走路了。
回家随便抹了把脸,王九群就将自己放到梨树下的躺椅上,眯起了眼睛。
躺椅是竹片拼成的,是她嫁进这个家的第二天,“那个人”给亲手做的。年轻那阵儿,每到月亮晃眼睛,“那个人”就抢先躺在椅子上去。王九群抢不过他,就一边咕哝一边用手掐。他一边哎哟一边拍拍自己的腿:“坐这里,沙发,真皮哟。”说着,一脸坏笑,一把就将她搂过去。“没得你皮。欠你的?”王九群恨他一眼,才半扭着身子,把他当成了躺椅。
几十年过去了,竹片该掉的掉,该断的断,已经变得稀稀拉拉,只能勉强兜住屁股。“那个人”过世时,家里人准备把这椅子一并烧给他。王九群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什么都可以烧,这个不行。他坐了几十年,我才得坐了。”
爷爷死后,张星和爸妈要接她去城里。
王九群不去:“人都不认识,去了怎么活。”
“一开始不认识,多摆几句不就认识了。”
“我摆了一辈子才把这块地摆熟,又去城里重新摆?指不定还没摆熟,我就死了。自己有的不要,老想那些没有的。”
无法。奶奶那张嘴巴,把爷爷哄得给她当了一辈子的跟屁虫。
“你一个乳娃娃,哼。”
也不知劝了多少回,也不知请了多少次,甚至把亲戚朋友都搬来了,王九群还是不去城里。
直到那次,王九群扭了腰,歪在躺椅上难受。张星一把将奶奶连同躺椅一起端起来,“老家就你一个人,你叫我们怎么摆?”
王九群双手抠着门框:“哪样叫我一个人啊?那些坟都在这里,梨树也在,躺椅也在。”像一个赖皮的孩子。
“梨树老了,躺椅也老了,你以为个人还年轻不是?”儿子张国林过来掰她的手。王九群更像一个不愿上学的孩子,脚乱踢,头乱摇,双手死不松开门框。“我不去我不去,那几窝包谷正在挂帽儿。”
一听到包谷,儿子张国林气不打一处来,一边吼妻子来帮忙掰手,一边吼叫:“叫你不种包谷不种包谷,这回把腰扭了该安逸了,哪个有时间来照顾你!”
“哎哟哎哟,我腰不行了,心上慌得很,快放奶奶下来,乖,快放奶奶下来。”
张星赶紧放下躺椅,王九群哎哟连声,说赶紧抬她到床上去。
张星一出门,王九群竟然从床上一溜烟儿起来,把房哐地一下关上了。
“奶奶,你动得了了呀?”
“奶奶哪时动不了,你们回去吧。”
还是无法。
“既然奶奶放不下那几窝包谷,给奶奶把包谷扯了,断了她的路,看奶奶愿意跟我们不?要下得狠手。”张星呆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儿子们走后,王九群把自己挪到梨树下的躺椅上,看淡蓝色的天空逐渐变暗,发了很久的呆,然后擦擦眼睛,开始做一个人的饭……
现在,王九群半躺在躺椅上,半眯眼睛,脸上皱纹深深的,地上一片片苍老的斑驳,像陈旧的胶片。张星在躺椅旁边铺了一张凉席。
“星,你喜欢哪种姑娘啊?”
“心好的。”
奶奶点点头。
“孝顺的。”
奶奶点点头。
“要有点小脾气。”
一阵风过,奶奶偏了一下头,接着理了一下头发,嗯一声,又点点头。
张星一边说,奶奶一边点头。张星说话声音越来越小,奶奶点头的速度越来越慢。
“奶奶,我要找个不准你种包谷的。”
“嗯,都乖……”奶奶悠悠地叹息了一声,“找个像包谷一样饱满的……早点抽穗挂帽儿,让奶奶看见。”
阳光一跳一跳,梨树投下随风微微摇摆的影子。王九群满身都是光和叶子,她眯着眼,不知道梦到了什么,一笑,皱纹盛开,白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
不知道是谁家放电视,声音低低传来。王九群睁开双眼,见张星在一旁睡得正香。
王九群双手撑住躺椅两侧的把手,将身体的重量全都放到两只胳膊上,想悄悄起身。但她忘了,自己是个老东西,椅子也是个老东西,身子一半都还没撑起来,骨头已经咔咔作响,连带着椅子也吱吱嘎嘎地叫唤起来。张星醒了。王九群叹了口气,重新躺回椅子上。
一连好几天,张星就像跟屁虫一样,她什么时候起床他什么时候起床,她去哪儿他去哪儿。
王九群感觉这小兔崽子就是故意的。
“不是回来实习吗?这么多天了,怎么还不去?”王九群一边不断翻炒着锅里的鸡蛋,一边嫌弃地说。
“等通知,你就不想我多陪你几天吗?”
“稀罕你陪,赶快滚去实习,叫你爹来把你领回去,去家里待着等,免得一天晃我眼睛。”
“哼,大王派我来巡山……”张星哼了起来。
“滚滚滚。”
“得令。”
……
“长好高了?水够不够?有没有遭雀啄?”
“我天天去望,绿油油的,长得好得很,像奶娃儿一样。”
“就好就好!屁娃儿整天把我跟着,肯定是他爹派来的特务。”
“我看也是,特务狡猾得很,是要防着点儿。”
“不管了,今天晚上死了都要去看看,不然我心欠欠的。”
王九群和柳芬窝在墙角,嘀嘀咕咕。院子的黄昏是清透的,吸口气,都带着天空的余味。
吃完饭,王九群无精打采地坐在躺椅上,夜色刚刚浸染远方悠悠的山野,王九群就说她眼睛睁不开,睡觉去了,留张星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不一会儿,张星也起身,进屋子里去了。
夜一点一点变深了。本应在梦里喂着猪的王九群,此刻正将耳朵贴在板壁上,侦听着隔壁屋里的动静。
从张星进屋开始,月亮每移过一格花窗,王九群就尖起耳朵贴在板壁上听一次。一开始,她能隐隐约约听见张星手机里传来的声音。等月光移过花窗,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王九群偷偷取下门栓,慢慢拉开一条缝,月光一下子闪进屋来。王九群心上一慌,手一抖,月光吱嘎一声,又退出门外去了。王九群定定神,长长呼了一口气,又把耳朵贴在板壁上。隔壁传来带着奶香味儿的呼噜声。王九群才又偷偷取下门栓,慢慢拉开一条缝,让月光又闪进屋来。把月光关在屋里的王九群,像个背着大人偷溜成功的孩子。
月亮很圆,明晃晃地顶在头上。村子里家家户户,高高的门上,矮矮的墙头上,都装有一盏盏声控灯,每每有脚步声经过,灯便亮起,照亮脚步,也照亮月光。
王九群轻着脚步,直到走出村子,她才只打扰了一盏声控灯的瞌睡。
顺着一条隐藏在草丛中的小路,一直往前,山风微微,像晃荡的月光。不知道走了多久,王九群的面前,出现了一块宽宽的土地,地里清香的杂草随风摇摆,像给这片土地穿上了一件毛衣。这件毛衣的中间,有一个大窟窿,如同天空中有一个月亮。月亮里长满了包谷,已经有小腿高了,在月光下泛着甜甜的光。
王九群闭起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像生活紧张时喝到了一碗包谷粥。她蹲下身子,目光在这窝包谷上抚一下,又在那窝包谷上抱一会儿。好几天没来了,她想知道,这一窝窝的包谷,是不是还乖。
王九群俯下身子,伸出手,将一窝包谷轻轻环进怀里,包谷叶子贴在她的脸上。月光摇晃,山风调皮。王九群好像听到包谷根须的吸吮声,她甚至听到了包谷叶子生长的声音。
“嗯,还乖。”王九群咕哝一声,心上一软,不知不觉间,王九群解开了衣襟,把胸膛喂在了一张瘦一点儿短一点的叶子上。
“吃吧,吃吧,那些年老老少少十几张嘴巴,就靠你们养活,太造孽了。”月光带着奶香,哺育着大地。王九群闭起眼睛,仰起脸,一脸的月亮,就滚落土地。
月光移过包谷林。王九群站起身,风从包谷叶上吹过,带着包谷的味道,和一丝丝的凉意。王九群笑了笑,移步往回走。身后山峦起伏,弯下去的弧线轻托着月亮,那里绿树成荫,小河梦呓,花香鸟语。祖祖辈辈的坟头,也在那里。
王九群站住身子,月光下万物生长,“那个人”,是不是投生成了一窝包谷?是不是最瘦最短的那一窝?自己刚才喂的那一窝,是不是就是“那个人”投生的呢?如果不是,那窝包谷为什么会那么“坏”?
月色溶溶,山风喃喃,草虫啾啾。王九群满脸泪水,像一个刚揭开盖头的新姑娘,像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小媳妇儿,像一棵正在抽穗挂帽儿的带露的包谷。
第二天一早起床,王九群精神抖擞,给张星煮面时,她一边炒着茶叶,一边想象着,等再过一段时间,那些包谷就长得和张星一样高了;再过一些时候,包谷挂帽儿,张星也要带着姑娘回来了,那个姑娘,肯定像包谷一样饱满。
想着想着,王九群哼起了不知哪个年代的小曲儿。面煮熟,去推张星的门,吱嘎一声,床上是空的。这屁娃儿,大清早的跑哪儿去了?不管他,继续哼小曲儿。
到中午饭的时候,张星回来了,一脚的泥巴,一脸的怪相。王九群正要问,柳芬喘着粗气闯进屋来:“肯定是这屁娃儿干的,就种那屁股大的一块包谷,都又扯得须须都不剩根儿。”柳芬看着屋里的张星,边说边拍大腿。张星坐在凳子上,就都当没听到。
王九群愣住了,半截小曲儿卡在喉咙,吐不出来,吞不下去。
柳芬还没唠叨完,“这都好多回了?哪个晓得,防住了大的,没防住小的。”柳芬依旧不依不饶地念着,仿佛张星扯的,是她种的包谷。“你读那么多书,就为回来当特务扯包谷啊?”
自从那回种包谷扭了腰,王九群年年种包谷,年年被扯。有年包谷都挂帽儿了,还是被扯了。王九群摇晃到院子里,梨树被风吹得摇晃,阳光破碎,蝉声隐匿。
王九群有些发呆,她这辈子只会做三样事:喂猪,种地,带娃娃。
王九群这辈子最骄傲的三样事,就是把猪当成庄稼一样呵护,把娃娃带得和猪一样肥,把包谷种得像娃娃一样大。
只是自从那回种包谷扭了腰,王九群最骄傲的这三样事,儿子孙子一样也不让她做了。
和当初想接她去城里时一样,王九群说什么都不答应。
“不种地猪吃哪样?”
“不养猪了。”
“不养猪娃娃过年吃哪样?”
“满大街都是猪肉。”
……
这一次,王九群没有犟得赢。猪圈空了,地荒了,她心也慌了。有时人也要死不活的样子,像要死不活的一棵苗儿。只是春耕一到,王九群就又像换血了一样,像个年轻人。
这天,儿子回去,发现她鞋上又堆满了泥。
“妈你是不是又种地了?”
“屋里什么都有,种什么地。”
“那你鞋上那么多泥巴?”
“农村哪点没得泥巴。”
不管儿子怎么问,王九群打死不承认。
见什么都审不出来,张国林也就不问了,出去溜达去了。
张国林前脚刚走,王九群就背着背篼出门了,一路上,她每走两步就会前后左右地瞄一下,跟张星小时候背着她去偷人家的杏子一模一样。偷偷摸摸到达包谷地,刚放下背篼,“妈,你不是说没种地吗?”儿子的声音出现在身后,王九群一把锄头就停在了半空,张着的嘴巴也半天落不下来。
“跟你说了不种地,家里什么都有,你一天没事就多休息哈。”
“就种了这几窝包谷,其他的什么都没种。”
“不行,不能种。”
“就一把包谷种,我一边耍一边就种完了。”
“叫你休息哈,你那腰……”
“休息了的,又没让你来种!”
张国林说不过,唉一声,转头冲进包谷地。没等王九群回过神来,秋风扫落叶,半块地的包谷苗儿,就被扯起来丢了。王九群想拦住儿子,却发现在儿子面前,除了这张嘴巴,自己连儿子的一根手指头都拧不过。
“哪个教你糟蹋庄稼的呀,你们都是老子一窝一窝种出来的……”王九群站在包谷地里,把那一棵棵包谷苗儿,捧起来,看看,满脸泪花。又回过头来看看儿子,就一脸的心痛。她一屁股坐在地里,“我不种了该行了。”王九群哭得像个孩子。傻傻站在旁边的儿子,眼圈一红,偷偷扭过脸去,闭起眼睛仰着头,背影像一个大人。
太阳要落山了,儿子张国林才把她抱进背篼里,背了回来。
一路上,张国林喘一口气,就说一声:“妈,不要种地了,种了一辈子,该休息了。”王九群窝在背篼里,一直哭。
“妈,你说,我这么大一个人,背你都费劲。”儿子又歇了一肩,喘了半天气,“你说你还要种包谷,哪个忍心。”
王九群窝在摇摇晃晃的背篼里,还是哭。
“那包谷,像你们小时候,奶娃儿大的个个,乖得很。”王九群好像在自言自语。
“那,我们就不乖哟?”
王九群眼泪又下来了,打湿了背篼。
“都乖……”
儿子一走,王九群又翻出之前种剩下的包谷种,背着背篼上坡去了。这一次,她选了离自家房子两三里远的撂荒了的那块地,她一边流眼泪,一边忙,忘了吃饭,也忘了流汗。再不快点种,就长不起来了。好不容易,包谷破土了,儿子张国林又回来了。
“你娃儿是真会算时间,快来吃饭。”张国林刚想说话,王九群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喊他吃饭。大葱炒腊肉,渣海椒,凉拌西红柿,洋芋汤,全都是他喜欢吃的菜……
想用好吃的收买我,哼。张国林将买的东西放进屋里,刨完饭,就出门巡山去了。回来将怀里抱着的包谷苗扔进院子。
再一次,张国林绕了一上午,在一处僻静的山沟里发现了已经被自家遗忘了很久很久的斜坡地,满坡的包谷。
又一次,张国林寻遍自家所有的土地,都没见到包谷的影子。正当感到欣慰的时候,却从幺婶柳芬的眼神里,看出了端倪,于是将柳芬家的地,也翻了一遍……
就这样,王九群防贼一样防着张国林,张国林抓贼一样抓着王九群。
王九群从最开始的指着张国林的鼻子骂,到后来的哭,到最后每一次都笑着保证:“不种了,再也不种了。”
气得张国林搬走了家里所有的种地工具,连张星小时候背的小背篼都给搬走了,最后撂下一句狠话:
“妈你要是再种包谷,我就把你背到城里去!”
……
张星扯了奶奶的包谷之后,就天天守着她,一老一小在这院子里,看日出,日落,又看日出,日落。
那天雨后的黄昏,张星端着一碗面坐在门口,远方山野翠绿,一道彩虹悠闲地挂在天上。
“我碗都快洗完了,你崽儿面吃完没有!”王九群站在池子旁,拿着一个刚洗干净的碗,面前的水龙头里,水哗啦啦地放着,水花四溅。“哐当。”王九群手里的碗掉了,身子也顺着池子缓缓滑下。
听见屋里的动静,张星半碗面也掉落地上了。
“晚期了……”医生说。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张星好像踩在棉花上,每一步都虚虚的。王九群正躺在床上呆呆看着窗外。
“奶奶,没事了,我们回家。”张星哑着声音说。
“我说没事没事,你们非要把我搬到医院来。快走快走,再耽搁几天,包谷都瘦了。”王九群从病床上撑起身,开心地催促。
回家后,王九群天天窝在躺椅上。她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清醒的时候,王九群让张星去给她取照片,很久很久之前她就让相馆洗好的,是那年进城,路过新修的大桥时,张星爸爸给她拍的,她说那张照片好看,满脸笑容。讲到好看时,她口气还很得意。
她拉着柳芬的手,说那些年为了巴掌大的地,几年没和她说话,过年都是各过各的,真的是傻。说感觉当她的大嫂像才当了几天,还没当够。
模糊的时候,王九群会流眼泪,说天都黑透了,那个背时的,还不来接她。
家里随时都挤满了人。王九群看见院子落雨,梨树开花,她听见山风吹来,她看见偷偷种在屋后的那几窝包谷,正长成一个个奶娃儿的样子,一道彩虹从包谷粉红色的花穗上生长,长到了天边。她披着盖头,像一棵包谷挂了帽儿,走上彩虹。那个人,站在彩虹的那头,正朝她一脸坏笑。她脸一红,低下头,闭起了眼睛。
走到彩虹的中间,她回头看见张星带着一个包谷一样饱满的姑娘,那个姑娘好像在朝她远远地喊奶奶。儿子张国林已经长得像一个包谷,一副欠掰的样子,好像说了一句“妈,我们不乖……”这话听起来好像浸饱了水。王九群嘴角泛起一朵笑意。
“星啊……”王九群睁开眼睛。张星立刻将脸贴着奶奶的脸。
“屋后,有块土……我种了几窝包谷,和你一样……”
张星听到奶奶最后咕哝的两个字是:“都乖……”
流着眼泪,张星来到屋后。他看见一块磨盘大的土地,地里荒草丛生,没有包谷。
一阵风吹过,荒草来回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