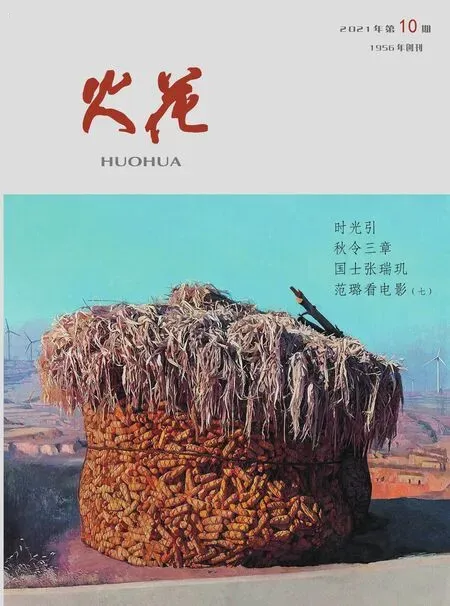时光的胎记
宋雨薇
被日子悄悄偷走的年轮,经历过各种空缺,却始终有那么一截儿失眠的记忆,宛如一块清晰的胎记被打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无论你身处何方,它都将不动声色地坐在每一个时间的出口等你,与时光签约。
从我懂事的那天起,我似乎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家庭里的一个特殊形态的劳动力。小伙伴们对我总是过于偏爱,不管我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们总会一股脑儿地给我编织了一篮子的绰号送给我。于是,过早地就有了自尊心的我,经常被那些绰号打击得一路哭嚎着跑回家。跑回家也无处告状,因为面对我的总是一个空荡荡的泥草房,和那些只要看见我的出现就会围着我唱出各种音符的大大小小的活物们,它们听不懂我的忧伤,更没有耐心听我诉说我的心事。
我一直怀疑,生长元素是不是在我的体内迷了路,否则为什么它成功地改变了我的生长方向。同龄的小伙伴们像吃了催化剂一样,拔着高儿地生长,而“小不点儿”却成了非我莫属的代名词。我不仅是小伙伴口中的“小不点儿”,我还是众所周知的“园长”。在众多的绰号当中,“园长”的绰号因为文明,才治愈了我懵懂的自尊,限制了我的泪水缓缓流淌。
我爸虽然一辈子没有走出大山,但是他却仿佛有着天生的领导才能。他会按照力气的大小给他的孩子们进行合理分工,却对他们的海拔高度不管不顾。孩子的年龄在他的感知里,似乎并没有清晰的界限。而且,他好像从我一出生,就看出了我与众不同的才能。由于过于相信我的能力,我家院子里那些连唱带叫的活物们,被他进行统一打包分配,全部归我分管。就这样,在我八九岁的光景里,我没有当上村长,却在无记名投票下成为了我家手下兵将最多的分管领导。于是,“园长”的代号由此而来,村庄里的大人小孩儿,似乎从来不提我的名字,一律以“园长”对我冠以“尊称”。
而我分管的那些兵将们,它们不会朝我巧笑,也不会朝我献媚,更不会哄我开心。它们五音不全,却完全不懂羞涩。只要我一放学回家,它们就会朝我欢呼雀跃地跑来,将我团团围住,卖力地奏响五花八门的“园曲”。它们的歌声一点儿都不好听,会让我头疼不已。不像我,只要一展歌喉,还能得到听众的表扬。
在村庄里,我可是出了名的小歌唱家,只要想起来,就会旁若无人地亮起歌喉,唱起动听的歌曲。有一次,因为得意忘形,我在课堂上正写着作业,竟然忘我地唱起歌来。年轻的班主任当时只是惊讶地“嗯”了一声,我一下子便如梦初醒。班级里顿时响起了一阵欢快的笑声。我没有害怕,也跟着放松地、使劲儿地笑着。那一次的得意忘形,老师竟因此提名任我为班级的文娱委员,让我第一次拥有了被认可的欣喜。
别看我是小不点儿,但既然荣升为园长,我就得学会继续提升我难得的自控能力,管理好自己内心的渴求,让它们不被忧伤侵略。直到现在,我都不得不佩服自己,有限的时间,总能被我在只有一位数的年龄里,清晰地梳理、妥善地安置。
每天放学后,我总是一路小跑回到家。放下书包,先是牵着那头有着足够的耐心、仿佛可以把时光走到天荒地老的大黄牛到树林里,找到合适的地点妥善安置。
下一步,我会争分夺秒,一路奔跑回家,认领另一个手下大将——那头活泼的小毛驴。它好像天生就是注定要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来训练我的短跑技能。只要一出圈,不管缰绳在我的手里有多长,它都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撒腿就跑,以最大的威力挑战我有限的耐力。
至今想起,仿佛从那时起,我手下的这两名大将,从那一刻起,就在我的命运里埋下了注定我从此一生奔波的伏笔。
我妈总是夸我懂事,因为我从来不像别的小孩儿,哭嚎着逼迫大人们,以此满足他们内心的需求。超强的自控能力,仿佛从我一出生起就尾随而至,扎根于我生命的脉络中,将所有秩序以外的混乱打得落花流水、仓皇而逃。我总会以惊人的能力,用沉默将内心的渴求深深掩饰,不露一丝痕迹。
但那一次,我破天荒地、惊天动地地宣泄着我升级了的忧伤,希望引起大人们的注意。因为我实在还只是一个小孩儿,而且是个子超矮于同龄小伙伴的小孩儿。我害怕树林里的寂静,更害怕树林里突然出现的声音。尽管我一直调动我全身的勇气,尽力安抚着我的恐惧,但沉默最终不能承受恐惧之重,忧伤的泪水一泄千里。我妈在我忧伤的哭嚎里,不停地哄着我,告诉我,只要我听话,一如既往地对我分管的工作恪尽职守,她就会在当晚奖励给我一包我最喜欢吃的炉果。
或许是因为难得的美食诱惑,我努力地掩饰着忧伤的情绪,抽泣着带领着我的两名大将走出家门。不同的是,这一次我的小伙伴———小狗欢欢一路撒欢地陪着我跑跑停停,向我们的阵地——远离村庄的大山曲折进军。
等我精疲力尽地好不容易将两位大将给整合到一个树林边的区域,进行统一管理后,一把弯弯的镰刀和大大的柳筐,便充分地发挥了它们的用武之地。寂静的树林里,两位大将的胃口让我望而生畏,我割草的速度,与它们一张一合咀嚼的频率相比,只能永远甘拜下风。
驴司令再驴,它似乎还懂得怜香惜玉,懂得留给我些许让我可以喘息的片刻。它狼吞虎咽地吃饱后,便安静地站在大树旁,优雅地咀嚼着寂静的时光。而那个慢条斯理的牛司令,却对我的疲劳奔波置若罔闻,看不出丝丝缕缕的怜惜之情。它那似乎永远也填不满的胃口,仿佛永远都不知道,黄昏与夜晚的距离会有多远。
傍晚,当柳筐里的清草再次清空,我已记不清,这是多少个割草的来回了。可此时的牛司令却依然旁若无人地、忘我地埋头苦吃,填满它的胃口,仿佛永远是一个遥远的未知数。
最后一次清空柳筐时,时已黄昏。此时,虽然恐惧侵袭了我的从容,但秩序感仍然在我清晰的意识里,淡定前行。
下山了,为了节省时间,我肩膀上挎着柳筐,一手牵着驴司令,一手牵着牛司令,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林子里。可是,贪婪的牛司令却仍然在我的催促中,一边惊惶失措地走着,一边还不失时机地啃上一口出现在它视线中的青草,全然不顾夕阳西下,我内心升级了的恐惧。
突然,一直欢快地跑在前面走走停停地等着我们的小狗欢欢,此时却在原地转着圈,凄惨地“汪汪”叫着,而后拼命地朝着村庄的方向跑去。受了惊吓的驴司令,拼命地挣脱我手里的缰绳,惊惶地朝着与村庄相反的方向一路飞奔。
而一向慢条斯理的牛司令,此时却仿佛像在打醉拳一样,圆睁着双眼,疯狂地甩着头,划着圈。彼时,尖尖的牛角,因为愤怒,仿佛都充满了血,变成了红色。它一边嘶哑地叫着,一边努力突围,寻找出口。最终,才冲出一棵棵树木的障碍,找到回家的道路。准确地说,是牵着我,跌跌撞撞地冲出树林,跑向回村的山路。
原来,一边走一边贪婪地啃咬青草的牛司令,不小心碰到了腐烂的树桩下一个极其隐蔽的马蜂窝。被意外侵袭的马蜂们气势汹汹地冲向它们的敌人,分工明确地抱团包围了我和我的大将们。在那个看似温柔的黄昏,血一样的夕阳,寂静的树林里,小狗欢欢惨烈的叫声、驴司令惊恐的奔跑声、牛司令那燃烧着痛苦和愤怒的嘶叫声,交织在一起,打碎了大山里傍晚的沉寂。
我的右手背,在被牛司令牵着我奔跑的过程中与锋利的镰刀热情亲吻后,洒下一路热血,这一切升级了我所有的委屈和恐惧。那一刻,我的情绪无处可去,终于让我为多日来的委屈和忧伤,找到了宣泄的出口。那个傍晚,我惊恐的哭喊声,响彻在充满血色温柔的黄昏里。从来没有任何合适的场合,可以让自己不加掩饰地宣泄情绪。那时,我甚至在心里多了一份坦然,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释放出口,可以不加掩饰地发出与自己年龄标配的哭声。
那一晚,小狗欢欢趴在狗窝里,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叫声。牛司令一改往日的安详,狂躁地将身体贴在牛圈的栅栏上,不时地蹭着被马蜂狂吻过的身体。而驴司令在那一晚,却彻底地被我丢失了。我悲伤地以为,它再也不会回来了。直到第二天清晨,或许是因为在奔跑的过程中被树木缠绕住缰绳而无法出逃,痛苦地挣扎了一夜的驴司令,在村庄出口的树林里有幸被乡亲们发现,从紧绷的缰绳下解救出来。最后,直到驴司令眼泪汪汪地、委屈地被好心的乡亲送回家,全家人才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长气。
我以为我要死了,在绝望的情绪中哭到睡着。醒来以后,却发现自己比死了还要难堪。因为马蜂们对我穷追不舍的爱恋,那个面容清秀的园长,一夜之间被马蜂们爱得面目全非,就连小狗欢欢都认不出我,不肯和我一起玩耍了。我躺在炕上,一边反复地看着缠满纱布的右手,一边暗自庆幸,庆幸自己仍然完整无缺。
那几天,我的幸福来势汹涌,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罢工,躺在温暖的炕上,躺在充满温情的奶奶的身边,没有任何心事地听着奶奶的故事,睡醒一觉又一觉。还可以不必为手下兵将们的饥饱担忧,因为我无法动弹,我一身伤痕,我无能为力。我开始渴望疼痛再长一些,这样我才有资格享受如此高配的待遇。
我爸在劳动之余替我上岗,暂时接管了我的园长职责。我妈本来承诺只给我买一包炉果,可是不知为什么,一向节俭的她却一口气买了好几包,一半放在奶奶的枕边,一半小心地放在我的面前。她说,这一次,要让我一口气吃个够。
看着眼前的美食,我没有之前想象中那样狼吞虎咽地消灭掉我的战利品。我只是挣扎着翻了一个身,学着我妈的样子,将它们放到了奶奶的枕边。这时候,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我的日子就会很长,幸福还会有增无减。而奶奶的日子,在缺乏能见度的未来里,已丧失单曲循环的能力。在无声的沉默里,清晰可见的年轮将往昔一圈一圈碾压,剩下的日子,变得屈指可数......
后来的日子里,我才知道,在盛开的年华里,还盛着童年以外、一些回不去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