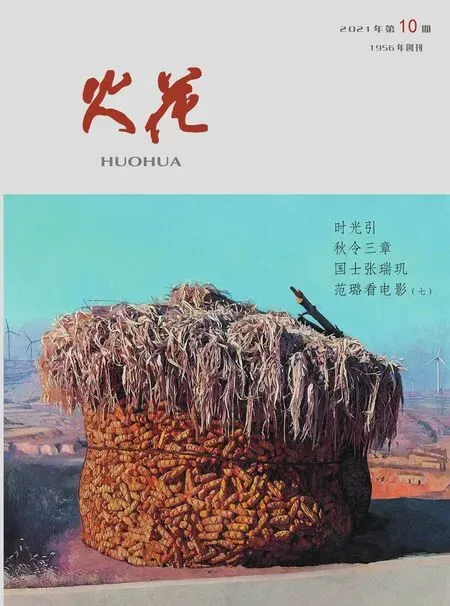李峰诗歌
在一枚黄叶中逃亡
盛夏。院子里的枣树一如往年,树干粗壮
枝繁叶茂。无意间,用手轻轻抚摸着那
凹凸不平的树身,瞬间,岁月在指间滑过
向上看去,树叶上有虫子叮咬后留下的洞,
阳光
泄漏出疼。去年还有几颗果实,挂在高高的
树枝上,容颜沧桑,有如几个山林中的隐士
一棵枣树与我,仿佛相依为命的两个兄弟
黄昏时分,一枚黄叶从枣树上飘落,很轻
很慢,就像一根指着落日的时针。此时,我
把那枚黄叶捧在手中,捂热。然后,迅速逃亡
末伏第五天
立秋之后,天空的蓝更加透明,每一朵白云
都穿起婚纱。一场空山新雨,大地之上,辽阔
舒展得更加宁静、端庄。经过一个夏天的孕育,
万物
都举起热烈的伞,涨满欲望。秋天,总要收获
院子里的枣儿,已露出半个红红的脸,如羞涩
待嫁的
新娘;清晨的凉风中,不知潜伏在何处的鸟儿,
鸣叫声
此起彼伏,仿佛只有你知我知的暗语;一朵刚
刚盛开
的月季,从花坛里探出头,像是玫瑰的伴娘,又
像是秋的一声问候
天凉好个秋。年年“七夕”,我会眺望远方的蓝,
深呼吸
一次。在月季花的影子里,把自己深埋进去。然
后,盯着
那一缸默默无语游动的鱼,在这一天,给自己
披件衣裳
喜欢平淡
现在,我越来越喜欢平淡这个词了。我眯着眼
把它拆成平安、淡然的时候,有一股清洌的泉
水
涌出,在我发僵的年龄上流过,渐渐舒缓成一
道
小溪。我如释负重,原来,这些年里,我背负的
都不是我想要的
视力好时,总是望着天空,看着那些耀眼光鲜
的
事物,手掌朝上,眼睛发亮。昏昏然几十年,一
手捆绑着幸福
一手揽着虚无。直到眼拙后,才发现布衣穿起
来是多么
舒服,粗茶淡饭吃起来又是多么有味。而此时,
脊梁已被荣耀压弯
我再一次凝视平淡这个词时,手掌朝下,脊梁
挺直
眼前一亮:原来,与平淡一字之差,淡定就是个
变本加厉的骗子
推开窗,就会有风进来
山与山之间是沟壑,如窗。风,穿行于此
夏日森林茂密,冬天白雪皑皑,几亿年里
风景如画。高耸的悬崖峭壁,也是山,无窗
如一道严实的屏障,刻凿在崖壁上的佛像、故
事
被风长年累月地抓挠着,风化成一堆又一堆的
悲剧
逼仄的日子,多有一块一块的块垒,横亘在那
里
如峭立的崖壁。心口紧闭时,胸腔内奔跑的
都是顶风、逆风。多少年里,长期的对峙,比石
刻刀
更锋利。风化的不仅是肉体,还有被灵魂一遍
一遍
拷问过的往事。释放和包容是万物的两个出口
一扇窗就是心灵的一束光。推开窗,就会有风
进来
在世间,我们彼此互不相欠
呼吸是生命的体征。用心浇灌培育的
一盆花,日夜向我献着殷情,枯萎后,那
落花,回到泥土,等待再一次转世;笼养的
一对鹦鹉,我必须保证按时喂水喂食,尽管
如此,也不会让我的手指靠近它们,听着它们
的
鸣叫,怎么听,都像是对失去自由的抗议。鸟殇
后
我把它们还给土地,也算还了它们自由。这些
年,在世间的土地上
行走,吃着土地上生长的五谷杂粮,住着土地
上建造的
房子,偶尔也会带起尘土。于是,我只能一边耕
耘,一边打扫心底
一盆花、一对鹦鹉,还有我,都平行于世间,各
自都是
一段呼吸的链接。断开后,我们彼此互不相欠
初始
一只刚出窝的小麻雀走失了。光鲜的
翅膀,还未沾染这世间的尘土。小眼睛
一眨一眨,像两滴纯清的露水。它可以
低飞,那高度刚好是一个洁净的童年。我的
目光与它对视时,它羞涩地躲在墙角,像个
无助的孩子。不知道,这算不算我们之间的一
个暗示
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孩童多好呀。至少,我们俩
的
童年,可以在一个高度飞翔。至少,不要用这
满身的尘土,满脸的皱纹,满头的白发,吓着它
在一场夜雨中,我掩埋着一切
连日的高温,树叶在崩溃,鸟鸣在
崩溃,蓝天在崩溃,白云在崩溃,河流
在崩溃,日子在崩溃。极限就是一场
预谋,一定有一种救赎,在暗中和解
盛夏总是被诱惑和冲动挟持。一条
咆哮的河,一片金黄的麦穗,一朵怒放的
花,如同认养的一头一头老虎,与季节
较劲成一场闪电、雷雨、冰雹,都是暗器
黑夜是谅解的道场。一场夜雨,就是
一把慈眉善眼的梳子。雨声中,没有刀枪
剑影,没有闪亮的词汇,在黑暗里听雨
所有的对垒都是温柔的情人,你只需要一点一
滴地掩埋
赏鱼
飞来飞去的鸟,用各种鸣叫声展示着
各自的语言表达才华,这世间的喧嚣
比鸟鸣更嘈杂。而我更欣赏那些水中
的鱼儿,用干净的水,把自己的身体包裹
起来,与尘世隔绝。如果死,那就跳出水面
我相信水中的每条鱼,心中都怀揣
信物,每张一次嘴,都在默默诵经
或祈祷,那摆来摆去的鱼尾,怎么看
都是对诺言的坚守。如果我有心动的秘密
一定要托附给一条鱼保管,它从不说话
听鸟叫总要仰起头来,时间久了,颈椎
会麻木、粗糙,这让我活得很累很累;而
观赏一条鱼时,心静如水,最关键的是
我的眼睛与它对视时,心照不宣,我已经谅解
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