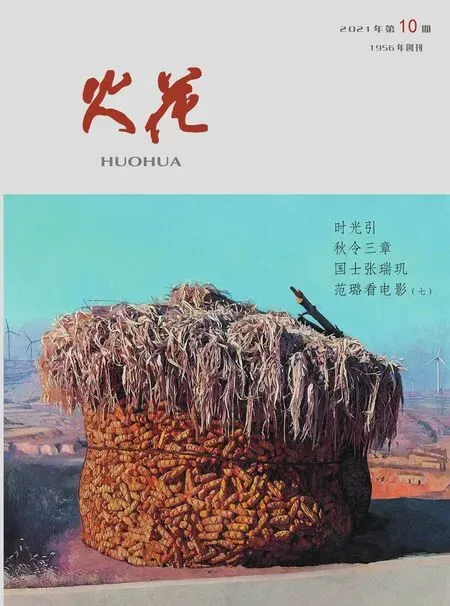村庄记忆
葛东兴
小院的树
农家的小院里,谁家也少不了树。一棵,几棵,都是乡村里极寻常的树。
但自家院子里的树最是亲切。
早春二月,院子西边的杏花开了,烟雨娉婷地,摇曳在春风里。站在屋前远远地看,眼睛里就荡起缕缕春意。
苹果树开花,是四月里的事。印象里只开过一次,一树的白,在那绿里,朴素的样子。那时不会觉得花的美,不会细细端详,只想着果子快些熟了,摘一个吃。
枣花是晚些时候开?不甚记得了。只记得小小的枣花密密匝匝地开了一树,又在风里簌簌地落了一地。
五月里,阳光还不是很热烈,只是满世界都水亮的白。石榴花开了,一朵朵红艳似火,娇嫩热烈,像十六七岁少女的心。那时节,屋门上新换了竹帘,挑帘而出时,一树火红直撞到眼里,心里也由衷地美起来。什么样的美,也根本不知晓。月上中天的时候,疏密的竹帘上映着石榴树的影子,勾起一个少年许多的想象。
那时,榆树上的榆钱大概已经被攀上树的我们一枝枝地捋光,一把一把地塞到嘴里吃掉了。有些被母亲骂着留下,做了榆钱饭。
椿树上新长的叶子也被钩下来,被母亲做了菜,嚼在嘴里有别样的香味。
桑树长出了叶子,又有得盼了。桑葚没有熟的时候,姐姐想要养蚕。母亲找来蚕卵,放到簸箕或者一只鞋盒子里,不知过了几天,蚁蚕从里面爬了出来,是一些黑色的小点。我们爬到高高的桑树上摘下嫩绿的叶子给它们吃,目不转睛地围着它们看。姐姐悉心地养着,我们都四处玩乐去了,哪天看一眼,蚕长大了,哪一天再看,蚕开始吐丝了,哪一天又看,它们结茧成蛹了。后来,它们被母亲收到了哪里,再见时又到了来年的初夏。
桑葚还没完全熟,红的绿的在枝叶间闪闪得叫人垂涎。爬上去,急急地摘一颗,送嘴里,酸酸甜甜。给母亲扔下几颗,她酸得直皱眉,爷爷摇着手说不要吃。等桑葚变成黑褐色,完全地熟了,轻轻地摇一摇树枝,桑葚就雨点似地纷纷而落。一颗颗拣到瓷碗里,用清水洗净,一颗、两颗、三颗地吃,手上嘴上都染成了黄褐色。
盛夏,散在小院里的几棵桐树早伸出茂密的叶子,遮出一片片绿荫。晴天或雨天,叶子上淌下一缕缕的光或淅沥的雨滴。记得五六岁时,我们透过那浓密的枝叶看到天上的月亮,院子里静悄悄的,弟弟说,看,月亮在跟我们走。
杏儿熟了,被我们吃掉了,石榴咧开了嘴,我们把石榴的颗粒一粒粒剥到手里,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往嘴里挤它的汁。苹果熟了,咬一口,酸的,枣子熟了,尝一颗,异常地甜。没什么可以吃了,邻家院子里的柿子树,挂满红红的柿子,远远地诱着人。一下子,忽然就秋天了。
风来了一场又一场,雨也来了一场又一场,叶子黄了,掉了,纷纷一地,爷爷把它们扫到一起,烧掉。每天傍晚,那些青烟都袅袅地散到了夕阳里。晚上,秋风一阵紧过一阵,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地响了一整夜,不知道又有多少叶子被吹落了。那一天,我们看到头顶的天空忽然变得那么空远那么萧索。
树们一年年地生长,以为会永远地生长着。
可是家里要盖新房,那些占地方的树要被砍掉了。有两株石榴树被砍掉了,剩下的那株也不再结石榴。我们没有在意,姐姐家还有一株,年年结出硕大的红石榴。后来,榆树也被砍掉了,我们没有在意,村庄外有更多的榆钱可以捋了吃。再后来,苹果树被砍掉了,我们仍是没有在意,每年的秋天,姑妈会送来更好吃的果子。杏树还在,只是那一年再长不出青杏,我们也没有在意,母亲会在集市上买来。可是家里的桑树被砍掉了,我们一下子变得沉默不语,我们再吃不到酸酸甜甜的桑葚了。那时,我们才发现许多树都不见了,只有桐树,散落在小院里,还有那几棵瘦弱的枣树,孤单地生长着。秋天的小院,更加寥落了。
再看天空时,月亮明晃晃地照在小院里,照到人的心上,一片空落。
没有人再种植新的树。小院便一年一年地寥落着。我们在风中一年年长大。
离开小院后,又走了许多路,遇到许多树,却再没有一株会叫人那样地想要亲近。小院的那些树,叫人永远地怀念。
风吹过玉米的叶子
故乡的夏天是绿的,是洋洋洒洒铺天盖地肆意盎然的绿。金色的麦子收割以后,麦茬还新着,套种的玉米苗就齐整整地冒了出来,它们急忙忙地,一天一个样,攒足了劲地长,拔节,抽叶,打伞,长成田田的样子,一片一片,像绿色的湖水,一天一天,悄然漫过人的脚,溢上人的腰,没过人的脖颈。
这绿,也不单单是玉米的绿。放眼望去,草儿是绿的,树叶是绿的,辣椒苗是绿的,棉花苗是绿的,豆角秧、西瓜蔓都是绿的。这醉人的绿从农人的汗水中一丝丝滋长出来,翠生生,亮汪汪,泼辣辣,生机勃勃的,在风中浩荡,在雨里涨潮,淹没了田野,涨满了人的心房,让夏天变得饱满又亢奋。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就像是在一望无际的碧波里踏浪。那绿,无边无际,蓬勃着生命的朝气,张狂着季节的色彩,肆虐着狂浪的心情,若万马奔腾,似大河奔流,如鼓胀的情感,要撑破人的心房,又如疯长的枝蔓,要一直伸向天边去。
生命真是一场倾情的舞蹈,是如此的放纵和肆意。
童年夏日,于田间采绿,摘枝上的青杏,偷蔓上的黄瓜,捋树上的榆钱,割山坡上的草。彼时,故乡宛如乐园,犹若宽阔马场,由着人撒欢,打闹,高歌,奔跑。在盛夏奔放的怀抱里,小小的梦想也开始伸展膨胀,折一根树枝,舞在手中就是横扫千军的金箍棒,骑在胯下,就是纵横万里的赤兔乌骓。
稍大,才知道,这广阔田园全然是农家的粮仓。颗颗粒粒,一瓜一果,一豆一穗,都混合了滚烫的汗水和期望,都凝结了岁月的甘苦。农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风里来雨里去,月亮下播种,日头下收割,以血汗谋生计,向天地讨生活,有艰辛也有快乐。
渐长,又知道,这无言山野居然是一只沉默的口。它默默地长出芳草、花朵、庄稼、果树、虫鼠,又悄然吞掉秸杆、树木、房屋、人畜、梦想、远方。它凹下去,就是一口流淌生命的井,它凸起来,便是一座埋藏生命的坟头。它养育了多少生命,就收藏了多少灵魂。
后来,又听说这方沃土也蕴藏着多少传奇。紧挨着的那座简朴村庄竟是赵盾故里,常去赶集的镇上曾为晋国故都,赵氏孤儿的故事在这里流传,黄沙一夜平晋国的惨剧在这里发生。远近村庄的名字也都大有渊源,大夫们学习礼仪之地称之习礼;太子们拜师求学的村庄名为师庄;屯兵习武展示军威之地号曰扬威;蓄养六畜的地方,就叫牛席;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三公议事救孤儿的地方,就叫三公村。北面挨着的曾是尉迟恭的封地,南边镇上曾有郑板桥教书的私塾。这些人物典故,让故乡一下子高大起来,有了历史的光彩,找到了生命的源头。这宽广无垠的原野也变得更加厚重了,好像在一颗麦穗里都能嚼得出历史的滋味。
然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几千年的风霜凋零了故事,年复一年的是村庄里日日升起的炊烟和一成不变的柴米油盐。谁家的牛生了牛犊,谁家的猪生了猪崽,谁家的盆碰了碗,谁家的爹打了儿。清晨,牛马出圈耕作田间,夜晚,犁锄归家闲置农舍。嫁人的新妇当了婆婆,听故事的孩子拈着胡子讲起了故事。张家长李家短,过了多少年,还是李家短张家长。历史风云,人物风流,都成了茶杯里的一碗茶,烟袋锅里的一口烟。田野,不再是谁的封地,不再是谁的疆场,不再是谁的都城,不再是谁的军营,而只是生长口粮安放灵魂的一片土壤。故乡,不再是谁的旧地,不再是谁的故居,只是走熟了的一条巷子,躲迷藏时的一堵矮墙,是能自由出入的一道柴门,能随意打滚的一方土炕,是能安顿身心的一个家,能储藏记忆的一个窝。如此平凡,又如此不凡。
夏日漫长,好像没有尽头。好像从远古至今就是这样的艳阳高照,就是这样的恒久热烈。阳光如不灭的灯火,绿色似不息的浪潮。蝉鸣之中,烈日之下,玉米们旁若无人,不停生长。它们列队整齐,寸步不移,悄悄地抽穗,吐须,结出饱满的颗粒。夕阳欲坠时,晚风渐起,那些风好像从飞鸟的翅下吹来,一丝丝,一缕缕,一股股,汇集起来,越来越汹涌澎湃,越来越浩大欢畅。风中混合着泥土的芳香,洋溢着玉米的甜味,夹杂着青草的气息。叶子们先开始说着悄悄话,慢慢有些嘈杂,渐又变得热烈喧哗,像是逗着乐,哗哗笑个不停,终于忍不住纵声唱了起来,这歌唱,此起彼伏,一声高过一声,一浪盖过一浪。风在它们头顶盘旋,像一只握着指挥棒的手,左一挥,高亢,右一舞,嘹亮。田野荡漾着无限的生机,像一团翻滚的云,像一片动荡的海。小路上奏响虫鸣,细细碎碎的,清新悦耳的,一切都在生长,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村庄原该是体面的老者,安详而静谧。此时,却像亢奋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翻来覆去,在庄稼的合唱中心潮澎湃,难以入眠。田间的风,像醉酒的人,歪过来倒过去,吹偏了银河。叶子们跟着它舞蹈,挥一挥长袖,扭一扭绿腰,如痴如醉,如颠如狂,仿佛永远也不会止歇,仿佛永不枯竭的生命永远奔腾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