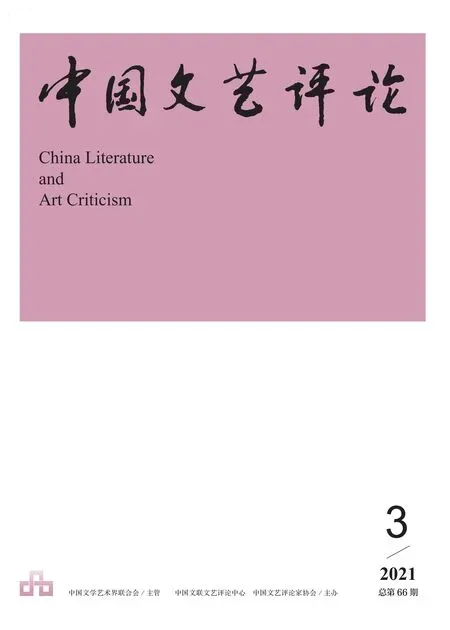在历史烟尘中勘探人性
——读长篇小说《七步镇》兼论陈继明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郎 伟 杨慧娟
陈继明费时数年写就的长篇小说《七步镇》,是一部意蕴复杂的小说。这部小说以作家东声的患病(东声分别患有回忆症、抑郁症等诸种病症)经历和治疗过程为显明的叙事线索,以东声执着寻找自己的“前世”为核心情节,其中穿插了大量的个人心史、男女情爱、时政思索、历史考证和田野调查等内容。如果一定要归类,《七步镇》属于“复调小说”一类。然而,由于作品意绪丰饶、虚实相生,且文体暧昧繁复,故又构成了小说本身的“迷雾”特质,带来了读解的难度。笔者与陈继明相识差不多有30年,对他的小说创作一向格外关注。初读《七步镇》,曾经有许多迷惑和不解。待读到第二遍时,内心的迷雾才渐渐散开。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读懂了这部杰作。但是,我们可能已经触摸到作品解读的门闩了,并使之有所松动。下面的见解,是门闩松动之后透出的一点光亮。
一
《七步镇》明显地存在着两个叙事声部:现实的和历史的。小说所呈现的现实图景是:有个叫东声的作家病了。他得了一种精神性疾病:回忆症。回忆症是一种心理强迫症,它的具体表现是:一旦开始回忆就没完没了,难以中止。任何一个偶然的因素都有可能触发某一段特殊记忆。东声十岁左右经历过一次死亡事件。那次事件的中心人物是童年伙伴小姑娘小迎,小迎死于铁道上的游戏,而铁道游戏的最初建议者却是东声。为此东声一直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导致了小迎的死亡,他的内心充满了悔恨和难言的伤痛。十年前,东声的母亲猝然辞世。前一天东声还在与母亲通电话,次日晚上却接到母亲急病住院的通知,第三天凌晨母亲就走了。东声感情上接受不了母亲突然离世的事实。母亲去世后,他一直模仿母亲当年的厨艺“喂养”自己,体重陡然增加。东声有过三次失败的婚姻经历,在婚姻生活中,东声总是处于弱势地位,“不像个男人”(这是其中一位前妻对东声的评价)。眼下,东声又一次坠入爱河,与女博士居亦爱得死去活来。居亦曾经是个被遗弃的婴儿,在重庆福利院长大,现在澳门与养父母住在一起。现实中的东声不是一个只知道独守书斋的知识分子,他关心混乱的伊拉克局势,对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与当年中国人的笨拙耿耿于怀。一个偶然的机会,东声接受了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博士的催眠,在睡梦中,东声发现自己回到了甘肃老家,居然成为土堡当中的一个土匪头子。于是,催眠醒来之后的东声开始了漫长而执着的寻找。他既想知道自己的“前世”是不是那个年轻的土匪头子“鹞子李”,又想拼命洗白梦境中自己手上可能沾染着无辜者的鲜血和曾经的罪孽。从这里开始,小说进入了两个声部的交替演奏。一个声部是东声重返甘肃故乡的仔细勘察和费力寻找;另外一个声部是故乡甘谷久远的历史生活由过去深潜于地底一变成为鲜活的人性和人的命运的生死荣枯。两个声部循环往复,共同构成了《七步镇》的雄浑和悲怆,也共同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部小说当中,现实的喧闹和历史的纷扰是如此紧密地拥抱贴近在一起,仿佛一对难解难分的恋人,读者又怎么能够把它们分得开?譬如东声意外得到的那只人皮鼓,当它鸣响的时刻,到底发出的是千年之前(唐朝)的幽鸣之声,还是现实空间里的异常声响,愚钝如我们者,又怎能分辨得清楚?是的,历史的浩瀚星河不仅在旷远的天边若明若暗地不停闪烁,也常常在我们头顶的现实苍穹中喧哗旋转。东声的“今生”不也是与他的“前世”有着永远切不断的血缘关系吗?
二
从小说叙事的总体面貌和艺术气象而言,我们倾向于将《七步镇》这部长篇小说视为中国社会近百年历史的一个寓言。如果我们的解读无误,《七步镇》涉及的最早历史时间是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同治年间,爆发了陕甘回民起义,小说中马家堡子的最初主人马如仓等于战乱之中仓猝离开甘谷,其具体时间背景即是清同治年间。小说当中另有一处别致的历史记载:光绪十年(1885年),一名人称巴尚志的澳洲传教士从广州出发,一边行医一边传教,于此年夏天进入甘肃甘谷的安家嘴。巴尚志此后再没有回过澳洲,他与当地一个女子结婚,最终老死在安家嘴。这一历史事实表明,西北虽然地处偏远,但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借传教士的宗教之行开始逐渐进入到西北的穷乡僻壤。1929年,甘谷(原名伏羌,唐武德三年设置)更名为今天的名字,但境内依然兵连祸结、匪患频仍。1931年,地方军阀马廷贤占据天水,七步镇盐商金三爷的大儿子李则广(“鹞子李”)应征入伍,后因战斗失利遂带手下人脱离马廷贤部队,占据了马家堡子,杀掉了土堡中原有居民26人,将马家堡子变成土匪窝。1935年,在甘谷、通渭一带做土匪的李则广投靠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接受整编,先后任副团长、团长。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爆发,李则广团参战,他的一团兵士大部分阵亡,他和几个卫兵侥幸生还。1942年,李则广脱离军籍,一人还家,从此再不问国事,只以饲养牲口为生。1966年冬天,在一次批斗会上,由于李则广自己坦承1933年曾带手下人袭击了马家堡子,杀死丁、罗两姓26人,遂使在场的丁家后人一时暴怒,用杀猪刀杀死李则广。李则广有一个同胞兄弟李则贤,原是20世纪30年代七步镇地下党的领导人。1937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国民党天水警备司令高增吉率人抓捕七步镇的共产党秘密党员,李则贤闻讯逃脱,后赴延安。解放后,李则贤在湖南溆浦担任县委书记。李则广死后,李则贤始还家,兄弟二人解放后一直没有见面。
我们费力廓清小说的叙事“迷雾”,努力还原小说的历史背景,是想说明:小说所讲述的故事——甘谷大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人的命运的生死歌哭、起伏动荡,恰是百年以来中国人命运的写照和高度概括。举凡大地烽火连绵、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状若猪狗;比如外敌入侵,内乱不止,同室操戈、亲痛仇快。甘谷的大地上所修筑的一千三百多座古堡,岁月深处的万般悲惨情状,不正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辗转挣扎于生死线上的如实描画和文学写真吗?我们从来不相信陈继明是一个只愿意咀嚼个人悲欢而对天下苍生不闻不问的创作家。从他的小说代表作《骨头》《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粉刷工吉祥》,到《一人一个天堂》《陈万水名单》《北京和尚》,再到眼前的《七步镇》,陈继明的灵魂深处一直充盈着悲天悯人的炽热情感。他来自西北大地,幼年又经历过贫困生活,深知稼穑不易、父老艰难;他熟读中外经典,深深懂得读书写作不是为金钱玉帛,而是为百姓命运呐喊,为社会正义呐喊。所以,我们把《七步镇》视为一部寓言,是一部以个人和西北小镇人的命运透视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小说。从这个角度而言,《七步镇》有着与《白鹿原》等当代杰作相同的精神血缘和共同的精神底色。
三
现在,我们需要进入作家陈继明的内心深处来探讨一下他写作《七步镇》时的精神立场和情感态度了。我们认为,如果说《七步镇》这部杰作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精神立场的话,那就是相当强烈的“罪感意识”和“救赎意识”。这两种意识在小说中相互交织、缠绕,共同构成了小说非常强劲的思想冲击力。众所周知,“罪感意识”和“救赎意识”来源于基督教。在基督教看来,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当年在伊甸园中,由于经不起诱惑,违背与上帝的约定偷吃了分辨善恶树的禁果,不仅当时就被逐出乐园,而且从此有了“原罪”。正因为人自出生起便背负着人类始祖犯下的原始罪过,所以人这一生都是“有罪的”,必须通过不断的忏悔和灵魂的净化,才可以完成心灵的“救赎”。“罪感意识”和“救赎意识”作为一种舶来品,近代以后开始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被接受,一些现当代文学作品当中也出现了它们的身影。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一篇有着强烈的“罪感意识”的小说。鲁迅在这篇作品当中不仅意识到了中国四千余年的漫长历史是一部“吃人史”,更是深刻地意识到“我”也是这“吃人者”之一。鲁迅之外,许地山、庐隐、老舍、巴金、曹禺等作家,都在写作中笔涉“人的罪恶”,希望“罪人”们通过忏悔和有意识的“受苦”等途径,获得灵魂的拯救。新时期以来,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家们对历史、现实、人性所进行的深度审视,在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土牢情话》、戴厚英的《人啊,人!》、张炜的《古船》等小说中,“罪感意识”和“忏悔心态”成为非常鲜明的精神价值立场。尤其是隋抱朴(《古船》)这一“忏悔者”形象的塑造,他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罪感意识”,他在磨坊里似乎永无止境的灵魂自我折磨,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最为动人的文学风景。
从文学创作思想传承的角度而言,陈继明的《七步镇》与“五四”先贤的思想和新时期早期作家们的创作是有渊源关系的。我们这样说,一点也没有看轻陈继明创作的创新之意。罗兰·巴特在《零度的写作》一文中说:“某一作家可能运用的写作只有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才能确立。”米兰·昆德拉也曾说过:“依我看来,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他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只有在历史中,人们才能抓住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的,什么是发明,什么是模仿。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为人们得以甄别并珍重的价值而存在。对于艺术来说,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坠落在它的历史之外更可怕的了,因为它必定是坠落在再也发现不了美学价值的混沌之中。”所谓“历史和传统的压力”和“诞生于他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云云,实际上都在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后起作家的创作都处于一个强大而历史悠久的谱系当中,文学传统构成了后来的创作者赖以建构意义的精神资源。我们发现,在陈继明的《七步镇》当中,“罪感意识”成为一个反复回响的主旋律。而“罪感意识”的承担者,即是叙事者——作家东声。前面已经说过,东声患有回忆症和抑郁症等疾病,这使得他总是反复回忆起前尘往事。童年伙伴小迎之死是东声的心结之一,也是促使他内心不断生成“罪恶感”的核心事件之一。悲剧过去了几十年之后,当重返故乡,东声依然在遣责自己:“我没有直接杀人,起码间接杀了人。”小说当中更意味深长的叙事设计是,在一场催眠治疗的“梦境”之中,东声的“前世”忽然成为混乱动荡的民国年代地方上的一个土匪头子,这个土匪头子生性残忍、杀人如麻。于是,从梦中回归现实之后,东声开始了颇受煎熬的田野调查和历史求证。与其说,东声想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真实“前世”,不如说东声想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柔弱身躯,承担故乡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残忍杀戮和血腥争斗之罪孽。也就是说,只要是曾经发生过的罪恶,迟早要有人站出来平静领受、真诚忏悔甚至接受审判。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简单把陈继明的叙事设计理解为单纯的艺术技巧了。如果我们用心揣摩小说文本,会惊讶地发现,生活于当下的东声,实际上每天都在承受着灵魂的被拷问。这个敏感、多思,“罪感意识”始终萦绕于心的知识者,不仅要承受早年生活的心理创伤所带来的内心折磨,更要不停地被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感反复逼问。无论是巴勒斯坦人的诉求,还是长达十个小时的纪录片《浩劫》中那些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脸上的“苦难者表情”;无论是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人皮书装订术”,还是1937年冬天七步镇三个共产党人被枪杀和一个孤单女人的自杀,人类所有做下的罪孽和犯下的罪行,都需要被知晓、被认领,并经由忏悔、反思等精神通道而达到彻底的清算和救赎。应该说,尽管东声始终疼痛和挣扎于人类曾经的苦难和罪恶之中,但他对人类还是抱有基本的信心的。在欧洲,他和居亦在调查了人皮书的历史和观看了大量的欧洲影片之后,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感受:“我们有很多感受,其中一个共同感受是:当我们对整个人类抱有信心的时候,对自己的信心对个人的信心,对男人的信心和女人的信心,也有明显的提升。尤其是,我们都认为人类是一个有缺陷的存在,我们应该对人类缺陷抱有警惕,但不要试图拿起手术刀,把人身上的所有缺陷剔除,只剩下好的、讲理的、文明的部分。有缺陷的人类,仍然值得尊敬和热爱。甚至可以说,更多的奥秘藏在人类的缺陷和绝望里。”正是遵循着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小说给出了人类的救赎之道:爱和温暖。因为“一个没有爱过的人,或者目前没有生活在爱中的人,会更凶狠更毒辣”。既然美国心理学家哈里·哈洛的实验结果证明,动物和人一样需要爱——实验表明:小猴子如果生下来之后缺乏母猴子的爱抚和保护,长大后会更有攻击性,更孤僻,性成熟后甚至不能交配,那么,高贵的人类为什么不能以深情之爱和长久的温暖去消弭残忍、杀戮、仇恨、恶毒、邪恶和一切人间不义呢?
四
陈继明1988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为止他创作小说已经整整33年了。三十多年来,他始终将创作的焦点对准西北的黄土地,从故乡甘肃(包括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第二故乡宁夏)的历史烟尘和现实生活的跃动当中寻找生存的故事,细致勘探人的命运和人性本身。他来自于乡土社会,乡土人生既是他个人生活的原初之地,也是他创作取材最为深切之处。他以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中短篇小说《北京和尚》《灰汉》《陈万水名单》《节日》《骨头》《粉刷工吉祥》等构筑了一个文学叙事当中的“西北系列”。在这个文学系列当中,他如实状绘西北社会岁月深处的苦难和挣扎,深切同情和深入思索刚刚跨入城市地界的农民的多舛命运。与流行的写法不太合拍的是,陈继明的书写笔致有时会逸出一些固定的写作范式,显现简洁劲健的叙述生活和穿透生活的艺术能力。在短篇小说《骨头》中,他叙述几十年前乡村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杀事件,如何给本家族唯一的幸存者父亲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并成为他此生最为浩大的话语资源。结局却是颇为出人意料的:在父亲的反复告诫之下,家族的后人们以一种温和而韧性的奋斗,完成了对于一度受到损伤的家族荣誉的修复。我们读陈继明的这篇小说,仿佛在读一个近现代中国寓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由野蛮、仇恨和暴力构成的凶险的世界当中,化干戈为玉帛的勇气和以柔克刚的生存智慧,正是东方哲学的最伟大最动人的真谛。对于受城市化浪潮推动而进入城市的农民命运的关注,一直是陈继明小说创作的敏感点。发表于2004年的短篇小说《粉刷工吉祥》(《上海文学》2004年第4期)是一篇当时就引起文坛格外关注的作品。这篇小说讲述农民工(粉刷工)吉祥因为在邮局汇款时与营业员的一个小小的争执,而在一天内受尽凌辱几乎丧命的故事。作者冷静的、压抑性的叙述以及对于吉祥“死而复生”后不愿提及往事的叙事设计,都在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文学方式向现实凌厉发问:城里人真的把受尽辛苦的农民工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看待了吗?如果没有,城市的明天将会怎样?评论家金理这样评价《粉刷工吉祥》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经常会看到,批评家们对今天的文学丧失介入、参与等积极品质的严厉批评。然而面对陈继明这个短篇,我们很难再轻易地判定文学沟通现实能力的匮乏,也很难判定,当代文学是否真的丧失了介入、沟通现实生活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成为当代创作最为重要的潮流之一。异常喧嚣而又复杂多变的城市生活,既给许多创作者带来创作取材的便利,也带来思想和艺术趋于同质化的困扰。作为一个以描写乡土人生见长的小说家,陈继明的城市小说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写作风貌。他发表于1996年的《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朔方》1996年第2期)是获得文坛高度称赞的一个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相当深刻的洞察力精确敏锐地捕捉到了市场经济体制初建之时,我国社会生活中一种带有弥漫性的消极心理(小说中称之为“集体无意识”)——“烦着呢”,并揭示出这种消极心理背后所潜藏的巨大危险性和可能带来的社会灾难。小说一经刊载,便以逼视现实的巨大勇气和思索生活的特殊深度而备受好评。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当时就将小说称之为近期创作中“罕见的好短篇”。2011年,陈继明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北京和尚》(《人民文学》2011年第9期)。这是一篇涉及坚守信仰还是拥抱红尘两难困境话题的小说。可乘和尚的诸多不舍和红芳们的百般缠绕,既是欲望至上、利益至上年代世俗生活的写真,也是内心动荡时期芸芸众生暧昧难辨的精神世界的尖锐刻画。十年后再读《北京和尚》,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可乘剁掉食指那一瞬间深入骨髓的剧痛和创作者止不住的泪水长流。
陈继明的创作曾经被大声地喝彩过,无论是作为“宁夏三棵树”当中的一员,还是后来生活和工作于华南之地,他皆以不合于时流的执着而获得过关注和肯定。然而,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被忽视的作家。现在,陈继明将色彩斑斓的《七步镇》奉献于我们面前。我们无法说,《七步镇》已经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崭新高度,但我们可以断定:《七步镇》不仅标志着陈继明小说创作进入高远的新境界,同时,它的出现也标志着当代小说具有了耐人寻味的新品质。在日常生活中审美已经被泛化,世俗化、狂欢化写作呈现强势的当下,《七步镇》深沉的思索和充满魔力的叙事,不仅充分证明“纯文学”的固有魅力,也给“纯文学”的未来发展点亮了一盏启示之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