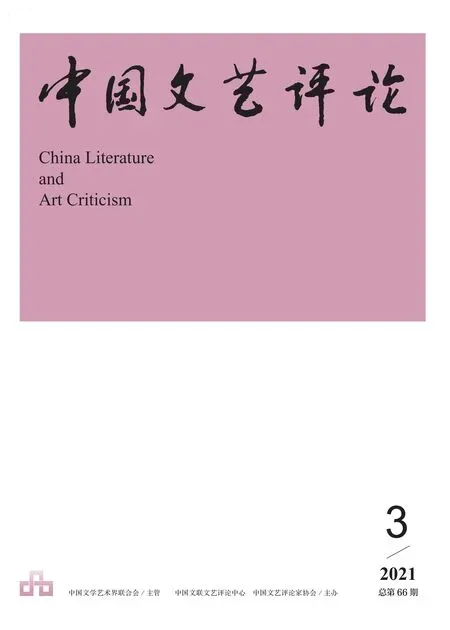喜剧表演中的形体夸张美学:以 《虚假丫鬟》为例
韩 鑫
《虚假丫鬟》又名《狡诈惩罚记》。创作者18世纪法国剧作家皮埃尔·卡莱·德·马里沃是享誉世界的法国喜剧大师、戏剧界泰斗。在他众多喜剧作品中,这部作品颇具代表性。马里沃自18世纪起已备受西方观众热爱。他的作品细腻、淡雅、含蓄、幽默,他笔下人物常隐藏在深色面具下。马里沃自己这样总结:我曾从那些形形色色隐藏了爱意的壁龛中窥探人心,而我的每一部喜剧都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些壁龛中藏起来的心。马里沃的剧作情节曲折,复杂的人物心理通常运用细腻变换的对话语言体现,如轻淡的微笑,而微笑背后带有一丝哀伤。其优雅、精湛、细腻、考究的语言特色被后人称为“马里沃式的风格”。在《虚假丫鬟》这部作品中,作者巧妙安排情节,意蕴深长。舞台戏剧作品《虚假丫鬟》的投排,是由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组织的“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以及中央戏剧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青年教师培养计划”推出的合作项目。受邀执导此剧的导演是来自法国的克里斯托夫·福特里耶,他是一位戏剧人类学博士,这一学科背景,让他对马里沃这部富含时代哲理、人类反思的作品理解得更加深入、透彻。他提出以马里沃喜欢的意大利假面喜剧形式来进行表导演艺术处理。这一戏剧形式以即兴表演为主,也称为即兴喜剧,对丰富创作手段,开启表演想象力和创作力具有一定优势。
一、空的空间与形体极致表现力
《虚假丫鬟》在中央戏剧学院东城校区的黑匣子剧场演出。黑匣子剧场是开放性的,没有传统式的舞台与观众席的明显区分。空间和时间在舞台戏剧艺术的处理中极其重要。彼得·布鲁克曾说,“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之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也就是说,在一个被选定的空间里,当演员开始表演,观众欣赏,就产生了观演关系,而这一空间就被定义为戏剧空间。面对黑匣子剧场特性,克里斯托夫·福特里耶没有遵照传统戏剧的思路,在《虚假丫鬟》的戏剧文本二度导演处理中进行了现代解构。他把舞台定义为一个抽象空间,即一个非常空旷、极其开放的空间,没有任何实体舞美设计和装置布置,舞台地面装上了白色灯光,从而构建了中性、抽象的“空的空间”。“一个空荡荡的舞台,由于演员的富于想象力的表演和观众的运用想象力的观赏,无形变成了有形,剧作家正是通过这种有形的外界动作的世界,进入观众的内心感受的世界。”
导演把演员放置在极简的舞台上进行创作,舞台周围坐满观众,演员在舞台上的创作被高度聚焦,一举一动被无限放大,没有任何的实体支点,只能依靠演员自身的表演技艺进行创作。看似自由开放的舞台空间,结合表演角色的自由创作,却要在高聚焦的灯光和眼光中完成,演员进行角色创作时,大到舞台调度、形体行动,小到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眼神,都必须无比精准。这一舞台戏剧美学,对于中国创作者并不陌生。中国戏曲艺术在极简空间运用上更是如此,比如,以一当十、以桨代船、以鞭为马,一旗便是千军、一圆场过万山。20世纪的戏剧舞台也曾大范围摆脱烦琐复杂的舞台布景,传习东方戏曲美学观念,运用精简道具、舞美等来构画舞台时空,为演员的表演提供无限可能,为观众的想象打开宽阔的大门。《虚假丫鬟》没有任何舞美的布景、装置,演员只能依靠自身形体(行动)的表演,将不同时间、空间的转化,精准地在空荡荡的舞台上灵动地呈现出来。
“‘空的空间’当然不仅仅指空荡荡的舞台空间,但空荡荡的舞台空间的确是一个最为直观的空的空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利用这个空荡荡的舞台空间,使之真正给戏剧演出的创作者提供广阔的创造空间,从而成为‘审美的空间’、‘哲理的空间’和‘生活的空间’。”导演对于一部戏剧作品的时空、主题内核等多种艺术处理,决定了演员在创作角色人物时可依据的技艺理念、风格美学。演员在塑造角色时,依据剧本中人物的文学描述,通过组织灵动精准的舞台行动,使得角色从纸上跃然而起,活在观众眼前。演员必须最大限度地挖掘自我角色表达的能动性,也就是在排练创作中达成的共识必须在空空的舞台上更加积极的行动起来。
据笔者了解,克里斯托夫·福特里耶让演员在角色塑造创作上自由发挥,鼓励演员之间碰撞、交流与创作。这与很多导演的排练创作不同。那些导演往往有预先构思限定好的一个模式或概念,在排练过程中引导演员往既定的模板一步步靠近、贴合。因导演的创作意志、主导意识比较强烈,对于一部作品的完成而言,可能比较顺畅、圆满。一定程度上,演员也相对比较轻松,在与导演的互动中很快能找到属于角色的人物创作。克里斯托夫·福特里耶在排练过程中,则非常注重演员个性化的自我创作,激发和肯定他们的主观性。首先,在合理的规定情境内挖掘文本与角色性格之间创作的有效精准的行动性。行动分言语行动与形体行动,演员在组织舞台行动中,运用了大量的形体行动,为扮演的角色设计创作了生动、独特的形体行动表演。比如,在导演眼里属于马里沃笔下的“小丑”、灵活狡猾的特里维林(扮演者吉璟津);动作笨拙、呆傻憨直的阿尔乐甘(扮演者毛云飞);做作阴柔、贪婪无情的莱里欧(扮演者刘澄宇);“女扮男装”、运用较多男性化外部形体刻画的骑士(扮演者海燕);扭捏作态的女伯爵(扮演者来喆);都运用丰富的形体行动进行了生动的喜剧角色塑造。而在观演中,第一个人物弗隆坦(扮演者梅杰)上场,对剧本信息及剧中角色介绍完,就在舞台上四处跑动起来,并在对角的路线上,以紧凑的形体行动起来。后来,弗隆坦和特里维林的对话中,又组织了更加丰富的形体行动,夸张、巧妙地完成角色之间的交流。“空的空间”变成了生动的“生活空间”“审美空间”“哲理空间”,一出好戏在一群演员们的一番精心创作下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二、打破观演关系的形体互动性
在黑匣子剧场中,《虚假丫鬟》的演员与观众互连互融在一起。本应在舞台上出现的实体舞美装置——三把固定的座椅被放在观众席中,分别给三位贵族阶层的人物角色坐。女伯爵是一个舒适的大躺椅,莱里欧和骑士各有一把高背座椅。他们在登台下场后,就坐在观众席中候场、休息,时而自由地与观众交流,或喝水,就像演员平时在休息室放松的状态一样,但他们时刻关注台上发生的一切,并与台上的演员进行剧情中的交流与互动。形成了登台便是角色、下台便是演员、自己兼观众的多重身份。如此在空间设置上打破了舞台和观众席的界限,演员坐在观众席中表演的模式,有着表现主义式的间离艺术效果。“间离效果的出发点是对于观众的尊重,是有助于提高观众对于戏剧行动的参与意识。”“间离就是断开、中断,把某个东西拿到月光之下,让我们再看一看。间离首要的是吸引观众亲自做出努力,接受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并逐步对这种接受行为更加负起责任来。”因此,观众在观演的同时常常会与演员“在一起”,此时剧情被打断,演员回归现实,角色骤然跳脱出来,观众也被拉回剧场,并以审视的视角反思剧中人物及台上发生的一切。
“表现主义戏剧强调表现人的心灵世界,表现作家的主观精神,揭示人的永恒品质。”“戏剧是视觉艺术,剧中人物的思想和心理活动,需要靠直观的形象、动作来表现。表现主义戏剧常常采用心灵外化的手法,直观具体地把人物心理活动内容呈现在舞台上,使其成为诉诸观众视觉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演员在空间、时间、自我、角色、人物、观众中跳进跳出,大胆畅快地跟观众进行直接互动交流,演员在演出时,自然轻松地与台下观众进行互动交流,依靠的是大量的形体行动。“后现代主义戏剧主张戏剧仪式化,模糊戏剧与一般社会表演之间的界限,强调戏剧的表演本质。后现代主义剧场没有观演的区别,也没有演员与观众、虚构与真实,艺术与生活的区别。场景随时移动变换,演出是随机的,不可重复,像生活本身一样。”比如,开场时弗隆坦说完开场白后,忽然从角色跳回自己,像很多演员演出时一样内心紧张、无所适从地在舞台上跑来跑去慌张地说:“第一句(台词)是我的”,其他演员焦急地催促他“快说台词,节奏要快”,将观众拉回到现实剧场的观演时空中来。而在第一幕的结尾,几位演员在台上摆出造型,然后一个响指,弗隆坦走上台,以开场报幕的形式说出:“第二幕第一场,特里维林独自一人”。再如,在二幕四场结尾,几位角色人物以演员本我身份走上台,他们围成圆圈简短地交流这部戏在此时的演出情况,就像球类比赛中场休息,球员互相交流赛场上的情况一样。然后,又以弗隆坦报幕“第二幕第五场,阿尔乐甘、特里维林”,这种直接跳出的表现形式,随时将观众带回到剧场观演的时空。
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贯穿全剧的演出过程,比如,开场弗隆坦跑向舞台一侧又跑向舞台另一侧说:“你们(指向一侧观众)演农夫,你们(指向另一侧观众)演农妇……”以及特里维林设计的出场——他边说台词边走进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过道,随机与在座的观众用眼神与手势交流;或在演出时坐在某一个观众腿上;将自己包裹成行李塞给眼前的观众。莱里欧设计的出场,也有意识地运用眼神、手势与观众进行交流;在质疑女伯爵时,跑到台下的摄像机前……演员和观众都是剧情中的角色,演员时常直接跳下或走下舞台,在舞台与观众席的过道追打、闲逛、爬来爬去。演员一边说着台词,一边对着观众眉来眼去,在毫无界限开放的状态下,实则是演员与观众共同完成了一出作品的完整演出。
虽然这种表现形式并非是在排练初期导演的设计,但所达到的实际观演效果却是生动有趣的。一方面在黑匣子剧场空间以及空旷的舞台设计中,观众成为共同的表演参与者,形成三角互动的观演关系。观众有时是角色人物,有时身临故事当中,有时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另一方面,如导演所考量的,跳进跳出的间离表演形式是一种舞台呼吸。可以让观众有时间“休息一下”。因为,剧情交待的信息量较多,观众来不及思考眼前发生了什么。所以,在偶尔拉回剧场空间的时刻,给了观众一个思考、停顿、休息的时间。而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形体交流则更好地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三、喜剧的节奏与形体的夸张美
喜剧的特征在于揭穿旧势力、旧世界的内在空虚本质和无价值形式,揭开以美所掩饰的丑的空虚、愚蠢及丑态百出,在审美主体的轻松与自由、游刃有余的形式中嘲笑丑、洞见恶的渺小、空虚。笑是喜剧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喜剧来自笑,通过笑的形式才得以实现人格的轻松。
节奏是戏剧的生命,像一个人心脏跳动的节律,节奏在喜剧艺术中的体现与其他作品类型不同,更加直接、极致。在演员们看来,在表演过程中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真实判断和交流适应的细腻过程,完全是跳跃式进行。在一部作品中,导演和演员体现喜剧节奏最常用的手法就是超越现实主义的内外部夸张,诉诸于台词的性格个性化的音色、节奏处理,以及人物形体行动的夸张体现等。夸张是喜剧的重要表现形式。无论是作品创作时的夸张手法,还是角色塑造中动作的变形扭曲,既要抓住作品内核作为基础进行精确生动地表现与艺术处理,还要避免过于浮夸而流于表面和浅薄,产生反喜剧性的效应。
《虚假丫鬟》的演员以快节奏机械化的状态说台词。比如,骑士和女伯爵在二幕八场的对话,两位演员的台词似乎故意重叠在一起,一个人的话还没说完,另一个人就接上。完全没有交流时的反应到思考再回应的正常生理的时间过程,让观者目不暇接。根据笔者与演员们的沟通得知,导演要求演员的语速不能快,但节奏必须紧凑。这让习惯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演员们刚开始略有不适应,总感觉没有把话说到观众的耳朵里,意思还未传达入心,更没有把话的深层潜台词表现出来,这句台词就已经被下一句台词覆盖了。当演员之间有真实情感交流时,整体节奏就慢下来了,演员自我感受很舒服,觉得是在顺畅的对话交流中真正生活了起来,产生了真实互动的情感碰撞。但是,导演却告知演员,节奏严重拖了,要求演员们必须严格控制演出的节奏。这种不适应的方式,或恰是属于喜剧节奏的最大特点,谋求在欢快紧凑的氛围中带给观众幽默、诙谐感。其外在形式诙谐可笑,但表达的内容又那么严肃深刻,甚至达到了喜剧背后是悲剧的美学极致追求。
在这部作品中,所有角色划分为两个阶层,贵族和仆人。两个阶层有明显的符号化特征。贵族的三位主人公在空间中走调度时用方形,体现为非常规矩有度的行动线,必须按方方正正的舞台路线走,转身变化等也不允许出现差乱。这体现出贵族阶层要有符合身份的行为规范,以彰显优越与高贵。而仆人在与主人对话时,往往会跟随在主人后面,也应遵循规矩的路线。可这部剧中的主仆关系已到了名存实亡的边缘。比如,骑士在和特里维林对话时,作为仆人的特里维林时不时会走一个捷径,跳脱出这一规矩,这是对主人极不尊重的行为。演员在展现剧情、人物、彼此关系时,遵循所谓规矩时,形体上却不断地满台跑,几乎没有原地长时间静止不动的时刻。每个人物像表盘上的秒、分、时针一样一直在动,又像热锅上的蚂蚁,焦灼不安,上蹿下跳,如此夸张的形体动态,呈现出紧张又欢快的气氛。联系到作品的历史背景,当时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贵族阶层整日沉溺于声色犬马、谈情说爱、无所事事,仆人阶层的身份和地位逐渐提升,阶层出现了混乱。剧中有一个象征性的处理——仆人特里维林扑到女伯爵的身上。此举是在整部剧临近结尾处暗场闪现的,女伯爵在躺椅上一声尖叫,一个男性扑向她,这个男性就是骑士的仆人,那个唯利是图的特里维林。正如同他在开场的自我评价中所说“有时是主子,有时是仆人,总是谨小慎微、勤勉灵巧,为利益以小人为友,因品味与忠良结伴……”一个在利益面前善于改变自己,因地因时多变的底层人,最擅于见风使舵。那么,在社会大变革到来时,这样的人必然第一时间冲破阶层笼,占到所有的便宜。这个夸张的动作,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喜剧特征,也象征着贵族阶层的衰败、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四、角色形体个性风格化的魅力
“‘戏剧’一词在古希腊的意思是‘完成着的动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员的自我修养》中提到:“形体动作比心理动作容易抓住。它较之那些不可捉摸的内心感觉要容易接近些;因为形体动作比较便于固定下来,它是物质的,看得见的;因为形体动作同其他一切元素都有联系。实际上,没有什么形体动作不带有欲望、意向和任务,不由情感为其提供内在根据的;没有什么想象虚构不带有这种或那种想象中的动作……”这就说明身体动作比语言动作和心理动作更容易掌握,因为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并且它有一定的心理依据。因此,角色形体个性化创作对塑造生动形象的人物角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部剧发生在18世纪的欧洲,在那个时代贵族阶层和仆人阶层的差距不仅是前面提到的行走路线的规矩,从妆容也能看出,莱里欧和女伯爵的白脸以及莱里欧的假发造型都是典型的贵族形象,仆人因为买不起昂贵的化妆品,会用白面抹脸。某些角色的妆容在今天看来,如同小丑一般,但诠释着那个时代某些人物人性的丑陋。这也符合喜剧角色所需要的以丑引笑、夸张演绎的特点。
演员在进行喜剧角色的塑造时普遍都将自己的形体表达加以突出和放大来表现,在很多对话场景中,演员都尽可能地调动形体行动,丰富人物的外在形象进行塑造。形体动作是通过视觉表现形象的手段,是人物无声语言的表达,最通俗易懂最有表现力和感染力,一般常说的“看戏”,恐怕就是这个道理。比如,弗隆坦和特里维林在第一幕第一场的对话,让人从话语和丰富的形体动作中感受到两个仆人间地位高低的差距。具体表现在弗隆坦与特里维林的交流中,形体动作不是拘谨的内收、踉跄闪躲,就是被打、被捉弄,在躲避挨打的单脚站立时被轻轻一推就跌倒在地……正好与高等仆人特里维林的灵敏圆滑、精通世事、身手敏捷形成鲜明的对比。又如,第一幕第五场骑士和特里维林的对话运用较为滑稽搞笑的形体动作加以演绎。特里维林得知骑士是女扮男装,先是一个跪地上前逢迎献媚,看到其美貌又展开了无礼地尾随和挑逗。骑士对他的无礼之举感到愤怒,用佩剑教训了这个油滑的仆人,在攻击与闪躲中两人展开了一段快慢结合、配合默契的形体打斗,即增添了喜剧氛围,又将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精彩体现出来。再如,在第二幕第三场莱里欧和特里维林的对话中,特里维林为了激起莱里欧的嫉妒之心,时而以威武矫健的步态模仿骑士对女伯爵的步步紧追、献尽殷勤,时而拿着手绢用扭捏的姿态模仿女伯爵的柔媚、娇嗔,将两个人偷情的场景还原呈现。而莱里欧为了不断引出特里维林的告密实情以达到另一个阴谋,听到心上人与自己邀请的朋友偷情假装生气,时不时拔剑挥舞,或在半推半就的动作中配合着特利维林还原偷情画面……将一场滑稽的闹剧展现在观众面前,引发阵阵笑声。
喜剧作品离不开夸张的表现手法,更不可缺少演员形体的运用和塑造。形体表现的准确性与丰富性,成为一个演员塑造人物角色的重要手段。《虚假丫鬟》的演员们在剧中大量外部形体的夸张运用和精彩表现,像极了宣纸上的泼墨人物画,一个个形象鲜明而独具个性、风格突出、特征迥异,使整部作品的呈现极简单又丰满,将空的舞台演绎得多彩灵动、妙趣横生。导演在与演员们探讨角色创作时提出,贵族和仆人在外部形态上必须要有鲜明的差异。因此,饰演贵族阶层的三位演员,在设计舞台调度行动线时,除了以规矩的直线行进外,还要有贵族的举止、步态。而三位仆人的扮演者则各有其独特的形体表达,依照人物经历、性格特点等不同,塑造各异的仆人角色形象。演员在全剧的角色塑造表演中,形体刻画上的亮点,值得品味。比如,“女伯爵”时常上扬着下巴,一副高贵、不可一世的样子,常常扭动胯部行走,夸张地表现出贵族阶层的雍容华贵及女性的魅力。而只有在心上人骑士面前,她表现出试探的身体紧张,得到骑士的爱慕之情时,她屈尊单膝跪在爱人面前,享受那一刻的爱情恩典。当得知莱里欧背弃誓言为一万元的借条和契约耿耿于怀时,她想爆发胸中怒火,手握拳头,身体紧绷,但又不得不压制自己的怒吼以夸张的形体动作表达出来。最终,她被骑士女扮男装的骗局气晕倒地,以全身颤抖的形体动作处理将贵族走向灭亡后的那种绝望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骑士”则一直呈现出一种中性的状态。因为女扮男装,她时刻保持着一副男性的沉稳、威严、挺拔,但在被出卖真实身份时,又突显出女性的娇羞和怯弱。可是在这出闹剧中,她始终以一个明眼人的身份将跳梁小丑们玩弄于股掌。回顾全剧的表演过程,以强化外在形体的运用和塑造,留下一个干练、机智、果断、稳重的女骑士形象,可谓个性鲜明,精彩生动。“莱里欧”的外部形体更多地保持着后倾体态,头部上扬,行走时常常以较为缓慢的八字踱步,手部运用绕手腕、绕手指的小动作。他时而形体上刻板僵硬,时而扭捏造作,夸张而顿挫……所有这些细节,外化突出了此角色人物高贵的虚伪与精明的算计,再到最后一切崩塌的惨状。“特里维林”形体动作上丰富多彩、敏捷多变,常借舞蹈、戏曲化的形体动作来设计人物行动,用机敏并略带挑衅的形体动作来展现这个人物工于算计、放荡不羁的形象。他在剧中与每个有地位的大人物交流时,周旋而蹦跳。在很多时候,他看似油滑地玩转于众人之中,但面对心中最大渴求的金币抛出的那一刻,却突然委身下跪,这一形体动作,一针见血地把此人忘我贪财的本质精准地暴露无遗。另一位仆人“阿尔乐甘”虽然台词不多,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丰富、略显笨拙的形体表达,将一个鲜活人物形象印在观众脑海中。一上场向特里维林问候时,不停地快速原地跺脚;对主人莱里欧的应答也是两手在头上快速绕圈;偷听骑士和特里维林谈话时在地上爬来爬去;得知骑士是女性,也想敲诈一笔的他扛起骑士就跑;后来没得到金币时,趴在地上号啕大哭。“弗隆坦”在仆人中老实、忠厚、脑筋不够灵光,是低一等的仆人形象。所以,在形体表达上也显得笨拙迟缓,就像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说出主人真实身份一样,同样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形体。不是跟不上主人的步伐,就是反应迟钝地激灵一下快跑,或者挨打逃走等。尤其是在自己主人或比自己聪明的仆人面前,更加凸显出紧张、慌乱失措的一面。综上所述,三位仆人的滑稽可笑与三位贵族的故作精明、高高在上构成了一出可笑却耐人寻味的闹剧。
一出以丑扬美的喜剧,抨击了在金钱利益面前情感分文不值的现实,反观并洞察了深刻扭曲的人性,让每一个进剧场的观众,受到了一场荡涤心灵的精神洗礼。一出18世纪的欧洲喜剧,在21世纪的中国舞台上演,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和价值,不仅是现代人与古代人的对话,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互鉴。导演深入且灵动的排演,以及演员的精心演绎,使作品往更高更深远的艺术境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