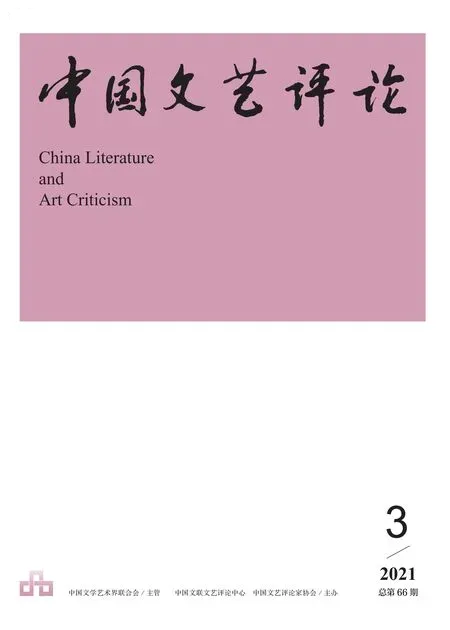从身体里发出诗性的声音
——论穆旦与中国现代诗的升华
王学海
读穆旦的诗,会让我们油然想起两个人物的经典之语。一是王国维在评论哲学与美术后亦谈到诗歌:“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为何,是因为“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也即是说,哲学与艺术,是为人类向往的美好,是为全世界朝向进步与光明的美的追求而存在的,它不会一定合拍于一个具体朝代所期利益的喜好,有时可能还是批判的。所以他在批评中国的哲学家后,又举了杜甫、韩愈、陆游三个大诗人的例子:“‘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而穆旦高擎“九叶诗派”之大纛,把中国现代诗发展引领至新的前沿,正是王国维多年之前呼喊诗人与哲学家、美术(艺术)家“不忘天职”的一种时代回应。
另一个人物便是庞德,他的经典之言是:“好诗决不是以20年前的老办法写就的。”穆旦本人对传统诗形式的叛逆、独具异质性的诗学表现,正是应了庞德之言。说庞德,还在于他在1913年哈里特·门罗主编的《诗刊》上宣扬“意象主义的诗学”,即认为“抒情诗歌必须有一种综合体——一种融合了传统意象(感觉意象)、智性和情感的异质的文本构成”。当穆旦的诗被公认为“凝重冷峻”时,他恰恰正是以其融合中国传统古典诗歌意象中的“形”与“神”,“意”与“境”,借客观之“景”抒胸中之“情”,而又叛逆于中国新诗形式上的因袭,“异质”地独自走在前列,开创中国现代诗正宗栈道的新文本的诗学主张,与庞德之言合拍。这里,庞德对艾略特《荒原》成诗的影响,以及“他坚持以中国诗歌为典范”去创作,无疑影响着穆旦。所以,穆旦诗歌创作的个性特征就在于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揽象征、指代、喻义和寓意为四合一圣体的那种诡异般的变幻中,又承继“中国传统诗歌意象抒情方式”,“首先是在古诗词中长期出入带来的对形式和语感的注重”。
苦难生活体验铸就的诗学美学
穆旦诗的自身美学特点,是苦难的生命体验。我们知道,穆旦与闻一多、徐志摩、孙大雨、卞之琳甚至挚交杜运燮不同的是,他的生命体验是一座特别苦难的高山,遭受苦难的诗人穆旦,却又用诗,对苦难与压迫作着最直接的反抗。在穆旦的名诗《冬》中,有“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名句。且根据王攸欣先生考证,其诗原稿第一章的四节中,每一节的收尾句均重复运用“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这一句,后来因为好友杜运夑提醒与建议才将它改样,以至在杜运燮编的《穆旦诗选》及以后的穆旦诗集的几个版本中,均以修改句本为主流行。然王攸欣先生认为,正是最初的版本(即每一节收尾重复出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才是反映晚年穆旦生存状态的最真文本,此句乃是穆旦这首诗的“情绪基调与核心象征”。“严酷的冬天”让人不由得想到策兰《死亡赋格》中的名喻“空中的坟墓。”当然,策兰“空中的坟墓”是由一种记忆生发的虚拟,正如克洛德·穆沙所说的,“它的形成之刻,也就是它的消解之时”。但这个“由空气垒成的坟墓”(克洛德·穆沙),和穆旦的“严酷的冬天”何其相似。说“严酷的冬天”是穆旦“严冬中文学的生存”,是一种直观的理解,没错,但若说是穆旦“对人生是严酷的冬天的意识”,则更是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公共空间,若如此,“严酷的冬天”也应是一种记忆的虚拟,它是彼时社会环境与政治氛围与穆旦一类人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更有意味的是策兰诗中脍炙人口的名句“清晨的黑牛奶我们晚上喝”在整首诗中同样重复出现。此诗共七节,此句共出现在四节中。不同的是穆旦把重复句放在每节的收尾,策兰则把重复句放在每节的开头。而且有趣的是,在诗的第三节,穆旦在每一段收尾,又重复出现了“因为冬天是……”这样的句子。这一节重复的不同,是第一第四段,诗人把冬天喻为“感情的刽子手”和“好梦的刽子手”,在第二第三段,诗人把冬天喻为使“心灵枯瘦”和“封住你的门口”的刽子手,我以为在这里的“刽子手”应作为索绪尔意义上的结构语言中的具有具体含义的“所指”理解。因为这显然是诗人在创作时赋予语词的意指作用:刽子手在这里已非单纯的粗莽的形象,而是能使心灵枯瘦的颇具谋略的“刽子手”,这不能不说是诗人智性的运用在诗的意象中的新创。与此相连的,是第二节中意象的极富多元寓意与精神反抗的质疑与指斥。“寒冷”——是“潺潺的小河用冰封住口舌”,随之“大地一笔勾销它笑闹的蓬勃”;“谨慎”——是“血液闭塞住欲望”;“奇怪”——是“年轻的灵魂裹进老年的硬壳”。可以说,《冬》的第二节、第三节,是本诗显示出文本把诗人从极左桎梏中解救出来,在短暂创作的瞬间,面对严酷的现实,以大无畏的勇气表达诗人率真的意识形态:他以批判的姿态,移愤怒、恐惧、忧虑于一体,将思想的自由赋于诗的独立精神,在富丽然又涵蕴极大痛苦的语境中,撒向公共空间,插入我们心灵的缝隙。
策兰是伟大的翻译家,他重点翻译了曼德乐施塔姆;穆旦也是卓越的翻译家,他重点翻译了普希金、拜伦和奥登。两人在何其相似中,对应的是生命的苦难体验。因为策兰同样经历过“国籍不明、纳粹苦役、逃亡”和长期流亡。我以为,策兰与穆旦在各自的诗中的相似和各人经历的苦难的相同性,为诗学补充了这样一个维度:他们同样以思想的营造垒成诗的名句,出现在公共的历史意识的空间,将时间锤炼成的词语投射到文学永恒的长河之中,让生活在社会环境中凸显个性的尊严以及美学追求,并给予历史永恒的思考。那空气垒成的坟墓和四季是冬的虚拟,更是良知与诗性的自由诉求。《冬》和《死亡赋格》,都是以对抗生活的姿态在创造着意义。也许它是戏谑的,但那又是中国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苦难中的变脸;也许它是无奈的,但无奈的模糊同样是内心清晰的精神所向。它们在诗的建构(“冬”与“坟墓”)中不断地解构,重复着一种呐喊的追求与解放,是诗性的闪烁中透露出的求索真理与公义的微光,因为诗的内核始终关注的是国家与人民。如果说坟墓与冬日是一种无声的存在,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诗性的语词,就蓄储着多重的含义以及由此带出的历史进程之中奋力挣扎、殷切期待和一颗永不枯萎的追求的勇敢的心。同时,相对发表的空间而言,它又是一种二元的对立。正是因穆旦当时的处境未能有使语言流畅的时空,才使它在流转的社会关系中具有了迂回性。然正是由于这迂回性,使得穆旦的诗具有了诗性语言新的可能性,也即在继九叶诗派之后的一段沉寂之后,它以一种新的张力,像夏日闷热中的一声清脆的霹雳,重新在写作与抵抗之中引出一阵不期而遇的凉风。一个诗人,即便微不足道,但他一旦选择了这支高贵而非低媚的笔,就会在两难之中自觉地融自然于精神之中,以夙愿驭于神话之背,在表面平静乃至屈辱之下,疯狂地进行着被压抑个性的蛟龙腾海式的创作,阐释着一个叙事者对生活最深刻的理解与向往,这当然也是中国诗学之人文精神的最深刻最本质的艺术显现。
由《冬》,我们还可回顾诗人在此诗31年前写的《旗》。其中有“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你最会说出自由的欢欣”;“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胜利固定”。这些诗句,其实与《冬》是连贯而从未割断过的。年轻的诗人,心中的红旗“为地面而拉紧”,可见他的心是始终扎根在百姓的沃土之中的。“是大家的方向”,正是《冬》所渴盼的那份希冀,所以,后来诗人才放弃在美国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优厚的物质条件,带着妻子冲破层层阻力,毅然决然地回国,准备投入新中国火热的建设之中。诗人创作的前提,是他的心始终扎根在中国。形式上虽然欧化,但并非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而是有的放矢,这个“的”,便是实质的中国。若作更深度的诠释,还可参见于《良心颂》一诗中。“虽然你的形象最不能确定”,但“背离的时候他们才最幸运”,此处不啻是一个惊人的真诚:因为只有在你遭遇不测与不幸的境遇中,良心才会真实地显现。这其实是在穆旦到了南开,遭受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依然率真,依然敬业,依然对生活对未来抱有期待的一种最好的注脚。在诗人的修辞里,我们同时可以见出的是词语结构里永远高昂着头的追求,是声音纹理里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最真挚最火热最深沉的那份爱。
《旗》的意义更可以和三年后的《世界》合观。当诗人明悟生活的真谛,降生人世的一刻,我们已渐渐进入社会和它的责任的范畴之中。于是,诗人便自省般地大声喊出:“假如你还不能够改变/你就会喊出是多大的欺骗”。尊重生活敬待百姓,真诚面对现实以及肩扛起社会责任,这是一种自觉,是诗人顿悟到的,也是他向一切还在懵懂之中的人必须大声疾呼的:对待贫困落后的祖国,对待饥寒交迫中的父老乡亲,对待愚昧麻木的灵魂,诗人非常形象地指出,“他把贫困早已拿给你——/那被你尝过又呕出的东西/逼着你回头再完全吞下;过去、未来,陈旧和新奇”。这一节可说是本诗的精华。应该格外关注的是,其时诗人已经考取自费赴美留学,其年又送未婚妻周与良先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且在天津1947年11月22日的《益世报》上以署名“亚珍”发表《送穆旦离沈》时写道:“两年来,东北不知有多少来的人,有多少走的人,算不了什么,你穆旦无非是万万千千中的一个。两年之前和两年之后的现在,你来,你走,这中间,你经历着兴衰样的变化,是你个人的,也是整个东北的,张大的说一说,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一切,就注定诗人会以《世界》表达对祖国无私的奉献。为了世界与人类,诗人再难也要独自前行。这就是穆旦。今日重读穆旦的诗,他与我们在就中国的现状以及她的未来进行着真诚的对话。
批判与自我剖析中的诗性认知
被穆旦称作戏作的《苍蝇》,是一首具有诗人本身潜在意识、颇耐人寻味的诗。“谁知道你在哪儿/躲避昨夜的风雨?”不知不觉,诗人已经身境移托。“我们掩鼻的地方/对你有香甜的蜜”。这岂不正是穆旦当年生活与生存的写照吗?《苍蝇》的创作,正是诗人状态一个最好的自注。所以,诗成之后,会即寄给好朋友杜运燮共赏。而自1976年始,重新拾起诗歌创作之笔的穆旦,便又进入了一发不可收的创作新时期。
说是穆旦诗歌创作的新时期,是穆旦从身体里发出又一次诗性独质的声音,是在他心灵中被压抑了17年之久的那份重新发现文学,文学又重新召唤着他的冲动。那个时期,正如诗人在《旗》中所说的:“你最会说出自由的欢欣。”也若在《良心颂》中所指认的:“然而孤独者却挺身前行。”现在,我们的诗人在文学里已不再顾及精神与现实环境的协调,不再畏惧灵魂与肉体互相残杀的痛苦,他唯一考虑和追求的,是精神与诗的完美,是处于逆境之中而仍具独特个性、对现实发出真实声音的一份作为社会人的真诚负责的态度。创作于1976年3月的《智慧之歌》是其代表作品之一。这首共六节的诗,第一节以“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和“都枯黄地堆积在心”的意象,对自我的过去作出了历史的纪实。第二节以“青春的爱情”作假托,隐喻着过去的理想都已经“永远消逝了”,满腔热情也“落在脚前,冰冷僵硬。”但诗人并未因此现实和不尽人意的归国待遇而沮丧和消沉,反而以“茂盛的花不知还有秋季”来再次宣告自我的率真与不惧不熄的追求之火,并且还保持了一份成熟的生活态度,以哲理辩证来评判现实:“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生活的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在第四节中作了自嘲之后,诗人又重返如诉如泣的现实:“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这既是一种高品质省醒,也是一种历史印痕的诗性流露。紧接着的两句:“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是越出现实的藩篱,作着高屋建瓴的批判精神的即时涌出。最后一节开首“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应该是本诗的诗眼,正因为智慧之树不凋,诗人才能唱出今天的智慧之歌:“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既是针对诗人自己的诗,更是针对诗人所处的这个社会和人而言,因为他坚持有一棵智慧之树在,森林必将迎回绿色的天地。“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作为收尾之句,凸显的反义显而易见,它与上一节收尾之句“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呼应,在这里诗人把被动的主语指听者转换成了一个主动的主语指听者,以对方主动的指斥打压和自我急速地戏谑又含蓄的反义性的主动调换,从而将诗人一生希冀的理想诗性地预示出来,那就是绚烂的天空下不会再有荒原,一片叶的碧绿必将会盈绿整座森林。在这里,我们借此诗人的智慧,听到了他的放声歌唱,听到了他具有形体摆动的身体中呼出的温度和热度。
现代诗歌的一个特点,就是抒情中的批判和尖锐的自我剖析,穆旦的《自己》就是一个典型。人是站在自然世界与社会中间的个体,具有两者的属性。《自己》就围绕着这属性而展开。当诗人自己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个体),该朝向哪里时,也许重要的不是姿势和方向,而是存在的中轴,“他在沙上搭起一个临时的帐篷/于是受着头上一颗小星的笼罩”。“沙、帐篷、星”这些名词,与“搭起、受着”动词的混合,把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复杂交融,以一个收割寂寞劳作者的心情和随星移向远方的视角,进行着破碎般的吟唱。于此,第二节中出现的“偶像”“崇拜者”“生活的小店”中的隐喻与暗示,批判着堕落的历史和申救被恶魔拘囚的文明。在文明理性遭受蛊惑而让历史堕落的时间段里,诗人是以人性假借神性一起组成共同体,来面对自我。有研究者认为,诗人写于1940年11月的《我》,与《自己》是最好的注解。然我以为,穆旦另有一首写于1942年11月的诗《控诉》,是对《自己》最好的回注。在“当叛逆者穿过落叶之中”,迷茫着“为什么世界剥落在遗忘里”时,看到“而有些走在无家的土地上”——“失迷的灵魂”,以及“有些关起了心里的门窗”——“走在失败的路程”时,诗人似乎已经感悟到生活的另一个真谛:“春天的花朵落在时间的后面”,为什么,因为“冷风已经吹进了今天和明天”。照理说,这样的感悟足可使诗人怀揣一颗明白而看穿人世的心。但在第二节里,诗人却又这样地接着说:“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生命永远诱惑着我们”,“在苦难里,渴望安乐的陷阱”中,“自己的安乐践踏在别人心上”……这样尖锐的自我反省与批判,事隔35年后,哲理性的他指在这里便成了谶语:“昌盛了一个时期,他就破了产/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自己》)。诗里的“自己”既是指诗人选择的创作——诗,也隐喻了世界与诗和诗人的关系。于是,“事物冷淡他,嘲笑他,惩罚他”,令我们至今仍倍感钦佩的,是诗人轻松地自嘲:“但他失掉的不过是一个王冠”,这是何等高贵的品性呀,对于虚荣,诗人把它与真正的诗彻底斩断了。当然,对于未来,他依旧不无忧虑,这于诗人当时的处境,十分贴切又十分形象。而那扇理性的大门,对诗人是不会关闭的。这看来是悖论,其实是反美学的美学。诗人所处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山河破碎、万众在底层抗争的年代。诗人写作《自己》的年代,也是一个极左思潮桎梏人心灵的年代。但诗人无论是创作《控诉》,还是创作《自己》,他的诗学意识始终是特立独行的。并且,它也不是一种词语的游戏,诗人在肯定和批判感性认知的现实里,以自由理性向往一种未可知的光明,并以他的诗中见出的,是更深刻地体会到对于苦难、战争乃至死亡的一种回到现实高度的认识。
结语
在穆旦的诗里,让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诗人对真实的那份自觉,诗人的品性,也就融在了他的诗内容的结构里面。诗人对真实的自觉,又往往以不同于九叶诗派其他诗人的审美视角,夹杂着某些捉摸不定的心情,去营造意象中显示出它的独特性来。所以,穆旦的诗,至今让我们心灵震撼。也有不少诗学者为之撰文赞叹。
穆旦是个非常有思想的诗人,他的诗往往由思想支配或引领着创新和超越语汇。在穆旦的诗里,感觉与时间像两个捉迷藏的小孩,时隐时现,但率真的笑声不时弥散在空间。它让我们感到,诗不单是语汇与语词的变化,它更是在跳跃的零散与即时中的美学:他要拯救的,正是他从未得到的,并且,他分明已远远瞅见活着的这个它。所以,穆旦的诗非但为穆旦所有,也同样为一切爱好穆旦诗歌的人所拥有。由此也证明了穆旦作为中国现代诗人,正是在苦难与挣扎之间,在历史与诗歌之间,在现代主义诗学的探索之路上,完成了对中国现代诗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