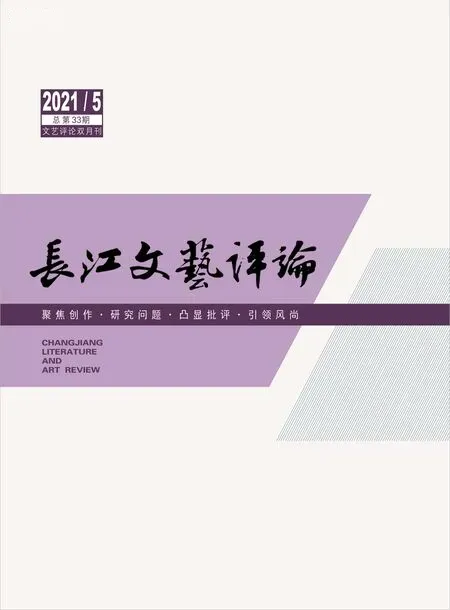中西会通视域下的文论研究与文学批评
——《王先霈文集》印象
◆魏天无
八卷本《王先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涵括作者1960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述、文学评论、随笔、序跋等。《文集》前五卷为学术著作,经作者修订后全文收录了《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佛语哲思》《古代小说序跋漫话》《文学美》等,节选录入者如《文学评论教程》《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国学举要·文卷》《文艺心理学读本》《文艺理论学科地图》等;后三卷为文学评论、散文随笔、序跋与讲演录等。作者后记自述道:“一个多年从事写作的人,到了老年,很少有不愿意将自己的著作整理集中出版,藉此作一回顾和小结,但是,同时我也会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要耗费不小的人力物力。古代的文人到了准备编次自己的文集的时候,常常会用‘灾梨祸枣’这几个字来形容。这种看似矛盾并且似乎有些言不由衷的话,描画出来的是忐忑而惶遽的心态……”《文集》的价值自有他人评说。作为一位写作者,一位罗丹意义上的“工作者”(“应当工作,只要工作。还要有耐心”),在六十年文字生涯中,作者于中西文论会通、中国古代诗学体系、文学批评学学科建设、文艺心理学本土化、文艺批评的价值与功能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值得深入探索和思考的问题。作者治学上既具“预流”的学养,又在若干关联、交叉学术领域精研覃思,加之兼容并包、从善如流的胸襟,使其研究成果超越一时一地的热潮,指向诸多问题的根柢处,予人长久的启示。学者、理论家、批评家刘保昌在评述《文集》时说:“根植于数十年的教学实践,王先霈推出的系列理论研究成果,接地气、近人心、重审美、线索清晰、知识丰富——这就迥异于近期学术界流行的以课题为中心的功利性的成果生产方式——它缓慢、执著、坚定、安静,却具有穿透时间重重迷障的无穷力量。”
作者曾在《大转折时期一次学术旅行》一文中,饶有兴味地回忆那一时期,与几位教研室同事为研究马列文论而游历全国,遍访名家。其后,由于个人兴趣变化,也顾虑到语言的障碍,作者并未在马列文论研究上继续深耕,而是转向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研究。这一转向可以看作作者学术研究的重新开始,亦可视为一次郑重的起步。1988年,作者与周伟民合著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该著计十四章逾六十万言,是国内最早系统梳理、诠释古典小说理论批评的厚重之作。时年九十高龄的黄海章为之作序,认为该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种重要的贡献”,指出“对自己的民族特色要加以注意和阐明,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来”。于中国的文学思想、艺术心理思想中挖掘中国精神的特质,但依然密切注意异域理论思潮的前沿性问题,这可以看作作者其后学术研究的一条主线,也是他倾尽心力所在。1992年出版的《古代小说序跋漫话》,则以通俗语言向读者介绍序跋对于了解小说,了解小说史和小说理论批评史的重要。之后,作者应邀参与汤一介主持的《国学举要》丛书,负责《文卷》(《文集》第五卷)撰构,介绍、评析中国古人提出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想。作者在《文卷》中明确提出:“谈历史,谈文化,谈文学,谈世界的文化史或者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忽略中国。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而中国的文学思想,把中国精神的特点体现得相当充分,相当全面。”这既是一种学术立场的体现,也是其学识、眼界的拓展、深化所致。在“国学”热持续不衰的今日,回顾作者二十余年前的撰述和言谈,不能不令人心生感慨;而在中国古代文论、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古代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中,辨析和阐发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是作者学术研究的旨归。数年后,当作者接受北京大学出版社《名家通识讲座书系》邀请,撰写《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文集》第四卷)时,他再次强调“文艺学家研究古代文论,切忌脱离古人的文本和语境,阔大空疏、游谈无根、望文生义、牵人就己”,赞成对古代学者“抱着理解之同情”。该著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向读者介绍古代诗学观念体系、审美观念体系的核心与精髓,对于存在于当时、也流布于今日的古代文论研究中的牵强附会、圆凿方枘的习气,是一种反拨,也是一股清流。
陈寅恪谈到“预流”时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又说:“盖今日治学,当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之比。”早在1988年,《文集》作者出版《文学心理学概论》。这本概论融会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自成一体,是新时期最早出版的文艺心理学著作之一,也是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二十年后,应出版社邀请,作者在《概论》基础上重新撰写《文艺心理学读本》(《文集》第五卷),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插图,介绍文艺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前沿问题。谈及当年为何会从中国古代文论转向西方现代心理学研究,作者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前接触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很少,而恰好当时有西方的很多理论传到中国来,很难再不予理会。此外,在《治学与人生———王先霈访谈录》中,王先霈曾说,“在时代变革的思潮中,对人生问题需要深入思考。研读文艺心理学的材料,思考一些问题,有时会触及你的心灵、你的人生的一些理念”。作者多次与笔者提及台湾杨国枢主张研究本土心理学的意见和成果。作者非常了解此种研究所遭遇的材料等多方面的困难,对杨先生的研究很是赞赏。源于自身的研究体验,作者认为中国的艺术心理非常有特点,有许多好的资源,遗憾的是中国的心理学尚未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他将《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文集》第三卷)一书视为一次“作业”。该著以西方艺术心理学思想为框架,来阐释本民族的艺术心理思想传统,以期建立本民族的艺术心理思想体系。童庆炳曾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作者“有一种难得的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自信,他深入中国古代艺术心理的堂奥,经过刻苦地钻研,以他独特的眼光和谨严的学风,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思想作了一次清晰细致的梳理、力透纸背的分析和切中肯綮的概括”;该著“给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理论和国学研究的一次重大收获”。将治学与自己人生的理念相结合,作者这一研究取向的另一成果是《佛语哲思》(《文集》第一卷)。可惜的是,这本近似读书随笔的小书并不为人关注,作者的用心也就很少得到回应。该书出版于1997年,作者谈到为何要写这本书时说:“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而在有关宇宙、人生的思考上所遇到的困惑、难题,与古人仍有不少重合相同之处。先哲为之冥思苦想的若干题目,今天的人未必都能给予完满的回答。佛语,可以说,乃是对于不可思议之物的思议。……文明程度越高,对终极问题就会越是关注,个人和群体都是如此。”“对于不可思议之物的思议”,不仅仅是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哲学家和思想家,也是科学家、发明家的共同使命与职责之一。今日,人工智能时代悄然临近,人类“永生理论”已被抛出,看似与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不相干的、遥远的终极问题,已近在咫尺。《文集》的出版,在新的语境中为读者的阅读、思考提供了新的机会。
《文集》作者不仅是一位严谨的,有自己的研究路径,有自己治学和人生理念的学者、理论家,也是一位声誉卓著的评论家,一位忠实、真诚、不知疲倦的文学读者。他对文学的欣赏和解读既令人肃然起敬,某些时候也令人“望而生畏”,因其渊博学识,也因其细腻、敏锐的洞察力。1986年,作者与范明华合著的《文学评论教程》(《文集》第一卷)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文学批评的专著,标志着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从文学理论中独立出来。倘若说,这本教材的诞生主要考虑的是大学文学教学的需要,回应中文教师应当参与到批评活动中去的愿望,那么若干年后,在论文《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文集》第六卷)中提出“圆形”批评一说,则可视为作者长期思索中国文学批评有别于西方(欧美)文学批评特质与功能的结晶。“圆形”批评指的是,以审美为中心,“感性与理性融合的、适合文学的审美特性”的批评观念和阐释方式。这一富有独创性的命题表明,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与交融中,在各种批评思潮、流派的此起彼伏中,需要探索和创建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批评体系及其核心概念。围绕这一命题,作者先后出版《圆形批评论》(1994)、《圆形批评和圆形思维》(2000)、《中国文学批评的解码方式》(2010)、《建设“圆形”的批评》(2016)等多部论著,其中的重要论文收入《文集》第六卷。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年,对文学批评的意义和功能,对批评家角色定位的质疑和诘难,不曾间断。这些质疑和诘难不仅来自普通读者,也来自作为评论对象的作家诗人。在大众媒介、尤其是自媒体上,以意在求胜为目的的“酷评”,似乎重新觅得生存空间,越来越多的受众被裹挟其间。《文集》作者曾在《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漫议》(《文集》第六卷)中谈到,文学批评“乱象纷呈”的原因之一,是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平实之论很容易被淹没、被遮盖、被忽略,于是,文学批评为了引起反响,走偏锋,发怪论,故作惊人之语,还有似乎是故意惹怒评论对象而用语尖刻的‘酷评’,就一再出现了”。美国作家、批评家苏珊·桑塔格也曾说:“我们很难听信那些以不带个人感情的健全音调说出的理念。有些时代太复杂,太容易被互相矛盾的历史和知识经验震聋,以致很难细听健全的音调。”毋需置疑,这一切正发生在我们眼前。因此,以《文集》出版为契机,重新思考和体认作者提出的“圆形”批评的观念、原则和阐释方式,追求文学批评主体的自谐、同他者的互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此外,学界正在展开的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不接地气”,与文学创作、文学作品脱节的讨论,不免让人慨叹,前辈学者身上的优良传统和人格风范——既在理论研究中有安身立命之作,又对文学、对作家诗人有纯正、醇厚又敏锐的审美感受力和洞察力——如何能在后学者身上传承与发扬。《文集》作者不仅致力于文学批评学建设,于理论上提出构建“圆形”批评的设想,而且数十年如一日关注当代作家诗人的创作,尤其把兴趣和精力集中在那些还没有怎么出道、不为时人所知晓的新作者、新作品,将这一工作视为文学批评家的社会职责,也从中获得很大的精神愉悦。文学理论研究者和批评写作者若将职责、使命、求真、向善视为“畏途”乃至笑谈,若非专注、虔诚于工作,以“理解之同情”贴近研究对象,即成为“困境”的制造者之一而不自知。
笔者曾数次访谈《文集》作者,也多次谈及文学理论本土化问题。他认为:“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只是文化现代化大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应该成为一个孤立的口号,不要成为一个孤立的目标。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和现代化、科学化应该是同时并进,也就是说,建立一种系统的、科学的,能够促进文学发展,能够使文学更好地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学理论,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在中西文论交切点上寻求创新的突破口,可以看作《文集》作者六十年来学术理论研究的合力所在,也是他在多个领域取得卓越影响力的重要原因;将文艺理论、批评理论研究与文艺创作、文艺作品评述、鉴赏相贯通,谈理论不离文本而自说自话,细读文本而常见理论的奇妙点化,此中道理说起来简单之极,做起来绝非易事。王先霈喜欢与青年学生、学人接触与交流,寄望于他们能够把治学和自己的修身,自己的人生追求、人生体验结合起来,“一个文科的老师,要是能够把治学和自己的修身,自己的人生追求、人生体验结合起来,那就会是比较快乐的事”。他的随笔、序跋、讲演等涵容治学之道与为人之道,说的是文学,见出的是人生。这是《文集》出版的另一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