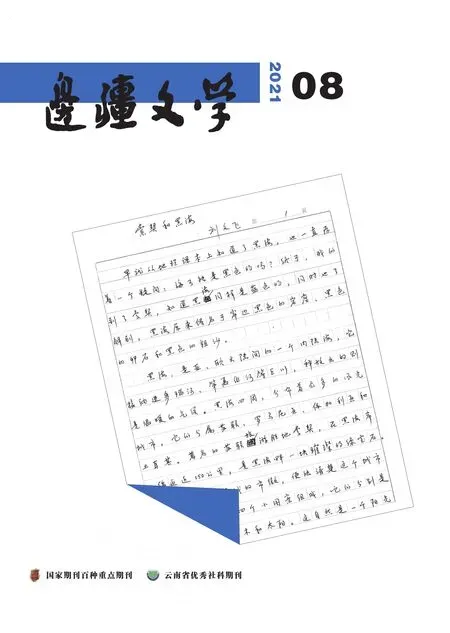赛虎这条狗
徐超洁
赛虎走了。我也只是听说。
赛虎走时,老屋旁应该有萧瑟的风漫卷起厚厚的落叶,四面埋伏的群山应该更沉默了。我想,它守不动最后的虚无了。
离开老屋很多年,偶尔回去。老屋还是老屋,还是几个高大的木架子,空落落地杵在一大片空阔的地上。两壁大山墙,如果按日子来计算,它应该被大风呼呼吹过几千个日日夜夜了。按分秒来计算,会是一个更为庞大的数字。雨当然也湿淋了很多年。原说是不朽的板壁,越来越朽了,泛起了潮色,有点发乌,甚至是黑,一种潮湿的黑,到处是漏洞,无论站在那个角落。我都能想象出,春天的讯息一来,发疯似的大风,从木板壁的孔洞里,到处肆虐灌进去的呼啸声,像孤魂野鬼的嚎叫。想想都打哆嗦。
腐朽是一种衰败。茂盛是一种更为蓬勃的衰败。老屋的前面,破了皮的地板下面会冒出来几株野草,或是几朵黄色的蒲公英花。再往下,是一块地,几年前,白露秋凉时,主人们曾用锄头翻动它的土壤,将野草根暴晒于秋阳之下,寒霜凝冻,甚至用炽烈的火焰来摧毁它们顽强的生命力。如果再从老屋后面拔地而起的高山梁上看去,会看到散布在山腰、山脚的那些土地,像农人们晾晒在大地上的片片方巾。一些遥远的,或是就在附近耕田里的农人,扶着犁铧,牛儿在前,主人在后,一主一仆,躬耕在夕阳和晚霞映红的山间,在天地之间形成一个最具农耕代表性的剪影。土地被一种不可抗拒的畜、犁和人的合力划开,露出肉红色鲜活的肌理,都能听到土地脉搏怦怦跳动的声音。牛的喘息声,农人的吆喝声,伴着滴落的汗水,一同唤醒了结痂的土地。它们会暂时苏醒,伸伸胳膊和腿,然后又在深冬的凝冻里,在覆盖着的大雪里随同万物沉沉睡去。好吧,我们还是回到老屋门前的土地里,随着第一声春雷,这块地和其他万物一样,会惺忪地苏醒过来,主人们再次用锄头翻松土壤。田间地头,到处是农人们劳作的身影,他们把板珈的土地平整出来。这时候的土地,开始像一个母亲,在孩子的侍弄下,梳洗打扮,不再垂暮沉默,变得年轻,朝气蓬勃。在自然节气神秘地运行里,每块土地的主人,都会在立春、雨水、惊蛰或布谷鸟的叫声里,播撒下谷粒和种子,再用酥松的泥土轻轻覆盖。种子就会在春雨里悄悄发芽,直到破土而出,直到把漫山遍野染绿葱葱茏。当然,门前的这块土地,它也生长过玉米、青菜、豆荚、小葱。它供养着主人,主人也依附于它。
只是,这是多年前的事了。
当一种人力的茂盛变成一种自然的茂盛,那就是荒芜的开始。这块地上长出的不再是稼穑,而是疯狂的野植。喇叭花、野草、癞蛤蟆叶、蕨藤,它们以不可抵挡的生命势力占据了房前屋后,用铺张开的藤蔓覆满屋墙,门前的小路,潮湿的石阶,像被施予巫术的蛇藤。瞬息之间,以不可抵挡的幽暗的游移之力,把一派繁华绞杀成落尽的废墟、生机勃勃的荒芜。它们仿佛铆足了摧毁的力量要对人类施以反扑式的报复,近乎恶意地生长。
老屋不是没有繁华过。除了老屋前的竹林,砌成的规整的水井,挺拔高昂的楸树,丛绿的韭菜,院子里的阳光,这里也曾人声鼎沸。老屋的主人们具备万千农民的美德,他们比太阳起得早,和月亮一起归。在还是松明灯、煤油灯照亮的很多夜晚,他们完全不像是疲惫不堪泥土里来的归人。他们拥有原始超强的繁殖力,育养了一个又一个子女。
他们以人多的天然优势,加上强悍的生存本领,很快在村庄里占据了重要地位。但他们飞扬跋扈的性格,不妨碍他们成为村庄里的霸主。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拥有了最多的土地。
这个村庄的很多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壮大了自己的人力、拥有的地表面积,以及宽敞的屋舍。那时的村庄和原始部落一样热气腾腾,充满着争夺土地,房屋的残酷斗争。他们也在残酷的斗争中以野蛮的方式对骂,或是以稍微巧妙的方式,于某个鸡鸣狗吠的夜晚在村口骂田地里的瓜、树上的果、冒着红胡须的玉米被盗于无形。村庄里的孩子像猪呀狗呀那样多,他们穿着简朴甚至破烂的衣服,却不妨碍他们在河边嬉戏玩耍,捉蝌蚪、泥鳅,玩蛇,打鸟。在散布着星斗的天幕下,爬上老树去唱歌。或是在玩到兴奋时,以尖锐、高亢、无拘无束的声音,而且这样的声音还是几十个孩子的混合音,像激扬奔腾的交响乐一样,掀翻了整个村庄的屋顶。惊飞了栖息在树的鸟,他们也银铃般无邪地笑,笑得星星都躲进云层。
总之,那时候的村庄,鸡犬之声不绝于耳,牛羊成群,高高的谷堆,云朵像冰川融化的冰一样涌动飘浮。
当然,小荣是没有这样的笑声的。小荣的笑声会让星光暗淡,让月光如井水般澈凉。小荣家住在村庄的最低端,据说,三代单传的小荣父亲看到小荣时,他的心情狂喜得像院里的喜鹊窝。毕竟已经生了两个女娃,但是,明媚的欢喜里有时常常暗含眼泪,只是人们不可预知。慢慢地,长到两三岁的小荣不能正常走路,腿脚软软的。在医学还不发达的年岁,小荣父亲带着他奔走求医,最后得到一个人们还陌生的医学答案:软骨病。三代单传,软骨病,住最低端,仿佛都让小荣一家和喧嚣的村庄格格不入。家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钱给他医治了,他就吃蛋壳。正值村庄生育的白热化时期,那时还盛行着月子婆扔蛋壳的习俗。月子婆坐满月子,趁天色拂晓之前,未有人踏上路,就把攒了整整一个月的蛋壳扔于大岔路口。细算着日子,小荣母亲早早等候,人家一边扔掉,她一边拾起,带于家中,臼成粉末当药,让小荣用水渡下。年复一年,小荣终于会走路了,只是走起来轻飘飘的,腰一闪一闪,像一根会走路的软皮条。那时村庄的娃,多得像洪水猛兽,他们以年少时未知世事的刻薄,嘲笑他,欺弄他,偶尔善意。大多数时候,他会很急。尊严之神住在每个人的体内,哪怕他是个蛋生的孩子,他更多一些傻气,嘴角有不自知流下的口水,嘴巴总是湿湿的,说话含混不清。他急的时候,会腰和腿一晃一晃地追着人家跑,大声地嗷嗷叫着。当然,毫无悬念,他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被人家抛去很远很远,像一只落单的无家可归的狗。
小荣的单薄,和村庄里牛犊一样的娃们一比,是蝼蚁和虎豹,但是,时间流经他们的方式别无二致。
后来,世界越来越辽阔,它的喧嚣已无处不抵达。那些诞生于村庄,长于村庄的人们开始像流水。从一个封闭的小口处,流向四面八方。
赛虎没有见证过这个村庄的繁华。它来的时候,很多人已经离开了。
赛虎也不叫赛虎,它叫吉利。人们常常把自己可能实现不了的愿景,寄托于一个兽物。所以很多家养的牲畜,就叫成了吉利、来福,骂猪骂鸡也骂个小发财什么的。仿佛这样,神灵就会赐福于这个家庭,虽然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总觉得,如果说吉利走了,多不吉利。又曾经遇到一只狗叫赛虎,所以,就给它换了个名字。
所以吉利就是赛虎,赛虎就是吉利。走都走了,一个名字已不重要。
赛虎才来的时候,就是一只不起眼的小狼狗,黑黑的,小眼神里透着一点狡黠。带上一个狼字,它就比其他小草狗机灵得多,当真有了狼的勇锐。它和它族类的忠诚,由来已久,天地可鉴。在村庄,人们更看重它的皮实,其实就是贱性。当人们以高昂的气焰互相对骂的时候,骂的是狗都不如、狗腿子、人模狗样。几代单传的人家,最喜欢给孩子取个带狗的贱名子,这样容易在大地上存活。贱性的东西,多具百折不挠的生命力。村庄也有几个这样的名字,什么大狼狗、小恶狗。叫大狼狗的论辈属叔伯,叫小恶狗的是爷祖辈,偏偏就养了一条最恶的狗。村人们串门或路过,那恶狗就吠叫着,朝人们拼命扑来,吓得魂飞魄散。又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说:你家的狗太恶了,直接是一只恶狗……总不至于这样说吧。这个爷爷借助这个狗名,从一个瘦弱的独苗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也凭借这狗名,无论他家的狗多凶多恶,和狗这捆绑的关系,几十年来,堵住了村人寨邻的悠悠之口。
当然,村庄和狗一直都是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们以一种不明显的存在方式和村庄同在。除了狗,还有黑色如幽灵般的猫、圈里的猪、长胡子的羊、核桃树、杏树、烟囱,和梨花树上比蓝天还蓝的炊烟,仿佛被上帝一同布设在群山之间。在村庄还像树上的喜鹊窝里的喜鹊一样热闹喧哗时,狗的世界也是欢腾的。它们和其他万物一样,带着无以言说的神秘力量。祖辈们围着火塘讲述的故事里,这种力量被放到最大。他们说狗的眼睛是能看到亡灵的,它能嗅到死神的气息。村庄有人死去之前的那些晚上,狗会彻夜嚎叫,或直接是嚎哭,在浓重的夜色里不停呜咽。还说它们除了能预知人类的死亡,也能预知自己的。在它们快要死于疾病或衰老时,会悄悄找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完成自己的最后一程。和狗相比,我们人类缺乏忠诚和自爱。仿佛也真没有人看见过一只自然老去的狗,无论是在高山的坡地,还是草丛中、老树下,反正,没有人看见过。这个来自神秘世界的物种,像一个巫灵,没有人知道它们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
总之,狗像是上帝派往人间的使者,或是某一个触犯了戒律被发配流放到人间的神灵。
赛虎带着狗的贱命,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一个破了边的小桶、小盆、小碗,就是它的衣钵饭碗,或是直接在地上吃。家里若有残汤剩饭,就给它倒上一点。像一个家庭成员,虽没那么重要,到底还是有一席之地。实在忙不过来,就忽略了给它留吃这件事,那一天它就得自谋吃食。慢慢地,赛虎长大了,像个毛里毛头的小伙子,平时很少有人正眼瞧它,冷不丁地,它就长成了个英俊少年。
越来越威风的赛虎,个头高大魁梧,面孔飒爽清朗,两只耳朵挺阔机灵,毛色黑亮,一身洒气。我想,我要是一只小母狗,也会爱上它,以一个雌性对雄性的崇拜。帅气也就算了,狗品还特别好,老让我觉得它不是狗,而是个绅士。家里做任何好吃的东西,人都忍不住的时候,它能忍住。在高高的门槛外,它就坐着,流着口水,哈着气,巴巴地看着,但绝不进来,除非主人召唤,特别有风骨,像一个古书里走来的有节气的寒士,绝不为一口狗食掉了自己的身份。
我们和赛虎若有若无地相伴着,人与兽物,仿佛也有一种无形的缘。大概缘于我太爱世间的一切了,我常常会想,为什么偏偏是这只狗而不是其他狗和我们的生命融在一起呢?它和我上一世是不是有过擦肩或回眸的错失?和我路过的花朵,我上山经过的一个松果,我在街角失之交臂的一个人一样。自然,赛虎没有追问那么多,他只是因为主人的陪伴,快乐着。
有赛虎陪伴的日子里,我们与村庄、老屋也是有活气的。它和四面埋伏千年的大山,山上黛绿的丛林,丛林里的蛇虫鸟兽,鸟兽的鸣叫,叫声惊扰了的流云和淙泉一样,属于村庄的一部分。有时,我甚至觉得它像一棵村口的老核桃树。它们,原本和这里的人们一样,生于斯,长于斯。可它们还在,人们就像流云。
村庄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不断涌向城市。在不可抵挡的工业进程里,人们仿佛又回到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成了时代转盘上的一颗螺丝。有时,又像一个源头流出去的水,涌向四面八方,没有停歇,落叶浮萍一样,身不由己,被洪流不断卷入、吸走、翻腾。那些多年前有长长麻花辫的村姑们嫁去远方,成了商人,教师,或是修鞋匠的妻子。那些多年前嘲笑过憨子小荣的人们也走了,有的进入发达城市的学府,成了高才生,有的在城市的某一个出租屋里吞云吐雾,一些在写字楼,总之,他们背井离乡,带着无法抹灭的土气,以各种各样的身份,混迹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他们把家园抛于千里之外的大山里,任其憔悴和衰老。或许,他们也在一个风起的街头,以微醉茫然的状态,夹克衫里兜满街风和廉价的乡愁,落寞地遥望过故乡万千星辰,但那也只是想想,他们最终不知道自己的根须在何处,即使知道,也寻不回。留下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老屋,门窗不再是朱红色,旧得发白或发黑。檐下是潮湿的苔绿,人们甚至都忘了,在这样的檐下,看过繁星闪烁在深蓝的穹幕上,像萤火虫轻盈飞舞的大海。忘了院子里的晒场,阳光一直没有嫌弃过这里的贫穷,常常温柔又慷慨地照临,无数的春分腊月,母亲在这样的晒场上用竹篱笆晒过米粉、血肠、红豆,我们用以果腹、生长。剩下的,是像陈皮一样的老人,而且他们还将继续衰老。叔伯老去的时候,我就在城市人潮汹涌的菜市场,电话里的死讯传来,一个冰冷的机器传达的一个更为冰冷的消息。我泪流满面,慌乱地拨开人潮,跑到一个旁边偏僻的小公园里,那么汹涌澎湃的人海,那么多飞驰而过的车,尖锐的汽笛声,那么多神色匆忙的路人,不会留意到一个失去故园,蒙头痛哭的孩子。我是想起了在排着长长队伍的省城大医院里,去看望他时,他黑色的骨头,在一层薄薄的皮下隐约可见。他吊着一口气,以微轻的身体重量,躺在薄板上,眼角流不下来最后一滴眼泪。还有他生前打理的院子,鸡鸭还在栅栏里扑腾鸣叫,辣椒红了,井水依然清澈冰凉,还有那长长的长满喇叭花的围墙。婶婶也走了,在一个欢聚回来的晚上。三分钟前,她还在自己老母亲面前撒娇、孝亲,三分钟后,她就被自己的车压在泥土之上。父亲走了,留下他的野兰草和凤仙花。后来,更多更多人走了,去另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维度里,他们已离开村庄的儿女们,后来回去,故园只剩越来越残破的瓦楞,原来栅栏里开满野花的菜葡,现在已是暮草荒烟,还是满树的梨花,自己开,自己在春风里纷扬,自己败。在村口走走停停,几个抹着鼻涕的孩子,脸蛋油光黑亮。此外,就是山谷一样的空旷寂静。
狗的存在,让村庄和人间多了些清冷里的热气,鬼气里的烟火气。
赛虎陪伴着那些个留守的老人、孩子。那时,我们也常在,赛虎可欢乐了。如果按人一生的时光参照计算,它应该正值芳华,还是个莽莽撞撞的少年。一天邀朋结友,带着本村的狗,甚至是十里八乡的狗们,常常在村庄里集会。它应该是个领袖人物,带领众狗们,各家门前屋后出入来去,撕缠滚打,常为一根没肉的骨头打得头破血流。也常争风吃醋,为一条母狗,和兄弟们撕破了脸。人们嫌它们吵、闹腾,辱骂它。它有时垂头丧气地回来,有时不屑,依然举着头颅,像个桀骜不驯的英雄。
有了狗的村庄,就有了活物的气息,这种气息生龙活虎。不会在黑夜里陷入一种寂灭,连鸟的叫声都能让人汗毛立起来。仿佛只有啾啾叫着的秋虫、蟋蟀,还活在人间。一些人家,甚至彻夜把灯亮着,像是回到远古时代,要借助一堆火的光亮才能驱走黑暗带来的恐惧。文明时代的可怜人。这个时候,赛虎和它的兄弟姐妹们显得尤为重要。它们成了一群忠诚的卫侍,尽心竭力担负起守护村庄的责任。每晚竖直耳朵,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就警觉地狂吠起来。众狗形成呼应,气势磅礴又恢弘,空荡荡的村庄里就有了一股热气腾腾的力量。黑夜中的人类多么渺小,渺小到需要一束光,几声狗的叫声,几床棉被,或相互炽热交织的躯体,才能渡过茫茫而漫长的黑夜。
我也是这渺小中的一员,那个最寒冷的冬天,下了一场最大的雪。天地苍茫,好像把所有的春天都覆盖了。但是,这般棉被一样厚重的雪,仍然没有掩盖住悲伤。已故的人躺在堂屋里一个多月了。一个棺椁,明灯有时亮,有时灭,微弱、躲躲闪闪。按习俗来,说是要挑个黄道吉日才能入土为安,一等就是一个多月。一家人,也只有四口,一个已年迈,一个小,还在襁褓中。两个才新婚不久的人,还没有学会生活,就要学会永别,在这样的漫长的冬天里。
在老屋,赛虎给了我巨大的支撑。我很害怕,黑色的棺椁和明灭的灯,被风卷起来,飘浮着的纸钱,烧尽或没有烧尽的,像无数黑蝴蝶,乱飞乱舞。我不敢去上一炷香,又怕被冠以不孝的名,只能勉强去。赛虎给了我巨大的勇气,仿佛这个世间,没有它惧怕的东西,寒冷、饥饿、黑暗或是死亡。一种勇敢的灵物。一个多月,它白天陪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买东西,请人帮忙,做事,都鞍前马后跟在身边。暮色沉沉拉开,它就在门口,用隔不了多久就响起的洪亮的声音提醒我们,它在。我和它在大雪缤纷落下的那一天,去树下拍照。雪地里漫无目的地玩,像两个共患难的兄弟。
后来,老屋的人都离开了。一些因岁月苍老而死去,一些奔走在红尘的烟波里。剩下了老屋,无人看管。无人看管的老屋不行,老屋在,根在。最后,只能让赛虎留下了。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偌大的世界,赛虎除了这里,没有他处可安身立命。在草狗群里,它还算英俊挺拔,可一拉出去比,就没有人家德国牧羊犬的警觉威猛,萨摩耶的娇美可人,哈士奇的贵气。城市海景房的天鹅绒地毯上,怎么可能踏上一只农村小狼狗的足印。校区不允许狗进入,我也只能做个袖手旁观者,无法带赛虎走。把赛虎留下的最大理由,还是老屋需要看顾。而这个重任,在这个几十口人的大家族里,最后,就落到了赛虎身上。
赛虎一守就是十年。一只狗,一座老屋。
很多狗,很多老屋,很多即将老去的人。
还有不会离开的青山、老树、瓦上的苔绿,乌黑过也明净过的天空。
老屋两层、六间,进深很深,是原来生产队的老公房,高大的木架子,感觉悬空了的。除了左右两道山墙,是土基砖砌筑而成,其他房体均是木料。据说,老辈人耗尽了多年努力得来的财富,人托人,加以各种谋略,才最终买到这所老公房。
好在,留下来守老屋的赛虎,旁边偶尔有几家邻人住,暖了一些。我不知道,赛虎看着当时空空的老屋,有没有潸然泪下。或是在它的心里,激荡起一阵阵的酸,眼神里有没有别人觉察不到的落寞。我只知道,每次我们回去,赛虎雀跃得像个久不见爹娘的孩子,拼命摇着尾巴,大口大口哈着气。它高兴地站立起来,朝着你扑,轻咬,不停围在你身边打转转,恨不得把两只前脚变成两条胳膊来紧紧拥抱你。这大概是我在那个大寨子里有过的最温暖的待遇了。
在老屋门前的院落里,落下的阳光散淡轻软。赛虎去村寨里逛了逛,慢慢摇着回来。孩子经常省下嘴里的肉,或是其他美味吃食,投给赛虎。看着它像人们中了五百万一样高兴,孩子也很快乐。觉得生活富足的赛虎,少了些为吃食奔走的疲顿。常常眯着眼,趴在被阳光炙烤得暖烘烘的地上睡觉,像一个平和安静的老人。
它也成了孩子最好的玩具,在它睡觉的时候,孩子们常常坐到它背上,揪它的耳朵,揉它的脸,抱住它的脖子,挠它的下颌。一个毛茸茸、臭烘烘、又暖呼呼的皮玩具。老好的脾气,任凭孩子怎么逗弄它,它都不发火,也不会吓唬孩子。有些捣蛋鬼小孩,朝它身上撒尿,对着它哈哈大笑,它也只是抖擞一下皮毛,不屑地走开了,仿佛在说:“小屁孩,懒得和你一般见识。”
一个包容了所有,承担了所有的赛虎,深情得像天空和大海。
我们的归来是短暂的,三五天的热闹之后,就都要走了,去往一个赛虎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每次离开,它都很着急,拼命摇着尾巴,窜来窜去的。车子开动了,赛虎会一直追着车跑。一路是稀落散住的人家,天空下是苍黄的大地、永恒沉默的大山。有时,车在路上行驶着,它会爬到路旁高坡上,或是耕地里,和车保持一个大概平行的位置,与我们遥摇相望,也常常被地里的土块石头绊得踉踉跄跄。像一个电影里的慢镜头,那条从生命的起点开始,延伸到天涯各处的路上,赛虎一直奔走相送的身影。我常常回想起它一路奔来的样子,跑上高高的坡顶看着我们的车越驶越远的样子,让我在这尘世,多了些柔软,眼里多了些潮湿。
光阴像射出去的箭,十年就过去了,我从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女,成了一个深夜痛哭的人。一把霜、一把盐,边洒边朝前走。时间在走,我们无法停留,赛虎也无法停留。和所有万物一样荣枯轮回。赛虎老了,它也累了吧。
除了赛虎,村庄里也常常看到小荣的身影。那次我回去,走在早已成为草滩的稻田旁边,大箱小包,像个异乡落魄归来的游子。远远有人叫我的小名,走近一看,才知道是小荣,小荣也老了,我以为,小荣是不会老的。远离村庄的人们已经把这个他们小时候常常嘲笑,欺弄的憨子小荣忘了,所以他的年龄还停留在少小时。所以他的衰老才令我有些吃惊。脸皮有很多褶皱,像老黄牛脖子上拉梗索的皮,还布满了黑色的斑。其实,他和我一般大小,这使我无比恐惧,时间也一样对我进行了剥夺。小荣和赛虎,和其他狗,和其他老人一样,在村庄里游荡,他们像被上帝遗落的弃儿。偶尔会碰在一起,在村口的草垛旁边,或是老核桃树下,搭个讪,重复地讲述村庄里老掉牙的故事,和远方儿女偶尔捎来的信息,阳光很懒地照着这里的早晨和黄昏。老了的赛虎和老了的憨子小荣就在旁边。在偌大的人间,世界的另一面是灯红酒绿的喧嚣、栉比鳞次的高楼下沸腾的人群,灯火通明阑珊。
……
留守村庄和老屋的赛虎一定有过很多孤独的夜晚。
村人们偶尔的言语里,满是对赛虎的同情:可怜了,这条狗……足以证明它这些年的心酸。在没有主人的空荡老屋旁,它的肚子从来没有吃饱过,饥饿难忍时,肯定也没脸没皮地去村寨里到处游走找吃的。遭受过的白眼,被人辱骂过的难听话,被棍棒、石头、土块打在身上的疼痛感。
老了的赛虎,依然没有可去之处。有一个果园,最后答应收留他,帮忙看守果园,一辆三轮车来了。老板揪着赛虎脖颈上的铁链,把赛虎拉上去。它在上车的瞬间,眼里滚落下一颗巨大的眼泪,砸到地上。我以为我是错觉,可明明又不是错觉。几天后,果园老板又来了,说是不敢收留赛虎。它在果园不吃不喝,要把它送回来。那天,我们去接它了,孩子给它带去了很多好吃的骨头,回来后的赛虎,调养了一段时间。
那年的春节,还是在老屋,依然是古旧的高高的门槛。两扇有些腐朽的木门,还是用木栓子上锁的,已经贴上了风调雨顺。朱红色的对联,尉迟恭、秦叔宝二将军也请上门了,他们还是那么威武雄壮。大门正上方,还飘着红色的剪纸须,风吹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吃过了简单的年夜饭后,大寨子里的烟火燃放就要开始了。从花花世界里归来的人们,用这些工厂流水线上的浓雾烟蛋,带给村庄短暂的热闹。
两个孩子和赛虎,像至亲的三兄弟,就坐在门槛边,等待烟火。那夜的烟火极美,从寨子底燃放,一冲上天。巨大的爆破声后,缤纷四散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天空,也照了两个孩子和赛虎的脸。他们一直仰望,像在仰望星辰,星辰也在望着他们。烟火映照里的树影,天空、孩子和赛虎的脸。被风吹得窸窣响起的联纸须,和古老沉重的木门,红艳艳的两个守门将军,是再也回不去的真实。我被三个看烟火的背影感动了,拍了一张照片,赛虎就坐在两兄弟的中间,高出去一个头,仿佛血脉相融的至亲。后来,照片保存半年后就弄丢了,像是一种预示。
那以后,我们离开了很久。赛虎没有等到我们回去。期间,有老家人打来电话,说是赛虎不见了,他们赶回去到处找。
赛虎再也没有回来,也再也没有人看见过它。
没有了赛虎的村庄又有了很多狗。没有了赛虎的人们依然在尘世的大风里飘摇。孩子们长高了。树茬绿了又黄,黄了又落,落了又绿。大山和青石木崖还在,天空的流云依然分合聚散,小荣还是一个人,嗷嗷地在村庄游荡。
我爬上村庄后面最高的山头,大雪纷飞而至,轻盈飘落,以一种永逝的姿势,无声无息。回望群山之间的村庄,那些炊烟稀落的屋顶像火柴盒。最后,大雪像一块巨大的白布,覆盖了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