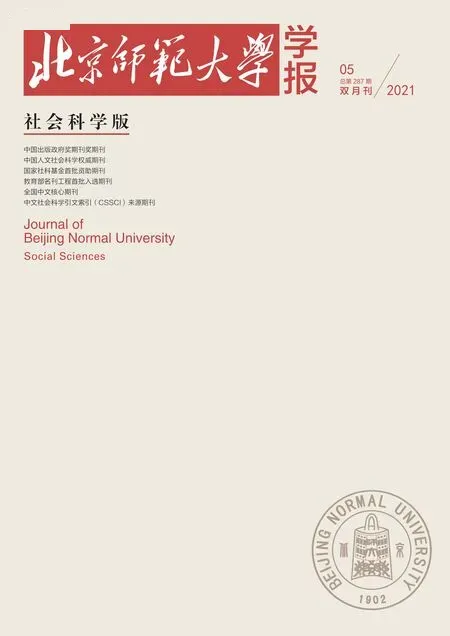重新发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要》与异化劳动逻辑的形成
孔伟宇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一、《摘要》的历史编纂与研究
在国内外学界中,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的内容及其与《1844年手稿》的关系鲜有学者讨论。MEGA2关于此部分的序言、注释、附录卷,对《摘要》的历史编纂、经济学与哲学定位、写作顺序作了详细的说明,为我们研究这一文本奠定了文献基础,也促使我们去重新审视这一被遗忘的文本。
第一,从手稿装订与历史编纂来看,MEGA2的编辑委员会对《摘要》的这两页手稿进行了详细地甄别,并作出了一些轮廓性的判断。
这两页手稿被发现时,是夹在《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第34页至第35页当中的。又因为该部分摘录的对象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将其与《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联系起来。所以,过去MEGA1以及国内的翻译编纂会默认将这一部分放在《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的最后。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是马克思有意将这两页手稿夹在这里的,甚至不能确定是否是马克思放的。
另外,《摘要》的写作材料是将一张白色的无横线纸对折(2张纸=4面)没有水印,纵向未分栏写作,前三页没有标记页码,第四页用阿拉伯数字标注“4”。而《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的写作则是用竖线分栏写作的,每一页用罗马数字进行排序,且与《摘要》是两套独立的页码。因此,无论从纸张和页码,还是从写作字迹和写作方式来看,《摘要》与《1844年手稿》的关系都“没有直接的记录成分”(1)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Ⅰ, Band2(Apparat), S.918.。仅就装订方面来看,MEGA2编辑委员会为了区分“笔记”(摘录和评论为主)和“手稿”(原创性写作为主)的不同文本编辑类型,特将这两页摘要放到了《巴黎笔记》当中。

图片来源: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Ⅰ, Band2(Apparat), S.918。
第二,从《摘要》中的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的关系来看,MEGA2编辑委员会试图从内容方面对这两页手稿进行定位。
MEGA2编辑委员会根据马克思早期与父亲的书信来往得出结论:马克思早就通读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那么,马克思此时又为什么重读这本书呢?他们认为,《摘要》是与《1844年手稿》的第三部分同时写作的,马克思此时一方面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文汇报”支持者的影响下去研究黑格尔体系,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客观必然性的生成;另一方面,在《巴黎笔记》前半部分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1844年手稿》对经济学的首次批判以及异化劳动范畴的发展,使马克思有能力对其已经进行多年研究的“现象学”形成新的判断,这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后对黑格尔现象学的清算。也就是说,MEGA2编辑委员会根据写作的主题将马克思的写作顺序推测为:经济学研究、异化劳动描述、《摘要》、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但这只是编委会的猜测。
同时,他们认为,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有意从哲学的观点来着手研究经济学问题的,并且夹杂着黑格尔批判的思辨方法的唯心主义阐释,马克思看到了《精神现象学》中决定性的“绝对知识”一章,以此将黑格尔的逻辑作为批判性变革的纲领。这一逻辑“构成了马克思关于黑格尔主客体逻辑最重要的范畴,并形成了马克思的固定思路”(2)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Ⅳ, Band2, S.38.。其实,MEGA2编辑委员会准确地把握到了黑格尔哲学在此时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却没有表达清楚:黑格尔主客体范畴是如何在马克思的分析和批判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尽管他们也试图克服所谓“西方马克思学”的桎梏,从内容和文献两方面进行编辑,但是该编辑方法仅仅停留在马克思的表层话语之上,导致很多问题值得商榷。
第三,由于未发表手稿的形式、内容较为复杂,关于《巴黎笔记》与《1844年手稿》之间及其内部的写作顺序众说纷纭,这一排序也关乎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内在逻辑的质性判断。
由于《巴黎笔记》中含有少量对勒瓦瑟尔、色诺芬以及黑格尔的摘录,MEGA2编辑委员会由此认为《巴黎笔记》在一定程度上是《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延续。也就是说,他们把《摘要》视为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一致性的内容。另一方面,MEGA2编辑委员会又强调《摘要》与《1844年手稿》第三部分的密切关系。除了上文讲到的《摘要》手稿被夹在《1844年手稿》第三部分的编辑原因外,MEGA2编辑委员会认为,马克思在写到《1844年手稿》第三部分时,在经济学研究中突然意识到要去批判黑格尔哲学,于是马克思找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发源地——《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进行阅读和逐字逐句地摘录,留下了现在我们看到的《1844年手稿》第三部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种判断不仅与《摘要》是《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延续相矛盾,而且马克思从经济学写作中突然转向哲学批判的解读完全是毫无逻辑的无根之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前秘书长尤根·罗扬(Jürgen Rojahn)对这一文本群的顺序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重组,他的根据是马克思在书信中提到的人物顺序、笔记和手稿提到的人物顺序和主题顺序。重组后的顺序大致为《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延续-《巴黎笔记》前半部分-《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和第二笔记本-《巴黎笔记》中间部分-《摘要》-《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巴黎笔记》最后部分(3)详见〔德〕尤根·罗扬著,赵玉兰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历史学——以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8期。笔者根据罗扬的描述将巴黎文本群的写作顺序概括为:B23a、MHa、MHb、B19a、B24a、B24b、B24c、B24d、B19b、B19c、B20、A7、A8、B21a、B21b、B21c、B21d、B21e、B23b、B23c、A9*(增补)、A9、B24e、B25、B26(手稿编码为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所编)。。其解释方法和手段,与MEGA2编辑委员会并无二致。
从对《摘要》的编辑和定位来看,MEGA2编辑委员会为这一文本群的编排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内外基本沿用了这一编排方式,默认将其看作是与《1844年手稿》第三部分同时写作的非重要性文本。并且,上文曾提到,MEGA2编辑委员会将笔记和手稿区分开编排,形成了我们现在在MEGA2中所看到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巴黎笔记》的所有编排顺序都是与《1844年手稿》的内容相对应编排的。
然而,MEGA2编辑委员会和尤根·罗扬都有一个隐性的逻辑前提:《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是同时写作的,也就是在《巴黎笔记》中做一部分经济学/哲学摘录,同时立刻在《1844年手稿》中写一部分批判性的研究。这种默认的前提并无证据,因为其依据只是两个文本提到的作者和主题相对应。笔者认为,这种按图索骥的编排方式恰恰可能重返“西方马克思学”的窠臼,而同时的隐性前提也可能遮蔽了青年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真实逻辑与来源。因此,有必要对《摘要》与《1844年手稿》的逻辑与环节进行再考察。
二、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与《摘要》
青年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总体逻辑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逻辑是继承关系,其一致性不仅在于《摘要》的文献支援,而且异化劳动理论在内容上也与《精神现象学》的逻辑环环相扣。正如马克思在《摘要》中所总结的现象学逻辑那样:“存在,本质,概念;普遍性,特殊性,单一性。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简单的对立,确定的、扬弃了的。直接性。中介。扬弃自身的中介。在自身的存在。外化。从外化向自身复归。”(4)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Ⅳ, Band2, S.494.
青年马克思异化劳动的逻辑出发点是“现象”,也就是作为对象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行为,与此对应,《摘要》中“绝对知识”章的起点也是“表象”。
第一,马克思所分析的对象是从表面看起来与劳动不相干的“劳动产品”,这种产品的直接特征是“作为一个与劳动者对立且不依赖于劳动者的力量”(5)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Ⅰ, Band2, S.364,367,368.,也就是说,对象(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关系直接呈现出独立和不相干的特点。马克思在《摘要》中摘抄道:“对象是直接的、漠不相干的存在”(6)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Ⅳ, Band2, S.494.。两者的出发点如出一辙。
第二,劳动产品真是独立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马克思要在看似独立的劳动产品中找到劳动的主体。其实,劳动概念是黑格尔极具独创性的范畴,它既吸收了斯密经济学中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必然性,也在主客体关系上解答了康德的难题,这恰恰引起了正在研究经济学的马克思的强烈共鸣。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关系是通过劳动行为勾连起来的,劳动产品就是劳动者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和现实化(Entwirklichung),所以劳动主体是在劳动产品中看不见的存在。而在《摘要》中,黑格尔按照对象的规定,认定意识必然会认识到对象就是他自己,物只有在与自我的关系中才有意义,但是此时意识与对象的真正关系还未被揭露出来,因此呈现出表象上的独立性,黑格尔提出需要在意识和对象相互运动的各个环节中揭示出真正的概念。马克思因此从异化劳动的结果——劳动产品——出发,试图去揭示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本质关系。
第三,在国民经济学的现实中,劳动产品却渐渐走向(treten)了自己的对立面,走向了一种异己的存在,在这样一种运动的环节中,工人劳动越多,失去的也就越多,由此走向被对象所异化和奴役。这在《摘要》中则对应着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经历异化世界的环节,自我意识沉沦在物的世界中。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这种惰性的沉沦被国民经济学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内蕴了被超越和扬弃的潜在环节。
第四,马克思从异化的结果追溯到异化的过程,他认为,因为“生产性活动本身”(7)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Ⅰ, Band2, S.364,367,368.是异化的行为,所以劳动产品才呈现出异化的结果,异化是在这一行为中展开自身的。马克思将这一异化过程称之为“事物的异化”。笔者推测这一从结果到行为的推衍逻辑同样来自于黑格尔,在《摘要》中,马克思摘抄道:“意识到它的行动同样是外在于自身的行动,就像它意识到对象只是直接的对象一样”(8)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Ⅳ, Band2, S.494.。
异化劳动理论的前两点分别从结果和行为描述了异化劳动的现象层面,而后两点则是要过渡到现象背后的本质层面。简单来说,黑格尔预设的本质给予了马克思逻辑上的启发,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关系论是马克思此时思考点的重要支撑。
首先,马克思认为,通过劳动现象的异化可以得出,人与自然界相异化、人与作为人类特有的自身生命活动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推断是怎么得来的呢?马克思关于人的类生活的异化是以人作为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为分析前提的,他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是否对自己的生命活动有意识,即是否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对象(对象化)。人通过对象化活动进入交换领域,把自身变成普遍的存在,从而成为普遍的类本质。但是异化的劳动将类生活变成了手段,个人生活变成了目的,普遍性被特殊性颠倒。这一思路正是《摘要》中黑格尔关于灵魂无限判断的表述,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其实是黑格尔所说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而作为类生活的生产活动则是缺乏精神却又最富有精神的体现,其内核在下一环节被呈现。
其次,马克思将类本质的异化归因于人与人关系异化的根本性体现,他甚至认为“人自身的所有关系,都是通过对其他人的关系中完成和表现出来的”(9)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Ⅰ, Band2, S.371.。笔者认为,这一描述道出了马克思此时关系论方法的基石。一方面,关系是类本质的基础。在《摘要》中,黑格尔将自身与他人的关系视为物的意义展开,这一基于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关系论是极其深刻的,而马克思继承了这一点,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建构起了人的类本质,也构成了人类本质的现实化。另一方面,关系是异化实现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自我异化只能在与他人实践的和现实的关系中实现。异化得以实现的工具本身就是一个实践的关系。”(10)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Ⅰ, Band2, S.372.根据词尾变化和上下文判断,最后一个形容词“实践的”后面的词应是中性词“关系”。中文版的翻译中没有补充。从总的过程来看,异化需要在与他人的现实关系中实现,也就是一个从自我出发、经过他者、再返回自身的辩证过程,即黑格尔的异化逻辑。马克思把异化的实现从根本上看成是一种“关系”,也是在这一关系性的现实异化中,工人才生产出了奴役自己的他者和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异化关系和支配关系都是自身生产出来的,不是他者生产出来的,这是自我异化的现实化。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劳动的关系,是关系生产关系!这已经超出费尔巴哈的线性思维了。“类本质”、“人与人”这些看似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更相近的概念其实与黑格尔的异化逻辑是一致的。
最后,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从现象到本质的透视,并非想完成一种认识论的分析,而是要超越和扬弃这一异化现象,这一扬弃环节无疑又是来自于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马克思曾在《1844年手稿》中“对笔记本Ⅱ的补充”部分评论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其中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11)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Ⅰ, Band2, S.404.称作黑格尔的伟大之处,由此足以看出马克思对它的肯定。这种否定性一方面体现在将对象化劳动看作非对象化劳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异化劳动。另一方面,否定的辩证法还在于否定之否定,也就是扬弃和超越异化劳动现象,回归劳动的真正本质。但是,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类本质,而是在经过了异化之后的扬弃环节,从而上升到一种“绝对”的环节,也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描述的共产主义。这种辩证逻辑显然与费尔巴哈的简单“回归”是截然不同的。根据《摘要》的印证,虽然马克思此时的逻辑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逻辑是基本一致的,但他在具体环节中对黑格尔进行了批判和超越。
三、异化劳动理论的环节与《摘要》
青年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具体环节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是扬弃和超越的。这不仅外在表现为大量使用和称赞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式的话语,而且内蕴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以现象学的逻辑统领了人本主义的概念,形成了显隐两层结构在冲突中并容的张力,体现了马克思此时思维的急剧变化性。
受费尔巴哈和赫斯的影响,马克思重新规定了“自我意识”环节:自我意识=人(工人)。在黑格尔那里,意识的运动表现为自我意识在外化的过程中自我设立对象,同时又包含着扬弃外化收归自身的环节,所以马克思在《摘要》中摘抄道:“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这种外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12)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Ⅳ, Band2, S.493.。但是马克思自从博士论文完成之后,鲜用“自我意识”这一概念,他真的放弃这一概念了吗?其实他仅仅是在显性话语上对这一概念扬弃,而在逻辑上却继承了这一环节。劳动异化逻辑中的人(工人)就是他给予自我意识概念新的内涵,工人外化创造劳动产品,最后扬弃回归本质恰恰与自我意识的环节是一致的。费尔巴哈是这一新内涵的始作俑者,他认为,“旧哲学的自我意识是与人分离的,乃是一种无实在性的抽象。人才是自我意识”(13)〔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7页。,对于对象的意识就是自我意识。由此费尔巴哈通过确立主体本质的向度改造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内涵,马克思也接受了这一判断,更换了自我意识的“外壳”。更进一步来说,费尔巴哈绝不是马克思这一环节超越的惟一理论来源,恰恰是在古典经济学的现实关系中,马克思逐渐抓住的是经济学家的共识:“劳动创造财富”,外部对象化(私有财产)其实是蕴含主体劳动本质的。马克思对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透视勾连起了黑格尔现象学的主客体关系与费尔巴哈的“人”。
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双重影响下,马克思重新规定了“对象”环节。其实他关于这一环节的改造是极具迷惑性的,从表面上来看,他在《1844年手稿》中认为黑格尔所说的对象只是意识的对象,因此只能在自我意识内部运动,同时又高度赞扬了费尔巴哈规定的对象,在话语上与费尔巴哈保持一致。但是,马克思真的像自己描述的那样“简单”吗?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费尔巴哈的说法:在他看来,对象正如地球与太阳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反映的认识层面的规定。无独有偶,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也使用了类似的比喻,他说:“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确证植物生命的必不可少的对象,就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14)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Ⅰ, Band2, S.408.马克思分别在“对象”、“外化”、“对象化”概念下面划了下划线。马克思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肯定了费尔巴哈关于对象之间相互肯定和外在化的规定。然而,费尔巴哈关于对象的规定仅停留在认识层面,是没有主体能动性的。一旦马克思将这种关于对象的规定嫁接到社会历史领域,就不得不再去求助黑格尔的逻辑,也就是在《1844年手稿》中将人形成的历史描述为“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15)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Ⅰ, Band2, S.409.。所以,在这一环节的改造中,马克思的显性话语是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语句,隐性话语却是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的逻辑。
由于马克思批判异化劳动的目的是寻求真正的复归,所以必须在复归的方向和路径上进行重新设定,这也呈现出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方法论交叉的复杂语境。从复归的方向来看,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悬设,承认从异化到复归的必要性,因为他认为这是人类全部力量发挥出来的必然环节(来自于黑格尔),但是复归的方向却是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类本质。在马克思看来,扬弃异化不能在异化形态中寻找,黑格尔在异化中扬弃异化不仅是不彻底的,而且是对上一个环节具有保守性本质的虚构,所以马克思要寻求费尔巴哈预设的抽象的类本质。费尔巴哈没有提供复归的路径与方法,只是线性的人本主义假设,每个环节被僵化地割裂开来,而黑格尔则在辩证法领域提供了扬弃和复归的中介环节,以此串联起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与运动,这被马克思继承。一方面,黑格尔说:“自我意识既然本质上即是中介与否定,它的概念里就含有它与一个他在的关系,从而它就是意识。”(16)﹝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5页。中介是内在于自我意识的,并且潜在地含有异化和外化的因素,推动自我意识向下一个环节运动,因而意识现实化的过程也是自身中介的必然过程。另一方面,中介又是在异化后复归统一的扬弃过程,两端通过中项的中介完成一种非直接的否定,即复归统一,最终完成否定之否定。
可以说,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扬弃逻辑是与黑格尔相一致的,是人类通过作为其生命本质的劳动中项完成异化与外化并最终扬弃异化复归统一的过程。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说道:“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是一样的经历。”(17)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AbteilungⅠ, Band2, S.387.不过,马克思也吸收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成果,将“绝对精神”改写为1844年马克思所指认的“共产主义”,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理论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