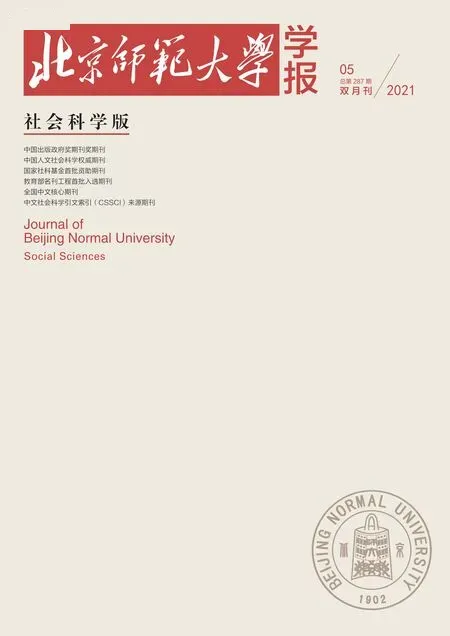古代文学作品整理与研究的反思和进境
——以韩愈诗为中心
孙羽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文史部,北京 100091
中国古代文学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价值理念,凝结着中华美学精神及话语特质。这种理念、精神与特质的传承光大,离不开历代整理与研究的层累建构。20世纪初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1949年后古籍整理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全面推进了校勘、注释、系年之学,还发展了标点、今译之学。在此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整理不断朝着系统化、学科化方向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文学作品的阐释与研究。若从广义讲,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献整理本身也是文学研究活动,前辈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往往就是某部经典文集的整理成果。只不过随着现代学科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发展,整理与研究才逐渐成为学术工作内部的两个分层。当然,一般意义上的古籍整理也自有其畛域,无论是校记还是注语,率皆要求简明扼要,点到即止,很少做长篇大论的发挥,以免喧宾夺主。与此相呼应,前人所认同的学术理念是“述而不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训着整理成果的面貌。要言之,由于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的叠加,目前对古代文学作品整理研究之得失的系统梳理和综合分析,尚不甚充分。
故业或未遑安顿,新潮已奔涌而来。激荡着新技术、新理念的数字人文浪潮,正以其高度规模化、精细化、计量化之禀赋,丰富并改变着传统人文学术的固有版图。对于古代文学作品整理与研究而言,数字人文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更深层面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总结前数字人文时代的经验、规律和方法,就难免导致C. P. Snow所谓的“两种文化”遭遇之际的“失语”,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数字”与“人文”的平等对话和深度融合,就会使人文学术在拥有强劲内驱力而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面前沦为客观对象物的风险不断提升。由此可见,无论历史因缘还是现实考量,深入发掘学术史所蕴含的经验、规律和方法,实为加快构建古代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题中之义,其意义自不待言。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规律和方法,则往往源于那些后世影响大、研究历程久、歧解异说多的经典作家作品之中。
韩愈作为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宗匠巨擘,在身后一千二百年间,其文学作品受到持续而广泛的关注,早在宋代已著“五百家注”之名号,今人更冠以“韩学”的盛称(1)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466—469页。。历代有关韩愈作品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在各种选本和札记类著作中涉及韩愈诗文的论述更是不胜枚举,剩义纷呈,共同构筑了深厚而开放的阐释传统,持续推进着韩愈作品的经典化历程。然而,从晚近的各类集注集释本来看,它们大多谨守定式,客观地呈现历代诸家复杂多元的见解主张,即使偶作按断,也仅指示所当然与或然,而鲜言其所以然。这种述而不作、集而不论的方式,体现了学者审慎克己的美德,诚为可贵。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或许正是由于这一传统体例,历代整理与研究成果长期处于以时间为序的线性分布状态中,其背后所蕴含的文本意义之错综、学术理念之异同、学术方法之沿革及高下得失,往往难以得到清晰的梳理和深入的辨析(2)钱锺书曾用“开会”来比喻集注集释的工作,委婉地批评当代学者只做会议邀请人而不做会议主持人,面对历代整理与研究成果,没有担负起“调停他们的争执,折中他们的分歧,综括他们的智慧,或者驳斥他们的错误”的责任。见氏著:《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86页。。今笔者不揣谫陋,在前人丰厚成果的基础上,试以专论形式对韩愈诗歌的典故注释、标点体例、系年方法等方面略作辨析,藉以窥见古代文学作品整理与研究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并尝试探求与当下蓬勃发展的数字人文研究的对话契机。
一、无过无不及:典故注释之边界
精准揭示文学作品中的典故运用,是文学阐释的基础与关键,是整理与研究水平的重要表征。特别是以韩愈这样的“涵泳经史,烹割子集”(3)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二引蒋抱玄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71页。的学者型作品为研究对象,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养和识力,恐怕不易达到理想的阐释效果。比如,韩愈《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铺叙了迷离繁复的诸多物象,遣词造句一如戛戛独造,向来颇难索解。直至清代,学者刘石龄才揭开其中的经传渊源:
公诗根柢,全在经传。如《易·说卦》:“《离》为火,其于人也,为大腹。”故于“炎官热属”,以“颓胸垤腹”拟诸其形容,非臆说也。又“彤幢”“紫纛”“日毂”“霞车”“虹靷”“豹”“鞬”“电光”“赪目”等字,亦从“为日,为电,为甲胄,为戈兵”句化出。造语极奇,必有依据,以理考索,无不可解者。世儒于此篇,每以怪异目之,且以不可解置之。吁!此亦未深求其故耳,岂真不可解哉?(4)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卷四引刘石龄云,清道光十六年(1836)膺德堂本,第12b—13a页。
沿着前人指示的这一重要思路继续追溯,便不难发现此诗不唯敷衍《离》卦之象,亦化用与《离》相对的《坎》卦之象。《周易·说卦》提及《坎》卦时,先概述“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而后分别论述《坎》卦对应于“人”、“马”、“舆”诸事物中的具体表现,并强调“其于人也……为血卦”(5)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卷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4、95页。。反观《陆浑山火》一诗后半有“顼冥收威避玄根,斥弃舆马背厥孙,缩身潜喘拳肩跟”、“梦通上帝血面论”数句(6)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第685页。,其中的“顼冥”,分别指北方水神颛顼、玄冥(7)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五,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6页。,合乎《说卦》所谓《坎》卦方位及为水之象;而水神的具体状态则饰以“收威”、“避”、“缩身”、“潜”、“拳”等一系列词汇,皆合《坎》卦的隐伏之象;又云“斥弃舆马背厥孙”,则在点出《坎》卦对应的舆、马二象的同时,标明本诗“斥弃”二象而不取,至“梦通上帝血面论”一句,遂见其独取“为血卦”之人象,凸显了造语使事的人格化倾向。由此可以确定,《陆浑山火》中的繁复物象并非韩愈凭空生造,而是在《说卦传》基础上敷衍《离》、《坎》二象,进而设置了水火相争的铺叙结构。
精准揭示典故的运用,不仅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作品的结构义脉,有时也能通过对关键词句的解读,深化对作品主旨的理解。如韩愈《元和圣德诗》“若杵投臼”句,诸本失注。唯文廷式《纯常子枝语》云:“‘遂自颠倒,若杵投臼’,形容近于儿戏。”(8)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16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9页。按,今人亦有引用此说者,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第638页。然而,如果详玩此句蕴含的语典,则知其不仅非同儿戏,反而十分贴切得体。今按《元和圣德诗》为韩愈称颂唐宪宗平定藩镇叛乱所作,其中“遂自颠倒,若杵投臼”用以形容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失败后投江自尽的场景。“若杵投臼”语出《周易·系辞传》,传文云:“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孔疏:“取诸《小过》,以小事之用过而济物,杵臼亦小事,过越而用以利民。”(9)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卷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7页。由此可见,所谓“若杵投臼”或许不只是将刘辟比作杵、大江比作臼那样简单,而是兼用杵臼为“小事”、“用以利民”二义,轻诋刘辟叛乱不过毫末细事,王师一至,刘辟便溃败投江,万民遂享太平一统之福祉。故知此语之设,实是韩愈站在中央王朝立场上的讽刺和象征,甚合扬厉朝廷盛德之主旨(10)韩愈《元和圣德诗序》云:“(臣)以经籍教导国子,诚宜率先作歌诗以称道盛德。”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第627页。。
以上二例,庶可见失注之憾与补注之功,然而,所谓精准揭示典故,亦非补注典故多多益善,一旦忽视文意而强加出典,反而会孳乳过犹不及的新问题。如,韩愈在与孟郊共作的《纳凉联句》中有“君颜不可觌,君手无由搦”二句,王鸣盛《蛾术编》以此二句似出《说苑》,略引其事云:“襄成君衣翠衣,带玉剑,履缟舄,立于游水之上。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遂拜谒曰:‘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而不言。庄辛曰:‘君独不闻鄂君子晰感于越人之歌乎?’襄成君乃奉手而进之。”(11)王鸣盛:《蛾术编》,卷七六《说集二·韩昌黎》,顾美华标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119页。按,今人亦有引用此说者,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四,第427页;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第2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97页。乍看或可备一说,而一旦复归原始语境,则多见抵牾。《纳凉联句》作于元和元年(806),此时韩愈刚刚结束贬谪生活,重返长安。联句多用对话体表现挚友交谊,如韩愈以“幸兹得佳朋”致意孟郊,孟郊以“殷勤相劝勉”致意韩愈。至全诗结尾,韩愈连作十数韵,向孟郊倾吐久别重逢之慨:
与子昔睽离,嗟余苦屯剥。直道败邪径,拙谋伤巧诼。炎湖度氛氲,热石行荦硞。痟饥夏尤甚,疟渴秋更数。君颜不可觌,君手无由搦。今来沐新恩,庶见返鸿朴。儒庠恣游息,圣籍饱商榷。危行无低回,正言免咿喔。车马获同驱,酒醪欣共欶。惟忧弃菅蒯,敢望侍帷幄。此志且何如,希君为追琢。(12)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四,第419—420页。
值得注意的是,此节以“与子昔睽离”领起,以“希君为追琢”作结,无论是“子”还是“君”,皆指孟郊,这是显而易见的。此节中“君颜不可觌,君手无由搦”,既呼应前面的“与子昔睽离”,意谓昔日远贬阳山、不能相与游处,又衬出后面的“车马获同驱,酒醪欣共欶”,以表达与孟郊重逢同游的喜悦。由此可见,此节前后义脉一贯,皆以孟郊为倾诉对象,“君颜”、“君手”之“君”与“希君”之“君”、“与子”之“子”一样,显然都是用以指称挚友孟郊的。
另有一条更为直接的证据:韩愈在同年所作《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中,以极为近似的笔触铺叙贬谪生活,表达了对另一位挚友崔群的情谊:
前年岭隅乡思发,踯躅成山开不算。去岁羁帆湘水明,霜枫千里随归伴。猿呼鼯啸鹧鸪啼,恻耳酸肠难濯浣。思君携手安能得,今者相从敢辞懒……(13)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第563页。
这里的“思君携手安能得”与《纳凉联句》的“君手无由搦”别无二致,不过是韩愈表现挚友交谊的惯用语而已。“君”是韩愈对挚友的敬称,这本是一目了然、不言自明的。然而,一旦采用《蛾术编》所出典故,反而徒生许多困惑。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原典中襄成君与庄辛原本是有距离感的,这种距离感来自君臣之间的身份差异。若以此典出注,则极易曲解《纳凉联句》的本义,甚至系联“君手无由搦”之下句“今来沐新恩”,把“君颜”、“君手”之“君”理解为当世之君主,即错贬了韩愈的唐德宗。而韩诗于历叙友情之际,阑入思君之情,不唯不合文理,亦乖悖情理。唐德宗晚年昏聩自专,黜抑直臣,信用奸佞,以致纲弛政紊。作为德宗晚期政局的亲历者与受累者,韩愈曾在《顺宗实录》中直言德宗“失君人大体”(14)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外集卷下,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97页。,其对德宗的态度可见一斑。同时,遍检韩愈贬谪诗作,鲜见恋阙思君之句,反而多是“脍成思我友,观乐忆吾僚”(《叉鱼》),“投章类缟带,伫答逾兼金”(《县斋读书》)这类思念友人的诗句(15)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二,第215、191页。。更何况襄成君与庄辛之事颇具狎亵性质,一向以儒家道统自膺的韩愈怎会以此来比拟自己与君主的关系呢?退一步讲,如果认为韩愈只是借用此典表达自己与友人的亲密关系,那么此处便成了以君臣之伦比拟朋友之伦,韩愈为了一个并不高明的修辞而不惜违背他所笃信的儒家的基本伦常,这又会有多少可能呢(16)韩愈曾在《原道》中着重阐述名位伦常之重要性,其一生出处大节尽本乎此。韩诗风格虽然奇崛诡怪,却始终不逾儒家伦常规矩,具有“诗性之超越与德性之醇正交结共生”的特质,参见拙文《奇诡托讽与诗派建构——以韩愈、卢仝〈月蚀诗〉为中心》,《文史哲》,2021年第2期。?可以说,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韩愈都不必援《说苑》之典作《纳凉联句》,“君颜不可觌,君手无由搦”本为平铺直叙,一旦强加出典,不仅无益于作品解释,反生歧义无穷,使原本显豁畅达的诗意变得扞格难通。
要言之,实现典故的精准注释,需要把握“无过无不及”这一总原则,以理取舍,因文损益,既要精准发掘作品背后的典故渊源,特别是文学研究者知识体系中相对薄弱的经、史、子部典籍,同时更应以文意为经、情理为纬,审慎对待“无一字无来历”的传统观念,尽力避免所注典故溢出合理性边界,造成过犹不及的状况。“无过无不及”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韩愈诗歌的注释,其他作家、其他文体的作品亦同此理。就“无不及”一端而言,历代诗文作品大多惯于用典,精准注释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即便是古代小说、戏曲作品,虽被归为俗文学,实则往往产生于宫廷文化、士林文化、市井文化和乡村文化的交融共生之中,具有复合型的文化品格,其对儒释道各类经典的化用程度并不逊于正统的诗文作品,那么,精准注释各类典故的必要性自然不殊于雅正之诗文(17)比如,有学者指出《聊斋志异》“具有士林文化辅以乡村文化的双重品格”,特别是作为士林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对小说创作起到了重要影响,准确揭示小说中蕴含的儒典,“是当代解析《聊斋志异》真义的关键所在”。详见赵伯陶:《儒家经典与古代小说关系窥管——以〈聊斋志异〉为中心》,《国际儒学(中英文)》,2021年第1期。。就“无过”一端而言,前述王鸣盛对韩愈作品的过度注释亦非个案。有清以降,仇兆鳌之于杜甫、冯浩之于李商隐、查慎行之于苏轼,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度注释问题,对于这一学术史现象,前修时彦已多有反思,兹不赘述。这里想要补充的是,在当前数字人文时代,“不及”的问题或许能够借助数据检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但过度注释的问题却可能因之不降反增。特别是文本型文献资源库向结构化数据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某个语词下系若干出典殊非难事,注释体量也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然而,新的问题旋即产生:不断增殖的出典究竟有多少被控制于合理性边界以内,会不会在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上淆乱文意,从而重蹈清代学者之故辙?这是我们在热情拥抱数字技术的同时,应予以高度警惕的。
二、普遍与特殊:标点方案之拓殖
比起典故注释,标点的重要性及其难度往往会被轻忽。其原因大概在于标点诗文的方案相对简单而明确,普适性较强。一般认为,非韵文的标点以文义为据,韵文的标点以用韵为据(18)参见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4页;胡渐逵:《古籍整理概论释例》,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165页。。这一方案的确扼要清通,据此可以准确标点大多数古代文学作品,但也并非放之四海皆准。比如,一些才力雄劲的大家之作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高古奇僻的文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韵文与非韵文的边界。面对这类情况,标点工作也要相应地从普遍性原则中派生出特殊性方案,以适应变体作品的复杂特征,否则难免会在标点时出现舛误,甚至是系统性舛误。今仍以韩愈诗为例,略作申说。
众所周知,韩愈向以变体为文著称,其诗更是“奸穷怪变”,面貌崚嶒,这给后人整理与研究造成不少障碍,即便标点一役,仍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比如,韩愈元和元年《送区弘南归》诗中叙述与岭南士子区弘交往一节,诸本标点差异颇多,今从各类标点本中选取专业性较强的25部(其中不仅有韩集标点本,还有各类总集、选本等,依出版先后列于脚注之中),可归纳出以下七种类型:
(1)我迁于南日周围,来见者众莫依稀。爰有区子荧荧晖,观以彝训或从违。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徽。虽有不逮驱,或采于薄渔于矶。服役不辱言不讥,从我荆州来京畿。离其母妻绝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19)第(1)种类型最为普遍,在笔者调查的25部标点本中,占了12部,几近50%,分别是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卷一二,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613页;《韩愈集》,卷四,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48页;《增订注释全唐诗》,第2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375页;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卷一二,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523页;陆时雍选评:《诗镜》,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77页;《张籍集系年校注》,卷九《送区弘》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88页;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35页;徐天闵:《古今诗选》,卷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9页;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卷一二,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523页;查慎行:《初白庵诗话》,卷上附原诗,《查慎行全集》,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30页;魏仲举集注:《五百家注韩昌黎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29页;乾隆御定:《唐宋诗醇》,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656页。按,以上诸本标点相同,文字略有出入,为省篇幅,不再胪列异文,下同。
(2)我迁于南日周围,来见者众莫依俙,爰有区子荧荧晖,观以彝训或从违。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徽。虽有不逮驱,或采于薄渔于矶。服役不辱言不讥,从我荆州来京畿,离其母妻绝因依……(20)第(2)种类型集中在高步灜《唐宋诗举要》的三个版本中,分别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4页;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第276页。
(3)我迁于南日周围,来见者众莫依稀,爰有区子荧荧晖,观以彝训或从违。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徽。虽有不逮驱,或采于薄渔于矶,服役不辱言不讥。从我荆州来京畿,离其母妻绝因依……(21)第(3)种类型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第576页。
(4)我迁于南日周围,来见者众莫依俙。爰有区子荧荧晖,观以彝训或从违。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徽。虽有不逮驱,或采于薄渔于矶,服役不辱言不讥。从我荆州来京畿,离其母妻绝因依……(22)第(4)种类型分别见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第1册,第389页;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卷一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8页;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卷一二,《曾国藩全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042页。
(5)我迁于南日周围,来见者众莫依俙。爰有区子荧荧晖,观以彝训或从违。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徽。虽有不逮驱,或采于薄渔于矶。服役不辱言不讥,从我荆州来京畿,离其母妻绝因依……(23)第(5)种类型见《御选唐宋诗醇·韩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79—80页。
(6)我迁于南日周围,来见者众莫依俙。爰有区子荧荧晖,观以彝训或从违。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徽,虽有不逮驱,或采于薄渔于矶,服役不辱言不讥,从我荆州来京畿,离其母妻绝因依……(24)第(6)种类型集中在闻一多《唐诗大系》的三个版本中,分别见朱自清等:《闻一多全集》,第4册,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第338页;朱自清等:《闻一多全集》,第4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338页;朱自清等:《闻一多全集》,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第395页。
(7)我迁于南日周围,来见者众莫依稀。爰有区子荧荧晖,观以彝训或从违。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徽,虽有不逮驱。或采于薄渔于矶,服役不辱言不讥。从我荆州来京畿,离其母妻绝因依……(25)第(7)种类型分别见宗传璧:《韩愈诗选注》,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58页;胡守仁、胡敦伦:《韩孟诗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82页。

柏梁体发展到韩愈这里,又遭遇了“以文为诗”的变体风格。前引《送区弘南归》一节中,大量散文句式充斥其间,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增强了以义脉而非用韵作为标点依据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种情形下,不仅要舍弃以往习用的奇偶交互标点法,更应严格依据诗歌结构义脉下标点,尽量避免人为造成歧义。今详考此节结构,包含投师、课徒、采渔、从行四个层次:
(一)投师
“我迁于南日周围,来见者众莫依稀,爰有区子荧荧晖,观以彝训或从违。”此四句诗总写区弘投师,前二句陪衬,后二句是主,谓韩愈谪居阳山时,投师者甚众,唯区弘才性光明,然尚不能全从经义。故在此四句后下一句号为宜,或以两两成句,亦无不可。
(二)课徒
“我念前人譬葑菲”,樊汝霖云:“《诗》:‘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兴不可弃也。”孙汝听云:“言此者,以譬弘虽未尽善,不可遂弃之也。”(27)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引樊汝霖及孙汝听云,第1册,第391页。
由此可知,此三句是韩愈比类《诗经》中的“无以下体”之义,自谓不嫌区弘有违彝训,规之如下斧斤、引徽,虽其一时不能尽合于道,无妨常加劝勉,如驱马使进步也。要之,“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徽,虽有不逮驱”三句用典设譬,合写韩愈谆谆课徒之事,义脉贯通无碍,故在此三句后下一句号为宜(30)宋人葛立方提及韩愈“以师道自任”、教诲区弘时,即连续引此三句,引至“虽有不逮驱”为止,客观上印证了笔者的观点。见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85页。。而前文列出的很多标点本在“落以斧引以徽”后下句号,又在“虽有不逮驱”后下逗号,与后面一节连属,未免磔裂诗义,不妥。
(三)采渔
“或采于薄渔于矶”,韩愈《送区册序》云:“有区生者……与之翳嘉林,坐石矶,投竿而渔,陶然以乐。”(31)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第299页。由此可知,此句实写师徒二人同往采渔。
“服役不辱言不讥”,是称赞区弘事师之恭谨。

(四)从行
“从我荆州来京畿,离其母妻绝因依。”谓区弘离家随韩愈北行。或于前节末句“服役不辱言不讥”后下逗号而归入此节,多是为前节误点所累,遂造成系统性舛误。

要言之,在一般情况下,诗歌标点可视为一种奇偶交互的模式化操作,而一旦遭遇像《送区弘南归》这类具有特殊文体风格的作品,模式化的标点方案便不再具有普遍效力,特殊性方案需要建立在文体识别和文义辨析的基础之上,这是一项不应被忽视的系统性学术工作。然而,从现有25部标点本的实际情况来看,标点方案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其间既有因循致误的因素,或许也有不明字句义涵、结构层次甚至文体特质的因素,凡此仍需在今后的整理与研究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完善。
正确把握标点方案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亦非仅适用于韩愈一家、柏梁一体,实是处理有唐以降古体诗作之公理通义。特别是七言古诗,由于其句式和用韵的灵活性,诗句义脉之承转也颇多变化,就像前述《送区弘南归》“课徒”一节“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徽,虽有不逮驱”这样,以三句连属成义的现象并不罕见,兹举韩愈以外诸家典型句例如下:
九族分离作楚囚,深溪寂寞弦苦幽,草木悲感声飕飗。(王昌龄《箜篌引》)(32)李云逸注:《王昌龄诗注》,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90页。
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33)安旗等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22页。
吾为子起歌都护,酒阑插剑肝胆露,钩陈苍苍玄武暮。(杜甫《魏将军歌》)(34)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1页。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35)廖立:《岑嘉州诗笺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23页。
浓沙剥蚀隐文章,磨以玉粉缘金黄,清罇旨酒列华堂。(欧阳修《鹦鹉螺》)(36)刘德清等:《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41页。
贞观之德来万邦,浩如沧海吞河江,音容伧狞服奇厖。(苏轼《阎立本〈职贡图〉》)(37)《苏轼诗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32页。
邺王城上秋风惊,昔时城中邺王第,只今蔓草无人行。(晁补之《和关彦远秋风吹我衣》)(38)吴之振等选,管庭芬等补:《宋诗钞·鸡肋集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15页。
秋风谡谡松树枝,仙人骨轻云一丝,不饮不食玉雪姿。(元好问《松上幽人图》)(39)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89页。
如果说奇偶交互标点的基本模式可以用ABAB来表示,那么三句连属成义的标点则呈现为AAB的特征。ABAB模式与AAB特征最大的区别在于:ABAB在近体诗和一部分古体诗中是可以一直循环下去的,即从起句到结句普遍适用;而AAB的可循环性是较弱的,只有在很少一部分古体诗中会始终保持AAB的三句连属状态,在大多数古体诗中,AAB往往是偶一为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ABAB可谓具有相对普遍性的标点“模式”,而AAB只能被视为标点“特征”。即便如此,作为“特征”的AAB足以打破ABAB这一惯用“模式”,构成对奇偶交互标点的重要挑战。在标点实践中,判断诗作是否包含AAB特征、AAB所处的具体位置和AAB是否具有可循环性,是准确标点的关键所在。在前述韩愈《送区弘南归》的25部标点本中,只有两部标点本明确标识出“课徒”一节的AAB特征,在其他23部中,有的把AAB置入“采渔”一节,有的则全部按照ABAB模式标点,无论哪种情况,本质上都是由于缺乏对AAB的准确判断导致的。在上述唐宋金人具有AAB特征的诗作中,各类标点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未能准确判断AAB特征而致误的亦不在少数,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处理好标点实践中ABAB与AAB的关系,对于近年来方兴未艾的自动标点研究或许也能提供一些启示。自动标点是数字人文研究起步较早的一个领域,从CRF(Conditional Random Field)模型,到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 from Transformers)模型,再到各类模型的综合运用,十余年来古典文献自动标点研究和实践取得了长足发展,标点准确率不断提高。特别是包括古诗在内的集部文献,标点实验的准确率高于经、史、子三部,这在数字人文学者看来,主要是由于集部文本具有较为规范的结构,因此在自动标点上表现优异。如果进一步从集部内部来看,较之词曲、骈散诸体,诗的结构化程度无疑是最高的;而在诗的内部,近体的结构化程度高于古体。今后若要继续提升集部文本自动标点的准确率,则有必要从诗体内部入手,侧重优化古体诗的标点方案,突破奇偶交互的ABAB模式,精准识别AAB特征。
三、事件与时间:“以本事系年”之策略
古代文学作品整理与研究的方法创新,不仅是当代学术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千年以来学术史演进的内生动力。只不过古人鲜有总结阐述方法变革与创新的自觉意识,而往往寓方法于实践之中,有待今人深入论证、准确提炼,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和优化。兹以韩愈诗歌系年问题为例,作一考察。
与其他文学经典类似,韩愈诗歌虽经历代整理研究,仍有一些作品难以确定写作年代,被归入疑年诗的行列。造成疑年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类作品因触及时政,不便指实,只能以借物托讽的手法出之,字里行间隐晦委曲,所讽人物、事件颇费猜详,给作品系年制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韩愈《咏雪赠张籍》一诗通篇写雪,并无确切的时地信息,却时时流露出以雪拟人的倾向,尤其是“松篁遭挫抑,粪壤获饶培。隔绝门庭遽,挤排陛级才。岂堪裨岳镇,强欲效盐梅。隐匿瑕疵尽,包罗委琐该”(40)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第2册,第952页。数语,讽意显豁。对此,宋人已有阐释。樊汝霖云:“《书》:高宗命傅说曰:‘若作和羹,尔为盐梅。’”(41)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引樊汝霖云,第2册,第957、953页。盐梅者,作相之谓,而韩诗云“强欲效盐梅”,则知是“专以讥时相”(42)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引樊汝霖云,第2册,第957、953页。之意。曾季狸亦认为此数语“皆讥时相”(43)曾季狸:《艇斋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6页。。而方崧卿不但认为是讽刺时相,还尝试将这层讽意接榫于具体事件之中,云:“公时以柳涧事下迁,疑寄意于时宰。”(44)方崧卿:《韩集举正汇校》,卷三,刘真伦汇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韩愈确于元和七年因为华阴令柳涧辨曲直有失,下迁国博,方氏既作此推测,却无具体论证,以致朱熹反驳道:“此诗无岁月,方说恐未必然。”(45)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朱说亦简略,其未必不认同韩诗存在讽意,要在指摘方说臆必太过,难以服人。
直到清代,诸家论说稍详,其中方世举、王元启二家最具代表性。方世举云:
公以柳涧事下迁,在元和初年。时宰相为郑余庆、武元衡,与诗所讥者不类。此乃为皇甫镈、程异、王播诸人入相而作。镈、异之相,在元和十三年九月,播之相在长庆元年十月,三人皆以聚敛之臣,骤登宰执,故因咏雪以刺之……(46)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41页。
方世举先列举时之郑余庆、武元衡诸相,这些人都是忠荩之臣,且与韩愈有交谊,不可能是韩诗的讥讽对象,由此反证方崧卿之说诚难服人。而后,方世举提出了另一种可能,认为该诗讽刺的是元和末期到长庆初年的三位宰相——皇甫镈、程异和王播。方世举之说影响较大,此后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陈克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等均依方世举之说,将韩诗系于长庆元年(821)(47)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徐敏霞:《韩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70页;陈克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605页。。然而,方世举之说亦存在明显漏洞,正如稍后的王元启质疑的那样:“播之相后于镈、异三年,不应于长庆初并刺元和之相。”(48)王元启:《读韩记疑》,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310册,第500页。从常理上讲,以一物事并刺三人的可能性本就不大,更何况三人入相时间尚有三年之差。不但如此,今从卒年上看,程异于元和十四年(819)卒于任(49)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8页。,皇甫镈于元和十五年(820)卒于贬所(5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第484页。,若韩诗果作于长庆元年(821),则三位宰相中有两位已经下世,此时作诗讽刺的意义还有多大呢?这样来看,方世举主张的长庆元年之说,恐怕也是禁不住推敲的。
王元启在批评方世举的同时,拈出诗中“隐匿瑕疵尽,包罗委琐该”、“专绳困约灾”、“威贪陵布被”(51)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第2册,第953页。数语,别立一说:
盖德宗末年,任用京兆尹李实,专事剥民奉上,而王叔文、韦执谊等,朋党比周,密结当时欲速侥幸之徒,定为死交,此诗皆有所指,疑亦贞元十九年春作。(52)王元启:《读韩记疑》,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310册,第500页。
在王元启看来,韩诗诸句意蕴与德宗末期乱政极为相近,故将此诗系于贞元十九年(803)。王元启虽然批评了方世举之说,但他同样列出了李实、王叔文、韦执谊等多个托讽对象,这大概仍是证据不足、难以进一步坐实所致。尽管如此,王元启的推断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比如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张清华《韩愈年谱汇证》等均将该诗系于贞元十九年(53)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二,第163页;张清华:《韩愈年谱汇证》,《韩学研究》,下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5页。。
另需说明的是,当代诸家除了认同方世举或王元启之说的,还有一派只是罗列诸说,亦认同韩诗有所托讽,但本事不明,作年存疑(54)宗传璧:《韩愈诗选注》,第68页;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第2册,第953页;《增订注释全唐诗》,第2册,第1421页。。
综观《咏雪赠张籍》一诗的阐释史,呈现为层层递进、相反相成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南宋樊汝霖、方崧卿为代表,他们较早地尝试揭开韩诗托讽之旨。第二阶段以清代方世举、王元启为代表,他们虽不满前人的具体结论,却无不认同韩诗寓事托讽的风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追溯托讽对象及其本事,最终推及作品系年,探索出一条“以本事系年”的研究路径,至少在这一点上,谓之迈越宋贤,当不为虚誉。第三阶段表现为当代诸家的莫衷一是,此亦有学术史之意义:沿用清人之说而详其系年者,无论主张哪一派观点,皆意味着对“以本事系年”之方法的默认;胪列前人之说而疑其系年者,则意味着对“以本事系年”之方法的疏离。一家一说是非事小,此种研究方法究竟能否成立,诚当考论。
一般而言,作品系年无非是摭取、系联作品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实存信息,并参照信史记载的相应时间或含有时间要素的相关信息,来确定作品诞生的具体时间。当然,对于不同作品而言,系年工作在具体步骤上有繁简之别,有的一望而知,有的需要推导论证。所谓“以本事系年”,本质上即依事件系年,只不过这一“事件”并非明示于作品之中,而是潜藏于诗义背后,需要在客观史事与诗句义脉之间构筑相对完整的、甚至具有排他性的映射关系。唯有如此,作为本事的“事件”以及与“事件”关联的时间才会被赋予确定性,作品系年才得以成立,否则只能屏诸疑年的行列。反观当代对前人论说的接受状况,或偏取,或阙疑,根本原因乃在前人所指托讽对象过于笼统,以致本事游移。
鉴于此,不妨仍回到《咏雪赠张籍》文本上来,重审宋贤以降屡屡提及的“岂堪裨岳镇,强欲效盐梅”二语,以期发现症结所在。首先,“强欲效盐梅”是否有更恰切的解释?前人既知“盐梅”用以形容宰相,便谓“强欲效盐梅”是“专以讥时相”,然详玩诗意,“强欲效”三字不过讽刺某人才德不配相位而已,并不能据以断定其身份一定是“时相”。当然,以“强欲效”讥刺已充相位之人固无不可,但若用以讥刺本无才德却骄纵自负、觊觎相位之人,或许更为贴切,更加入木三分。其次,既然“强欲效盐梅”讽意明显,那么与之相对而出的“岂堪裨岳镇”一句是否也有所讽呢?所谓“岳镇”,宋人旧注云:“岳,五岳。镇,大山也。”(55)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引孙汝听云,第2册,第957页。若依旧注,则“岂堪裨岳镇”一句不过实写雪势未能对山岳有所裨益,这说明雪势并不大。然而从原诗语境看,无论是此句之前的“隔绝门庭遽,挤排陛级才”,还是此句之后的“隐匿瑕疵尽,包罗委琐该”,皆见雪势之巨,且其人格化倾向颇为明显。由此可见,“岳镇”当非旧注所谓“山岳”那么简单。今按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藩岳作镇,辅我京室。”吕延济注:“藩岳,谓诸侯也。谓惠帝弟吴王晏,出为大将军以镇吴,机为郎中令,故云‘辅我京室’也。”(56)萧统:《六臣注文选》,李善等注,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8页。到了唐代,多以“岳镇”代指诸侯或诸侯所辖之藩镇,这种用法十分普遍,不妨举几个韩愈同时期的典型用例:
况岳镇之方,表章继至。(权德舆《中书门下贺恒州华州嘉禾合穗表》)(57)董诰等:《全唐文》,卷四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47页。
儒衣登坛,岳镇荆蛮。(吕温《续羊叔子传赞》)(58)董诰等:《全唐文》,卷六二九,第6349页。按,这里的“岳镇”是名词作动词用。
岳镇阙而不知所取,台省空而不知所求。(白居易《为人上宰相书》)(59)董诰等:《全唐文》,卷六七四,第6886页。
不仅当日外部语言环境如此,从韩诗内部结构来看,“岳镇”又与下句象征宰相的“盐梅”相对,由此可以比较肯定地讲,“岳镇”并非泛指山岳,而是用以指代诸侯,即当时藩镇节度使,“岂堪裨岳镇,强欲效盐梅”实即托讽某人既不堪辅佐节度使、安定藩镇,又骄纵自负、觊觎宰相之位。
比照清人推测的若干托讽对象,无论是觊觎权柄的王叔文、韦执谊,还是身居相位的皇甫镈、程异、王播,均不如李实之生平与诗意吻合程度之高。据《旧唐书·李实传》载:
(贞元八年)嗣曹王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复用(李实)为节度判官。皋卒,新帅未至,实知留后,刻薄军士衣食,军士怨叛,谋杀之,实夜缒城而出。归诣京师,用为司农少卿,加检校工部尚书、司农卿。
贞元十九年,为京兆尹,卿及兼官如故。寻封嗣道王。自为京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人皆侧目……陵轹公卿百执事,随其喜怒,诬奏迁逐者相继,朝士畏而恶之。又诬奏万年令李众,贬虔州司马,奏虞部员外郎房启代众,升黜如其意,怙势之色,謷然在眉睫间。故事,吏部将奏科目,奥密,朝官不通书问,而实身诣选曹迫赵宗儒,且以势恐之。前岁,权德舆为礼部侍郞,实托私荐士,不能如意,后大录二十人迫德舆曰:“可依此第之;不尔,必出外官,悔无及也。”(6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五,第3730—3732、3729页。
由此不难看出,李实昔年曾有藩镇任职经历,初为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此即藩镇僚佐,后为留后,竟不能安定藩镇,反以刻薄致乱,正合“岂堪裨岳镇”之讽。至李实归京后,因得德宗宠信,不仅未加罪,反而窃据升黜之权,凌驾公卿百官之上,其“怙势之色,謷然在眉睫间”,虽未拜相,实已“权倾相府”(6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五,第3730—3732、3729页。,更契“强欲效盐梅”之刺。从本传中还能看出,遭李实欺压者,不乏赵宗儒、权德舆这样的骨鲠之臣,究其原因,乃在于李实“托私荐士”,凡此又合“岳镇”二句之前的“松篁遭挫抑,粪壤获饶培”之喻。
除此之外,李实过恶之极者,乃在贞元十九年天旱人饥之际,施刻剥之故伎,肆征求以固宠事,据《资治通鉴》载:
京兆尹嗣道王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6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604页。
对此,韩愈曾痛心疾首,自谓“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63)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王十二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三,第288页。。此后不久,韩愈因拜监察御史,上疏痛陈云:
右臣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过春阳,租赋之间,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放至多;上恩虽弘,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64)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第655页。
由此反观《咏雪赠张籍》一诗,在以“岂堪裨岳镇,强欲效盐梅”讽刺李实拙劣而龌龊的政治生涯之后,又出“巧借奢豪便,专绳困约灾。威贪陵布被,光肯离金罍”(65)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第2册,第953页。数语,诚与贞元十九年信史所载、韩愈疏奏李实之恶政相为表里。其中,“巧借奢豪便,专绳困约灾”二语意谓李实巧借给进奉而刻剥征求,以致生人困顿不堪;“威贪陵布被”即韩疏“上恩虽弘,下困犹甚”之意,谓李实专行暴戾贪狠之政而欺瞒德宗,致其恩泽不得布被于民;“光肯离金罍”,《毛传》云“人君黄金罍”(66)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8页。,此以雪光附离于金罍之描写,暗讽李实媚上邀宠。
考证至此,通过外在史实和韩文内证双重论据,可以基本确定《咏雪赠张籍》一诗的讽刺对象是贞元时期先失意于藩镇,而后权倾相府、暴戾贪狠的酷吏李实,此诗的托讽本事即贞元十九年李实“务征求以给进奉”之恶政。由此便可将“事件”的确定性转化为“时间”的确定性,将《咏雪赠张籍》一诗系于贞元十九年。反观前人诸说,唯王元启系年可从,然谓兼寓王、韦事则无据。
要言之,古代文学作品整理与研究的方法创新,往往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不断试错的过程。宋人解诗,臆必太过,但首次揭示了诗歌的托讽性质,为后世深入探究本事指示了基本方向。清人在事实层面否定宋人,而能继承并深化宋人的研究路径,孕育出“以本事系年”这一新方法的雏形。今从正反两方面经验出发,尝试在客观史事与诗句义脉之间构筑相对完整的映射关系,将游移的“本事”还原为确凿的“事件”,足证“以本事系年”这一方法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以本事系年”的方法实践,比起前述注释、标点等工作更为繁难。在今后的研究中,亦不妨借助大数据技术,先行做出批量分析处理。比如,通过词性标注、语义分析等方法,批量处理现存大量的疑年诗,以期发现诸如“岳镇”、“盐梅”、“金罍”这样的多义性词汇,最大限度地标识其象征义、隐喻义、双关义,这些词汇存在于某一作品中的数量越多,多义性越丰富,与同主题作品相比,其异质性越明显(67)有关《咏雪赠张籍》的异质性,清人汪师韩《诗学纂闻》中已有体悟:“自谢惠连作《雪赋》,后来咏雪者多骋妍词,独韩文公不然……《咏雪赠张籍》一章,所以讥贬者甚至……岂直为翻案变调耶?”见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37—938页。在数字人文时代,或许能够通过“妍词”与“讥词”的分析比对,将《咏雪赠张籍》这类诗作的异质性更加直观地呈现出来。,该作品存在寓意的可能性就越大,“以本事系年”的可能性即存乎其中。借助机器完成可能性判断,然后再转由人工做出事实性判断,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研究效率、扩大研究规模,而且可能性阶段的语义分析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也势必能够提升事实性判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以上通过韩愈诗歌典故注释、标点体例和系年方法的探讨,可见系统总结历代学者正反两方面经验之重要性:某个词句的标点或注释,时或关系着一类文体的认知,牵涉到古代文学作品整理与研究的一般规律;而一首作品的阐释史中,甚或反映学术思想之异同,涌动着若干方法创新之潜流。凡此,皆当予以系统梳理发掘,并合理运用到新的学术实践之中,庶可为古代文学学术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略尽绵薄。
在推动“两创”的过程中,我们尤当瞩望于不久的将来,以守正出新的立场积极寻求传统学术研究与数字人文的对话契机。近年来,借助数字人文的技术利器,古籍整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化发展,各类作家作品全校全注全评本层出不穷,甚至机器自动标点注释也已成为可能。我们在热情拥抱这一技术红利的同时,也要积极应对与技术红利相伴相生的学术内卷:在这个拥有数千年积淀、百余年充分发展的传统学科范式之下,除了数字技术带来的整理成果的体量性膨胀,究竟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拓展主体性学术创新,实现学术思想、学术方法上的突破?处理好这个问题,既是当代学人对于学术史的一份责任,也是未来数字技术与传统学术实现深度交叉、融合发展的前提所在。结合本文多维度的个案研究,或许可以说,在数字人文的时代浪潮中,尤需注意调适“数字”与“人文”二者关系,尽量避免疏离冷峻的对象化言说和裹挟包办式的单向度建构,当在持守“人文”端的基础上发展“数字”端,以“人文”端的研究经验、规律、方法及其不足之处为依据,为“数字”端开具需求清单,持续推动“数字”与“人文”的交互赋能,以期真正实现人文学术研究的观念迭代与方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