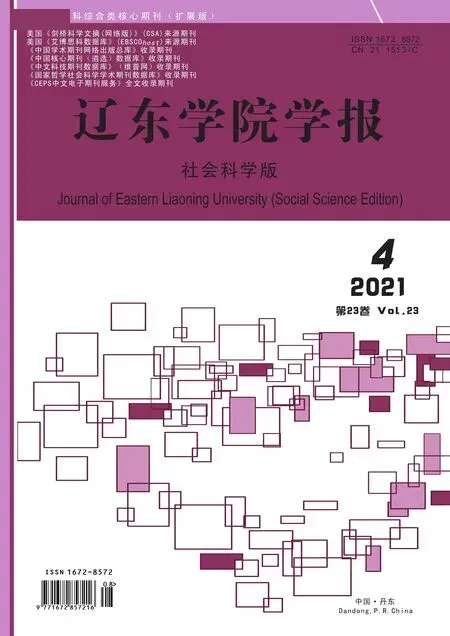北魏女性教育初探
杨启明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她们一般处于从属地位,无法主动参与社会交往活动,也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北魏由于建立于部落体制之上,在母系氏族遗风的影响下,女性社会地位较高,其社会中更有着“专以妇持门户”[1]38的社会风尚,女性也有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关于北魏女性教育问题,相关学者曾有研究,如王永平的《迁洛元魏皇族与士族社会文化史论》[2]391-466,当中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北朝士族“女教”的部分。柏俊才的《民族融合与北魏女性地位及文化修养》[3]1-7,认为北魏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促进了女性文化修养的提升。王晓卫的《论北魏文明太后的族属及所受教育》[4]11-16,认为北魏文明太后称制以前所接受教育内容主要为北方部族文化,称制以后逐渐接受了汉族传统文化,比较深厚的文化素养为她主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前人的成果虽然大都关注到了北魏的民族传统与女性地位及其教育问题,但没有系统的对女性教育进行研究,有鉴于此,笔者试对北魏女性的教育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北魏接受教育的女性群体
以《魏书》为代表的北朝史书大都关注于社会上层,尤其是皇室宗亲以及高级官吏,对于社会中下层记载较少,特别是女性记载更少,而出土的墓志则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通过史书和墓志记载可以发现,北魏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一般受教育者和罪孥受教育者两大类。
(一)一般受教育者
北魏是拓跋部在部落制基础上建立的政权,最初受教育者只集中于男性,但随着汉化的推行,一些来自贵族与豪门的女性也由于自身的地位或家族成员的学识而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北魏孝文帝时的要臣李彪,其女“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5]1399。史载李彪“家世寒微,少孤贫,有大志,笃学不倦”[5]1381,尽管他凭借学识而身居高位,却仍为人所鄙:大中正宋弁虽与之交好,私底下宋弁却“犹以寒地处之”[5]1398;李彪为子求官时,吏部尚书郭祚也以旧第的方式处置。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重视培养儿子,李彪对教育女儿亦尤为看重,这不仅有其女早慧聪令的自身因素,还包含着他对于家族由寒转士的希冀,这当为“此当兴我家”[5]1399之解。

又,高肇的长姐高氏,她的志文言其“兼悦书典,女戒及仪”,可能缘于此,她被宣武帝任命为内侍中[6]153。史载其父高飏于孝文帝初时由高句丽进入北魏,“拜厉威将军、河间子,(飏弟)乘信拜明威将军”[5]1829,孝文帝又娶其女,其女后“生世宗”[5]1829,即宣武帝生母。高家的发迹基础就在于这层关系上,高肇一支又有本非士族而后攀附渤海高氏将自身士族化的嫌疑[8]60-72。于此,高氏接受的教育可能具有较强的目的性——高氏一家本为外来者,仅凭与皇室联姻也不一定就能完全得到士族社会的认可,所以高氏受教或与保证家族成员在才学、言行与风度上与士族对等以取得士族社会的认同有一定关系。
要之,女性教育对李彪、薛辩、高肇等虽然实际门第还不高,但却身居高位甚至具有任官传统的家族而言,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用,是促进门户发展、实现家族士族化转变的重要手段。
此外,北魏皇室宗亲由于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孝文帝汉化改革后亦对女性教育较为重视。“(李)彪亡后,世宗闻其名,召为婕妤,以礼迎引”[5]1399,李彪的女儿在入宫后,为后宫九嫔之一的婕妤,“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5]1399,承担起教育公主的责任。直阁将军冯邕妻元氏出身北魏宗室家庭,她“少好讽诵,颇说诗书”[6]129。上述的高氏也因“椒帏任要,宜须翼辅”而“授内侍中,用委宫掖”[6]153。这些现象大致说明皇室宗亲的女性会进行较为系统的学习。
综上,北魏受教育的女性一般都集中于社会中上层家庭,部分高品阶官吏家族更将女性教育视为兴盛家族的一种渠道。
(二)罪孥受教育者
由于南北朝时长期的战争以及北魏时的严刑峻法,不少女子以罪孥之身被没入宫中[9]92-94。她们当中存在幼年入宫的现象,其中一些女子在宫廷当中接受教育,成绩或学识优异者便得以选拔成为女官,如女尚书王氏讳僧男年仅六岁便由于父亲罔法而被没入宫中,但她“聪令韶朗,故简充学生。惠性敏悟,日诵千言,听受训诂,一闻持晓”[6]124。女尚书冯迎男也年仅五岁就“因乡曲之难,家没奚官”,“年十一,蒙简为宫学生,博达坟典,手不释卷”[6]123。二位女尚书的墓志均告知了宫中教育机构“宫学”的存在。

不过,北魏何时设立宫学这个机构并不清楚,目前已知最早入学的人是上述的王僧男。按墓志她于正光二年(521年)去世,时六十八岁[6]124,推算其应是兴安二年(453年)生人。从句读来看,王氏入学的年龄模棱两可,“时年有六”[6]124仅是她入宫的年龄,是否同时是她入学的年龄,并不清楚。若按六岁的话大约是文成帝太安五年(459年)时入的学,以上文冯氏的十一岁来算,则冯迎男是文成帝和平五年(464年)入学。不论如何,至少可以肯定“宫学”在文成帝执政的中后期便存在了。
宫学的教育观念在于给本是戴罪之身的女性提供经典教育,而在此前的中原历史当中女性接受经典教育本就存在争议(详见后文论述),遑论罪孥出身的宫女,虽然这其中当然会有务实的因素,但是这样的观念依旧超越了性别与身份上的限制。如此观念,应该与出身罪孥而手握权柄的冯太后有关,因而北魏女主政治中对于女官的实际需求是宫学成立的一个要素。
二、北魏女性教育的施教者
通过对受教者身份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受教育者的身份不同,其施教者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家庭教育中的施教者,另一类是宫廷女子教育的施教者。
(一)家庭教育中的施教者
女性家庭教育的施教者,多数情况下应该是由父母来充当,尤其是父亲,如李婕妤便是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文化,形成了较深厚的文化素养。薛伯徽应也是如此。还有一部分女性的家庭由于战乱、父母早逝,而由受过教育的其他家庭成员充当施教者。《魏书》卷九十二《列女传·房爱亲妻崔氏传》载:
清河房爱亲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孙之女。性严明高尚,历览书传,多所闻知。子景伯、景先,崔氏亲授经义,学行修明,并为当世名士。[5]1980
崔氏出身北魏门阀世族之中的清河崔氏家族,其家族家学渊源深厚,崔氏的父亲是崔元孙。据史载,崔亮“父元孙,刘骏尚书郎”,父亲死后,母亲房氏“携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于历城”[5]1476。后因慕容白曜平三齐,崔亮一家被迫入魏,“内徙桑乾,为平齐民”[5]1476。后从兄崔光劝崔亮投靠李冲,并以冲家多书相诱。亮曰:“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5]1476在崔亮与从兄崔光的谈话中可见“弟妹”二字,其中“妹”字当指崔氏。因此,崔氏当初应该是随母亲和兄长崔亮一道投奔崔道固的。崔亮为平齐民时年十岁,由于“居家贫”崔亮不得不以“佣书自业”[5]1476的方式为生,可以想见这与观书于市一起构成了他学习的主要方式。还值得注意的是崔亮的母亲在上述对话里未被提及,可能那时她已经去世了。总之,这般艰难下作为家中女性成员的崔氏不可能像寻常的高门女子那样接受教育,可以推测崔氏应该是借由崔亮那段抄书与观书的时光接触到相关书籍的,而负责施行教育的应该是她的兄长崔亮。
再如文成文明皇后冯氏父“(冯)朗坐事诛,后遂入宫。世祖左昭仪,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5]328。冯氏的姑姑冯昭仪本为北燕公主,由于两国联姻而进入北魏,她有着较好的文化素养,充当起了她的实际教育者,冯太后“自入宫掖,粗学书计”[5]328,应该都源自其姑母冯昭仪的教导。宣武灵皇后胡氏“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5]338。胡太后出身安定胡氏家族,其家族虽然并非汉人世家大族,却也是官宦之家,但是可能因为一些家庭变故,她自小为出家的姑母抚养,并跟随姑姑学习。
(二)宫廷教育的施教者
有关宫廷的教师,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首先,根据李婕妤教公主来看,北魏皇室成员的教育可以由嫔妃充任;其次,皇室女性成员的教育也可由女侍中来担任。
女侍中虽然也是北魏女官中的一员,但她们也与其他女官有着明显的差异。普通女官大都由宫女选拔而来,而女侍中则一般选自皇室宗亲或豪望家族,如献文帝女常山公主、顿丘长公主以及献文帝孙太尉咸阳王元禧女元英、于忠妻王氏、前述宣武帝姨高氏都曾被选为女侍中,她们有着较高的学识。学识则是女侍中选拔的重要标准,如“(于)忠后妻中山王尼须女,微解《诗》《书》,灵太后临朝,引为女侍中”[5]746。另据《魏故仪同三司闾公之夫人乐安郡公主元氏墓志铭》载:
女节茂于公宫,妇道显于邦国。永熙在运,诏除女侍中。倍风闱壸,实谐内教。[6]338-339
可见,女侍中身负对宫内成员进行教育的职责,其教育对象应该就有宫内的公主。
略之,在北魏嫔妃、公主的教育中,首先能够确定的是由嫔妃群体内部的有识者或者女侍中担任施教者。当然,这样的教师主要教授的内容应该是她们所掌握的经典知识,这毕竟是她们得以入宫的重要因素。对于宫学是否负责嫔妃的教育尚不可考,但是其中学习有成的学生是否会教授嫔妃则可以从前代的做法中一窥端倪。在西汉赵飞燕的传记中能见到这么一条记载:
后数月,司隶解光奏言:“臣闻许美人及故中宫史曹宫皆御幸孝成皇帝,产子,子隐不见。……官婢曹晓、道房、张弃,故赵昭仪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宫即晓子女,前属中宫,为学事史,通《诗》,授皇后。”[11]3990
“中宫史”按一般理解,应该是协理皇后文书诏令的女官。学事史的职能则在于教授皇后经典。按记载,似乎能够理解成名为曹宫的女子曾身兼二职,或者二职实为一职。总之,由于两种职位所要求的学识基本一样,因此两者(或一者)对嫔妃进行授课并不为奇。所以像上述王僧男和冯迎男那样的女尚书,可能当过嫔妃的女师,尤其是王僧男,志文中言她负有管理后宫嫔嫱的责任。此外,孝文帝“改定内官”设置的女职中有女史、女贤人、书史[5]321这样的职位,倘若北魏确实贯彻了设置女职的政策,那么就其职名而言,大概也担负教育之事,如《汉书·班婕妤传》中就有“顾女史而问诗”[11]3985一说。关于女工,上述内司杨氏为文绣大监的时候进行过女工技艺的传授,所以北魏时宫中教授女工的任务大概是由文绣太监这样的女官来担任的。另据《北魏王遗女墓志》,北魏宫官中有傅姆一职,与之相关的教务文中仅概言王氏有因“蒋训紫闺,光讽唯阐”的功绩而超升傅姆[6]124。按《礼记·内则》,“姆”的职责是在女性十岁以前传授一些关于四德、女工以及为祭祀准备酒食的知识,并非文书类的教育,即所谓“姆教婉、娩、听从,……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12]870-871;有学者认为先秦时的姆、傅、保均是贵族女子的导师,分别对她进行妇礼教育[13]109。原本两者在职能上有何不同并不明确,总之傅、姆在北魏合为一个女职。此外志文中并未言及王氏具备何种独到的才学,只言其品行优良,“尤辨鼎和”[6]124,故北魏的傅姆至少负责在宫内教授四德,对象可能也是幼女。
宫学的教师缺乏明载,由于宫学经典教育的性质,加之前述前秦苻坚做法的先例,官学的博士官可能会为罪孥们授课。像冯、王二氏那样的宫学生是否可以回到宫学担任教师尚不清楚,墓志撰写的一般原则是褒美,二位女尚书为学生的事既在志文中,那么当然是属于值得赞扬的事,以这样的逻辑而言,若是曾为女师,应该会提及才是。不过考虑到女官当中的某些职位,即包括上述女史等职在内的书女、小书女,或许宫学教师当中也有宫学曾经的学生。另外鉴于内司掌管教务的职责,可能曾担任内司者,如杨氏“以忠谨审密,择典内宗七祏”[6]126,似也参与过宫学的教学活动。
三、女性教育的学习内容
由于女性缺少从政的渠道,持家、孝悌是社会对她们的主要要求,因而北魏时期对于女性的教育内容也多是基于礼仪规范方面。
(一)规范学习的普及性
在目前已知的北魏士族女性墓志中存在着很多符合史书所记《女诫》中“曲从”与“和叔妹”[14]2786-2791规范的描述。
《魏代杨州长史南梁郡太守宜阳子司马景和妻孟氏墓志》载:
奉舅姑以恭孝兴名,接娣姒以谦慈作称。[6]72-73
《北魏李夫人(3)因李氏名讳不止一解,故以“李夫人”代称。墓志》载:
夫人幼而聪悟,长弥谦顺,诸姑尚其恭和,伯姊服其孝敬。自来仪君子,四德渊茂,逮事太夫人,曲尽妇道。[6]103
《魏故穆氏元夫人墓志》载:
及其虔顺舅姑,抚遗接幼,居室弼谐,闺房悦睦,乃有识之所景行,达者之所希羡。[6]218-219
由上可知,《女诫》应是当时女性教育中流行的教材。另外在北魏女性的墓志中还多看到四教、四德、五训、六行、阴教等语,其中四教与四德基
本为《女诫》囊括,六行[15]156和阴教[15]108则见于《周礼》。总之,墓志中记载当时女性学习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些伦理与道德规范,除了女工这样的技巧,大致上包含了当时女性所要学习的一般内容,可以以女学、规范来概括。
除了规范以外,北魏女性也存在学习经典的现象,如第一部分提及的薛伯徽,其墓志载:
夫人讳字伯徽,河东汾阴人。……年七岁,……先考授以礼经,一闻记赏,四辨居质,瞥见必妙。及长,于吉凶礼仪,靡不观综焉。虽班氏闲通,蔡女多识,讵足比也。[6]174
从“及长,于吉凶礼仪,靡不观综焉”来看,此“礼经”不是(或不仅是)前述的道德与伦理规范,而是有礼制之学在其中。促成她学习经典的因素应该就如第一部分分析的那样,与北魏的政治转型、薛氏家族的士族化有关。就受教因素而言,前述李婕妤、高氏二人与薛伯徽应该是同一类型,都与家族的状况分不开。另外学习经典的人群还有上述如王、冯二氏那样的罪孥以及皇室宗亲和一些高门女性。
(二)经典学习中的困境
北魏时期像薛伯徽等人那样能够学习经典,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状况,因为当时女性学习经典还是存在着受压抑的现象。《魏直阁将军辅国将军长乐冯邕之妻元氏墓志》载:

据志文,元氏应该本习“女传”,知列女,但后来逐渐觉得自己好诗书是违背女性规范的表现,所以在学习态度上有了较大的转变。另有于忠妻也是一位经典学习者,史书言其“微解《诗》《书》”[5]746。而冯太后入宫后,即便是由太武帝左昭仪亲自教导,也只是“粗学书计”[5]328。可见,由于北魏时期社会大环境的限制,女性对于经典的学习一般很难深入,即便个别女性存在“博达坟典,手不释卷”[6]123的情况,能够达到“微解”或“粗学”的阶段已属不易。
实际上,对于女子学习经典,东汉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事,被认为是不守规范的,通常都会受到来自家人的压力,尤其是母亲。《后汉书》卷十上《和熹邓皇后传》载:
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14]418
《三国志·魏书》卷五《文昭甄皇后传》注曰:
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数用诸兄笔砚,兄谓后言:“汝当习女工。用书为学,当作女博士邪?”后答言:“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16]159
《晋书》卷六十六《刘聪妻刘氏传》载:
刘聪妻刘氏,名娥,字丽华,伪太保殷女也。幼而聪慧,昼营女工,夜诵书籍,傅母恒止之,娥敦习弥厉。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10]2519
三人的事例均反映了女性学习经典所存在的压力,尤其在邓绥与刘娥身上表现得更直白,然而她们坚持学习经典,最终学有所成。相比之下,作为北魏皇族女性的元氏,本是鲜卑族裔,主客观条件上应对学习经典有更包容的环境,却不如前代的中原女性邓绥、甄氏、刘娥那样坚持,个中因素还有待探讨。
综合前面曾经提到过的李婕妤等人的事例,可以看出北魏女性在经典的学习上因为一些政治性因素本有着一定的空间,而元氏之例则表明经典中本就蕴含着的规范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依旧发挥作用,让女性教育向着规范化、单一化的方向收拢。
结 语
北魏的女性教育在汉化转型的背景下存在着力求规范的现象,但对于那些仍然处于士族化并已经进入权力核心的家族中,他们依然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对女性进行经典教育,期望她们能为门户的发展做出贡献。罪孥受教者能够存在,与北魏女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表现出性别与身份上的突破,她们的存在也是宫中汉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宫中的施教者有因才入宫的女性,她们主要负责教授经典,有些女官则负责教授妇事。关于宫学,虽然囿于史料,这一机构还存在着诸多疑问,但是结合孝文帝的女职改革以及女官们的墓志,它的存在似乎昭示着当时北魏宫廷中已经具备比较系统化的女性教育体系了,就其流变而言,隋唐后宫的六尚系统中的尚仪,应该就是这一体系的发展。对于家庭教育而言,由于南北朝频繁的战争以及北魏的严刑峻法,一般的父母教育时常得不到保障,为了维持门户,崔亮教妹那样的代教局面应该时有发生。
北魏对于古代女性教育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这一特殊性与北魏本身的一些政治因素,例如鲜卑的女政传统、频繁的战争与人口流动以及激进的汉化转型有关。上述所提及的种种事例中,共性在于对女性的经典教育都是为门户的发展做出贡献,不过具体而言,虽然同是发挥这样一种作用,但是动机还是有些不同的:对于李婕妤等并非被迫入北魏的女性而言,基本是单纯地助力门户的发展;而对于崔氏这样被迫由南入北的女性而言,她们本身的地位便因为这一过程一落千丈了,因此她们受教的目的除了维持门户,更重要的是在一种新环境下帮助突显家族甚至个人的价值,一定程度上这能解释为对生存的争取。总之,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北魏的女性教育有着较为宽松的环境,罪孥的教育、对女性学习经典的支持则是宽松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