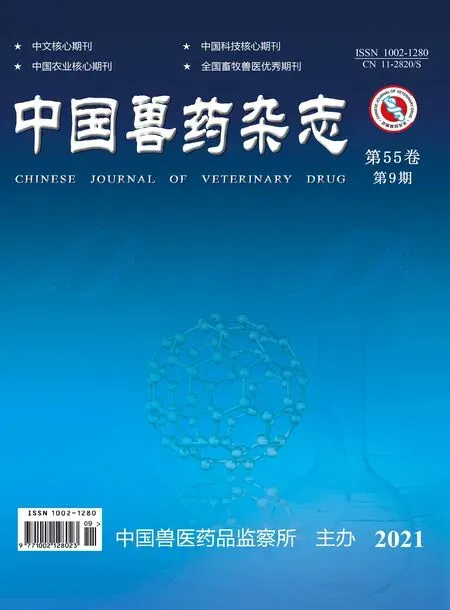产气荚膜梭菌及其公共卫生危害
范学政,李文平,秦玉明,丁家波,杨劲松
(1.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北京100081;2.全国畜牧总站,北京100125)
产气荚膜梭菌(Clostridiumperfringens)是一种革兰氏阳性厌氧菌,能形成孢子,广泛分布于自然环境、动物和人类的肠道[1]以及生肉、脱水汤汁、生蔬菜和香料等食物中[2]。产气荚膜梭菌与人类和多种动物的系统性及肠道疾病有关。在人体内,产气荚膜梭菌可引起气性坏疽[3]、食物中毒[4]、胃肠紊乱[5]、肝肾损害等疾病[6-7]。在动物中,特别是在猪和家禽中,产气荚膜梭菌是坏疽性皮炎[8]、肠毒血症[9]和坏死性肠炎[10-11]的主要病原体。该菌在猪肉类和家禽产品上生长良好,具有较强的温度适应能力,即便在相对较高的温度下(45 ℃左右)也能生长。生肉及其制品易被产气荚膜梭菌营养细胞或孢子污染而引起食源性腹泻。抗菌药是控制产气荚膜梭的主要手段,但随着该菌耐药谱的增加使得人们通过抗菌药对该菌的控制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进一步突显了该菌的公共卫生意义。为全面阐述产气荚膜梭菌的特点和危害,提高大家对其公共卫生意义的认识,本文从产气荚膜梭菌的流行与危害、毒素、耐药基因、食品加工等环节进行了系统梳理。
1 产气荚膜梭菌的流行与危害
产气荚膜梭菌可导致动物猝死症,发病急、病程短、死亡率高。近年来,产气荚膜梭菌流行情况较为严重,鸡、鸭、猪、牛等食源动物受到的危害越来越多。
产气荚膜梭菌对鸡、鸭的危害较为严重。意大利学者Profeta F等检测了167份样本(117份环境样本和50份家禽尸体),其中151份检测到产气荚膜梭菌α毒素基因(阳性率90.4%),31份(20.5%)为G型产气荚膜梭菌(netB基因阳性)[12]。印度东北部放养鸭携带cpb2和cpe基因的A型产气荚膜梭菌和携带cpb2和cpe基因的C型产气荚膜梭菌发生率高达17.5%[13];我国山东4个商品化养鸭场肛肠拭子的产气荚膜梭菌阳性率为41.82%~72.52%,分离株均为A型,其中cpb2基因阳性率为30.85%,cpe基因阳性率为0.5%[14];在北京和山西检测的鸡、猪产气荚膜梭菌携带率分别为23.4%和72.0%,且对庆大霉素和磺胺类药物高水平耐药[15];我国中部地区23.1%(130/562)肉鸡和15.1%(38/252)零售鸡肉样品中存在产气荚膜梭菌,以A型为优势型,3%为cpe基因阳性[16]。据估计,产气荚膜梭菌所致的坏死性肠炎每年给全球家禽业造成的损失在20亿到60亿美元之间[17-18]。
产气荚膜梭菌对猪、牛的危害同样不容忽视。Baker等在早期对美国中西部16个地区农场180头猪直肠拭子进行检测,发现89.8%的仔猪携带产气荚膜梭菌,对猪生产带来较大影响[19]。产气荚膜梭菌能使不同年龄、不同品种的牛发病,且一年四季均有发生,严重危害中国畜牧业的发展[20]。2019年,笔者所在实验室对我国5个省49个奶牛场1000头健康奶牛进行抗体检测,发现α毒素抗体阳性率为57%~90.0%,β毒素抗体阳性率为1.0%~34.0%,ε毒素抗体阳性率为0~23.0%,说明我国规模化牛场普遍存在产气荚膜梭菌污染。近年国内各地发生的产气荚膜梭菌病虽以A、D型为主要病原菌,但B、C、E型产气荚膜梭菌也很普遍[21]。产气荚膜梭菌还是乳房炎的主要病原之一,导致奶牛产奶量下降、奶牛过早淘汰,造成巨大经济损失[22]。
产气荚膜梭菌对羊、骆驼等经济动物也存在一定危害。Nazki S等证实,在克什米尔山谷中死亡的绵羊和山羊中携带A型和D型产气荚膜梭菌很普遍[23]。骆驼养殖场带菌也比较严重,从健康和腹泻单峰骆驼、牧场和牧民的465份样本中共检出262株(56.3%)产气荚膜梭菌,主要是产气荚膜梭菌A型(75.2%)、B型(4.2%)、C型(13.7%)、D型(6.9%)[24]。
产气荚膜梭菌也会引起犬、猫发病。A型产气荚膜梭菌是犬和猫中最常见的型,其中10%~30%分离株呈cpb2基因阳性,cpe基因阳性也很常见[25]。A型产气荚膜梭菌被怀疑与轻度自限性腹泻到迅速致命的出血性坏死性肠炎等疾病有关[26-27]。
关于产气荚膜梭菌引起野生动物肠道疾病的报道非常有限,主要是因为难以获取这些物种的粪便样本,使得对患病和健康动物的研究非常困难。有报告称,A型产气荚膜梭菌在几种野生鸟类中引起的死亡率高,如天鹅、山雀、白鹳、乌鸦、西方蓝知更鸟、鹦鹉和山鹑等[25]。
产气荚膜梭菌食物中毒通常与轻度和短暂的腹泻有关,但偶尔也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并发症,如坏死性肠炎[1],约0.1%的病例死亡[1]。产气荚膜梭菌A型也可引起产气荚膜梭菌肠毒素(CPE)介导的感染性[5]或抗生素相关腹泻[5],通常比传统的食物中毒更为复杂、持续时间更长。这种形式的疾病通常发生在老年人和医院获得性病例,往往与抗生素治疗有关。Blakey对高危早产儿肠道菌群发育规律进行的研究认为,在出生体重较低的早产儿粪便中出现产气荚膜梭菌可能预示死亡危险[28]。
然而,非肠毒素产气荚膜梭菌经常是正常肠道菌群的一部分,常从健康人体的粪便标本中分离出来,因此临床上检测产气荚膜梭菌阳性的同时还需分析相关流行病学因素。产气荚膜梭菌带菌量是一个重要的致病信号,与产气荚膜梭菌相关疾病患者相比,在正常人体粪便中发现的微生物数量通常较低(一般为104~105CFU/g),在某些群体(如老年人群)的健康个体中也可以观察到含量较高的产气荚膜梭菌[1],产气荚膜梭菌腹泻病例的孢子计数可达105CFU/g[5]。
2 产气荚膜梭菌毒素
产气荚膜梭菌的致病性主要取决于它们产生的各种类型细胞外毒素和酶[29]。在20世纪90年代,产气荚膜梭菌根据菌株产生的四种主要毒素(α毒素、β毒素、ε毒素和ι毒素)的组合被分为A至E五种毒素型[30]。2018年,这一分型方案增加了另两种毒素,肠毒素(CPE)和孔形成毒素(NetB),将原CPE和NetB阳性的A型菌株现分别划为F型和G型[31]。以毒素为基础的产气荚膜梭菌分型方法表明,不同产气荚膜梭菌对宿主有不同偏好,并引起特定疾病。例如,B型菌株主要是从患痢疾的绵羊身上分离而来;F型(以前是CPE阳性的A型)菌株与人类食物中毒有关;G型(以前是NetB阳性的A型)菌株包括导致鸡坏死性肠炎的分离株[32]。这些类型的毒素有不同的遗传基因位置,如α毒素基因位于染色体上,另一类型毒素基因通过移动遗传元素,一般大型接合质粒。最近证实,产气荚膜梭菌的七种分型毒素基因的核苷酸序列保守性较好,cpb、cpe、etx和netB基因的核苷酸序列一致性均超过95.0%。iap和ibp基因相对保守,同源性在90.0%左右,绝大多数plc基因的序列一致性超过97.0%[33]。这就为利用这些基因序列进行菌株分型提供了便利。
为了分析产气荚膜梭菌的毒力基因分布,Yuqing Feng等分析了173株分离株的毒力基因,发现有29个与已知毒力基因的核苷酸高度同源(cloSI、cna、colA、cpb、cpb2、cpd、cpe、ebpC、etx、iap、ibp、lam、nagH、nagI、nagJ、nagK、nagL、nanH、nanI、nanJ、netB、netE、netF、netG、pfo、plc、srtC、tpeL、zmp),所有菌株均为α毒素基因(plc)和κ毒素基因(colA)阳性,50%以上的菌株含有α梭菌蛋白酶基因(cloSI)、β毒素基因(cpb)、θ毒素基因(pfo)、透明质酸酶基因(nagH、nagI、nagJ、nagK、nagL)、zmp基因和唾液酸酶基因(nanH、nanI和nanJ)。16株来自犬和马的菌株毒力基因最多,多达18个[33]。
3 产气荚膜梭菌耐药性
由于抗菌药物的大量使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产气荚膜梭菌对四环素、林可霉素和红霉素耐药性显著增加[34],突显了加强对气荚膜梭菌耐药性认识的重要意义[35]。
产气荚膜梭菌耐药性也是感染后治疗失败风险因素之一。四环素耐药质粒是产气荚膜梭菌中最常见的耐药质粒[36],tetA(P)和tetB(P)基因常与四环素耐药相关[37],猪、鸡或牛的分离株对四环素耐药性最高[38-40]。erm(B)或erm(Q)基因常与大环内酯类-林可酰胺-链阳霉素B耐药相关[41-42],erm(Q)基因是目前报道的产气荚膜梭菌最常见的红霉素耐药决定因素。
据报道,从陕西部分地区分离的A型鸡源产气荚膜梭菌对磺胺异噁唑、复方新诺明、多西环素耐药率较高,均在70%以上;对万古霉素、氯霉素、杆菌肽的敏感率均在80%以上;大部分菌株为多重耐药[43]。Saeid等鉴定了屠宰场牛、羊酮体中A型分离株的耐药性,发现牛和羊分离株对四环素耐药性分别达到45.8%和92.3%,显示较高耐药模式[44]。
通过全基因组测序,产气荚膜梭菌含有糖肽类、大环内酯类-林可酰胺-链阳霉素B、β-内酰胺、甲氧苄氨嘧啶、四环素和氨基糖苷类抗菌药耐药基因,还存在编码多肽和多重耐药外排泵的基因[45]。为揭示产气荚膜梭菌基因组中耐药基因(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Gene, ARG)的分布,Yuqing Feng等对173个产气荚膜梭菌全基因组进行解析,通过CARD数据库对已知ARG进行搜索。结果表明,产气荚膜梭菌基因组中只有18个ARG,其中编码多肽抗性因子F的mprF基因是产气荚膜梭菌基因组中最常见的ARG(169/173,97.7%);四环素抗性基因tetA(P)和tetB(P)的携带率也很高,分别占65.3%和35.2%。有趣的是,来自现代谱系(V)的菌株比来自其他谱系的菌株拥有更多的ARG,所有18个ARG都可以在谱系V中找到,而其他4个谱系中只包含3个ARG。从地理上看,来自亚洲和非洲的菌株比来自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菌株含有更多的ARG[33]。
值得注意的是,产气荚膜梭菌与其他细菌之间存在潜在ARG交换。产气荚膜梭菌与55种不同细菌ARG高度同源,有16种链球菌和6种葡萄球菌至少有一个ARG与产气荚膜梭菌共有。erm(B)基因是产气荚膜梭菌和其他细菌中传递最多的耐药基因。这些结果表明,虽然产气荚膜梭菌的ARG数量不算多,但它可以很容易地与其他细菌交换ARG,甚至与系统发育上较远的细菌交换ARG[33]。
质粒在产气荚膜梭菌耐药性产生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种间质粒转移可增强受体菌的致病性和对抗生素的耐受性[46]。对173株分离株中存在的质粒研究发现,超过90.0%(173株中的157株)的基因组中含有质粒序列。鉴定的18个ARG中有9个在质粒中,含有tetA(P)和tetB(P)基因的分离株分别有23.9%和37.7%位于质粒中[33]。
抗菌药相关性腹泻(Antibiotic-Associated Diarrhea, AAD)是医院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住院的老年患者中。通过检测医院腹泻患者粪便样本,证明产气荚膜梭菌也是导致AAD的原因[47]。Asha等人同样证明,产气荚膜梭菌肠毒素是AAD病因之一[48]。
产气荚膜梭菌耐药性也可通过土地施肥(粪肥)在土壤环境中传播[49],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土壤散播的产气荚膜梭菌耐药性导致人类健康和食品安全的问题。有学者研究了产气荚膜梭菌在沼气池和粪肥中的潜在致病性和耐药性。该研究小组对筛选出的157个分离株(其中92个来自粪肥,65个来自沼渣沼液)进行鉴定,粪肥和沼液中鉴定出的毒素类型为A型(78.3%)、G型(16.7%)、C型(3.6%)和D型(1.4%)。值得注意的是,该小组在从所有粪肥和发酵槽收集的样品中发现了多种抗菌药物耐药分离株。其中,12.3%对部分抗菌药高度耐药,特别是对克林霉素和替米考嗪。一些分离株对人用抗菌药,包括万古霉素和亚胺培南等耐药。tetA(P)、tetA(P)-tetB(P)和erm(Q)基因的总阳性率分别为31.9%、34.8%和6.5%。这提示(粪肥)沼渣沼液可能是产气荚膜梭菌多重耐药的载体[50]。
以上研究表明,产气荚膜梭菌耐药基因会给人类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提示在食用动物中使用抗菌药物时需要谨慎。我国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兽用抗菌药综合治理,目前正在推进养殖业减抗、禁抗、产品无抗的行动计划,对于从源头解决耐药性问题有重要作用。
4 产气荚膜梭菌在屠宰零售及食品污染中的传递风险
产气荚膜梭菌食物中毒在世界上非常普遍[1],其引发的食物中毒是发达国家最常见的胃肠道疾病之一[4]。据估计,产气荚膜梭菌是引起美国食源性疾病的第二大常见细菌,每年造成约100万人患病。在英国,产气荚膜梭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细菌性食源性疾病中排第三[2]。这是因为,产气荚膜梭菌分布广泛,在人类和动物的肠道中高度流行。其生长速度快,毒素类型多,易引发疾病。2019年6月27日,因切碎牛肉中含有产气荚膜梭菌,导致参加希腊北部手球锦标赛的47支队伍中有4支队伍的运动员患上肠胃炎[51]。
Grass等通过对美国1998-2010年产气荚膜梭菌引发疫情进行分析发现,在由单一食品引起的疫情中,牛肉是最常见的商品(46%),其次是禽肉(30%)和猪肉(16%)[52]。
屠宰环节产气荚膜梭菌污染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引起重视。Milev等对牛、猪、羊屠宰环节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产气荚膜梭菌在肌肉组织、肠系膜和身体淋巴结及部分实质器官中尽管没有检测到,但粪便中产气荚膜梭菌分离率高达83%~100%[53]。因此,食品中产气荚膜梭菌主要是来自屠宰后胴体的污染,以及食品加工过程中污染所致。雅典学者同样证实,活猪屠宰过程存在较高的污染,且产气荚膜梭菌孢子耐热而较难在加工过程中被杀灭[54]。
Saeid等鉴定了牛羊屠宰场酮体中含有cpe和netB基因的A型菌,表明在牛的90个阳性菌落和羊的70个阳性菌落中,分别有40%和35.7%的疑似菌落被鉴定为A型产气荚膜梭菌[44]。我国对牛屠宰场污染研究较少。马迎晖等对陕西牛屠宰场、排酸和分割车间内各环节样品进行检测,检出产气荚膜梭菌污染阳性率为21.19%,主要为A型菌(81.31%),其次是D型菌(18.69%),但肉样带菌量≤10 CFU/g,远低于致病量106CFU/g[55]。笔者所在实验室对北京某牛屠宰场进行了监测和风险分析,也取得了类似的结果。
陕西关中地区熟肉制品、生鲜肉中产气荚膜梭菌的检出率分别为50.91%和43.14%;鸡肉、猪肉中的检出率分别为53.06%和33.90%[56]。Yu Liu等对泰安市四家主要商店的鸭产品进行监测,发现主要为产气荚膜梭菌(A型)污染[57]。
产气荚膜梭菌的孢子耐高温,因此能在蒸煮过程中存活[1]。产气荚膜梭菌孢子有6%耐过95 ℃ 30 min,而有1.9%耐过100 ℃ 30 min或更长,这使得在香肠中产气荚膜梭菌携带率高达38.9%[54]。
产气荚膜梭菌在12~54 ℃的温度下均可生长,就可能在冷却、再加热和熟食热保存的过程中生长[1]。孢子萌发后,在适当环境中大量繁殖,当摄入大量产肠毒素的产气荚膜梭菌细胞(通常105CFU/g)时,就会发生食物中毒。正是这种生长特性使产气荚膜梭菌成为一种食品安全隐患[58]。在英国,产气荚膜梭菌暴发的主要原因是温度控制不佳和肉类存储不善[2]。
动物内脏在许多国家被允许食用。然而,评估各种可食用内脏的微生物质量和专门调查引起食源性疾病的病原体污染的研究很少。韩国学者调查研究了六种食用内脏的微生物质量,样本来自韩国11个猪屠宰场和8个牛屠宰场。食源性致病菌检出率最高的是沙门氏菌,其次是产气荚膜梭菌(猪内脏和牛内脏分别占11.1%和7.1%)[59]。
有学者还根据流行情况、贮藏温度、贮藏时间和年消费量等因子,对泡菜、奶酪等的产气荚膜梭菌所致食源性疾病的概率进行了风险分析。研究表明,食用泡菜而引发产气荚膜梭菌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可以被认为是非常低的[60];食用奶酪引起产气荚膜梭菌食源性疾病的概率也较低[61]。
鉴于产气荚膜梭菌的公共卫生危害,一些国家食品管理部门建立了生肉产品中产气荚膜梭菌的限量标准,比如韩国对生吃肉类产品实行零容忍政策,美国的标准是热加工后在稳定环节(冷却)中不超过1log[35]。
5 风险控制建议
由于环境中普遍存在产气荚膜梭菌,消除污染可能很难实现。且产气荚膜梭菌是条件致病菌,菌株的毒素类型和耐药基因复杂多样,导致临床上确定其与疾病个例关联性存在挑战。但该菌的致病风险却不能忽视,应尽可能减少致病菌株污染的风险。如果在屠宰场避免生肉污染,后面经妥善处理和加工,尤其是在餐饮加工环节避免交叉污染,爆发该病的风险是可以预防的。
为降低产气荚膜梭菌污染风险提出以下建议。(1)来自养殖环节的产气荚膜梭菌可通过屠宰加工环节进行传播,建议加强养殖过程和屠宰环节的卫生管理以及对产气荚膜梭菌进行必要的监测,主要是监测不同毒素型产气荚膜梭菌流行情况;考虑到我国有食用动物内脏的传统,有必要监测屠宰场动物内脏的微生物数量和食源性致病菌的流行情况。(2)建议制定我国食品中产气荚膜梭菌限量标准。为防止大面积污染,应制定合理的卫生标准,提高肉食品加工者和经营者对产气荚膜梭菌食物中毒的认识,以确保肉食品加工和经营环节的卫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