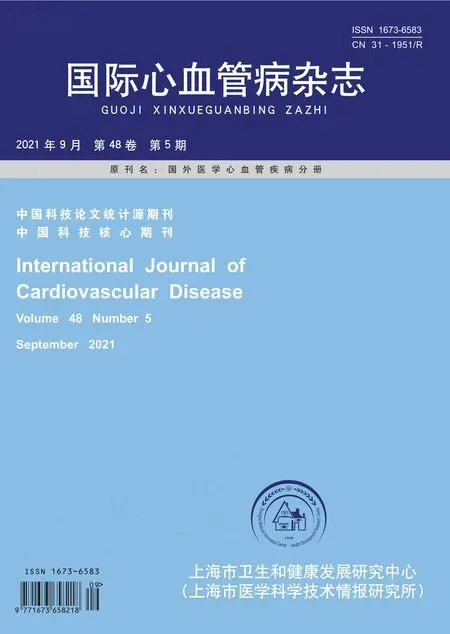预测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后支架内再狭窄的新型生物标志物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是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的重要方法,尽管具有抗增殖功能的第二代药物洗脱支架(DES)已在临床上大规模使用,但是支架内再狭窄(ISR)仍然是PCI治疗晚期失败的主要原因[1]。置入第二代DES后,10年内靶病变血运重建(TLR)的发生率约为20%[2]。ISR指在支架段或其边缘(与支架距离5 mm以内)再次出现管腔直径狭窄>50%,诊断的金标准是冠状动脉造影,狭窄程度由2名或以上有经验的介入医师判断[3]。冠状动脉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TA)是最好的诊断ISR的无创手段,但厚柱支架、分叉处支架显影效果较差[4]。
生物标志物是可以指示正常的生物学过程、致病过程或指导治疗的生化指标,有重要的科研及临床意义。联合使用生物标志物有望提高ISR诊断的准确性。本文介绍对ISR具有早期诊断潜力的生物标志物。
1 代谢组学生物标志物
近年来代谢组学发展迅速,代谢组学可以对某一样品(如血样)中相对分子量<1 000的小分子代谢产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判断生物体的病理生理状态。这些小分子代谢物可能整合了近端遗传、表观遗传、转录组和环境影响等信息。在人体内,鞘脂和磷脂脂质激活途径不同,使用富集分析显示,包括4种磷脂、1种鞘磷脂和1种神经酰胺在内的6种代谢物的水平可以用来预测ISR,为识别支架置入6个月后可能发生ISR的患者提供依据。6种代谢物水平预测ISR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94,预测ISR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1%和89%[5]。一项纳入400例PCI术后患者的临床试验,在PCI术后1个月对患者血浆进行代谢组学分析,发现并验证了一组血浆代谢物(由6种代谢产物组成)有望用于诊断ISR。与对照组相比,该组生物标志物诊断的敏感度为91%,特异度为90%,独立诊断的准确度为90%,提示与常规影像手段相比,代谢组学可提供更早期的诊断信息[6]。另一项回顾性研究中纳入ISR患者50例,正常对照者50例,多元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高密度脂蛋白相关1磷酸鞘氨醇(HDL-S1P)是ISR的独立预测因子(OR=0.846,95%CI:0.767~0.932,P=0.001),最佳截断值为30.37 ng/mL,敏感度为90%,特异度为52%[7]。
2 非编码RNA的生物标志物
非编码RNA(ncRNA)是不翻译为蛋白质的RNA,直接在RNA水平上行使生物学功能,可用于预测ISR。其中微小RNA(miRNA)是能够调节大量基因表达的短链RNA,已被建议作为多种心血管疾病的生物标志物[8]。一项纳入42例患者的研究发现,首次出现冠状动脉单支病变的患者行PCI治疗1年后,发生ISR的患者血清miR-17水平显著升高,而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物-1(TIMP-1)和白细胞介素(IL)-6水平则显著降低。TIMP-1和IL-6的水平随着miR-17的升高而降低,这表明miRNA-17可反映血管内炎性反应水平,预测ISR[9]。多项观察性研究显示,不同类型的miRNA可用于预测ISR,见表1。长链非编码RNA(lncRNA)是长度大于200个核苷酸的非编码RNA,由RNA聚合酶Ⅱ转录形成。因其可反映多种病理过程,已有研究将其作为ISR潜在的生物标志物[10]。在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中,linc-POU3F3可通过POU3F3/miR-449a/Krüppel样因子4(KLF4)途径促进VSMC的表型转化,促进VSMC的增殖和迁移,通过检测miR-449a水平可以预测ISR的发生[11]。一项纳入444例患者的研究中,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浆lncRNA抗体单独作为ISR的预测因子时,OR=2.21(95%CI:1.68~2.92,P<0.001),提示lncRNA抗体可预测ISR预后[12]。

表1 非编码RNA作为ISR生物标志物的临床研究
3 血细胞相关参数
血细胞相关参数可反映炎性反应和血小板活化过程,预测DES置入后ISR的发生。研究发现,红细胞分布宽度(RDW)与许多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预后有关[16]。在一项纳入261例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根据第二次造影结果将患者分为非ISR组(n=143)和ISR组(n=118),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术前RDW可独立预测ISR的发生[17]。在另一项纳入281例不稳定心绞痛术后患者(ISR组47例、非ISR组234例)的研究中,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RDW是ISR发生的独立危险因子,OR=1.5(95%CI:1.32~1.76)[18]。由于炎性反应可使RDW升高,因此RDW可能是通过侧面反映炎性反应严重程度预测ISR。单核细胞计数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比值(MHR)可以预测裸金属支架(BMS)置入后发生的ISR。一项纳入468例心绞痛患者的研究在成功置入BMS后随访14个月,发现与非ISR组相比,ISR组的MHR显著升高,(OR=3.64,95%CI:2.45~4.84),提示MHR可作为BMS置入后ISR的独立预测因子[19]。
4 炎性反应相关生物标志物
炎性反应在PCI术后ISR形成中的作用已被证实[20]。支架或球囊可造成血管内皮机械损伤,引起局部炎性反应,促使白细胞募集,引发炎性级联反应,最终引起ISR。检测炎性反应相关指标,可以提前预测ISR的发生[21]。白细胞、树突状细胞(DC)等表达的Toll样受体(TLR)是经典的天然免疫模式识别受体,在ISR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一项纳入107例患者的临床试验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将患者分为初发组(第一次接受DES置入,n=38)、非ISR组(置入DES后未发生ISR,n=36)、ISR组(置入DES后发生ISR,n=33),结果发现ISR组TLR3和TLR4水平明显高于非ISR组,甚至高于初发组,提示TLR3和TLR4有望成为预测DES发生ISR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22]。多项前瞻性研究表明,炎性反应相关生物标志物与术后ISR的发生关系密切。一项纳入198例PCI术后患者的回顾性临床试验根据第二次冠脉造影结果将患者分为再狭窄组和非再狭窄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肝素结合性表皮生长因子(HB-EGF,OR=2.185,95%CI:1.103~4.014)和IL-18(OR=2.079,95%CI:1.208~4.027)是再狭窄的危险因素[23]。一项纳入100例研究对象(ISR组50例、非ISR组50例)的临床研究根据内皮细胞特异性分子-1(ESM-1)水平的四分位数分为4组,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4组间ESM-1水平是ISR的独立预测因子(OR=8.65,95%CI:3.56~20.94)[24]。此外,将反映炎性反应的S100钙结合蛋白A12(S100A12)纳入已建立的ISR风险预测模型中,该模型的预测能力可显着提高[25]。尽管血管内首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与PCI术后ISR触发因素不同,前者为内皮细胞功能失调,后者为血管损伤、内皮剥脱,但是两者之后的发展过程有相似之处[26]。基于炎性反应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中的作用,反映炎性反应进程的因子如趋化因子等,也具有成为ISR生物标志物的潜力。
5 其他
ISR的发生涉及多种机制,因此联合反映不同途径ISR进程的生化指标可提高临床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凝血酶诱导的血小板纤维蛋白凝集强度(TIP-FCS)因反映术后血栓而可预测ISR。在一项纳入170例研究对象的临床试验中,ISR组(n=70)的TIP-FCS明显高于非ISR组,该指标具有预测ISR患者血栓前状态的潜力[27]。非对称二甲基精氨酸(ADMA)能够反映ISR中的新动脉粥样硬化和钙化的进展。在一项纳入45例ISR患者的研究中,经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证实,有新动脉粥样硬化和支架内钙化的患者ADMA水平升高明显。使用多变量分析显示血浆ADMA水平是新动脉粥样硬化(P=0.008)和支架内钙化(P<0.001)的重要预测指标,可预测ISR中新动脉粥样硬化与钙化进展[28]。血清中基质金属蛋白酶(MMP)、髓过氧化物酶(MPO)水平的升高可预测BMS植入后ISR发生。Pleva等[29]对222例患者(ISR组111例、非ISR组111例)的血清进行检测,使用多变量回归分析后发现,ISR组MMP-3(OR=1.013,95%CI:1.004~1.023)、MMP-9(OR=1.014,95%CI:1.008~1.020)、MPO(OR=1.003,95%CI:1.001~1.005)明显升高,具有预测BMS后ISR的潜力[29]。
反映氧化应激的生物标志物也可以用于预测ISR。在对283例发生ISR的老年患者(≥80岁)进行血清学分析后发现,超氧化物歧化酶3(SOD3)、一氧化氮(NO)水平明显降低,丙二醛(MDA)、丙烯醛(ACR)水平明显升高,这些生物标志物可以反映ISR晚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这提示反映氧化应激的生物标志物有预测老年患者术后预后的潜力[30]。
6 展望
新型生物标志物预测PCI术后发生ISR的真实性及有效性尚需要循证学证据支持。代谢组学指标特异性较强,但花费较高;ncRNA种类繁多,如何选择仍需慎重考虑;血细胞参数、炎性因子指标廉价易得,但特异性略差;反映氧化应激等的指标预测ISR不够全面,仍有较大改善空间。如何从众多的新型生物标志物中找到最佳选择对加快临床转化至关重要,未来新型生物标志物将有望发挥诊断ISR的早期无创性优势,进一步完善ISR诊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