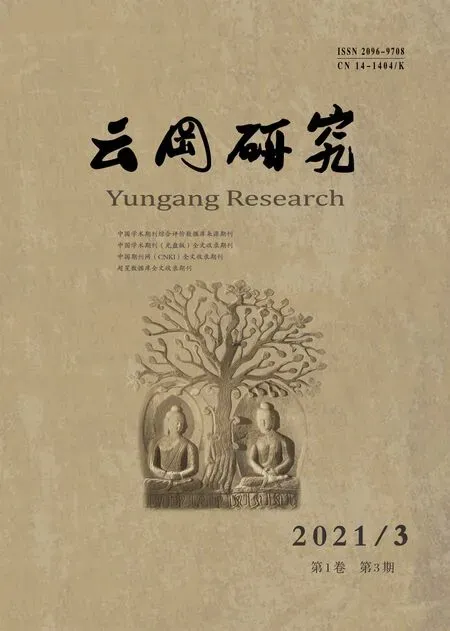辽金时期云冈石窟的修造与保护
古 艳
(云冈研究院,山西大同037004)
辽金二朝是大同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云州(大同)从辽天显十二年(937年)正式归入契丹版图,到辽保大二年(1122年)四月为金军所取,在辽国统治下共计186年。自金收国元年(1115年)至天兴三年(1234年)前后120年间,由女真人创建的金王朝经过一系列闪电式扩张,划淮而治,拥有了北方半壁江山。大同从金天辅六年(1122年)被金军攻取,到金贞祐三年(1215年)被蒙古军趁乱所夺,期间一直作为金朝的西京共计93年。由此知道,作为辽金西京的大同府,已然经过了278年的历史过程。在西京鼎盛时期,大同府及周边州县人口一直呈增长态势。这里资源富集、物产丰盛;城邑壮丽、治所严谨;注重国学、人才辈出;佛教盛行、塔寺林立,是一座综合实力强劲的大型古代都市。辽、金二朝大同的佛教文化极为繁荣,仅保存至今可见的佛寺,就有古城内的大华严寺、善化寺,还有城郊外的佛字湾摩崖石刻、观音堂等。与此同时,对于创建于北魏时期的大型石窟寺院云冈石窟,更加关注和重视。既有文字铭刻记事和文献记录,也有塑造修理雕像及其在云冈建设修缮的活动遗迹。
一、文字记载
不外乎两种形态,一是洞窟内的铭刻文字,二是文献记述。
(一)铭刻文字
在云冈洞窟中为数不多的历朝各代修造工程的文字雕刻记录中,有一条被证明是来自于辽代的铭记,即在第13窟南壁的《张间□妻等修像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云冈进行考古学调查的日本学者于1952年至1956年出版16卷本《云冈石窟》,其第二卷(第五洞)发表的《云冈金石录》中,记录了这条铭刻文字,曰:
□□□□□□□彳?马」□张?间?□妻寿?□□」□□征?□□□□□□」契丹□□□□郭?四?」□□耶律□□□教?征?」妻□□□□□」郭?署传?彳?□□妻□氏」张通?判?官行□□□□」□□□妻张氏□」□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戊?午?十二月一日建,六月三十日毕。
鉴于此记中“契丹”“耶律”“戊午”等字样,确定其为辽代刻字大约无误,具体时间应该是辽道宗太康四年(1078年)。“一千八百七十六尊”,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无论是修补完善,还是新刻塑造,都具有相当规模。
(二)文献记述
早在1947年,学生时期的宿白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之碑文,并于1956年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一文。[1]碑文显示,此文是“皇统七年(1147年)夷门曹衍应当时传菩萨戒提点西京大石窟寺沙门禀慧的邀请撰并书的。”[2]文中所涉辽金时期对石窟的修造保护至少有以下五条:
一是,“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示,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教,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
二是,“辽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天庆十年赐大字额,咸熙五年禁山樵牧,又差军巡守,寿昌五年委转运使提点,清宁六年又委刘转运监修。”
三是,“天会……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
四是,“先是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
五是,“皇统初,缁白命议,以为欲图修复,须仗当仁,乃请惠公法师住持。师既驻锡,即为化缘,富者乐施其财,贫者愿输其力,于是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香厨、客次之纲常住寺位,凡三十楹,轮奂一新;又创石垣五百余步,屋之以瓦二百余楹,皇统三年二月起工,六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
以上各条所记辽金在云冈石窟的工程建设,均投资巨大而规模不小。虽因历史悠久,这些工程建设项目不能一一“对号入座”,但在多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及其对洞窟内造像风格的考察中,依旧可以见到不少“蛛丝马迹”。
二、考古发现
以现代技术对云冈石窟之窟前和山顶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始于20世纪30年代。近90年的工作证实,辽金时期的建设维修遗迹遍布云冈石窟各处,与相关文字记载基本相符。
新中国成立前的考古发现有两则与辽代云冈有关。一则是,1933年,在建设“云冈别墅”时在第5窟前面西侧发现辽代石柱础;[2]二则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学者在第8、9、11、12和第13窟外和昙曜五窟前的地面下,掘出辽代铺地方砖、沟纹砖、兽面瓦当、迦陵频伽瓦当,指纹版瓦当和陶片等。又在东部窟区和中部窟区之间的龙王庙旧址掘出辽代兽面瓦当、指纹版瓦当、瓷片和残铁器等。[3]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考古发掘主要有4次:一是1972年至1974年五华洞窟前遗址和崖面遗迹清理;二是1987年龙王庙沟石窟群窟前考古发掘;三是1992至1993年的大规模窟前考古发掘;四是2010至2012年的山顶考古发掘。这些考古活动,全面揭示了云冈石窟古代各重要历史时期的修建遗迹,其中辽金遗迹较为普遍多见。
首先是五华洞(第9—13窟)窟前遗址和崖面的清理。[4][5]清理中发现,在第9、10窟窟前发掘区域东西长30m,南北宽13m的范围内,辽金铺砖覆盖了东西长约24.6m,南北宽11m,面积达270.6㎡。在第9、10窟前室窟顶上方平台新发现了6组排列有序的方形梁槽,与1938年日本人发现过的一排紧靠列柱的柱础(穴)遗迹对应,柱础(穴)与崖壁平行排列,规格、大小不等,柱础顶面与铺地方砖齐平,似为一座5开间窟檐建筑遗迹,断代为辽金。
其次是龙王庙沟石窟群窟前考古发掘。[6]这次考古发掘清理出厅堂、蓄水池及僧房基址等3处遗址。发现了辽代方砖,以及出土的瓦当、板瓦等建筑构件,还发现了白釉碗、白釉盘、瓷枕、黑釉盘、鸡腿瓶、盏托、澄泥砚等生活用品,并发现了“太平通宝”“天禧通宝”“景德元宝”等辽钱币。从以上建筑构件的形制以及出土的货币、古砚等推断,龙王庙沟建筑其使用时代为辽。
第三是窟前考古发掘。[7]此次大规模考古活动,对云冈石窟前的地面遗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4000余㎡,清理出石砌河坝1道,建筑遗址4处,出土各类遗物2000余件。这次发掘初步探明云冈石窟窟前建筑遗址发展脉络,为研究石窟历史状况及《金碑》的“十寺”记载等问题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石窟寺窟前遗址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
考古活动中所发现的辽金遗迹至少有3处:一在东部窟区的第3窟辽金文化层中发现东西向柱基夯土遗迹,间距在5m左右,根据窟前情形推测是一处面阔9间的辽金建筑遗迹;二在第11窟至第13窟及无名窟(现编号第13-4窟)的窟前沟纹砖地面上发现有大柱穴及方形柱础,由南至北排列3排,呈东西向构成一处面阔9间的建筑遗址。这些柱穴及柱础可与北壁窟壁上的小方形梁孔相对应,应是辽金时期的木构建筑遗迹;三在第9与第10窟的窟前发现的沟纹砖地面与方形柱础的建筑遗迹,由北向南前后三列呈东西向排列,共有6个方形柱穴(础),构成一个面阔5间的辽金时期建筑遗迹。此外,在这次大规模窟前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瓷器主要为辽金时期遗物,有黑釉和酱釉的大缸和瓶、小盏以及胎有洁白的白瓷碗、盘、碟等残件。
第四是第5、6窟上方山顶的考古发掘。[8]此次发掘出的古代遗迹,既有北魏的,也有辽金的,还有明清的。其中辽金遗迹有:北魏至辽金塔基1座(图1),辽金铸造场1处,熔铁炉30个,水井1口,石墙1处,灰坑116个。

图1 第5、6窟山顶塔基遗址(摄影:张海雁)
辽金塔基围绕北魏塔基扩建而成,塔基下宽上窄,平面呈八边形,塔基间填砂岩片石和石块等,有踏道,位于塔基北部,西南至东北走向,上窄下宽,塔基边缘和踏道系用砂岩石块垒砌。
辽金铸造场地位于发掘区中南部偏东(塔基北部),包括1座铸造井台和环绕井台的30座熔铁炉坑遗迹。铸造井台遗迹由方形井、圆形工作台、通气道和工作通道共同组成。
出土的遗物中,有辽金时期的兽面纹瓦当、板瓦、檐头板瓦、陶罐、瓷碗、瓷罐等,其中1件绿釉碗底的圈足内刻“枕天、长寺”,另1件陶罐内底亦压印有文字。
在云冈第5、6窟上方山顶的佛教寺院遗址中,出土遗迹遗物的时代主要是北魏和辽金。其中,塔基最为重要,是北魏至辽金寺院佛塔演变的实例。铸造场地应与辽金寺院建设有关,初步推测其生产的铸件应是提供给佛教寺院使用的铁钟类宗教器物。
三、洞窟造像
主要是辽代的修整与塑造。上述第13窟的铭刻文字中所谓“一千八百七十六尊”,数量堪为不小,但并未说明是修补完善,还是新刻塑造。就现存遗迹观察,知道辽时修整云冈造像,有的在剥蚀的石像外面泥塑,有的就空白石壁上补刻。[9]其中第11窟中心塔柱南面下层立佛两侧的2身立姿菩萨和第13窟南壁窟门上方七立佛中东侧的两尊立佛之头像最为明显。
第11窟中心塔柱南面下层的2位胁侍菩萨面相丰满、身材修长、亭亭玉立(图2)。无论是造像风格,还是人物所着衣饰,均与云冈北魏人物造像有着极大的不同。结合大同市内下华严寺辽代塑像特征和考校云冈石窟铭记即文献记载中有关辽代在云冈石窟曾经大兴土木、建造塔寺等记述,学术界普遍认为,此2像应是辽代时期在云冈所行工程之一。

图2 第11窟中心塔柱南面下层主尊两侧的立菩萨(摄影:张海雁)
我们在2012年洞窟调查时发现,七立佛中的东侧2尊佛像的面容与其它5尊佛完全不同,属于两种造像风格(图3)。其头顶肉髻略显扁平,头面宽大,额头稍窄,眼皮鼓垂,鼻形浑圆,耳廓肉圆,下颌纹明显等,特别是严肃的表情,与北魏人物造像均略带微笑的喜悦之表情差异明显,却与大同市内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辽代塑像风格相似。近距离观察发现,此两尊佛像头后与壁面连接处均有缝隙,说明是后来的补塑加装。因此,比较辽代佛教塑像艺术风格,我们认为七立佛中的东侧2尊佛头大致为辽代制作安装。如此结论不误,则二佛头已“补位”将近千年而坚固无损。其给我们的提示是,石质粘接方面尽管今天有很多办法,但如何按照辽代工艺,千年牢固且无任何副作用,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并向古人学习的重要课题。

图3 第13窟南壁窟门上方七佛之东侧两尊佛像面部(摄影:张海雁)
四、云冈十寺和改拨河道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中提到的“云冈十寺”以及“改拨河道”之事,当可在洞窟考察与考古发掘中发现其端倪。
(一)关于十寺
又称云冈十名,即指云冈石窟群在历史上曾经有过10个并列的寺院名称。宿白先生认为,《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中所列辽金时期对云冈的修整,可与数次考古发掘发现的具有辽代特征的建筑遗物相互印证,说明辽代在云冈的建筑工程规模十分巨大。[2]因而推测“十名之说,约自辽代开始”。但因辽末灵岩曾遭焚劫,所谓“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而后不久,在金初的皇统年间即又恢复,所谓“皇统初,……乃请惠公法师住持。……重修灵岩大阁九楹,……凡三十楹,轮奂一新……皇统三年二月起工,六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关于云冈十寺的位置,宿白先生认为,十寺的情况“大约和现存清初所建后接第5、6两窟的石佛古寺相同”,[9]并列举现存石窟群第1窟至20窟崖壁上的梁孔遗迹及其洞窟前的遗迹和遗物推断认为,这些应是与十寺有密切关系的辽代建筑遗迹。同时,宿白先生又指出,“十寺的位置,如果不与洞窟连接起来考虑,那么就要调查一下石窟附近地区是否还有其他相当于辽代的寺院遗迹”。[1]如此,在上述第5、6窟上方山顶的考古发掘中,就发现了一处北魏至辽金的大型塔基遗迹,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云冈十寺”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二)关于改拨河道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所记,[1]“天会……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当是女真之金代进行的一项大型古代石窟保护举措。元帅府的掌门人是金代西路军主帅宗翰。宗翰在大同建立西朝廷后,对广大汉族人民施以奴隶式的压迫和掠夺,却下令以“三千人改拨河道”使云冈洞窟不受“侵啮”,亦十分难能可贵。
在1992—1993年云冈石窟窟前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东西向大型石砌河坝(图4),距离洞窟仅为25m左右,在雨季河水较大时对石窟的威胁可想而知。经1000多年前的改拨河道,现十里河道与石窟最近的距离也在300m以外,①测量数据显示,从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昙曜五窟前的北魏河坝遗址向南至现十里河河道中心的距离是399.52m。在数百近千年的历史变迁中,石窟寺前的人员聚集(寺院以及村镇范围的不断过大)和工程建设(如明代云冈下堡的建设)都在不停地变动推进中。这些人类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使石窟前的面积不断扩大而使武州川河道不断向南推去。由此,现在石窟群与南向河道的距离,并不能代表是金代“改拨河道”所形成的距离。彻底杜绝了河水对石窟的正面侵蚀。

图4 昙曜五窟前发现的北魏河坝遗址(摄影:赵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