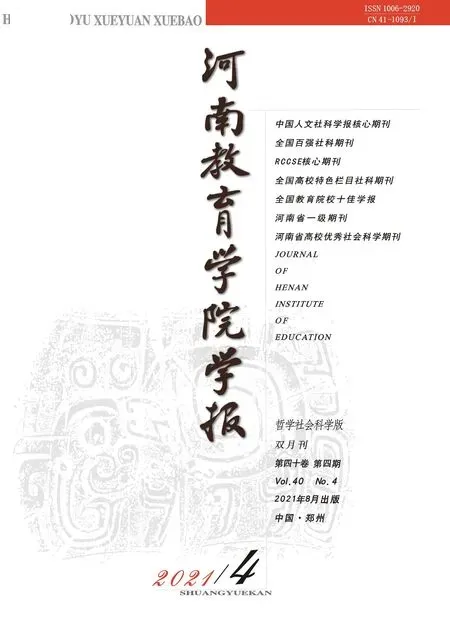试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以杨宪益和霍克斯英译《咏白海棠》为例
程蒙蒙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内涵
生态翻译学从生态学的角度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认为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和选择的活动。[1]76译者要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做出同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其中多维度包括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交际维度。翻译生态环境是指作者、作品、译者、译文、出版商、译入语读者之间动态的、互联互动的整体。[2]胡庚申教授指出,翻译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原文为主导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也可理解为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第二个阶段是以译者为主导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由此可见,译者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翻译过程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和制约,另一方面译者作为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进行选择和支配。[2]翻译过程的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适应”与“选择”的翻译过程
二、《咏白海棠》原作及两个英译本简介
咏白海棠(一)
薛宝钗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
欲偿白帝凭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3]491-492
杨宪益译文:
For the sake of the flowers the door is closed by day,
As I go to water the pots with moss overgrown;
Immaculate its shadow on autumn steps,
Pure as snow and ice its spirit by dewy stone.
Only true whiteness dazzles with its brightness;
Can so much sadness leave a flawless jade?
Its purity rewards the god of autumn,
Speechless and chaste it stays as sunbeam fade.[4]539
霍克斯译文:
Guard the sweet scent behind closed courtyard door,
And with prompt watering dew the mossy pot!
The carmine hue their summer sisters wore
These snowy autumn blossoms envy not—
For beauty in plain whiteness best appears,
And only in white jade is found no spot.
Chaste,lovely flowers!Silent,they seem to pray
To autumn’s White God at the close of day.[5]416
咏白海棠(二)
林黛玉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3]492-493
杨宪益译文:
Half-rolled the bamboo blind,half-closed the door;
Crushed ice serves as mould for jade pots.
Some whiteness from the pear-blossom is stolen,
Some of its spirit winter-plum allots.
The goddess of the moon sews a white gown,
The maid’s weeping in autumn chamber never ends;
Silently,shyly,with never a word of complaint,
She reclines in the autumn breeze as night descends.[4]540
霍克斯译文:
Beside the half-raised blind,the half-closed door,
Crushed ice for earth and white jade for the pot,
Three parts of whiteness from the pear-tree stolen,
One part from plum for scent(which pear has not)—
Moon-maidens stitches them with white silken thread,
And virgins’tears the new-made flowers did spot,
Which now,like bashful maids that no word say,
Lean languid on the breeze at close of day.[5]417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探春提议,宝玉和众姐妹一拍即合成立诗社,《咏白海棠》乃开社之作,共得诗六首。众人皆推黛玉的诗为上,李纨则讲,“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3]493,宝玉则执意“蘅潇二首还要斟酌”[3]493,于此暂且不论诗文高下,读者们可以透过作品了解到二位不同的性情和命运。
杨宪益、戴乃迭是一对堪称中西合璧的翻译家伉俪,在二位共同生活的半个多世纪,他们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红楼梦》的英译工作,最后于1974年完成,并于1978~1980年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此译本在国内外皆获得好评,并有广泛的影响。霍克斯是英国的汉学家。1970年,在中国同事吴世昌的鼓励下,霍克斯放弃了牛津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全身心投入《红楼梦》的翻译工作。霍克斯用了十年翻译前八十回,分别于1973年、1977年、1980年出版了英文版分册,最后四十回由其女婿闵福德完成。
三、《咏白海棠》译文多维度适应性选择
(一)语言维度的适应性选择
在翻译过程中,语言、文化、交际三维的适应性选择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当然,语言层面的适应性选择是译者首先需要考虑的。
翻译这两首诗除了对语义和意境的考量,最大的难点在于限韵和限字。从宝钗诗的翻译来看,杨译本重在将诗逐字逐句直译出来,对韵律并不严格考究;霍译本则巧妙而又自然地保留了原诗的韵脚。原诗中限了“门盆魂痕昏”韵,霍克斯分别将其译为door(门)、pot(盆)、not(魂)、spot(痕)、pray(祷告)、day(昏),达到了80%的精确度,实为翻译史上的奇迹。[6]181文学作品的翻译就像植物的移植一样,需要对周围的环境经过反复适应和调整才能存活下来。故就对原诗限韵的翻译处理而言,霍译本更胜一筹。在跨语言跨文化的前提下,译入语读者读此译本仍能够从语言层面领略到宝钗的才气和曹雪芹的匠心独运。
黛玉诗中第一联第二句,想象力丰富,语言干脆利落,大刀阔斧,一气呵成。杨译本回译为中文即“将碾碎的冰作为玉盆中的土壤”,较原诗逊色不少,语言显得拖沓冗长。霍译本则几乎等同于原诗,ice for earth和white jade for the pot还原了原诗中的排比句式,且crushed是crush一词的过去式,在诗句中充当谓语动词,与原诗中“碾”字相呼应。杨译本则用crushed作为形容词修饰ice,即“碎冰”,未能体现原诗形象生动的语言特点。
(二)交际维度的适应性选择
杨译本倾向于直译,如宝钗诗中第二联,杨译本选择将原诗中秋阶、露砌、冰雪魂等意象都展现出来。这种直译的方法保留了古诗词中的文化精髓,有助于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杨译本对于想要深层次了解和学习古诗词的译入语读者来说是很好的选择。
霍译本更倾向于意译,其中宝钗诗第二联回译为中文即“她们夏天姊妹的胭脂红,这些雪白的秋花并不嫉妒”,霍克斯抓住“胭脂”这一核心词语,并将这一词的内涵解析和延展,同时摒弃了原诗中秋阶、露砌、冰雪魂等这些颇具中国古诗词特色的意象。译者就是考虑到这些意象对于中国古诗词了解甚微的译入语读者来讲稍显晦涩。虽然霍克斯没有将原诗逐字直译出来,但是他成功地将原诗的精髓译出。原诗要表达的恰恰就是白海棠如洗掉涂抹的胭脂而现出本色,这正是宝钗钟爱淡雅、藏愚守拙、不爱争风的真实写照。霍克斯可谓“嗅觉”灵敏,抓住了原诗所要表达的核心。杨译本的直译“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却漏掉了诗句中的核心词——“胭脂”,正是这一词语传神地将宝钗恬淡不与争风的脾性刻画出来。就此而言,杨译本更注重形似,霍译本更注重神似。翻译,应着力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中文和英文在语言表达方面有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二者非要有所取舍,那定要将神似放在首位。当然,将神似放于首位并不是说形似就不重要,这样做主要是考虑西方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古诗词文化,从而更好地达到交际目的。
(三)文化维度的适应性选择
人们都是在特定的文化中成长,时刻都接受着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翻译并非只是简单地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而是要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因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考虑文化因素。原文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译入语读者不一定能够接受。
宝钗诗第二联,意欲表达的是白海棠不涂脂粉的淡雅,霍克斯巧妙地补译出their summer sisters wore(夏天姊妹所拥有的胭脂红),简直妙绝。这样适当的补译,有利于开拓诗的意境。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学有悲秋的情结,而英诗则更注重夏季和冬季的意象[6]191,霍克斯的处理虽然有“抹杀”中华文化之嫌,但是很好地适应了译入语文化,有助于译入语读者接受。
黛玉诗中第二联,杨译本将“三分”“一缕”均处理为some。的确,这两个数字并非实指,但some一词于此未免显得过于笼统。虽然原诗中的数字也有其表达的模糊性,但在诗词中这看似平淡无奇的数字,一旦经过诗人的巧妙构思,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美学效果和艺术魅力。此处“三分白”与“一缕魂”前后相呼应,数词“三”和“一”相对应,量词“分”和“缕”相对应,中心词“白”和“魂”相对应,前后对仗工整,简洁凝练。杨译本用some一词简要带过,未将原诗中这种对称之美译出,表达不够精准。霍译本则将其译为three parts of whiteness,one part from plum scent,与原诗表达极为接近,对仗工整的表达方式能让读者更清晰地领会到诗人笔下白海棠的姿色和神韵:梨花的洁白高雅以及梅花的香魂傲骨。另外,针对诗中的“魂”字,杨译本将其译为spirit。从字面意思看,spirit一词看似等同于原诗中“魂”一字,然译入语读者会比较费解,何为梅花的精神?梅花原产于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省份居多,在西方国家中极为少见,即使有也是后来经过移植栽培引进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独自凌寒开放,傲霜斗雪,冰肌玉骨,芬芳依然,象征着一种刚毅、坚贞的品质。此外,梅花不与百花争春,领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象征着一种不趋荣利、奋勇当先而又自强不息的精神。梅花的这些精神品质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写照。梅花乃至梅花精神对绝大部分西方读者来说是一种陌生有距离感的存在,译入语读者如若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有研究,在阅读此译文时会一头雾水,难以理解。霍译本则将“魂”字进行具象化处理,将其译为scent,即香味。“香味”一词从字面上乍看同原诗中“魂”字相去甚远,其实原诗作者笔下的白海棠就同时拥有着梨蕊的三分洁白无瑕以及梅花的一缕香魂傲骨。译者于此另辟蹊径,借用“香味”来代指“魂”,表达效果更加形象和具体,译入语读者也更容易领会原诗的真谛和精髓。黛玉诗中第三联,将白海棠花比作仙女缝制的漂亮舞衣,比作秋闺中擦拭泪痕的幽怨少女。这种比喻十分巧妙,黛玉的才气跃然纸上,顿时使白海棠的形象更加生动逼真,时而是月宫中仙女手中缝制的舞衣,时而又变为秋闺中幽怨拭泪的少女。然而这些表达对于三百余年后的母语读者来讲已颇为费解,对于译入语读者来讲理解起来会更加困难。霍克斯熟谙这种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巧妙地规避这种差异,将“缟袂”一词直接译为花朵,且将原诗中拭泪少女这一意象舍弃,转而用“眼泪在新缝制的花儿上掉落”承接上句,一笔带过。
四、译者的适应和选择
(一)对自身需要的适应和选择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们只有在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有更高级别的需要。对于人类来说,最基本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译者也不例外,同样需要为自己寻求生存空间。
杨宪益有着扎实的汉语语言和文化功底,译著百余部且都作为经典之作流传于后世。这位供职于外文社的翻译大家在临时受命翻译《红楼梦》时表示,自己不喜欢读《红楼梦》,小时候一半都没读完,可人总是要吃饭的,翻译何种作品是由不得自己的。杨先生言谈饱含风趣,但表达的却也是人之最基本的需要。然而《红楼梦》之于霍克斯来说可谓真爱,他为了能够全身心投入《红楼梦》的翻译工作,辞去了牛津大学的工作。霍克斯曾指出《红楼梦》虽然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却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呕心沥血写就的,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食粮是其他物质替代不了的,也是弥足珍贵的,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最高境界。
(二)对自身能力的适应和选择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文学造诣与艺术价值颇高,就连母语为中文的读者都要将原著读上数遍方能略知其中一二滋味。因此,译者不仅要有扎实的汉语功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要有扎实的译语功底,方能于两种语言之间自由切换。
杨宪益幼时饱读经书,汉语功底深厚,后长期留学英国,接受英语环境的熏陶。戴乃迭母语是英语,她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加入中国协会并同杨宪益相识、相恋。毕业后,二人几经周折进入编译馆,从此踏入漫漫的翻译长路。众所周知,合作翻译是最理想的翻译模式,中外学者合作,中国人对作品透彻的理解和诠释加上英语母语者地道的表达,当有压倒性优势。可见,二位的学术背景和双语功底很好地适应了翻译的需求。
虽然霍克斯大学期间才开始接触中文,但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花费近五年时间准备《红楼梦》的翻译工作,又花费近十年翻译《红楼梦》。试问人生有几个十五年?十五年磨一剑,这是何等的执着和坚韧!《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少年时期家道中落,于北京西山隐居十余年,凭着坚韧的毅力,创作出《红楼梦》。可见,译者霍克斯和作者曹雪芹有着同样卓越不凡的品格。个人的语言文化知识以及成长背景决定了适合翻译某种风格的语言,译者应选择和自己语言风格相近的作品,来者不拒则难译出精彩的作品。
(三)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须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同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成功的译作更是能从多个方面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如原作、译入语读者、社会、时代背景等。
第一,对原作的适应。通常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本人所著,后四十回则由高鹗续写。霍克斯认为原著由两位作者完成,其文笔风格不免有出入之处,所以决定由自己翻译前八十回,让自己的女婿闵福德翻译后四十回,以便这种文笔的差异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第二,对委托者和读者的适应。翻译目的是由翻译委托人决定的,因而翻译策略和方法间接地受委托者的影响。杨宪益夫妇受外文出版社之托,旨在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因而他们更倾向于异化翻译策略。杨先生认为翻译毕竟是翻译,要尽量保留原文中的“异国情调”,因为翻译本身就是文化交流,应尽量将这种异域文化传播出去。[7]霍克斯同英国最具权威的企鹅出版社合作,该社素来要求外文译本须有很强的可读性,要通俗易懂。因而霍克斯不拘泥于原作的字句结构,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更多地融入了译者的诠释和创新,让译入语读者更易于接受,从而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8]
第三,对社会、时代背景的适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翻译几乎与文字同时兴起,然而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会受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的限定和制约。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国家也意识到了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外传播中国文化。[9]19《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朵奇葩,肯定是首先要被译出去的。杨宪益夫妇被委以重任,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翻译工作。其实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传教士、外交官或政府官员,在承担着本职工作的重任之余为《红楼梦》在西方国家的传播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10]他们认识到了此书的文化价值和语言魅力,迫切想要向同胞们分享这一文化瑰宝,甚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过度劳累而英年早逝。因而,霍克斯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启了《红楼梦》的翻译工作,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为其翻译的创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在过去的将近半个世纪,杨宪益夫妇、霍克斯及其女婿约翰·闵福德的《红楼梦》全译本一直是经典之作,在译林的地位不可动摇。这两个译本之所以有经久不衰的地位,原因在于译者对以原文为主导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主导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