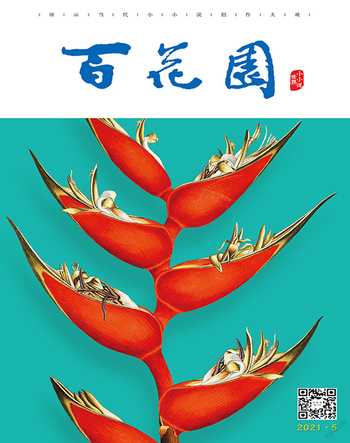想象和它所创造的
大解是著名的诗人,在全国的诗人中颇有声望。他的诗歌气息丰盈,善于从一个生活微点出发陡然上升,达至耐人回味的超拔和俯瞰,善于从一粒沙中变出一个性灵的世界,善于在平常事物中发现贮含在其中的光……近年来,他突然地迷恋上了小说写作,而且是真正地乐此不疲,就像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在飞翔中的另一只翅膀。这个“意识到”又让他更加著迷……他写,不断地写,在小说写作中投入的精力甚至已经比诗歌还多。这,大约可算大解先生的另一次“变法”,就像他在诗歌写作中的数次让人惊讶的调整一样。
我极为欣赏他的这一新变,好的诗人、好的作家一定是对自我不满足的,是对自我的固定和既有成就带有“敌意”的。诗人奥登曾经谈到大诗人和小诗人之间的区别,他认为这个区别就是:大诗人会在一种技艺成熟、完成之后立即转向自己陌生的领域,重新开辟一条新路并不断地试错,而小诗人则会继续在原路上……这一区别其实适用于任何艺术门类的艺术家,而大解在近六十岁的时候才开始由诗歌向小说“跨越”则更为孤绝和冒险。这可比一般的“衰年变法”更有挑战性。
必须承认,大解的小说也不同于一般的小说,这是一种让批评者难以置喙、难以归纳的新方式:它是魔幻的、荒诞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种“现实”能够困住它,将它拴在拴马桩上,然而它又时时露出现实的影子,与魔幻的、荒诞的部分交融在一起,像水融在水中那样自然自如;它是寓言化的,在每一段落的荒诞言说中都有隐喻的成分,然而它的寓言化指向却并不固定明确,时有有意的滑移——你以为它在这里隐喻的是A,而在后一段B的成分又出现了,而且与A形成了张力甚至对峙……他似乎在建立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譬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河湾村,但时有逸出,变成没有历史、没有时间、没有地域性和地域特色的可任意放置的“孤立事件”或“孤立行为”。一般而言,小说会有意地强化“现实喻指性”来凸显深度。大解的小说应当说不缺乏深度,然而他又时常会不断地否定和消解,用另一层的深度和深刻来对抗它、游戏它——游戏,具有智力博弈式的游戏在大解的小说写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核心性的。——他的这一做法,我曾在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宇宙奇趣全集》和《命运交叉的城堡》中隐约地见到过,当然它们很是不同。
《影子人群》寓言化的成分明显,我在读到一半儿的时候以为抓住了它“隐喻”的影子:衣服和身体意味了现实负重,而人影的存在则意味着“灵魂”“信仰”一类的东西,大解有意化虚为实,将它们有意地分开。——就在我以为抓住的时候,小说的叙述又有了新波澜、新转向,我又猜度前面提及的“模糊的人影”可能代表着引领,是宗教的、哲学的或精神的,后面人们的跟随是对“教主”的跟随,等等等等。它在“忽然有一天,村里来了几个过路的陌生老人”的时候又一次转折,奔走成为生存的方式和本能,它似乎喻示我们的人生本质上是在“奔走”的过程中度过,即使它不再有目标,即使它不再有瞻念和期待。我以为自己再次抓住了它,然而影子的队伍又“独立”地经过了村子,这次经过这里的是另一层的剥离之后……它不过是不足两千字的小短文,却迂回反复,寓意在其中不断地置换、叠加和否定,伸向旷远。在《影子人群》中出现的“长老”又出现于《雪色》之中,而在这篇小说中,荒凉和悲凉成为其中模糊的底色,就像是覆盖的雪。出嫁的姑娘,纸扎的、满身都是漏洞的毛驴,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白马,“重演的”旧日情景。——这份悲凉或荒凉来自哪里?它为何会与女孩的出嫁联系在一起?纸扎的、满身都是漏洞的毛驴喻示的是心灵、灵魂,还是死亡?重演又说明着什么?我觉得,作为诗人的大解有意只经营了喻体而不固定住喻指对象,他让我们在进入的过程中不断猜度,而且这些猜度往往是,一说即错。《是谁在走?》同样如此,它在标题中即埋伏下了疑问,这疑问兴致勃勃地追赶着自己的尾巴,让我们也跟着它在趣味和不断地出神中迷失。
??[责任编辑?晨?飞]
李浩,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著有小说集、诗集、评论集二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孙犁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