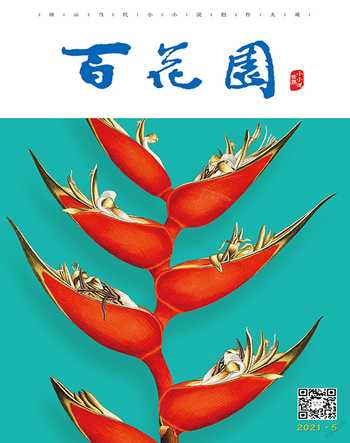父 亲
刘希本
我一夜未眠,辗转反侧,犹豫不决,该不该给父亲打电话说这个事?
后天上午,二哥要做心脏开胸手术,二嫂一辈子没开怀,身边再无其他亲人,医生说手术有很大的风险。我和二哥商量,决定先瞒着父亲,因为父亲已经八十多岁,而且血压高,患有“老烂腿”。让他知道后牵肠挂肚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如何是好?
其实,我心里清楚,即使打电话对父亲说了,他也未必会来,说不定会在电话的另一头暗自高兴呢!父亲和二哥之间有隔阂,时间久了,亲情演变成了仇结,这种仇结已有二十多年了。
那年,二哥十七岁,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整天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搅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父母省吃俭用养了两只羊,晚上睡觉害怕贼惦记,把羊拴在屋里的床腿上。俗话说,小心能驶万年船。村里其他人家喂的牛羊,都被贼牵去卖了或杀吃了,唯独父母饲养的这两只羊还在。
可是,那天早上,父母起床,发现羊没了,哭天号地,到处找,心疼得一整天滴水未进。二哥掏出一百块钱给母亲:“羊没了,人还在,该吃吃该喝喝,还得往前看。这一百块钱呢,您老人家再买两只小羊羔喂着。狗日的贼心恁黑,叫我逮到非抽他的筋不可!”
母亲打掉他递过来的钱,径直来到二哥睡觉的床底下,找出了两根拴羊的绳子,扔在二哥面前:“拴羊的绳子在你床底下,羊呢?昨晚你把你爹娘灌醉,安的啥心?嗯?你今天不把羊给我牵回来,我打断你的腿。”母亲说着抄起门后的扁担,朝着二哥劈头盖脸砸过去。二哥呼地站起来,顺势一挡,扁担飞出三尺远,母亲被闪倒了,胳膊磕断了。
原来,头天晚上,二哥把父亲母亲灌醉,把拴在床腿上的两只羊拉去杀了。
母亲深夜的哭声,从此就没有间断过。母亲见人就说:“我这辈子造孽,养了个不孝的儿子,能打娘了。这个遭天杀的,咋不死呢?”母亲的白发越来越多,从此卧床不起,昼夜躺在那儿唉声叹气。
母亲离世的那一天,离家多年的二哥突然回了家,他是从村里人那里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的。二哥在外这些年确实不容易,先是被劳教五年,出来后找了个女人,也就是现在的二嫂。我们想叫二哥他们回家,提了几次都被父亲拒绝了。一提这事,父亲就大动肝火,骂声连天。
当二哥回到院子里,全家愣住了,随之而来的是父亲的谩骂:“你滚!不要让我看到你!我没你这个儿子。”
二哥丢下三百块钱,领着二嫂含着泪走了。父亲把钱当场撕碎扔进烧纸盆里,边用火点钱边说:“孩儿他娘,你二儿子学会孝顺你了。”随后他又接着骂:“你这狼心狗肺的畜生,你这三百块钱,还抵不上你娘生你时剪脐带的医药费呢!”听邻居大妈说,母亲生二哥时难产,险些赔了性命。
母亲出殡这天,二哥没回来。五七祭坟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的坟头上多了两束白色的花。
我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我怕那束鲜花会再一次激起父亲刚刚平复的情绪。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二嫂打来的,她说:“三弟,以前千错万错,都是二哥二嫂的错。现在,你二哥有病了,手术成功也未必能活几年。他手术前想见一见父亲。”
嫂子在电话那头儿的哭声,深深地刺痛了我,毕竟是一母同胞呀!我来到病房时,看到二哥刀削似的蜡黄的脸和被病魔折磨得无神的眼睛,心里便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俯身在病床边,抱着二哥低声哭泣起来。
我打电话给父亲,结果遭到父亲的一顿臭骂,说二哥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是老天长眼叫他死。
我没有告诉二哥给父亲打电话的事。从他那无助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他希望能在手术前看到父亲。二嫂叹了口气,说:“别等了,再等也就咱几个人。”二嫂说这句话时,幽怨地瞪了二哥一眼。
二哥没有说话,闭上双眼,任由那高大的男护士推着平车出了狭小的病房,推过漫长的走廊,推进电梯。电梯缓缓下降,在一个楼层停下,咣当开了门。护士推着平车出了电梯,朝手术室走去。到手术室门口时,二哥忽然睁开眼睛,抬起头,朝电梯口看。电梯口空无一人,只有洁白的墙壁、冰冷的电梯门,宽大的后窗外天空灰暗陰沉。二哥垂下头,闭上眼睛,泪水从眼角潸然而出。咣当一声,他被护士推进了手术室,门冷冷地关上了。
二嫂站在门口,跺了跺脚,两手抱头蹲在地上。我站了一会儿,胸口沉闷,掏出一支烟,走向电梯后面的楼道口。一个瘦小的老头儿正坐在楼道拐角的台阶上,闷闷地抽烟。
“刚进去?”他问。
“嗯。”我点着了烟。
“不着急,慢慢等。”他说。
我在他身旁坐下,任由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儿子……进去一个半小时了。”默然良久,我听到他说,“该出来了吧。”他抽了一口烟,烟雾在他的脸前笼罩着,慢慢地散开了。
?
?[责任编辑?徐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