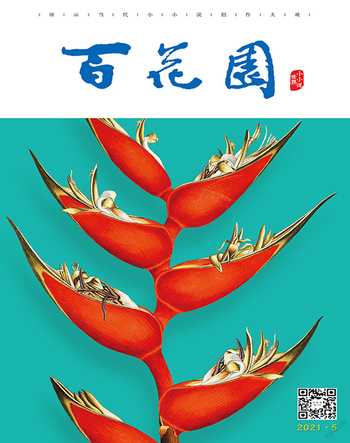豆腐心
李海燕
爹每天凌晨两点钟从炕上爬起来,然后穿过那条窄巷子,向生产队的队部走去。有月亮的晚上,爹狭长的影子跟爹一起,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晃悠着。
到了队部,爹去驴棚牵那条老驴。饲养员丁老三的鼾声跟鸡打鸣一样响。
老驴性子温顺,跟爹一样。爹把老驴拴在磨道上,给老驴戴上蒙眼,然后把盛着黄豆的大铁盆端过来,泡好的黄豆饱满得像正值好年华的女子。那时候爹四十多岁,笑容还很灿烂。
爹用手温柔地拍一下老驴的屁股蛋子,老驴就慢悠悠地走动起来,蹄子呱嗒呱嗒地蹬着地面,一圈又一圈。爹一边往那个小小的石洞里填黄豆,一边往里倒水,一静一动的两片石磨,发出吱吱的磨合声,而后从中间的一道缝隙中,淌出乳黄色的浆渣混合的黏稠豆汁来,一股豆腥味儿便在磨坊里荡漾开来。
磨完黄豆,爹把装着豆汁的水桶,拎到一个悬空横陈的木头“十字架”前,爹要进行做豆腐的下一个环节——浆渣分离,这是力气活儿。
一块豆包布的四个角分别拴在“十字架”的两根木头顶端,下面是一口大号铁锅。爹把豆汁舀到豆包布里,豆包布形成一个气球状,沉甸甸地垂挂在“十字架”上。爹叉开双腿,两只手用力摇动那个“十字架”,身子左右前后地摇摆着,很有节奏感,吱嘎吱嘎的声音冲击着潮湿的空气。乳白色的豆浆滴滴答答地洒落在大锅里,一灶木头柈子,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爹的额头已经布满了汗珠子。
豆浆烧开的时候,约莫凌晨四点钟,爹把烧开的豆浆舀进一口地缸里。爹一把竹糜刷子在左手,一只卤水碗在右手,刷子蜻蜓点水般在碗里蘸一下,甩在豆浆里。爹用刷子轻轻荡着豆浆的水平面,再甩再荡,直到水平面上出现豆花为止。
这时,丁老三揉着眼睛,手里拿着一只绿漆斑驳的军用水杯,一瘸一拐地走进来。丁老三早年当过兵,残了一条腿,一辈子没娶上媳妇,生产队队部就是他的家。
爹给丁老三的水杯里灌满豆花,这是丁老三的早餐。丁老三冲着爹嘿嘿一笑,吸溜着边走边喝。爹把一舀子豆腐渣,放在老驴的槽子里,然后摸摸老驴的长脸:“吃吧,老伙计。”老驴看一眼爹,把嘴插进豆腐渣里。
爹做了二十年豆腐,卤水点豆腐是一绝,做出来的豆腐松软,有豆腐味儿,但翻豆腐包的技术,爹一直不行,粘包的事差不多每天都上演一次,至少有一板豆腐长着麻坑。
家家房顶上冒起炊烟的时候,爹担着四板豆腐和一铁舀子豆腐渣上街了。豆腐渣被爹放在担子下面,用一块豆包布蒙着。
“五保户”崔三爷佝偻着腰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带着豁牙儿的蓝边碗。爹走到近前,放下担子,把带有麻坑的一块豆腐,放进崔三爷托着的碗里。崔三爷看着碗里的豆腐:“老四,翻豆腐包你就是差火候。”爹笑着说:“不差火候你老就吃不上豆腐,只能给你豆腐渣吃。”崔三爷跟爹对视一笑。
爹走到生产队队长大林家门口,大林老爹拿着两只碗走出来,把两毛钱递给爹,爹只收一毛,把一块带麻坑的豆腐放在一只碗里。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给您老一块粘包的吧。”然后掀开蒙在豆腐渣上的豆包布,在另一只碗里填满豆腐渣。队长老爹说:“老四,谢谢你了,要不这八口人,一块豆腐不够塞牙缝的。”
爹说:“还不全靠大林兄弟罩着我!”队长老爹说:“没事,你做的豆腐好吃,我跟大林说。”爹拱拱手。
到村西头的时候,爹的豆腐卖得差不多了,豆腐渣也送出去一多半。爹在一户房子破烂的人家门口停下来,喊一声“豆腐”,那扇破烂的柴门闪开,一个脸色发黄的十三四岁的丫头,拿着一只大碗走出来,低低地叫声:“四叔。”爹在碗里填满豆腐渣,又把一块豆腐切下一半儿,放在碗尖儿上,问一声:“你娘好些没?”丫头抿着嘴摇摇头。爹说:“进屋吧。”丫头便往回走,走了两步,回过头来:“四叔,我妈说谢谢你。”爹摆一下手,离开了。
爹把卖空的担子挑回家,把剩下不多的豆腐渣和一小块豆腐端进屋子里。娘看一眼:“又给丫头娘儿俩了?”爹点点头。娘又说:“别惹出闲话来。”爹说:“我知道。娘儿俩可怜,咱少吃一口。”娘把豆腐和豆腐渣放在一起炖了。盛的时候,爹舀一勺子放在一只碗里,余下的端到饭桌上。那一勺,是爹留给娘的。
爹走二十年了。那年娘得了脑梗,神志不清了。每天早晨,娘呆呆地坐在前門那儿,不错眼珠地看着大门口,嘴里念叨着含糊不清的话。说着说着,一条晶亮的水线,从嘴角淌出来。
那个原来脸色枯黄的丫头,已经成了有些富态的中年妇人,她上前用卫生纸轻轻揩去娘嘴边的那条晶亮的水线,说:“娘,咱该吃饭了。”
娘摇摇头:“等你爹送豆腐来。”这句话,娘一直说得很真切。
丫头跟我说,那天爹还没到村西头,她就慌慌张张地跑到街上找到爹:“四叔,我娘叫你去一趟。”爹愣了一下。丫头说:“我娘怕是不行了。”爹撒开两条长腿,向丫头家跑去。
那天丫头的娘走了,临终时跟爹说:“老四,你五个儿子,让丫头随便配你一个儿子,我才能闭上眼睛。”从那天起,丫头便成了我家的一员。
爹跟娘说:“丫头比老疙瘩小一岁,等长到岁数,配给老疙瘩吧。”
七年后,丫头成了我媳妇。丫头来我家的时候,大哥二十三岁,和二哥三哥四哥都没配上媳妇呢。
丫头拿着一把梳子,给娘梳理着花白的头发:“好,咱等着爹送豆腐来。”娘便痴痴地笑了。
?
?[责任编辑?吴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