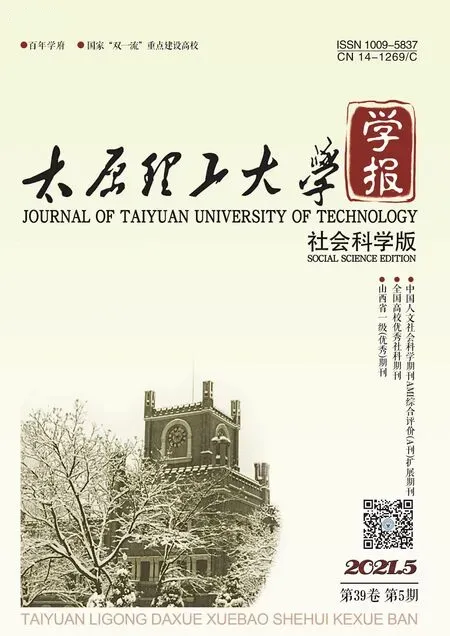历史与人学的伦理交织:《醉生梦死》对《朱诺与孔雀》的剧本改编
田 菊
(山西财经大学 经贸外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20世纪爱尔兰最著名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之一。他的戏剧主要以都柏林贫民窟为剧作场景,将爱尔兰人民为争取独立而抵抗英国统治的历史作为故事背景,突出表现殖民统治与战争带来的大众苦难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伪善行径。其中,作为其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都柏林三部曲”之一的《朱诺与孔雀》,是其戏剧艺术创作的最高峰。在这部不朽的传世佳作中,作者凭借自身丰富的生活感悟和对现实生活唯物辩证式的深刻洞察力,以其独特的创作视角,对爱尔兰解放运动爆发后一户爱尔兰普通家庭的世态生活进行了微观描写,生动刻画了多个人物在面对问题时的心理变化和行为选择。特别是对爱尔兰民众在长期艰苦抗英斗争中所出现的人性异化和道德扭曲的社会悲剧进行了充分刻画,成为反映当时爱尔兰底层民众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由于该剧在艺术表现和时代反思上的巨大成就,伴随着在剧院演出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成为爱尔兰戏剧运动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代表性剧作。
随着爱尔兰戏剧运动在中国影响的不断深化,著名戏剧、电影导演,电影艺术教育家章泯先生于1937年将《朱诺与孔雀》翻译改编为剧本《醉生梦死》,为左翼话剧舞台奉献了一部佳作。在改编过程中,章先生认为该剧反映的时代危机、社会矛盾和伦理道德等问题也正是当时旧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奥凯西在原著中通过呈现小人物的社会经历与主人公之间的情感交流,不仅充分挖掘出故事发展的社会语境,同时更加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其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的创作风格,使人为其折服。在改编过程中,章先生充分借助原著的创作经验,在剧本改编过程中,突出表现人物正义与反叛、高尚与卑微的二元对立,将人物的伦理道德置于文学批评的醒目位置。近百年之后,我们再次将两部剧作进行对比和分析,通过运用新的视角和维度探究改编作品与原作品间隐含着的逻辑脉络,从而挖掘出两部作品之间若隐若现的伦理线(ethical line)。
一、伦理语境的历史逻辑重现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源于人类伦理表达之需,将文学视为道德的产物,坚持文学批评的道德责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1]文学伦理学批评不同于传统的道德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进入文学的伦理环境中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进行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做出道德评价。可以看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聚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切实履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任务、目标,并有效借鉴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创作资源[2]。
(一)《朱诺与孔雀》的创作历史背景回溯
奥凯西1880年出生于都柏林一个贫穷的新教徒家庭,幼年丧父,从小因患眼疾而失学,直到青年时代都目不识丁。在都柏林街头流浪多年并进入铁路工厂做工9年后,他参加了1913年都柏林运输工人大罢工,并领导了1916年爱尔兰公民军发动的复活节起义。在他的作品中,将爱尔兰工人阶级反抗英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壮烈、悲惨的社会现实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写进剧本中,真实再现了工人家庭的悲惨遭遇,披露了英国和爱尔兰资产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以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民族主义观念表达对民族独立的理想追求。在创作风格方面,他擅长对真实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本质特征;在创作手法方面,把倾力塑造形象作为审美追求的重心,以生动的感性形式表达对现实人生的独到发现,表达了通过阶级斗争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自由的坚定信念。特别是擅长通过对残酷现实的批判,对比映衬出爱尔兰人民的伟大力量。因此,从艺术创作思想看,奥凯西认为写实的“真”本质上就是艺术的“美”,就是要用写实手法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各种典型人物搬上舞台,并成为主角和焦点。他的作品不仅增强了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更体现了复兴凯尔特民族的伟大愿望[3]。
(二)《醉生梦死》改编的历史背景
伦理学研究的是处于人类社会和人的关系中的、现实社会中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现象[4]。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与爱尔兰追求的时代历史背景相似,20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民族生存危机。因此,《醉生梦死》的改编将剧情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完全将读者带入了一个连年战争、时局动荡、风雨飘摇、民不聊生的历史背景之中,使得该剧在历史语境、生活环境及伦理环境方面被赋予了鲜明的中国化标签。正如当时对《醉生梦死》剧本的介绍所言,“《醉生梦死》的原作者是奥凯西,是爱尔兰的一位有名的剧作家。他的作品曾引起伦敦评论界很深的注意。甚至有人誉他为‘近代的莎士比亚’。这剧的原名是《朱诺与孔雀》,是一个现实的喜剧,具体说是一幅在爱尔兰动乱时代小市民的讽刺画,暴露了一帮醉生梦死的人的丑态”[6]。《醉生梦死》的故事改编将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物矛盾都进行了中国式置换,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故事发生在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时代,对于无辜可怜的老百姓而言,战争就是残酷和血腥的代名词。不仅造成国家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更引发时局动荡,整个社会兵荒马乱。在这样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环境中,财匮力尽、民生凋敝,生灵涂炭、水深火热。北平普通人家的贾福全一家也难逃凄苦酸楚的残酷现实,过着艰难拮据的日子。一家四口除了妻子勤劳善良、本分务实之外,贾福全和他的儿女都生活在自己放纵无度、虚无卑劣的世界里,他们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生活堕落沉沦。剧本围绕这样的伦理环境展开叙述,为后来跌宕起伏的剧情发展、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令人唏嘘的无奈结局营造了一个独特而成功的内外环境。从整体看,该剧的伦理环境不仅包括人情冷漠、精神空虚、道德败坏的社会环境,还包括自私自利、不切实际、自欺欺人的家庭环境,营造出了浓重的沉沦、虚无、荒诞的悲剧气氛。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结合可以创新文学批评话语体系, 拓展并深化现有文学批评理论的叙事方式。”[7]作为本剧的改编者,章泯先生亲身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惨绝人寰的肆意屠杀和国民党对劳苦大众重重压迫的黑暗社会。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民众的表现却大相径庭,有人参加革命、积极抗战,甚至战死沙场、以身殉国,表现出强烈的献身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情怀;而有的人却在国难当头不关心国事,推卸责任,没有担当,依然利欲熏心、欺瞒狡诈,暴露出卑微低劣的道德沦丧。而作为共产党员的章泯,当读到《朱诺和孔雀》剧本后产生了一种不期而遇的喜悦,他一直希冀能够通过一部反映中国普通城市家庭的剧本,来关照反映小市民的所思所为,批评那些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民众,唤醒那些沉睡的国民,教育和启发中产阶级积极投身抗战,号召更多的人团结起来,为民族的独立献身。《醉生梦死》就是对这些反面人物的刻画,讽刺这些麻木愚昧的民众,揭露他们丑恶卑劣的行为。这种中国式改编更容易使中国读者和观众在欣赏之后产生强烈共鸣,使麻木不仁、愚昧落后的小市民成为大众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有利于转变民众思想,使他们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关心国运、关爱群众,改良社会风气,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两剧相关情节的对比见表1。

表1 《朱诺与孔雀》与《醉生梦死》相关情节对比
二、伦理线结的人学逻辑呈现
文学的本质是人学,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文学要反映和表现的核心,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阐释和发掘文学道德伦理价值的重要维度。通过伦理线(ethical line)和伦理结(ethical knot or ethical complex),发现伦理线上伦理结的形成过程,或者是对已经形成的伦理结进行解构,挖掘出文学文本内在的伦理关系,从而帮助读者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重新认识文本,赏析文本。爱尔兰戏剧运动中的戏剧创作对人的关照正是要达到这一目标。其所表现的从社会学层面向人学层面的转向,深层的社会原因是在英国几百年的殖民统治下,爱尔兰人民的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束缚,整个爱尔兰在走出英国阴影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开始了对人们的意识、认识和思想等精神潜力的开掘,使人们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现实、历史与文化,去思考人、民族与人类在戏剧中的体现。这些戏剧家以现实主义所特有的那种沉重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去描写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去思考社会、历史和现实,去呈现人生的复杂多变,去真实地反映社会本质与历史发展的趋向。同时,更注重现实中人与人的生存状态,力求挖掘出广阔的现实生活底层涌动的时代大潮或积淀的民族心态,以及蕴藏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深处的民族、历史与文化根源。剧本在对人的权利、价值和人格的追求中进行审美探求,从而展现惊心动魄的历史发展。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反思和审视,以艺术的审美方式,表达出对现实个人命运的思考和关照。这种宏观视野的思考和微观个体角色的表达与交织,聚焦于伦理与道德人学逻辑的伦理线结之中。这反映在《醉生梦死》这部改编剧本中,依托原著所蕴涵着的深厚人本主义情节,存在鲜明的明暗两条平行的伦理线。每条伦理线上都附着多个大大小小的伦理结,呈现出人物迥异的伦理选择。
(一)明线:贾福全及儿女人伦丧失
故事叙述了在北平的一个普通人家,父亲贾福全是个没有职业的破落户,懒得做事,一提起工作,他就会腿疼。他和一个鬼混的朋友老皮,整日酩酊大醉、酒后滋事。儿子江男,做了伤天害理之事,为了获得小利而卖国求荣做了汉奸。他向日本人告发了自己的爱国青年朋友的藏身之处,被出卖的爱国青年被日本人逮捕并残忍杀害,而他得知此消息却无动于衷,如同一个冷血动物一般没有丝毫的自责和反应。女儿丽贞是个参加援绥运动的中学生,她嘴里常嚷着“国总是要爱的”,貌似是一位正义爱国的热血女青年,却在私下偷偷摸摸地跟小学教员纪德文谈恋爱。此时,丽贞一位朋友彭丹传话,贾家的亲属中死了一个人,有一笔很大的遗产可得。当贾福全和其儿女得知此消息后,像暴发户一般疯狂地购买贵重用品,甚至还向家具店、衣服铺赊了很多东西。女儿丽贞被彭丹的花言巧语和伪善的爱情所欺骗,陷入了彭丹的爱情漩涡,两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当证实了这消息误传后,全家愕然。彭丹丢弃了丽贞,纪德文在发觉丽贞怀孕时,嫌弃并抛弃了她。
从伦理意义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斯芬克斯因子是文学作品伦理表达的核心内容[8]。正因为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不同行为特征和性格表现,形成不同的伦理冲突,表现出不同的道德教诲价值。伦理学基本原理认为,所谓人性因子,就是人之为人的因素,其核心是理性意志,体现在对伦理秩序和伦理禁忌的遵从。而兽性因子则是人的动物性本能,是一种非理性因素,其核心是自然意志,体现在人对不同欲望的渴求。如果人性因子控制了兽性因子,人就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 相反,如果兽性因子战胜了人性因子,人便更多地体现出伦理意识的丧失、道德的缺失等。在作品中,贾福全作为唯利是图、自私伪善、推卸责任、没有担当的一家之长,忘记了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伦理身份。在家庭负债累累,儿女不务正业,家庭矛盾最激烈的时刻却选择抛妻弃子,逃避现实,听任在原始本能推动下产生的强烈原始欲望的支配。最终他放弃了自己的伦理身份,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伦理责任和义务,也意味着对社会认同的伦理秩序的破坏,反映了他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冲突、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对立。
女儿丽珍受其父亲的影响,缺少人伦教育,缺乏对原始欲望的理性控制,其行为和意识全凭本能的驱使,原始欲望最终取代了理性,丧失了道德和社会规约意识,导致她误入迷途,不能自拔,未婚先孕,背叛了爱情,失去了贞操,颠覆了中国传统女性温良恭俭、贤良淑德的形象。社会的伦理规则是伦理秩序的保障,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必然要受到伦理规则的制约,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丽珍由于欲望脱离了理性的控制,其行为破坏了当时的伦理秩序,最后受到惩罚,以致遭到彭丹和纪德文的抛弃。儿子江男,更是兽性因子完全吞噬了人性因子。人性的野蛮战胜了文明、残忍战胜了善良,这种二元对立完全被非理性的猛兽性情所重构,表现出毫无人性的冷漠与凶残。他抛弃了人应该具备的理性思维和行为,将精神意识中的非理性自我放在第一位,从而抑制了本我的理性思考和行为,展现出如同野兽一般的违背道德、人性和良知的行为,将朋友之间的信与义抛之脑后,成为众人唾弃和鄙夷的卖国贼。
(二)暗线:妻子的伦理意识升华
与贾福全及其子女截然不同的是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这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刻画。剧作家对贾福全妻子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泼墨较少,似乎是一个次要人物角色,但丝毫没有影响对这位传统女性形象的正面塑造,恰恰反衬出这位默默无闻、甘愿牺牲自我的老妇人高尚的伦理道德和安平乐道的伦理选择。剧作家通过长镜头断断续续地对妻子勤俭持家、处理家庭问题和矛盾关系的行为进行描写,话语不多,善良本分、勤劳朴素、安于现状、直面现实。对待“飞来横财”她半信半疑,不去理会;对待丈夫的游手好闲,她也仅仅低声嘟囔几句,从不唠叨吵架;对待佯装的儿子,他牵肠挂肚、叮嘱不断;对待女儿的不耻行为,她既包容又安慰,带着女儿离开这个令人痛心凄凉的家,给予她最温暖永恒的母爱。
《醉生梦死》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同《朱诺与孔雀》中的人物一样栩栩如生,同时剧情和结局的处理,更加突出对比了人物的伦理选择。《朱诺与孔雀》的结局是丈夫离家出走,留下了妻儿在家度日如年;而《醉生梦死》的结局改为妻子带着女儿离家出走,女人的伦理意识更加强烈。在面对丈夫的伦理缺失和儿子的人性沦丧,作为没有地位、没有话语权的封建时代女性,她想要摆脱残酷现实,逃离没有伦理意识的家庭环境,远离被压抑、被指责的现实。但悲剧色彩在于,至于去往哪里,如同娜拉的出走,没有目标,没有目的地,一切未知。剧本在人物最后的抉择方面加重笔墨,做了意想不到的着色,凸显戏剧性的发展和结局,增强了故事的悲剧色彩,更突出了妻子的伦理意识的升华和反抗现实社会和反抗不公家庭的伦理选择。 与改编剧本情境和伦理选择相类似,在原著《朱诺与孔雀》中以妇人朱诺在面对一个个家庭遭遇依然坚强果敢为主线,塑造了与其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自负懒惰的丈夫、被诬陷枪杀的儿子和虚荣无知的女儿的形象,从一户普通市民的世俗表现透视出风雨飘摇的爱尔兰,在动荡的时局中矛盾重重,社会不安,民众生活没有保障。故事讲述了船长波尔在爱尔兰大范围失业的背景下也难逃此命运,没有了工作,在巨大的家庭债务下,整日游手好闲,到处游逛、吹牛、酗酒,既不去找工作,也不管家务。而意外的朋友馈赠的遗产让他欣喜若狂,也加剧了他的懒惰和自私。用“孔雀”来隐喻波尔的傲慢自负、好逸恶劳的堕落本质。而“朱诺”本是罗马神话中的天后,是母性和婚姻之神,丘比特的妻子,代表着慈爱、温柔和美貌。该剧为波尔的妻子取名“朱诺”,寓意深刻,突出女主人公高大和坚毅的正面形象。她心地善良,每天忙于家务,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她在家庭重创面前却表现得镇定而坚强,做到直面人生,坚强接受。正反面人物的塑造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人物性格和人性的描写入木三分。奥凯西有意刻画对比强烈的人物性格,真与假、美与丑、热情与冷漠、直面与逃避,鲜明地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巨大反差。
三、伦理艺术的现实逻辑再现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文学同其他艺术一样,都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是客观世界在人类观念领域的反映。文学是作家依据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生活进行的艺术创造,具有认识性、倾向性和实践性。文学对人的描写也不会脱离人的生存环境——社会来孤立地进行,在审美经验、道德言说与理性思辨之间找到了共同的语义场,使美学反思在艺术、伦理和哲学的维度展开[9]。因此,文学伦理学理论认为,文学所构筑的虚拟世界离不开现实的参照,现实生活的伦理秩序必然要在文学中显现,文学中所塑造的人物及其道德观念必与现实伦理秩序相联系。从道德伦理角度入手对文学存在所作评价和判断,能更真实地呈现整体社会的道德伦理状况,把握社会伦理秩序、道德规范的特点和规律。
(一)现实风格中的象征主义色彩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叶的世界文学发展历史中,西方文学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融合的艺术思潮,为爱尔兰戏剧运动的艺术性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发展思路。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爱尔兰戏剧运动的戏剧作品主要体现出两类文学思想,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现代文学。在不少作品中出现了象征与现实的完美融合,体现了顺应时代、暗合社会的现代性审美追求,实现了在现实主义批判阐释中融合了象征主义的变现手法,在对人物外貌和性格深入到对主体思想的刻画中注重主体的情感发掘的独特艺术表现形式。起源于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以对自然或当代生活准确、详尽和不加修饰的描述为理念。这种文学思潮始终紧跟时代的变化,关注人们对当时社会的主观想法,是运用文学手段折射社会现实,抒发人民心声的有效途径。爱尔兰戏剧运动的剧作家在创作风格中暗合了他们自我解救的政治抱负,渗透出浓郁的现实主义特征。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奥凯西的现实经历和情感表达方式蕴含着深刻的现实主义风格,这与其毕生坚定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息息相关。他主张基本创作要从社会现实的考察中获得材料,以参与者的眼光和冷静的头脑仔细剖析,然后如实地描写出来。他的作品不仅增强了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更体现了复兴凯尔特民族的伟大愿望。在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中,奥凯西巧妙地将象征主义表现手法融入现实主义的题材作品中,将两种手法巧妙结合,实现了对现代象征主义文学的创新。在真实的现实描写中蕴藏着诗意的内涵,在真实的描写中暗示着难以测知的奥秘。现实主义描述与总体象征相互交织,融为一体,真实向读者展示了更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实现了美与现实的协调统一。例如,《朱诺与孔雀》中的圣灯象征着约翰尼的命运,圣灯的熄灭预示着约翰尼被杀的结局,都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来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心灵上带来的压抑与创伤。正是这些细节的刻画,使得作者能够借鉴现代主义的审美感知方式,赋予创作更多的历史内涵、文化意蕴和哲理思辨,使现实主义戏剧在对现实的审美观照中贯注着强烈的现代意识。
(二)改编剧作的社会意义与艺术追求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文学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特点或是作家创作文学的伦理学问题,而更在于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解读文学与社会、与作家、与读者等关系的种种问题。此外,作家从事写作的道德责任与义务、批评家批评文学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甚至包括学者研究文学的学术规范等,都应该属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范畴。正如勃浪在《业余剧人协会上演〈欲魔〉〈醉生梦死〉〈大雷雨〉的意义》一文中介绍了《醉生梦死》的一些上演情况:“《醉生梦死》是业余剧人协会第三次公演时的三个上演剧目之一,第一次和第二次公演得到了大众的拥护,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该协会意识到了黑暗的势力在消亡前正在作最后的挣扎,向人民大众作着更残酷的束缚。他们不得不沸腾着胸腔里的热血,冒着眼睛里的火花,从他们的灵魂深处,冒出光辉的火星来!为了保持原著的喜剧型而在其中增加了些笑料……总之,业余剧人协会的这次演出,在各方面都使我们感到非常满意。尤其在介绍世界名剧的这一点上,它是有着极大的收获。”[6]这是因为剧本改编对这样的社会现象进行抨击和批判,通过强烈的反差感来引起读者的深刻认同,将中国大城市生活现实和人民对战乱纷飞的中国迥然的认识和表现进行了生动刻画。由于该剧深刻的人文内涵和深远的社会意义,而成为业余剧社的演出剧目,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四、结语
文学伦理学认为,文学与伦理之间有着历史建构的关联。从文学活动的自身逻辑特性来看,存在于社会空间之中的文学也难免与人类的伦理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10]。正如前文所述,在现代文学理论中,文学伦理学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突出体现文学的人性,集中关注的是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目的是使不同时代、地域的读者都能对文学作品产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美感。更为重要的是要强调文学现实价值,突出批判作用,体现人文关怀。正如奥凯西在作品中彰显的“人文性”对“人性”的关怀,不仅体现了剧中人的失落与追求,而且凸显了对特殊时代背景下人的惆怅与茫然,人的残缺美和悲凉感。这种人文情感不仅融入了作者多年来对人与人性、社会与自然、民族与人类的共同焦灼、困惑和深沉思考,更是剧作家通过剧本创造出超越国家、民族、时代的人学内涵。作品的深层语码中体现着对人的境遇的关注,引导人们去追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从文学伦理学角度看,剧本的伦理学价值既表现出审美客体的“人”的生存、命运、复杂性与丰富性等,又表现出审美主体的“人”的真实——戏剧家的人生体验、生命感悟和对现实的独特发现。在这种历史和人学的伦理交织中,即是从现实维度体现了对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所共有的生存境遇与困惑的思考,同时也是从艺术维度拓宽创作主体与接收主体心灵对话和情感交流的精神空间,体现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正是基于这种文学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可以清晰展现出在《醉生梦死》中揭示出当时历史环境下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为了实现生命的意义、个人的意志和对自由的想慕,从中体现出人的尊严、人格和生命的价值,力求在民族现实的描写中表现人类生存的欢乐与痛苦,人类面临的困境和艰难选择。可以说,通过对原著和改编作品的分析和思考,不仅体现出文学人学价值的重要理论意义,更是文学社会学意义的集中展现,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上实现了彼此交织与升华,体现了剧作者深层次的人文关怀与时代之思。这也是我们今天思考两部作品的重要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