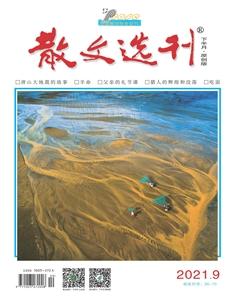羊命
王文富

一
“咩——咩——”羊撕心裂肺的悲鸣声穿透了隆冬的夜空,也搅醒了酣睡的家人。
父亲亮起煤油灯急切地奔到羊圈。我家母羊生崽了,羊羔前半身已出来了,两只前腿耷拉在母羊屁股后的褥草上,羊嘴翕动发出细小的“咩咩”叫声。
母羊抽搐,铆足了劲儿,可羊羔后半截就是出不来。
“羊難产了……是难产!”父亲焦急地对母亲说。那时,我们那里几个大队才有一个兽医,这大冷天,半夜三更黑咕隆咚的,上哪请兽医呀!
母羊已奄奄一息,羊羔“咩咩”的稚嫩叫声也一声比一声弱。动物生产与人生产颇为相似,父亲想到了生产队里的接生婆。
我与母亲借着微弱的星光,在田埂边的一条羊肠小道上摸索着前行,在小道的尽头,母亲敲开了接生婆的家门。听说为羊接生,接生婆连说晦气,一口拒绝,并关上了大门。母亲站在窗下苦苦央求,说羊为我家一年挣了很多工分,光羊屎蛋子沤的绿肥就能抵上一个劳力劳作半年的工分呢!它要是死了,我家可能因少了工分成为超支户了。那时,队里分粮分钱分物是按工分计酬的,家里人口多而劳力少,挣的工分少,分的粮不够糊口,就得向生产队借,借多了便成为“超支户”。做一个超支户会被人戳脊梁骨,很丢脸面的,在社员面前抬不起头。母亲好话说了一堆,承诺给接生婆一份“冲喜”钱,接生婆才怏怏地答应试试。
接生婆探查了母羊宫口,又熟练地捺了捺母羊肚子,说肚里就一只羊,羊羔的两只后腿屈在母羊子宫里。接生婆接了队里许多孩子,我姐我弟还有我都是这个接生婆接生的,她接人在行,老到,驾轻就熟,可为羊接生她是“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
接生婆心急如焚地对父亲说,若保母羊风险大,羊羔和母羊可能都会死,保羊羔尚能活一命,两命只能留一命,让我父亲速做决断。
父亲迟疑半晌,下不了决定,不得已由接生婆做了主。母羊死了,是被接生婆用剪刀硬生生地剪开肚皮后死去的。
我家一只母羊死了,消息在生产队里不胫而走,由队里也传到队外。邻大队一个偷偷收兽皮的贩子(这个贩子曾因贩卖牲畜被公安局处理过)与父亲磨破了嘴皮,花了三块钱割去了母羊的皮。不知忌讳什么,父亲说下崽的死母羊吃不得。其实,即使吃得,在那时我们当地人的餐桌上鲜有羊肉的一席之地,乡民们过年过节抑或操办红白事的大荤是以猪肉为食材的。就这样,母羊的肉身被父亲埋人屋前的一块菜畦里,一如它沤绿肥的羊屎蛋子成了土壤的肥料。
羊羔活了下来。翌日晌午,肉墩墩的小家伙拱开父亲给它保暖的棉被胎子,站起身子,迈出了它生命的第一步。
母羊没了,羊羔也没了羊奶,母亲把玉米糁子没在水里浸泡,直至酥软后放在石臼里舂成粉,再人锅里煮成玉米糊,父亲扒开羊嘴,用汤匙小心翼翼地把玉米糊喂到羊羔嘴里,羊羔怕是饿极了,一口连着一口吸吮,肚子撑得圆滚滚的,“咩咩”两声后不再张嘴,似乎告诉父亲吃饱了,然后它很满意地挣脱父亲的臂膀,下了地。羊羔下地后并不走远,在父亲的胯下绕来绕去,身子蹭着父亲的腿,还用头拱拱,像极了小孩在撒娇。
父亲把羊羔视作了自己的孩子,给它起了个名字——“羊羊”。冬日正午的太阳和煦,羊羊被父亲抱到屋外,放在苇草围挡的背风处,躺在褥草上慵懒而舒坦地晒着太阳,洁白的绒毛泛着白晃晃的光,酷似老母羊那惹眼的一身毛发。入夜,父亲把它放在他床沿下铺着衾褥的箩筐里,羊羊也乐意享受这份舒适,叫上一两声“咩咩”后安然入睡。母亲说她生下我们那会儿也没见我父亲这般呵护过。
一个多月后,羊羊头上隆起嫩嫩的粉红色犄角,羊腿也长得壮壮实实,父亲掰开羊嘴瞧见满嘴长齐的牙,表情亮了,那表情里漾着收获硕果般的丝丝惬意,也溢满了美好的期待。父亲开心地说道:“羊能断‘奶了。”羊羊断了“奶”,家里就省下了一张吃饭的口。
羊羊吃上铡碎的枯玉米秆,那曾是母羊吃剩下的料。
二
那时,羊是我们那里社员家的稀罕牲畜,我家的那只母羊,还是队里一户人家因多养了一只羊羔被队里割“尾巴”(“文革”时农家饲养牲畜超过规定数量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后硬塞给我家饲养的,这只母羊便成了我家的大牲口。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羊羊熬过了食物最艰难的时光。地里、路边、田头、河堤上、沟坎处野草疯长,父亲在队里放工回来,担着的箩筐里装满小羊吃的嫩嫩的青草。羊羊的身体随食量一天天见长。放学后,我拿上粪铲子,挑上粪箕,打开栅栏,把羊放出羊圈,牵到家旁边的河堤上觅食。那时,河堤上长着茂密的槐树,林荫间长着徐徐菜、马齿苋、婆婆纳、猪毛草等鲜嫩的野菜、野草。小羊在河堤上悠闲地啃草,我在不远处寻觅着狗、耕牛的粪便,抑或人应急时留下的粪便,当然,也顺便把羊屎蛋子铲到粪箕里。那时的粪便是农人为土地增肥力的宝贝,拾粪也成了我孩提时为家里挣工分的最轻松的活儿。一次因专注找粪便,忘了看羊,羊啃了队里近半垄地的麦子。那时破坏田里青苗,轻则戴高帽子游街,重则几年牢狱。见闯下大祸,我慌乱得不知所措,拿起粪铲子撵着羊打,麦田里烙上了我与羊零乱的脚印。
麦田里的“证据”,让公安民警轻易地找到了我家。父亲一面把毁坏青苗的责任竭力往自己身上揽,一面频频向生产队长打躬作揖,大队民兵营长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也在一旁帮腔,报案的生产队长顺势打了圆场,最后以扣我家200个工分的处罚了结了这事。
经历这次浩劫,父亲再也不容许我放羊了。每天放学后,我便背上竹篓子,拿上小锹子到河堤上薅羊草。河堤上弥漫着槐树花淡淡的清香,甜甜的气息。那时食物短缺,在青黄不接的春天,槐树花常是母亲给我们爆炒的果腹小菜。既然人能吃,羊肯定也能吃,我便攀爬到树上在其杈枝上捋下一篓槐树花,羊羊竟吃上了瘾,一直吃到槐树花凋谢。
过了春季和初夏,羊羊长得膘肥体壮,拉出的羊屎蛋子撮成一堆堆。父亲从水沟里摘来淤泥,与枯树叶、青草和羊屎搅拌,制成两个3米长、半米高、1米宽的长方形绿肥堆,外面用烂稀泥抹平封实,经历夏天高温发酵,秋收后,队里组长、记分员测量大小并甄别肥堆里有无牲畜粪便。质量好的一块绿肥堆算60个工分。
过了秋,便进入1975年的冬天,羊羊将近一岁了。这年的冬季,雪较往年下得早,11月初开始下雪,断断续续绵延了近一个月。父亲在离家80里外的挑河工地上挖泥,大雪没有阻断挑河的进程,队里隔三岔五地到社员家筹集粮草运到工地上,我家的柴火也贡献了一部分,其中有羊吃的玉米秆。
母亲担忧队里还要筹集我家柴火,羊料不够过冬,便将玉米秆铡碎,掖进河堤陡坡一处地窖里。生产队长第二次到我家筹集柴火时,竟然看中了羊,与母亲游说,说把羊给生产队,可以冲抵被扣的工分。第一次来时,母亲就察觉队长有觊觎“羊羊”的心思,只是没道破,这一次生产队长张了口,语气坚定,似乎没有商榷的余地。
没过几天,生产队长带着大队干部再次来我家,是专为羊而来,说挑河已到了最吃力的扒河底阶段,河工伙食需要改善,以增强他们体力,这事不能耽搁。
后来,父亲从工地上回来,埋怨母亲没护好羊,没悲悯心,让羊羊丢了命。
父亲心疼能挣上工分的羊羊,可母亲就狠心呀?母亲委屈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嗫嚅着说:“羊抵了工分,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