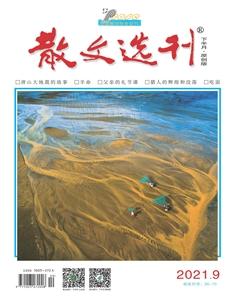怀念
易格滋
父亲走后,母亲一人独守着老家的屋院,拒绝了我要她来城里一起住的建议。我说,你守着这院落,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母亲指着趴在她脚边的黄猫道:“有它Ⅱ阿!”这只猫是父亲走的那年冬天流落到我家院子的,十余年来它享受着跟母亲相同的食宿待遇。
田地征用后,不能种麦种稻的母亲,喜欢上种黄豆、白菜、空心菜、萝卜等,松土、锄草、施肥,实在没事儿,她便在那块土地上晃悠,她那时大概觉得自己像个女王,她想这样就这样,想那样就那样。母亲嗅嗅空气里的土腥味儿、青草味儿,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四月底爬满院墙的金银花绽放如一片初雪,端午节还没到,池塘边那棵她从老宅基地移植过来的,已有十多岁的栀子树,一片油绿的叶子里浮起洁白的花骨朵,初夏的风吹得骨朵们颤颤悠悠,母亲嗅嗅香气,得意地摊开双手道:“城里有它们吗?哈!没有吧?我当然不会去你那儿。”
菜地在屋子后面,地是人家盖工厂剩下的“边角余料”,形状也是曲里拐弯,母亲一锄一锨开垦出来。冬天里,萝卜、白菜,青葱一片;春夏之际,黄瓜、番茄、南瓜、冬瓜、西瓜、香瓜,绿藤紫茎,满地疯长,姹紫嫣红。田野里的野兔、野鸡和各种小兽,纷纷赶来会餐。母亲从不在地里下农药,也不驱赶它们,久之,那些野物不再惧怕她,见她走来,顶多让一让。母亲蹲在那里锄草,小动物吃一口青蔬,望一望她接着吃。菜蔬吃不完,先是送邻居,再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将菜蔬送给进城务工的农民。
母亲娘家贫穷,穷不当长子,富不做幺儿。母亲是长女,下面有四个弟妹,童年时她牵引着一头黑水牛,放牧到坡岗、河滩,狗尾巴草、丝茅草缠着她的裤腿,荆棘和野花粘满她的衣服。放牛多年也不知“牛”字怎么写,母亲说:“一个字,两个叉,它认识我,我不认識它。”母亲嫁过来,靠种地为生。
“这老家伙肯定怕吓着我,一次也没回来过。”母亲说父亲走了十余年,居然从没梦见过他。我不太相信母亲的话。很可能,父亲在某个漆黑或皓月当空的夜晚,从磙子河堤脚出发(父亲安眠于磙子河边),像生前那样摆着两只手,踩着铺满星光的小路,路过曾经耕种过的田地时,他在田头坐了坐,他吸着烟,烟头在夜气里明明灭灭。他甚至在与母亲打过架的那块水田边,默默站立了一小会儿,轻轻地自语道:“别记恨我,主要是那时太穷了,整天愁吃愁穿,心里烦得要命,才忍不住动手打了你……”父亲回到老家,院子里的桂花树和樟树,叶子上沾着露水,湿漉漉的,像下过一场小雨。父亲脚步极轻地走到母亲的窗口,透过玻璃他看到了熟睡的母亲,只是母亲不知道这一切。
母亲曾在一个夏日午后对我抱怨:“你父亲这个死鬼,把我忘了。”随后又自说自话:“唉,他就是那样一个人,怕打扰任何人。”其实母亲也是如此,她甚至在临走前的那个夜晚,对守护的我们说:“人都是要走的,只是,我舍不得它们。”她说的“它们”,大概是指院子里的植物、地里的菜、那只黄猫。
没有父亲和母亲的屋院,寂寞如一只空洞的蝉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