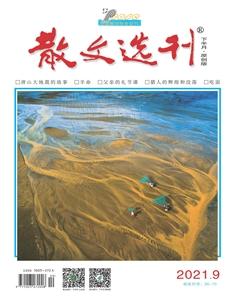香草
张少辉

香草是村北头莲婶的女儿,娇小,白净,完全是城里人的打扮,同我家墙上张贴的画中的女孩儿差不多:白衬衫,红裙子,脚穿一双乡下罕见的塑料凉鞋。
这也难怪,香草的爸爸是工人,专造大桥的工人,每月拿的工资很高,乡下人恐怕一年也挣不了那么多。
因而香草吃得好,口袋里常有一些稀罕的零食。香草常吃一种奶糖,四方形乳白色,裹一层薄薄的膜,外面则是彩色的玻璃纸。我们老远就能闻到她口中奶糖的甜香味。有时围上去,目光馋馋的,香草便发几颗,大家分着吃,吃完了再想要,香草便说:“给多了妈妈打。”
香草在乡下人眼中有特别的地位。称赞某家刚出世的女婴好,只要说长得和香草一样,这家人便欢喜,满眼含笑说:“哪能呢,哪有那个福气呢。”也常見大人持竹竿追打自家脏兮兮的孩子:“你这个泥猴,才上身的衣服就滚这么脏,怎不跟人家香草学学!”香草干净,一身上下从来清爽,在大人眼中特别受用。
乡下人办喜事,香草总是受到邀请。大红的色调中,香草显得格外的水灵。站在新人身边,那新娘脸上便似乎蒙上了一层自卑。老者们啧啧有声:“出人呵,我们村!”言下是姑娘还是我们村的水灵,心理上便胜了一筹。而新娘的家人们见此景也似乎消退了原先的许多锐气,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占不了上风。
奶奶是极喜欢香草的,我们家的一些零食香草总有缘尝到。有时奶奶坐门边,抱着我弟弟唱当时很流行的一首儿歌,内容忘了,意思是找对象的。唱完便问:“要哪个做对象呵?”弟弟毫不犹豫:“要香草!”奶奶继续调侃:“要二妞好不好?”弟弟便撒赖:“要香草嘛!”奶奶乐:“坏东西,就晓得找好的要!”
而香草的结局是如此的不幸。七岁那年的雷雨天,在岗上玩耍的香草被雷击倒在一棵大树下。听到消息后,我们的头发都爹了起来。飞跑到那里一看,香草平平地躺在那里,手里紧攥着一把葛巴草,那是我们常用来编织小篮子的。香草的脸雪白,平静,我从来没有注意到香草有那么长的眼睫毛。覆盖在眼睑上如一片小小的森林。香草的母亲疯了一般跑来,那哭声撕心裂肺的,所有的围观者都流下了痛惜的泪水。
奶奶也惊呆了,好多天都愣着神,一手抱我弟弟一手擦眼喃喃着:“多体面的孩子,雷公老爷见她好,收去了,收去了……”
很多年后,我回故乡给奶奶上坟,顺便去香草的墓前。香草那小小的坟茔上长满青草,一些不知名的紫花白花星星点点开着。有一堆冷透了的纸灰在那里四散飘动,这是谁烧的呢?该不是她的父母烧的吧,不管是谁,香草,还是有人记得你的。
——根据课文《乡下人家》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