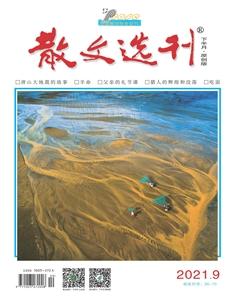唐山大地震的故事
冯立新

一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醒着,之前刚刚在瓦罐里撒完尿。撒尿前,我摸到炕沿下的灯绳,用力去拉,钉子串着的缝纫机的线轴清晰地叫了一声,开关的簧片也随着“哒哒”叫了两声,灯没有亮,又拉,灯还是不亮,知道电还没有来,惺忪睡眼中发现屋子里漆黑一片。
奶奶在家的时候,我和奶奶、三哥、四哥睡一盘炕,奶奶睡炕头,其次是我,再次是四哥,三哥睡炕尾。奶奶出门快一个月了,去看她的小姑子——嫁到王禾庄我的老姑奶。对面屋是大哥、嫂子,还有刚满周岁的侄子小兵,母亲和两个妹妹在前排房,父亲不在家,他那时在一百里地外的尖坨子运输公司的马车队里赶马车,二哥已经入伍一年多了,他参军去了二连浩特。
因为黑,也因为想奶奶,我趴在炕上没有睡意,瞪大眼寻找板柜上的掸瓶。正在这时,房子开始晃动,那晃动像一只巨大的簸箕在剔除高粱里的秕糠,又感觉有个大疯子在不要命地摇动风门,风门上的那块玻璃哗哗地响。
四哥喊,地动——地动!
感觉几秒钟,不过六七下的样子,房子稀里哗啦倒了。
我家的房子,是北方常见的那种焦顶平房,1971年盖的,前排房是1975年盖的,两排房的中间还有两间平房,因为儿子多,父亲早早动手,为儿子们盖够了媳妇本儿,那时能盖八问平房的人家算是上等户了。
四哥喊完地动后,往前一蹿,刚刚探出半个身子,房顶下来了,腿担在炕沿上,卡住了。我也被倒下的房顶捂住了,但没有受伤,窗扇上的窗插抵住了我的后背。
我喊,三哥,三哥,我被砸里边了。
三哥是我的主心骨,是兄弟姊妹七人里边我最信服的人。记得有一次,二哥、四哥我们去新陡河淘鱼,都过中午了,水也没有见底。这时候,三哥送饭来了,他一看这情形,决定放弃我们正在淘鱼的那块地方,重新堵了块漂子(河水中水浅的地儿),他说水浅的地方水暖和,鱼肯定多。结果,真应了三哥的判断,天黑之前抓到了鱼,弟兄四人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老半天三哥那边没有回音。我喊道,三哥,我被砸里边了,快救救我。
你等着吧,小新,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救你。三哥断断续续地说完这句话,然后就没有声音了。
我继续执拗地喊,三哥,三哥!
四哥说,小新,别喊了,三哥可能是“不中了”。那时候年幼无知的我啊,不明白“不中了”替代的是死亡。
二
我开始安静下来。废墟里一片黑暗,过了许久,感觉头顶上有蓝白色的光亮透过来,并伴着习习凉风,头顶出现了一条缝隙,有喊声、哭声刺人我的耳膜,撕心裂肺,遥远缥缈。四哥说,小新,我有点闷得慌,你给我扒个缝儿。我伸手试了试,我和他之间隔着芦苇的苇箔,还有一根木头,我没能扒动。倒是接下来的一次余震给四哥晃出了缝隙,四哥不再喊闷了。这时候,我感觉到了尿意,却无法移动身体,无奈撒到身体下的炕被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到头顶上有喊声,是妈妈和隔壁的大改叔在上面焦急地喊我们的乳名,“贺子,小强,小新,你们在哪儿?”
那焦灼的声音明明在头顶,却感觉非常遥远。我和四哥大声回应着母亲:“妈,我们在这呢。”
房顶上的人们循着声音,用力搬开焦子坯,捌开苇箔和箔泥,把在过梁弯里圈起来的我扒了出来,对,那棵柳木的过梁有些弯曲,那个弯曲,成了我的避难所,救了我一命。接着,四哥也被扒出来了,但已经不能走路,后背上血肉模糊。大妹妹小娟震亡了。三哥被扒了出来,母亲抱着他,试图唤醒他,但他的头无力地下垂,四肢乱晃,像失了线的木偶。他是脊骨断裂,伤了内脏死的。
对面的哥嫂先我们一步被扒出来,嫂子在大口大口地喘息。他们伤心地抱着刚一周岁的孩子,孩子已会扶着窗台挖挲着走路了,房屋倒塌后,窒息在嫂子的怀里。
这时,飘起了雨,母亲给我披上一个褂子。忽然有人喊,天塌地陷啦,快跑吧。
我随着家人往外走,脚下是破碎的焦子坯、折了的房檩和椽子,倔强的苇箔和箔泥拧巴在一起,倒了的青砖墙和红砖墙,露出了勾缝的白灰茬口。它们相挽着,共同构筑着一个支离的狰狞。
我住的房子倒了,妈妈住的房子也倒了,一个温馨的家被地震彻底肢解,满是尖锐的棱角。
当时没有恐惧更谈不上悲哀,感觉非常麻木,光着脚低头小心躲避着脚下的杂物,看到家里的中院和前院有两处地方往外冒水,泉眼一样,伴着黑沙与黄沙,已经喷成了一尺高的沙丘。
天已然亮了,但看不到太阳,天空布满黑灰的云,天地呈混沌状。我跟着人群往西走(每家的栅子和树木依稀能辨别方向),村庄里到处是撕裂的伤口,房子的伤口,村里的房子,像槽头永远站立的骏马,地上打个滚却散失了气力,无奈趴在了泥土上。但也有一些土墙还挺着,扛着幾根檩条,像战场上不屈的战士的浮雕。似乎每个房子跟前都有人在哭泣、在喊叫。
顾不上了,谁都顾不上了。接着又上了北电道。路的两边有人已经支起了两顶硕大的帆布帐篷,帐篷的边上支起了锅灶,有人在做饭,浓密的炊烟在细雨中飘荡,像村庄无助的手,伸向天空,更像招魂的白布幡,舞动、聚散。
令人意外的是,老村外面的房子一间也没倒。惊魂未定的母亲被一户人家邀请去吃早饭,母亲带上了我,那户人家房子没倒,人丁更没伤耗,我记得那餐早饭是大米粥、烙饼,还有炒肉,堪比过年。和母亲的交谈中,知道那肉是马肉,来自生产队的饲养处,那时候,我们村有六个生产队,都养着许多的骡、马、牛等大牲畜,地震了,饲养员死的死,回家的回家,饲养处倒了,牲口拴在槽头愈发动弹不得,人们拿着刀子也不管牲口是活是死,见到被压住的牲口照屁股蛋就割。
临近中午的时候,父亲骑车从尖坨子回来了。母亲没有哭,只是把家里的事和父亲说了,父亲忧心着奶奶,让大哥骑车去王禾庄探听奶奶的情况。
下午,雨大了起来,北电道上一片泥泞。电道旁的河沟与田地里都积满了水,雨滴砸在水面上,冒起一个又一个水泡。这要在往常,我一定和小伙伴们跳着脚扯嗓子野喊,“下雨咧,冒泡咧,王八顶着草帽咧!”可现在大人的脸上神色哀戚,眉宇间落了锁。我不敢乱动,望着远处那黏稠的雨线,把铅灰的天空和死寂的大地慢慢缝合在了一起。
天暗下来,有人往帐篷里抱麦秸,铺在地上,有人拆来门板,准备在上面过夜。
帐篷里,人们很少交谈,家家都是房倒屋塌,亲人罹难,都在用安静止复着流血的心灵,心焦、叹气。奔走中一些被忽视的伤口,疼痛着醒来。
我在父亲的怀里睡熟了,记忆中少有的一次,睡梦中,几次大的余震把我晃醒,我想挣扎着坐起来,父亲把我搂得更紧。
第二天早晨,天晴了。一个人骑着枣红马来了,腰间别着一把枪,枪把上拴一块红绸,枣红马小碎步奔跑,红绸迎风摆动。大人们说,那是公社书记,从地震后一直没闲着,骑着他的马四处巡视。
接着又听人说,大队组织社员用排子车把死人都拉到周家坟埋了,包括我的三哥、妹妹,还有侄子。
三
去王禾庄打探奶奶消息的大哥回来了。说奶奶死了,老姑奶也死了,老姐俩死在一个炕上,还有一个三表叔也被砸死了。奶奶的尸骨在姑爷的操持下暂时埋了。父亲听后,深深地“唉”了一声。
在父亲十几岁时,爷爷就过世了。爷爷死得早,老姑奶担心年轻的奶奶守不住,走道另嫁,会屈了父亲,她便舍了自己的幸福,陪嫂子过了十几年,白天一起生产劳作,晚上陪嫂子说话唠嗑,以此来消磨奶奶的寂寞和孤独,直到父亲长大成人,奶奶老了年岁,老姑奶也三十多了,这才嫁到王禾庄给人做了填房。奶奶感激这个小姑子,拿她当亲妹妹看,每年都要见几次面。
实际上,父亲早和母亲商量好的,等再过几天,天凉下来,父亲就把奶奶接回来,可谁知会是这样。母亲说,在家焉能好到哪去?这就是命啊!
大哥说,河头那边也都震塌啦,骑车路过直属库,人们都在那里抢粮食,也没人管,便也顺手驮回了半袋面。
震后的第三天,父亲领着一家人回了家,在老宅的一片废墟瓦砾中找了一块平展的地方,用帆布搭起了自己的帐篷。扒出了铁锅,重新垒上灶台,扒出粮食、衣服和能用的被褥,一个熟悉的家,一个陌生的家;一个温馨的家,一个伤心的家。在炊烟串起的日子上各要素重新结组、慢慢黏合、悄悄蜕变。
四哥还是不能站起来,他趴在门板上,后背上有七个八钱酒盅样大的伤口,冒着津水,无法愈合。
七天头上,抗震医疗队来了,检查四哥的伤势,发现腿骨断了,需要立即转院。同村的阁平叔砸坏了牙巴骨,后来他们结伴坐火车到安徽合肥去治疗。
十天后,父亲用秫秸搭了一个简易抗震棚。两个月头上,大队发了七根檩子的救灾物资,父亲又从废墟中清理出一些物料,用嫂子背回的大队部的秫秸把,盖了三间轻便草房。
四
过“五七”的那天早晨,我被越支庄巨大的哭声惊醒。
先是暗淡的天光中,看见自己的父母跪在院里一堆火的前哭。從火中冲出的黑色纸页向渐白的天空飞腾。接着,听到了远处一个妇人的哭声,悠悠扬扬的,像点数着某个人,再接着,掺进一个男人的哭声,扯开嗓子的号啕大哭。
一个村庄瞬间被哭声点燃了,一个多月的悲伤、思念、恐惧、压抑、苦楚,似乎全都打开了闸门,找到了宣泄的渠道,并且一股脑顺流而下。
几百人同时死亡的“五七”祭奠(我家附近的四五个门,死了23口),这是越支庄自元朝立庄几百年来绝无仅有的一次。一个村庄在痛哭,呼天抢地,哭爹喊娘,呼儿唤女,上气不接下气地抽噎,此消彼长的号啕。睹物思人的悲戚,家园被毁的忧伤……哭亲人,哭邻人,哭自己。
我不知道,一个村庄的泪水,浇灌在这样晨昏交接的微明里,会开出怎样的花朵?
我没有哭出声,只望着简易棚顶抹眼泪。泪光中闪现的,是绾着发髻的奶奶,一双小脚盘坐炕上,微笑着,等我拎着酒瓶去打那八毛四分钱的白薯干酒;不停干咳的三哥,大了胆子,背着母亲抽旱烟;还有热心肠的大妹,拦住路人永不疲倦地问,你奏(干)啥去呀?还有蹒跚学步的侄子……
哭,开了头,是会产生惯性的,像辕马受惊,无法收缰。“五七”后,小范围的号哭,总在某个清晨或是夜半没来由地响起。
对门的无关老太是我的棋友,小时候玩象棋,往往第一步提炮巡河,然后瞄象,趁对方不备,打象将军抽大车。还有就是炮走当头,拱中路兵,再拱,对方拱掉,打掉对方的老将。我的这些招数,无关老太皆能识破。
地震中,无关老太死了。无关老太爷烧火做饭,想起老太来,忘掉灶膛里的火,也忘掉锅里翻滚的玉米碴粥,跑到北门外,用烧火棍划拉着的泥地,哭,老婆子,你去哪了呀,快回来呀,咋撇下我不管我了呀。
他哭得撕心裂肺,老泪纵横。
无关老太爷有名有姓,非常诙谐,也非常豁达,他的年龄活到了坎上,别人问他,有关吗?他答,无关呐,无关老太爷的绰号由此得来。老太死那年,他73岁。
我不知道,除了无关老太爷,越支庄这样的悲痛的怀念还有多少?
五
震后,陡河里的鱼特别多,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多到你下到了水里,鱼会咬你的脚,你抬起脚来,鱼会钻进你的脚窝里翻腾。捉鱼,易如反掌。
双喜和双全说,那是因为河里的鱼吃惯了死漂,喜欢上了人味儿。
地震那天大河里都是死漂(死尸)。也许他俩说得对,他们一家上了陡河埝。他俩还说,还有牲口,有活的也有死的也顺流漂下来。
大河里的死漂我没看见。老得儿说,北坑里也有死漂,北坑里的我也没看见,但一次在西坑摸鱼时,我在一个人的头盖骨里捉到了一条黑鱼。不知道这个兔崽子钻到那里去干啥?
借助高大植物的掩护,越支庄外的青纱帐里跑着许多猪。那是被地震吓怕了的“震漏儿”,它们躲到了庄稼地里,啃食高粱、苞谷不肯回家,慢慢地有了野性,也许,它们不敢奢望,倒下的村庄的温馨与祥和是否会重新站立,所以才皈依了田野,当作它们甜美永久的故乡。
那时候,民兵手中还有枪,七九、半自动全有。打猪,不仅可以练枪法,履行护秋职责,还有猪肉吃,三全其美。
到了秋后,青纱帐倒下,猪,亦没有了踪影。
我家的猪圈塌了一个角,孕中的老母猪被砸,却命大自己钻了出来。
等到母猪下崽的时候,生一个是死的,生一个是死的,一连七八个都是死的,母亲见状灰了心,一赌气回屋睡觉。到天亮时,老母猪在圈里哼哼,一个小黑猪拱着它的奶头吃奶,母亲给老母猪炖了锅米汤,倒进猪食槽里。
但小黑猪后腿无法站立,只能拉着后腿走路,它豁出命去吃,豁出命去长,九死一生的猪,最后在它挨刀见阎王之前,也没能长得像模像样。
唐山大地震给万物生灵带来的恐惧感,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够消除的,很可能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