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绛是我心目中的大先生
沈祖炜
学养深厚、温良谦恭的社科院前辈
我在1979年到上海社科院读研究生时就认识陈绛先生了。
陈先生在“文革”前是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员。“文革”结束,社科院复院时,他没有回社科院,而是去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教授。因为他是近代经济史的专家,人品又好,所以经济研究所的学术活动都会邀请他前来加盟。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们的专业老师。他同丁日初先生的关系特别亲近,我又长期跟随丁先生工作,所以我同陈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很多。陈绛先生常常来社科院参加外宾接待和学术研讨会。丁先生发起成立经济史学会、组织中山学社、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和《近代中国》丛刊,或是组织《上海近代经济史》课题研究,许多工作都喜欢找陈先生商议,邀陈先生参加。中山学社的《近代中国》第一辑出版时丁先生任主编,陈先生和我是副主编,陈先生丝毫不摆老资格,令我颇受抬爱。《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出版时,丁先生是主编,我任副主编,陈先生和多位前辈学者都是课题组成员,但是陈先生不计个人名位,积极支持我的工作,令我大为感动。丁先生、陈先生和我曾先后担任上海市经济史学学会会长,在如此的学术传承关系中,陈先生的道德精神、学术魅力都让我折服。中山学社的《近代中国》从2003年的第13辑到2016年的第25辑都是陈先生任主编的,而陈先生的实际贡献在先前协助丁先生主编的12辑中都有卓越的体现。陈先生主持《近代中国》的特点:一是视野开阔,汇聚中外学界关于孙中山研究和近代中国研究的各种成果;二是包容性强,只要言之有理,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三是提携后进,特别乐于采用一些年轻学者的论文;四是治学严谨,编辑工作细致规范。直到如今,《近代中国》屡屡获评CSSCI来源集刊,这与陈先生打下的基础也是密不可分的。

1990年,陈绛(前排右一)在上海社科院与张仲礼(前排左一)、王元化(前排中)、丁日初(前排右二)、姜义华(后排左二)、李华兴(后排右一)等合影
上海社科院张仲礼院长主持《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现代化》以及《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重点课题时,都邀请陈先生前来参加相关的研讨会或论证会,所以我觉得上海社科院的许多经济史研究成果都蕴含陈先生的智慧和贡献。陈先生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温良恭俭让”的美德,一副谦谦君子的架势,说话不紧不慢,做事细致认真,让所有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深受教益。我们经济所的蒋立先生晚年写了一部自传《学生·战士·学者》,2001年病危期间,希望看到书稿校样。为达成他的夙愿,各方面都给予他大力支持。这本书并不是由出版社出版的,而是经济所帮助印刷的,所以需要的是义务劳动。这时,同蒋立先生颇为熟悉的陈绛先生二话不说,接手担任书稿的校订工作。辛苦了整整十天,将书稿清样交到蒋立先生的病榻上。蒋先生宽慰地抚摸着清样,安详地离开了人世。陈先生急人所急,无私地帮助老朋友的精神令我深为感动。我从心里敬重他,既从他那里学到了专业知识,更学到了待人处事的品行。

陈绛先生最后几年以病床为书桌,治学不辍(沈飞德摄)
陈先生的英文功底十分扎实。他曾撰文评述美国学者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的两个中文译本。他极为仔细地将两个译本进行比较,并同英文原著进行对照,指出了不少翻译上的错误。陈先生还有一部厚厚的译著《赫德日记》,我觉得翻译这部书是非常难的,其中牵涉的人名、地名、机构名也十分复杂,当年赫德写日记时,并没有中英文互译的规范,在其记述中还有不少按照粤语发音写成英文的名称。陈先生对于其中可能有歧义的地方一一做了考证,在译著中用注释清晰地加以说明。正因为陈先生的精准翻译,《赫德日记》才能被大家读懂。
积极履职、老有所乐的文史馆馆员
2009年我到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上任,首先想到要向身为馆员的陈先生报到。上海文史馆是一个统战性、荣誉性的文化单位,能被市长聘为馆员,足见陈先生的学识人品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可是陈先生没等我上门看望,就来文史馆参加馆员的学习会了。陈先生一点架子都没有,我称他老师,他却回称馆长、领导,弄得我很不好意思。陈先生是福州人,他是晚清大吏陈宝琛的侄孙,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我觉得,他是远离政治时髦、勤勉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典型,是我心目中的“大先生”。但是对于文史馆的活动,他却是积极的参加者。后来即使身体不佳,步履艰难,他也会努力争取到场。文史馆组织研讨会等,他会积极撰文参会。
2013年,馆里组织部分馆员编写口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郭志坤馆员自告奋勇,为陈绛先生口述史执笔。郭先生说,因为崇敬陈先生的学问和为人,十分愿意做点贡献。陈先生和郭先生的合作开始后,我也常常过问。陈先生醉心于自己的学术活动,对于郭先生的撰稿,力主添加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样两位先生难免意见相左。我觉得,口述史还是要以人生经历为主线,反映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从个人展现社会,不能写成学术自传,所以要大大删减学术著述内容的详细介绍,而要讲出撰写这些学术论文背后的心路历程,写出历次学术交流活动过程中觉察到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而反映出学术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进程。陈先生虚怀若谷,很快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割舍了自己曾经非常执着的内容。《陈绛口述历史》和其余十几位馆员的口述史陆续出版,成为上海文史馆的一个工作亮点。因而我特别感念陈先生的大家风范和大局观念。
2018年文史馆为逢十整寿的馆员举办集体祝寿活动,九秩高寿的陈绛先生也来了,当然他是由儿子用轮椅推来的。我这个70小寿星与他90老寿星相会,见他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打心眼里感到高兴。2019年春节前我偕妻子去他休养的徐汇区中心医院探视,见他半张床上都堆着参考书,小桌板上放着手提电脑,他不顾医生的劝告,每天敲击键盘,他正在为自己的姑妈、一位著名的文化女杰编写《年谱》。陈先生的学术精神与工作热情令我十分感动。临告辞时,陈先生坚持移动脚步把我们送到电梯口,怎么劝阻也没用。陈先生所体现的老一辈的礼数太周全了!

沈祖炜和陈绛合影
豁达睿智、不偏不倚的人生智慧
2019年8月20日突然接到陈先生逝世的消息,学界朋友纷纷表示哀悼之意。据其公子说,陈先生接到刚刚出版的上海文史馆编《仁者寿:文化名人的学术人生》,就在病床上挣扎着要看看书中怎么写的他,看着看着就慢慢地睡着了,此后再没醒来,也算是平静地走了。在为他举行丧礼的那天,恰好是上海社科院举办的中国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我因有任务在身无法前去为陈先生送行,只能在心中为他默默致哀。在会上许多经济史专业的同行,得知陈先生仙逝的噩耗,无不为之动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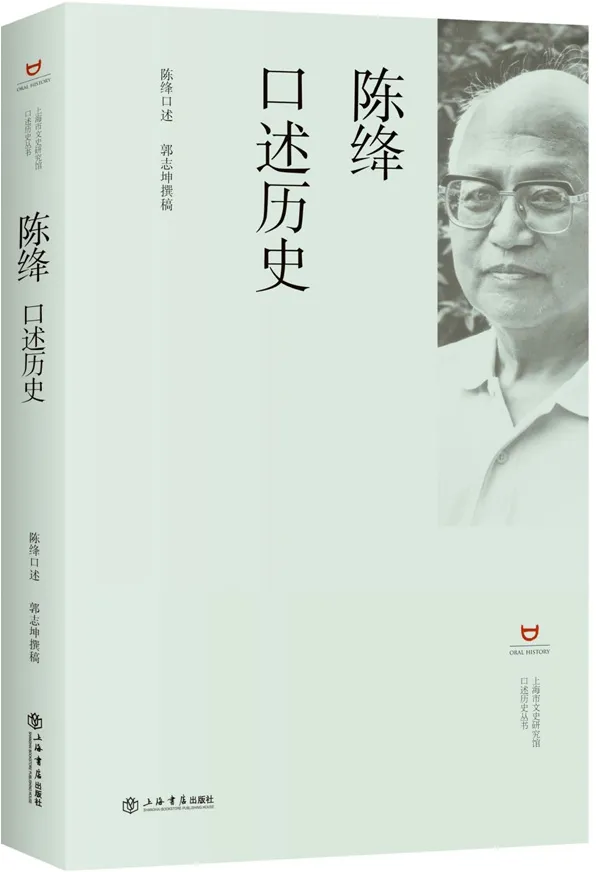
《陈绛口述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在后来上海中山学社召开的陈绛先生追思会上,各位学社同仁纷纷表示缅怀之情,大家都对陈先生的学识、人品深表敬意。华东师大的易惠莉教授说,在中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陈先生是没有受到重大打击的少有的人之一,因为他一生谨慎,从来没有过激的言行,遇到委屈和不平,总是“忍”字当头,其实内心是非常苦的啊!确实,陈先生除了曾被“发配”黑龙江,以“慰问”下乡知青为名,在边陲之地经受过一段艰苦生活的磨难,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大的打击和波折。我以为,这同陈先生在复杂的政治情势下始终采取不偏不倚的处事态度和豁达睿智的待人之道也是分不开的。他不激进,也非守旧,他能够中道理性地守住底线而做到独善其身。尽管他的内心也会很苦,但是他得以平安度人生,这难道不是一种大智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