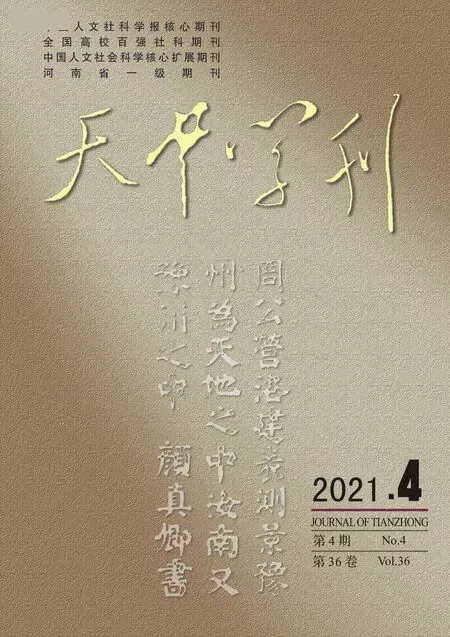清代辞赋发展三论
孙福轩
清代辞赋发展三论
孙福轩
(浙大城市学院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15)
清代辞赋作品众多,体式兼备,集历代之大成。然因经典性不足,多有“胜形旨微”之论。然其承续元明辞赋衰落后复兴的创作轨迹、作品的多元与集成特征、作家的地域和流派归属,实为辞赋创作史和赋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对于当下的辞赋研究亦不无启示意义。
清代;辞赋;特征
辞赋文学由“诗”“骚”发端,经两汉骚体赋、散体大赋,魏晋六朝骈体赋,至唐宋律赋兴盛和其后的文赋创生,体变已穷。后经元明两代之复古,至清代又大盛,可谓“轶迈前古”“奄有众长”“集周秦汉魏唐宋元明之大成,合性理、训诂、考据、词章而同化”[1]2。据马积高主编的《历代辞赋总汇》“前言”称,全书合计收辞赋作家7450余人,辞赋作品29100余首。而清代辞赋作家竟达4810人,辞赋作品达19499首①,超过清前历代辞赋作品一倍之多,当然这还不能说是清代赋家赋作的全部。虽然文学史上从来不以作品的数量多寡来确定文学的“经典地位”,但如此众多的赋家和赋作,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十分重要的现象。它的发展演变轨迹、多元与集成的创作特征、作者的地域与流派归属等,实为清代赋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命题和范畴。
一、轨迹:承衰复盛
古代辞赋,缘于“诗”“文”之间的游移,体式上有诗赋、骚赋、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分,至宋而体式渐尽。如果按照时代而言,又呈现出发展脉络的“马鞍型”特征:汉魏至宋金,或为一代之文体,或缘于文笔之辨、文体细分对赋艺的骈俪化追求,或出于选荐和科举考试之需,辞赋创作呈现繁荣态势;元明两代辞赋中衰,且多以古体赋创作为主,律体赋不显,尤其明代更是如此。这一方面缘于科举制度、文教制度的变迁,元代延祐年间变律为古,科举改试古体赋,明代易之以八股文,只在制科、礼部吏部试、翰林院馆课和庶吉士试有个别考赋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性理之学大兴,元明两代浅陋不学、俚俗少文,面对“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之文体博识雅致、笔法精研之要求,自然从主客观角度来看都没有可能做到力挽狂澜。特别是明代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时代因素更是对辞赋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包括明初的政治高压与文化强权政策对文学的破坏、台阁体盛行、对作家群体的摧残,重理轻文、八股取士制度对文学思想的束缚和文艺才能的侵夺以及复古秦汉与唐宋古文的主流散文话语对骈俪体式排斥倾轧,李梦阳“唐无赋”对律赋的排斥,等等,造成“明代辞赋本身整体成就不高,不仅没有形成新的体式,而且在艺术上也无新的拓展,所论问题均是在原有模式上的局部选择、重组和改良”[2]100。这里,对明代后期辞赋要稍做辩解。马积高说:“清代辞赋同明代后期辞赋的发展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汉文赋体和骈赋体的复兴就是从明后期开始,至清而益盛的。”[3]150清代辞赋继承的是晚明的汉文体赋、骈体赋和骚体赋。对清代辞赋而言,晚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它上承南宋以来辞赋创作之衰,下启清代辞赋之盛,站在一个孕育文学质变的历史转折点上。
清代承元明之衰而臻于“极盛”。辞赋体制兼备,风格多元。如律体赋创作继承唐宋而在格律、题材方面有所深化。唐代科举试律而律赋起,以王起、李程、谢观等为代表的著名律赋家创作的气象正大之作成为辞赋创作的典范。唐宋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的核心理念和散句单行的行文风格,以道为本,以六经为根源,把文学的重心放在道德方面,一种抬高儒学性理、轻视词章修辞的主流倾向得到不断强化,社会在潜移默化中经历着由文学时代向理学时代的深刻转型。唐代的科举试赋兴替、宋代的诗赋与经义之争也无一不对律赋的地位发起挑战。至元而以情立体,改试古体赋,赋得以兼综,至明代赋因华而不实被彻底废弃。清代重拾科举试赋,这种科考是绾合汉代荐举与唐宋(元)科举试赋而为一代之文教制度,并以对理学、经义的推崇而确立规范。前期题材不拘,多有冠冕正大、博纵肆恣之风。嘉道以来由唐律而转向时赋,追求格律谨严,法度细密,遵循“醇雅”“清丽”的赋风,越唐赋而尚时趋,终成一代彬彬之盛。以古体赋创作而论,清代兼有诗、骚、散、文等各种体式,且随着时代思潮涨落起伏,尽态极妍。清初骚、散、骈赋居多,以骚体赋为主,寄寓家国情怀;康熙朝以来舆地赋等散体大赋振起,形成多元发展态势;咸丰、同治以降,由于政治形势和国运的日渐衰落,抒写情志的骈体、散体、骚体赋居多。终清一代,古体赋祖骚宗汉,因情立体,有汉大赋的博综闳衍、纵恣汪洋,有六朝骈赋的含蓄婉转、清丽自然,有宋元赋的因理生义、风格苍然。虽然不主一格,但对情感的重视和文学性表达是其最为鲜明的特征。
就创作现象和体式而论,仍然需要对元明辞赋“中衰”做出更深层次的观照。一般来说,学界认为元明两代辞赋留存数量不多,创作成就不高。浦铣《复小斋赋话》说:“唐人赋好为玄言,宋元赋好著议论,明人赋专尚模范《文选》,此其异也。”又曰:“雅不喜明人赋,以其模仿而无真味也。”元代改试古体赋,性理之学兴起,义理成为辞赋表达的中心,刘埙在《隐居通义》提到赋的“义理深长”,其总论古赋云:
作器能铭,登高能赋,盖文章家之极致。然铭固难,古赋尤难。自班孟坚赋《两都》、左太冲赋《三都》,皆伟赡巨丽,气盖一世。往往组织伤风骨,辞华胜义味,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是以浩博胜者也。六朝诸赋,又皆绮靡相胜,吾无取焉耳。至李泰伯赋《长江》、黄鲁直赋《江西道院》,然后风骨苍劲,义理深长,驾六朝,轶班、左,足以名百世矣。近代工古赋者殊少。非少也,以其难工,故少也。其有能是者,不过异其音节而已,而文意固庸庸也。独吾盱傅幼安自得深明《春秋》之学,而余事尤工古赋。盖其所习,以山谷为宗,故不惟音节激扬,而风骨义味,足追古作。[4]卷四
追求义味与风骨相结合,老峭与清峻互渗,要有老味。明代文学复古,模拟之风盛行,所以浦铣才言其缺乏真味。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赋由诗、骚而散,虽多汪洋恣肆、铺采摛文之风,却缺少应有的婉转隐约、情韵悠长。后由散而入骈、入律,虽多格律声色之美而乏动宕开阖之姿。此后宋代解律为散,却引来“一片之文只押几个韵耳”之讥。可以说,随着唐宋以来的科举试律赋,宋初的以经义命题,辞赋越来越失去情感的感染力而走上格律、字法、句法的形式追求。元代改试古体赋,祖骚宗汉,以情为本,又重新开启了辞赋对情志的归依;明代改试八股文,但前、后七子和唐宋派、晚明的六朝派以复古为创新,把文学从理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成化、弘治年间,以前、后七子为主体的复古思潮,挣脱理学对文学的控制,使各体文学逐渐走上以情为主的审美化道路,直接将宗法的文学范式上溯到秦汉、六朝,在辞赋上的表达即是提出“唐无赋”“赋属诗”说,使辞赋创作回归到性情之路上来。
追溯辞赋历史可见,自宋以来,辞赋创作的衰落一直是与理学的发展扩张相关联的,以道统为指向贬抑文学的倾向经元而至于明,不仅被持续继承,而且还通过与中央政治文教体制、国家意识形态的结合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终于在明初废弃元代的古体赋而改试八股文,从此辞赋创作变得或为肤阔之辞,或为谀颂之言。针对文坛的空疏之风,明中叶终于爆发了对这一理学化趋势的反抗,祝允明大胆喊出“学坏于宋”,对统治思想文化界数百年的程朱理学给予坚决的否定。以吴中文士的思想和创作一变而为对古典文学审美主义的重拾,从而再次建构起辞赋创作需求的思想基础。反过来,这股文学思潮对于理学统治的渗透也起到了强有力的解构,前、后七子的辞赋创作和晚明的辞赋创作、编纂,已经注重辞赋的情感内涵和排偶谐律等文学因素的表达。明中叶的辞赋创作是当时整个时代文学审美主义新潮下的产物,它从根本上阻断了唐宋以来性理之学对辞赋文学属性的侵蚀,结束了辞赋长期沉沦的命运,开始走向晚明乃至清代辞赋创作的复兴与繁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对于辞赋创作的元明中衰不能笼统视之,元代的祖骚宗汉、因情立体是对辞赋文学属性的回归;明代辞赋创作前期确实因理学盛行而无所成就,中后期以来则慢慢呈现复苏的态势。所以无论是明代辞赋史还是整个辞赋发展史而言,明中叶都是一道由衰返盛的分水岭。虽然清代的辞赋创作并没有完全遵循元明以来“以情立体”的传统,但在经历了长期科举之后,特别是宋代解散赋体而“横骛别出”“流丽有余,琢练不足”的创作末路后,还是起到了使赋回归“正统”的作用。
清代辞赋承元明而复盛,近人刘咸炘在《文学述林·文变论》中云:“赋之为诗,诗之为词,词之为曲,其变也乃移也,非代也。盖诗虽兴而赋体自在也。铺陈物色固有宜赋,不宜诗者矣。”[5]1819从文体的描绘性、抒情特征说明诗赋绵延“自在”的文体原因。清代辞赋之盛一方面是文体自在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制度的推动,表现在“众体兼备,争胜前朝。从各体赋中剥离最典型特质,加以充分表现。如用大赋应制,富丽如《甘泉》《上林》,而旨归于醇正,强化其润色鸿业的功能”[6]112。清赋之盛,表现在作家作品众多,出现了一批辞赋名家,如律赋四大家吴锡麒、顾元熙、陈沆、鲍桂生,古体赋家王夫之、张惠言、王闿运等,终成一代之“经典”。此外还有众多的赋总集、别集,总数应该在500种左右。收录千首以上的大型赋集至少也有十数种,至于像《历代赋汇》《赋海大观》收赋数量都在万首,《赋海大观》更是宣称两万有余。出现了辞赋批评的热潮,有数十部的赋话和序跋、书札等论赋文字,成为辞赋批评最系统、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
对清赋之“盛”的理解,当然不能完全以数量言之。置于中国辞赋发展史来看,一些学者甚至直接以清代为赋的衰落期,如叶幼明在《辞赋通论》中把辞赋发展分为五期,先秦为发轫期,汉代为发展期,魏晋六朝为转变期,唐宋为高峰期,元明清为衰落期。因为清代辞赋在体制形式没有新的变化,在主题和题材没有新的拓展[7]121–135。许结也认为清代辞赋是“形胜旨微”。形胜是指数量多,体裁风格多样,无一物不能入赋等;旨微是指体式、主题、内容的创新不足,没有产生有重要影响的赋家和赋作等。谈到清代辞赋历史命运时,而又直接以五穷命之:一是时序之穷;二是体式之穷;三是风格之穷;四是资养之穷;五是文词之穷。合此五穷,中国古典辞赋至清代的衰亡,也就不可避免了[8]6。这些说法都是十分有道理的。一种文体经典形成以后,后世就很难完成“超越”,只能是横鹜别出,另辟蹊径。对清代辞赋“复盛”的理解,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看待,既有形胜,数量上的绝对“超越”,其中亦有部分经典的形成。但无论如何,其体式、风格确实没有多少新变,因而创新性不足。对于其“盛”的一面,不能做过高评价。
二、作品:多元与集成
清代由于科举试赋,同时出于兼综和集成的心态,无论从作者人数和辞赋数量上均达到高峰。虽然辞赋发展至清代,体式已穷,清人也没有太多的创新,但却以自己的理解和时代气象的凝聚,显示出恢宏开阔的气势,表现出集成与多元的特征。
谈到清代学术,郭绍虞有很好的总结:“清代学术有一特殊的现象,即是没有它自己一代的特点,而能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它没有汉人的经学而能有汉学之长,它也没有宋人的理学而能撷宋学之精。他如天算、地理、历史、金石、目录诸学都能在昔人成功的领域以内,自有它的成就。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义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种以外,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9]6由此也可以观照清代辞赋之风。
其一是无一己之特点,兼有以前各代之特点,这既是言清代学术,亦是言清代文学。清代辞赋的多元性首先表现在体类的齐备。清代辞赋创作从大致面貌来看,实可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特性鲜明的时段:清初承袭晚明,推尊六朝辞赋,有着明显的复古倾向,文体赋、骚体赋、骈体赋等创作繁兴,而律体赋创作明显不彰;康熙推尊律体以后,出现古、律争盛的局面,在乾、嘉以至道光朝表现得十分明显;咸、同之际,律赋创作出现嬗转,由“趋唐”转向“时赋”,风格一变初、中时期的沉雄博丽而追求清丽芊眠的艺术境界,而古体赋因时局衰变而复兴振起,祖骚宗汉。从其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虽然每个时期的创作风尚不同,体式各异。但清代辞赋众体兼备,集历代辞赋体式之大成,则是处于历史总结期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俞士玲在谈及清代这一特征时说:“众体兼备,争胜前朝……对于律赋,清人以唐律为典范,但在用韵上,‘唐二百余年之作,所限官字,任士子颠倒叶之。’(王芑孙《读赋卮言·官韵》)而清律必依次用足官韵,因难见巧;其句法也更为谨肃整饬。”[6]112清代辞赋在前代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泛入众体,正与清代学术心态上的兼容历代而精益求精的精神密切相关。

其三表现为体裁与主题的扩大。在题材的选择上面,清代辞赋也有超越唐宋律体赋之处,“律赋之则,气主条达,无象不呈;象属高华,靡气弗适。其畛域为历代所未备,至我朝而后能事必著,厘然灿然。”[11]660真可谓“无事不可入,无境不可绘,无意不可通”。刘熙载《艺概·赋概》说:“赋家之心,其小无内,其大无垠,故能随其所值,赋象班形。”[12]132今人詹杭伦说:“清代律赋出自唐代律赋,而在题材之广阔,立意之深邃,层次之绵密,押韵之规范等方面确有突过唐人之处,取得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文学成就,成为一种更加规范、可操作性强的文体。”[13]398在对唐代辞赋的倾慕与模拟中超乎其上,在律赋创作上不断精益求精,尤其是在格律严谨、声韵谐美、层次绵密、立意深邃等方面尤为突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唐律赋,呈现出“无象不呈”“厘然灿然”之态。
其四是理论的集成。清代作为古典赋学理论的集大成期,其上溯楚骚,中包唐宋,兼括元明,表现出对历代赋学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和海纳百川般多元并呈的格局,对此前的赋作、赋家均有较系统、较深入的评论与研究。即使是对于历来遭受非议的宋代文赋,也不乏褒扬之论,如姚鼐《古文辞类纂》唐宋赋作选录甚少,但仍选入了苏轼的《赤壁》二赋,并引用方苞言:“所见无绝殊者,而文境邈不可攀。”[14]1309对于元、明两代的复古赋作,清人浦铣也多有评骘。然就主导倾向而论,清代律赋宗唐,古赋祖汉宗骚的主旨没有改变,理论批评多体系性建构,而缺乏应有理论创新。
三、作者:地域与流派
文学和地理的关系极为密切,《诗经》十五国风即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特色。汉代班固《汉书·地理志(下)》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评论《诗经·国风》的特点及其成因: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邰,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15]1642。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15]1644
班固以风俗为中介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将《诗》与其产生的地理环境加以对照,可以说是地理与文学交叉研究的早期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班固《汉书·地理志》已经开创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先声。此后魏晋时期的曹丕和南朝齐梁间的刘勰亦论及地域和作家才性之间的关系。最为著名者是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出的南北文学之别:“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6]1730后世沿承其说,一直到晚清民国初年的刘师培撰写《南北文学不同论》,基本仍是同一理路,只不过多了一些现代学术层面的观照,在思想史、政治史的密切互动之中,呈现出一种超出文论史的暧昧性与复杂性。
文学地理是基于地理的分野而呈现出的文化的差异,由此而影响着此地的文人性格和文学面貌。刘跃进在《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中把秦汉的文学地理单元划分为三辅地区、三楚地区、鲁、齐、河西走廊、江南、巴蜀、黄河以北(三晋)等地,近年来的江南文学研究、地域文学研究,也无一不是这种思路和观念的典型表现。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人口的流动性很弱,一个地域的风俗习惯相同,容易形成一个地域的语言和文化,也会影响一个地域的思想观念和文学创作,文学由此表现出不同的气质和风貌。
辞赋作为文学的一种形态,产生之初即有明显的地域分野。如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赋和以荀子为代表的散赋即是不同地域的表现。但随着汉代献赋之风的盛行和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渗入,特别是唐宋以来的科举试赋,作为一种极富政治性的文体,由于受到政治和文教政策的极大约束,规范性越来越强,其地域性表现反而并不是太明显②。与其说是文学的地理性,倒不如说是赋家的地理分布更为准确一些。
从赋的发展史而言,先秦的南北分野自然是文化地理的影响所致,至汉代,初期形成藩国作家群,这基本上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并不必然表现出辞赋的地理性分布。张建伟、王静《论汉赋作家的地理分布》一文据《全汉赋》等文献统计:三辅、河洛、齐鲁、江南四个文化区汉赋作家人数较多,均在15人以上;荆楚、幽并文化区汉赋作家人数在10~15人之间;河西、巴蜀文化区汉赋作家人数最少,均在10人以下。幽并文化区中河北赋家数量占总数的92%,江南文化区中江苏赋家数量占总数88%。相比西汉,东汉时期陕西、河南、河北、湖北赋家人数明显增多,甘肃、宁夏、山西、浙江赋家人数实现了零的突破。该文分析造成赋家地理分布不平衡的因素主要有地理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教育因素、家族因素等[17]。文章并没有给出各个区域辞赋的创作面貌和地域差异性分析。从全汉赋的创作来看,除去赋的地理书写的差异外,赋的地域性特色并不明显,如果勉强命之为作家群落,也只是由于归属地的相同,作家的个性差异,包括语言、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并没有形成后世诗文或者文学团体的共同主旨或者创作风貌③。
这种辞赋创作的倾向自汉代以来,经魏晋南北朝基本如此,隋唐科举肇兴,辞赋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因文教制度的强制作用使得地域色彩越来越淡化,一直发展至清代也是概莫能外。可以说清代辞赋的地域性,依然表现的是创作群体的文化地理归属。只不过清代和前代有所区别的是,辞赋创作的兴盛是由江浙等东南地区而渐次北上南下,并进而达于全国范围的。这和辞赋作为清代亲和政策一部分的作用相关。清初南方的复明运动,强大的士绅阶层和社党势力,使得清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疏于南方人士,直到顺治末、康熙初年,清廷基本上消除了南方的复明势力,缙绅阶层得到有效抑制。特别是康熙帝几次南巡,逐渐以辞赋等作为亲和的文教政策后,辞赋才逐渐兴盛起来。俞士玲言:“清代辞赋,最初是在康熙皇帝与他身边的南方儒士一些文学活动中渐呈兴旺之状的。如康熙十四年(1675)瀛台宴上,单是昆山一地就有叶方蔼进献《瀛台赋》、徐乾学进献《经史赋》等,之所以选择辞赋,一因辞赋最能体现作者才学,‘非学优才高者,不能当也。’(沈作喆《寓简》引宋初进士孙何语)二因历代奏御自献有影响者,多用赋体。此后,不少南人渐抵京师,效忠新朝,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18]76康熙十八年(1678年)举行博学鸿词科,试题为一赋一诗,赋即为《瀛台赋》,应试者152人,中式者50人,其中40人来自浙江和江南,由此可见一斑。康熙五巡江南,其目的也多半是为此。期间他敕令浙江海宁人大学士陈元龙编纂《历代赋汇》,并亲自为之作序,明确辞赋对于简拔人才的重要作用和政治用意。首先,清廷第一次以辞赋号召天下,辞赋的影响由东南扩大到全国,这是清代辞赋文学地域性深受政治影响的显明特征;其次,它标志着作为南方亲和政策一部分的辞赋的消失,辞赋将以自身“闳肆漫衍”等特长,在清代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辞赋和八股文等文体一样,作为清代文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制着当时的文风,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这也可以从赋集编纂者的籍贯来一窥端倪。清初期的赋集编纂者以江浙一带为多。如康熙朝几部重要的赋选中:《历朝赋格》的编选者为陆葇,平湖(今属浙江嘉兴)人;《历朝赋楷》的编选者王修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代赋汇》的编选者陈元龙,海宁(今浙江海宁)人。此前和此后一些重要辞赋选本的编纂者也很多为江浙等地学者,如《华国编赋选》的选者孙濩孙为高邮(今属江苏)人,《国朝赋楷》的编选者胡浚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国朝律赋偶笺》的编选者沈丰岐为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律赋衡裁》的编选者周嘉猷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本朝馆阁赋前集》的编选者叶抱崧、程奂分别为南汇(今属上海)和长洲(今属江苏苏州)人,《律赋清华》的编选者吴锡麒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赋海类编》的编选者关槐为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一直到清代末年,最大的赋总集《赋海大观》虽然不能确定编者具体为谁,但从诸多线索中大体也可以说和浙江相关。从入选的赋家来看,“现存律赋较多的赋家有:汪由敦、全祖望、齐召南、胡天游、金门诏、冯浩、朱摘、汪学金、吴锡麒、侯凤苞、王芑孙、杨棨、鲍桂星、张澍、李宗昉、陶澍、顾元熙、佘文铨、王家相、翁心存、夏思恬等。其中为选家所瞩目者有:汪由敦、齐召南、汪学金、吴锡麟、侯凤苞、王芑孙、杨棨、鲍桂星、顾元熙、佘文铨、翁心存、夏思恬等”[18],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人。只是中后期以来,其他地方书院、选本才逐渐增多,如江西、福建、广东、陕西之类,后期广东经济发展,文化重点南移,刻印的数量也不少。总体上呈现出由江浙向全国辐射的趋势。
和赋家的地域性相较而言,辞赋的流派表现得更为微弱。我们知道,文学流派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文学观念和风格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群体组合,是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走向自觉与独立的产物,是文学趋于成熟和繁荣的重要标志。无论是有意识或曰无意识,文学流派都必须是在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才得以产生的,必须要有一定的统系、代表作家和大致相类的创作主张和风格。魏晋以来,诗、词、文形成不同的流派。清代作为历代文学的集大成时期,诗、词、文等各类文体都有不同的流派呈现,如诗有河朔诗派、岭南诗派、虞山诗派、浙派、常州诗派、同光诗派等;词有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文有阳羡派、桐城派、湖湘派、六朝派;骈文有六朝派、三唐派、宋派,按地域则有常州派、扬州派、浙派等。至于各派别之间的论争,从流派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而明代尤剧。清代各诗文派的论争,某种程度上既是前人文章之争的延续,同时又是当时思潮的反映。如考据派、史学派和桐城派在清代乾、嘉、道时期展开了较为激烈的文章正宗之争,目的是为自己的流派争宗夺统,借以取得政治上和文学上的话语权。但和清代诗文有所不同的是,由于清代试赋和辞赋的政治属性,辞赋并没有表现出和诗文相类似的流派的多样性,而仅仅是创作取尚的不同。从清代辞赋发展来看,其辞赋创作仅有取向汉魏、六朝、唐宋之殊异,其实是就风格和宗旨、古律而言的,自始至终并没有形成如诗、词、文那样鲜明的作家群落和流派。
而如果仅仅出于地域考虑,可以大体上根据作家的地域区分来做一些简略梳理,把清代赋家分为浙江赋家群、常州作家群、扬州作家群、湖湘作家群等。此外还可以根据辞赋主张之不同分为馆阁派、古文家派、骈文流派、经史家派等。总结起来,就是三体和三派:三体为律体、古体与时体(亦为律体之一种),三派为汉魏、六朝、三唐。但正如上文所言,各派之间并没有表现出过于殊异的流派特征(古律之辨也没有前代表现得明显)。这与当时骈文家的分宗立派以及古文家宗主韩愈、欧阳修是明显不同的。至于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和统治者的提倡试赋并以唐律赋为最高标准有关,虽然律赋的写作可以借鉴古体赋作的气韵和格调,但考官看重的毕竟是以唐律为准则的起结、音律、典实、对偶等内容。创作是如此,以此为基础的律赋理论自然也不能例外,从而形成唐赋独尊的局面,由此地域和流派的特色自然也就表现得不那么突出和明显了。
综上所论,清代辞赋虽然没有汉、晋、唐赋的“经典”地位,但因作品众多、体式多元而在古代辞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清代辞赋创作上承元明之衰、因科举试赋的刺激而“复盛”,作品兼备历代赋的体式而有所推广,辞赋家由于对唐代律赋的推尊而表现出地域和流派色彩减弱。如果放在整个辞赋发展史和赋学研究的视野下,这些都是清代辞赋的主要特征,值得关注和研究。
① 当然这还不是清代赋作的全部,尤其是律赋遗漏甚多。马积高在《〈历代辞赋总汇〉前言》(《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中说:“这次辑录进行得是比较广泛的,除了宋人郑起潜《声律衡裁》所载的唐宋人律赋的残垣断壁未进行一一比勘辑录外,对明以前的总集、别集及我们所能找到的部分地方志所载的辞赋作品,做了广泛的全面的收集,较以前的几种辞赋总集,如陈元龙《历代赋汇》、鸿宝斋主人《赋海大观》,篇幅都有较多的增加,可能还有遗佚,但不会太多了。至于清代辞赋,我们虽收有作家4000余人,作品近20000首,但清人集部到底有多少,目前尚无精确统计数字,恐怕还有许多手稿未被发现。故清代可能遗佚较多。但主要是清律赋。”
② 潘务正有《清代赋学特征三论》(《天中学刊》2019年第5期)一文,其中所言的第一个特征即为“赋学的地域化倾向”,从嘉道以来科举试律赋的衰落和文学性增强的创作实况谈及以地域命名的赋集开始出现、在赋学研究中贯穿地域流派的学术思想、在赋集与赋话中凸显地域流派的文学主张。虽然上述诸端有一定的倾向性,但还谈不上赋家和赋学的地域性特征。
③ 此外,涉及赋文学地理相关的论文有叶晔《游与居:地理观看与山岳赋书写体制的近世转变》(《复旦学报》2018年第2期)、徐明英《地理视域下的汉赋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邓稳《赋体缘起的文学地理探源》(《天中学刊》2015年第2期)、安娜《汉赋与汉代地理》(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等。
[1] 黄人.《清文汇》序[M]//沈粹芬,黄人,王文濡,等.清文汇.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2.
[2] 李新宇.论明代辞赋之演进[J].文学评论,2010(2):100–105.
[3] 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1:150–151.
[4] 刘埙.隐居通义[M].道光二十九年(1849)海山仙馆丛书.
[5] 刘咸炘.推十书[M].影印本.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
[6] 俞士玲.论清代辞赋的变革[J].南京大学学报,2000(1):112–120.
[7] 叶幼明.辞赋通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121–135.
[8] 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751–862.
[9]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
[10] 戴纶喆.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M].光绪七年(1881)四川瀛山书院刻本.
[11] 黄承吉.《金雪舫文学赋钞》序[G]//中国文学批评资料汇编:清代卷.台北:成文书局,1979:660.
[12] 刘熙载.刘熙载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132.
[13] 詹杭伦.清代赋论研究[M].台北:学生书局,2002.
[14] 姚鼐.古文辞类纂[M].影印本.北京:中国书店,1986.
[15]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6]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730.
[17] 张建伟,王静.论汉赋作家的地理分布[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8(3):45–48.
[18] 俞士玲.论清代科举中辞赋的地位与作用[J].学术月刊,2000(3):76-81.
I206
A
1006–5261(2021)04–0063–08
2020-11-1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24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240);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重大攻关项目(2018GH007)
孙福轩(1971―),男,山东济宁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