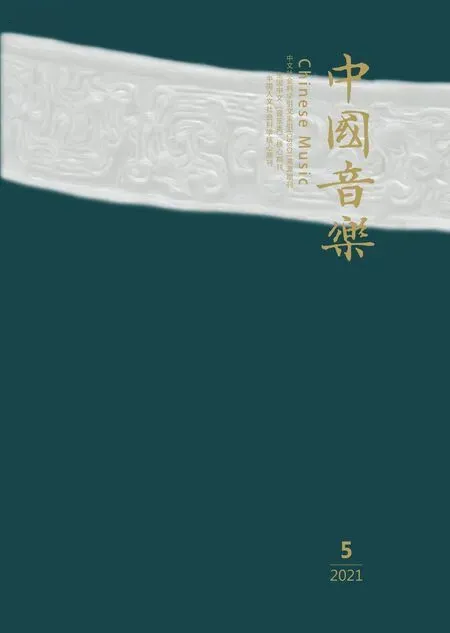从《文子》的听道哲学探赜儒道两家听乐的基本性格
○ 蒋 晶
一、《文子》听道的基本理论
《文子》属战国文献,是汉初已有的先秦古籍,东汉时班固将其列入道家,唐时与《老子》《庄子》《列子》同为四大真经,历经了“驳书”“真书”“伪书”,再到“真书”的认识过程。《文子·道德》篇曰:
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达智也,将以成行也,将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达。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故听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尽其精,不能尽其精,即行之不成。凡听之理,虚心清静,损气无盛,无思无虑,目无妄视,耳无苟听,专精积精,内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长久之。①〔战国〕文子著,李定生、徐慧君校释:《文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本文《文子》引文,皆出自这本书,不再一一注明。《文子校释》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57年出版的《正统道藏徐灵府通玄真经注》十二卷为底本(道藏本),参校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十二卷本(缵义本)、朱弁《通玄真经注》七卷本(道藏七卷本)、《道藏》辑要本(辑要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四部丛刊缩印《通玄真经》十二卷本(丛刊本),并参考了张元济《通玄真经校勘记》。
《文子》这段话道出了几层含义:第一,听的目的。获得智慧(圣),实现行为(行),取得人生的成功(成),即孔子所谓 “成于乐”。第二,听的进阶。耳听:物理层—浅表层—下学;心听:艺术层—深入层—中学;神听:哲理层—超越层—上学;耳听—心听—神听的不同层次,反映了心性、能力、智慧的高低;仪式伦理—法则伦理—心智伦理的进阶,反映出自然人到社会人到美人的进化。朱熹云“声入心通”,如果心境不是很平静,那么在听的过程中,不仅身没有入,心也不通。正如《国语·周语下》中所讲:“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因此,最好的学问是用神去领会,中等的学问是用心思考,下等的学问是仅凭生理感觉。凭感觉学习的,仅学到了表面上的东西;用心思考的,便学到了内里的东西;用神去领会的,才能学到实质性的东西,听的世界同时也富含伦理。第三,“善听者不以耳听,而不以心听而以神听,以神听者上也,以心听者中也,以耳听者下也”。②〔明〕贝琼:《听松楼记》,《清江文集》,卷二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听的终极目标是哲学的。《文子》的“神听”正如欧阳修《赠无为军李道士》中所描述的:“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可见,自然、社会、文化、哲学都通于听。
中国音乐艺术强调感物之心性,音乐与个体内在精神的对应,正是以唤起内心深沉的情感和超越日常语言与思想的道德良知,以造就人的心灵与人格而为其终极关怀:
琴者,禁邪归正,以和人心。是故圣人之治将以治身,育其情性,和矣……凡鼓琴,必择净室高堂,或升层楼之上,或以林石之间……值二气高明之时,清风明月之夜,焚香净室,坐定,心不外驰,气血和平,方与神合,灵与道合。若不遇知音,宁对清风明月、苍松怪石……故曰:“德不在手而在心,乐不在声而在道,兴不在音,而可以感天地之和,可以合神明之德。③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288页。
明代琴家杨表正的文字分别从琴乐的功能、听琴乐的环境、听乐的自我要求、听乐的对象以及听乐的感受、终极目的等五个方面来阐述古琴这一文人乐器。第一句“琴者,可以和人心、治身、育情、得趣、去邪归正等,”不仅明确了古琴的功能,还表达了琴是成就文人雅士个人生活意趣的道之“器”,暗含了中国古人尚清的生活方式和审美理想。第二句对鼓琴和听琴的环境提出了要求,必选择没有任何污浊、高大的厅堂,或草木葱茏、山林泉石之间,或高山之顶,或亦水亦岸亦草的水湄旁,亦或置身于道观佛寺的庙宇之中。第三层面提出了对自我听乐的要求,坐定、焚香、气息平稳、凝神定气、心无旁骛、集中专一、听乐冥想,方能体悟乐之道。第四句,假若听的对象未遇知音,莫不如鼓琴给大自然中的苍松、河流、峦石、动物而听,也倒是自得其乐。于是乎,体会这种“听”的乐趣不在于器,不在于手,而在于自我内心;其次,“心”的感受对象非“声”,亦非“音”,而是天地人世之间的“和”,此之为终极目的。重要的是,由心到气,再到神,终抵“道”这样的体验与《文子》强调的“听道”并无二致。道家认为,听耳为下,听心为中,听气为上。因为“气”的虚柔任物正是“道”的特性,所以,听“气”即是听“道”,此非神听无以听。与有声之乐比较,可知此听非彼听,觉听非神听,觉听是感官的审美,神听是精神的体悟,这里,涉及耳听、心听、神听三个层次,④罗艺峰:《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288页。而心与道相应,才能感天地之和,以合神明。正所谓“上士学道受之以神,中士受之以心,下士受之以耳。以神聴者通无形,以心聴者知内情,以耳聴者闻外声”。⑤《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句话同时表达出一个对应关系:

“闻”是最低层次的,暗含被动的知道、了解,而“知”是更进一步的认识、懂得,“通”谓通晓,是一种浸入骨髓的了解,因此可以“通无形”。“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庄子·盗跖》)乃人之常情,“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列子·杨朱》),可见,“听”是满足人类正常生理需要和定位文化空间的重要方式。
二、《文子》虚实并举的听之道
儒、道两家都有圣人情结,道家圣人多是所谓真人、至人、高人,儒、道的圣人有不同的文化性格。为什么要讨论圣人观?圣即聖,因为与听觉活动有关,作为主要体现道家思想的《文子》,它的圣人理想当然也是如此,不过又表现出一些自己的特点,即在听的观念方面,是虚、实并举的,以下试为之论。
一般认为,《文子》可能存在于《老》《庄》之间或之后,继承和发展了老、庄的思想,故其圣人观也当然与《老子》和《庄子》近,所谓圣人,不过是些“为腹不为目”不乐于感官的享乐,只致力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老子·十二章》),“忘其肝胆,遗其耳目”的“逍遥乎无为之业”的人物(《庄子·大宗师》),是些“放任于尘累之表,逸豫于清旷之乡”者(成玄英疏)。《文子·道原》集中论到“圣人”,认为圣人也就是“至人”,是能体道的“大丈夫”,他们“怡然无累,淡然无虑”,“唯圣人是能遗物反己”,能够“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特别明确地指出:“是以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王利器先生对这句话里的“本”和“末”作疏义说:“内正一心,外斥杂伎”⑥王利器:《文子疏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页。,明确指出“外斥其末”的“末”,是与声色对象有关的“杂伎”,故道家圣人自然不会去外求实听的对象,而强调内听、自听,乃至于虚听,《庄子·人间世》所谓“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意思是不要求对外物起反应⑦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113页。,认为只有这样“能游道德之乡,放任乎至道之境”(成玄英疏)者才是圣人。准此,道家圣人的虚听就往往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渐阶玄妙”的神秘倾向,而将所谓“神听”视为最高的听之道就是必然,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文子·道德》中的听之道才有了完整的建构。
《文子》有关“学问不精,听道不深”这段话,对于中国文化传统里的听之道所表达的思想,非常值得分析。一般来讲,中国文化里“学问”一词多是指系统的知识,也有“道理”之说。《荀子·劝学》:“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天文地理,人生阅历,政治伦理,识字明理,都是知识;二是指态度,《易·乾》:“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对待自己不懂得的事情,要思考辩论,能知善识,明白了解,顾炎武《日知录·求其放心》:“夫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另指学习和问难。⑧陈复华主编:《古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788页。显然,《文子》这里说的“学问”,即是关于听的知识和态度,缺乏这样的学问,一定会在听的问题上浅薄鄙陋,即“听道不深”。那么,这一段关于听之道的理论,其内涵如何呢?
《文子》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听道”的观念,《文子》的“听”,远非是“实听”—听赏音乐那么单一,也反映出道家智者“虚听”的追求,但其论“虚”,却也是建立在“实”的基础上,涉及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领域。
《文子》关于听之道的论述,有一个听的进阶:由生理性的“耳听”,进而为情感性的“心听”,再及超越性的“神听”,正是所谓“渐阶玄妙”。耳听肯定是实听,有听的声音对象,谓之“下学”,是一种简单、平易的学问;心听则更进了一步,涉及了精神性、情感性因素,即庄子所谓“情虑”,是“中等”的学问;而神听则完全是超越性、哲学性的听,正是道家推崇的虚听,要理解和达到它,则需要“上学”的高级学问。不奇怪的是,以实论虚和以虚论实,在《文子》当中都有表达,有许多涉及哲学、政治和人生的哲思,是用实听来论述的:
圣人初作乐也,以归神杜淫,反其天心……至于亡国。⑨葛刚岩:《〈文子〉成书及其思想》,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113;79页。(《文子·上礼》)
这里的“圣人初作乐”无可怀疑作的是实听之乐,其思想有儒家色彩,我们不难发现儒家论乐文献里与此相同、相似的痕迹,《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⑩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0年,第151页。同样的认识,在《文子》中也有体现:
上古的君王,无不以天下为己……其由击鼓而欲无声不应者也……故听其音则知其风,观其乐即知其俗,见其俗即知其化。⑪葛刚岩:《〈文子〉成书及其思想》,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113;79页。(《文子·精诚》)
这里的“听音”“观乐”皆是实体性的听,《文子》肯定了审乐知政的道理,承认礼乐有教化作用,显然这是儒家思想。但《文子》究竟是道家色彩为主的著作,所以不难发现这样的观点:
法制礼乐者,治之具也,非所以为治也。故曲士不可与论至道,讯寤于俗而束于教也。(《文子·上义》)
法制和礼乐作为治国的工具,不是根本之道,所以不可与寡闻陋见之士讨论至道的问题,这是因为其浸染于习俗的政教所束缚的原因,“礼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礼乐能使人止欲,不能使人不欲,不开嗜欲。《文子》的作者认为,真正能起到归神杜淫作用的,是人心归于自然,听心听和的“虚听”之道:
其听治也,虚心弱志,清明不暗。是故,群臣辐辏并进……即治国之所以明矣。(《文子·自然》)
为君之道处理政事,能“虚心弱志”则神清智明,因此群臣才能像辐条都集中于毂轴上一样,齐心协力共事一君。君主掌握了用臣之道,所以臣下得到事君之法,这就是重要的治国之术了,相关文字在《文子·上礼》中也有记载。
圣人制礼乐,却不为礼乐所制约;制定规则的人不被规则所束缚。治国犹如师况调五音一样,了解法度准则的人才能治人:
譬犹师况之调五音也,所推移上下,无常尺寸以度……而知规矩钩绳之所用者能治人。(《文子·上礼》)
执一世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犹胶柱调瑟。圣人者,应时权变……随时举事。(《文子·道德》)
这里的治乐之道,与治人之道,是相通的,其可通之处即是“道”,虚玄、无形、却是根本的。以上可以看出,《文子》在这里,既强调用儒家“实听之道”制礼乐来规范人群,维护君臣等级秩序,协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提倡道家的“虚听”之理,世人归于人神和谐,杜绝和防止淫乱,返其天心,归于自然。“守内”“不听”“不虑”“贵虚”,也就是不被外在的声色现象所干扰,而沉入极深极静的本我,在这里,本我与道体进到通达为一的最高哲学境界:
天地之道,至闳以大……人之耳目何能久熏而不息?……嗜欲寡则耳目清,而听视聪达,听视聪达谓之明。(《文子·九守》)
精目不视,静耳不听,闭口不言,委心不虑……是谓大通……(《文子·守平》)
目悦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声,七窍交争,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文子·下德》)
听失于非誉,目淫于采色,而欲得事正即难矣,是以贵虚。(《文子·下德》)
这些思想,固有养生学说的内容,但是,从听之道的角度去解释,则可以发现非常突出的对虚听意识的强调,若要达到“大通”的境界,需“不视、不听、不言、不虑”,才能神清意平,百节皆宁。而一般人则志小而忘大,是不可取的:
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闻雷霆争声……故小有所志,则大有所忘。(《文子·九守·守静》)
《文子》的作者无疑是能够实听的,也熟悉音乐,同时特别强调虚听,以道论乐。所谓“治天地之道也,虚静为主,虚无不受,静无不持,知虚静之道,乃能终始,故圣人以静为治,以动为乱。”⑫蒋晶:《〈文子〉音乐思想研究》,西安音乐学院2006年硕士论文,第128页。“故静默者,神明之宅;虚无者,道之所居”(《文子·九守·守法》)。这些道理,都使《文子》不能不强调虚听,但也兼及实听。
故而,《文子》“听之道”是复杂的,这与其书的思想杂糅性质有关,故其思想基础是儒、道均有。它不否定耳听—实听,也不否定心听—情听,承认这些实听形态存在的同时,却更推崇神听—虚听。关于耳听—实听和心听—情听的观念,与儒家听的思想接近,而神听-虚听的观念则肯定是道家的思想,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儒、道两家听觉文化的特点,也与儒、道两家圣人观有密切联系,儒家圣人是耳听—实听、包括心听—情听者,而道家圣人则主要是神听—虚听者。
三、道家的圣人观与听之道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⑬参见白欲晓:《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老、庄等道家智者的圣人观,与儒家不同,老子强调“圣人不仁”,庄子宣扬“绝圣弃智”,而提出自己所谓的“天人”“神人”“大人”“至人”的理想。《庄子》⑭〔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庄子·应帝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8页。里这些思想,很不同于儒家的世俗气味,而有世外高人之风: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
——《庄子·天下》
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古之至人,天而不人。
——《庄子·列御寇》
庄子说,“圣人有所游”,这种“游”是对外物空间的遗忘,他们超凡绝尘,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所以这些“大人、真人、神人、至人”都是非常自由的,是向内的“游心”,代表着生命的一种本质状态,一种真实状态。庄子认为,理想人格因其无为,所以没有任何矫饰,最纯真也最自然,最能容纳万物,保守天真,只有在虚静状态下的心才能应物而不藏,才能够明察秋毫,成为万物的镜子,外物成为心的镜像,于是天地万物在他面前就会显现其本真的面貌。
《文子·道原》篇更详细地讨论了道家至人、真人与听的关系,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
夫至人之治也,弃其聪明,灭其文章,依道废智,与民同出乎公。
真人体之以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不与物杂,至德天地之道,故谓之真人。
在《文子》看来,“真人”贵在治身,守虚、守平、守清净,相比“至人”要更懂得了解和修养自身。
吴泳曰:
仙圣之所重,惟教耳。然圣人以身教也,真人以神听也,以身教,故不悦道之华,以神听,故不逐言之迹。⑮参见〔宋〕吴泳:《演教堂记》,《鹤林集》卷三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在道家看来,贤人不及圣人,圣人不及真人,其得道有深浅,品级有分别。就听道而言,儒家圣人和道家真人就很不相同。儒家多讲实体性的听,如听风、听声、听德、听律、听情、听政,在听中发现政治、伦理、道德,“声音之道与政通”;而道家多虚拟性的听,如听神、听气、无声之听,在听中发现哲学、精神、灵性,这是超越性哲学在音乐文化里的体现,前者多是社会性的,而后者多是心理的。
故圣人所以动天下者,真人不过,贤人所以矫世俗者,圣人不观。夫人拘于世俗,必形系而神泄,故不免于累,使我可拘系者,必其命自有外者矣。
——《文子·精诚》
所以,圣人是教化天下,贤人不过矫正世俗,至人、真人则能够让人成为一个内省的、自知的、本真的、超越性的人,这是在听的传统里,道家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身体”可谓是生命的代名词,它不是简单的肉体(身),也不是单纯的精神(体),而是两者的高度统一(身体),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德性充实。⑯赵保佑主编、高秀昌、杨懿楠副主编:《老子思想与人类生存之道—2010洛阳老子文化国际论坛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6页。而声音与身体的关系认识非常古老,不仅道家强调,儒家也强调,但道家养生理论更突出。所谓养耳,其实是养生。《国语·周语下》中记载了单穆公劝谏周景王勿铸大钟,说明古人对声音不仅有生理影响的认识,也更注意到精神影响的问题。《荀子·礼论》说:“故天子大路越席,以养体也;载睪芷,以养鼻也;有错衡,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濩》,所以养耳也……”⑰安小兰译注:《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7页。荀子认为人的欲望,包括对声色之美的欲求,都应该尽可能得到满足,但如果这种满足失衡,就会使社会陷入混乱而无法维持,因而这种满足必须是合理的,有节制的,受社会制约的,同时他认为礼仪性情应该是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阮籍《乐论》中记载“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好音之声者不足与论律”⑱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7页。,是说只有通晓平和准则的人才能谈论音乐,贪图音声悦耳,不顾这一准则,便不配谈论音律。嵇康的《琴赋》中与阮籍一样,都以“平和”为音乐的审美准则。
因此,顺应自然,修身养性,符合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郭店竹简43号记载:“目之好色,耳之乐聖(聲),鬰陶之气也,人不难为之死。”简文说眼睛之好美色,耳朵之好乐音,都是内心郁结之气,人很容易为其而死。⑲刘钊:《郭店楚简较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关于“耳目聪明”多见于典籍,《易·鼎卦》:“巽而耳目聪明”;《管子·内业》说:“耳目聪明,四肢坚固。”这些都和养生有关。守和对于圣人来讲,就是强调顺认自然,随时而动,达性命之情,节制爱惜自己而不放纵,与天地、万物、人道合一,达到“和”的境界理想。总结起来说,道家听的传统里养生的内容,表现出突出的中国文化特色,这也是道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出道家听之道、听的哲学的深刻思考,值得今天的人们重视。
四、儒家“实听”与道家“虚听”的哲学分析
史家钱穆说:
中国人重实,又更重虚。音乐亦最实,又最虚。小戴《礼记》有《乐记》篇,备论古人对乐之观念。谓乐以象德,又谓乐通于政通于教,其义深矣。⑳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97页。
在中国文化中,重视“听”是儒、道、释三家都强调的。儒家所谓君子听德,小人听欲;道家所谓大音希声,自然天籁;释家所谓闻声悟道,美音演法,如是我闻等等,无不与人类的耳朵密切相关。作为战国晚期文献,《文子》在音乐思想史、音乐美学史上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但文中有关“听”的三层次的论说,又与其前后的圣人观念有密切联系,这都涉及了中国传统里极为发达的听觉文化和听的思想,值得我们讨论和研究。笔者认为,圣人观念在由宗教性向世俗性的历史发展中,分化出儒、道两家不同的圣人观念,因此,提出了儒家多为“实听”和道家强调“虚听”的观点。
如前文对核心概念的解释,所谓实听,是指有确定的听觉事件发生,有发声对象,有实存的听觉作品。这方面儒家文化里为多,也与儒家实用主义的世俗理性倾向有关,儒家非常重视“实听”之道,认为实听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它把人带入到生存感之中,而其实质,则是客观时间哲学。
我们知道,“听”涉及时间概念,而“视”是一种空间概念,虽然儒家也强调了在不同空间里声音的不同功能,但听的实质则还是时间性的。孔子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邢昺疏:“绎如也者,言其音落绎然,相续不绝也。”这里的“始作”到“从之”到“以成”,是一个时间过程,而“翕如”到“纯如”再到“皦如”,更是音乐形态的过程,尤其是“绎如”一词,更把乐曲连续、连贯的相续不绝的声音形态描写了出来,这个过程当然也是时间性的,正如《礼记·乐记》论歌声之“象”:“故歌者,上如抗……累累乎端如贯珠。”这个“累累乎端如贯珠”的声音形态,也在时间之中展开,这些美妙的音乐都是实体的有物理属性的声音,是我们生命时间的乐象化表达。《荀子·乐论》中的舞蹈“俯仰屈伸”是时间的,礼仪的节奏“进退得齐”也是时间的,乐器演奏所象征的清明象天,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则更是空间和时间兼有的。㉑同注⑰,第196页。这一文艺的客观时间哲学,把儒家的思想世界拉回到现实之中,使它不能不是实听的,因为人内在于客观时间,时间也内在于人,这也是为什么儒家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的原因之一,儒家知识分子特别愿意回忆往古,特别向往上古圣王时代,也是他们反复回味六代乐舞的审美动力。在听的传统里,儒家也因此而特别享受实听,而不是虚浮的玄思之听,儒家知识分子数千年来对季札观乐的礼赞,对孔子乐教的实行,对音乐象德、象政、象教的崇拜,乃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听到了人的生存意义。孔子的仁道、墨子的义道、孟子的立人之道㉒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都是实际的现实生活,也当然是在一维的客观时间之流中,故儒家的听之道不能不是实存的、无外于实听的。
要之,儒家实听的传统,建立在生命的时间哲学和音乐的时间哲学之上,而这一时间哲学则是自孔子以来的儒家思想传统,它给予了实听以坚实的基础。
一般来说,道家推崇寂寞无声,高蹈玄虚,自拔于一般世俗之意识的,在听道里也特别把“神听”“虚听”当作“悟道之由”,这个“道”的哲学就是虚听的根本哲学。在笔者看来,与儒家建立在一维的客观时间之上的实听的生命(性命)哲学基础不同,道家强调的是一种多维弥散的气机哲学㉓气机哲学是罗艺峰教授提出的中国哲学一脉,主要是道家哲学。目前这一哲学思想尚未见深入的论述。。所谓气机哲学也就主要是一种意识哲学,它必然超拔于儒家世俗世界之外,当然也就是虚听的世界:
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包裹六极。㉔同注⑭,第403–493页。(《庄子·天运》)
在道家看来,万物从道(气)受命而生,触机而生,道气合一,才能同乎大顺。只有具备“无”的性质的“气”才是宇宙的来源和根本。道家对“无”(气机)的赞美远多于对“有”的言说,因此关于无声、无音、虚听的观点就建立了起来:
无音者,声之大宗也。…无声而五音鸣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㉕同注⑩,第143;151页。(《淮南子·原道训》)
朱弦漏越,一唱而三叹,可听而不可快也。故无声者,正其可听者也。㉖同注⑩,第143;151页。(《淮南子·泰族训》)
无声作为声音的本源,虽然听不到却能使五音震响。所以有生于无,实出于虚。有声之乐出于无声之道,这正是道家听之道中所体现的“虚听”。庄子哲学的核心是返回“道”,而要返回“道”,则必如《庄子·在宥》所要求的: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
这里反映了道家圣人的听觉特点:由心—气—神—道之间的进阶关系,从耳听到心听,在通往“心斋”的路上更近了一步。当然,因为“气”是弥散的、多维的,机是随机的、触机的,所以道家“气听”的世界肯定是虚玄的,耳实际听到的世界则是线性的、单维的。道家建立的倾听方法,是不用耳听,而用心听,不用心听,而用气听,耳朵反而成为了达到心斋“不染尘境”的障碍,“气”则是对心听、耳听的超越,气就是虚,而虚就是道,“唯道集虚”,道超越了实体性的听。总之,建立在弥散气机哲学上的虚听,远比实听更具精神价值,但也更难为一般人所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