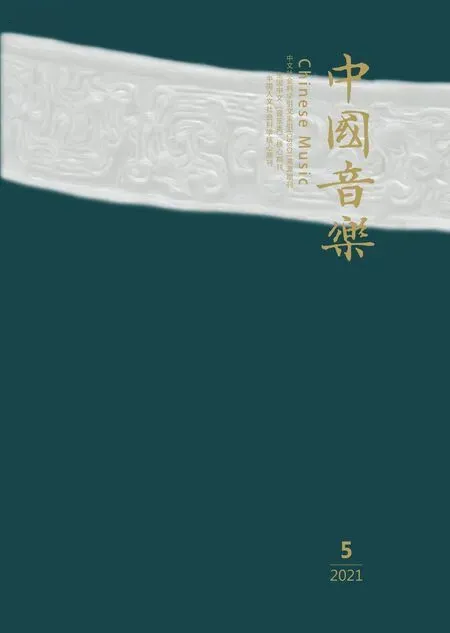曾侯乙编钟测音数据不能反映律制倾向
——“基-角”“曾-基”音程与两种律制大三度的再比较
○ 宋克宾
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曾侯乙编钟64件,镈1件。出土时编钟分3层悬挂于曲尺型钟架上。除挂在下层二组6号位置楚王赗送的镈钟外,编钟均有标音铭文,标识每钟双音的理论设计音高。这些理论音高,并不能明确指明曾钟的律制归属,于是测音数据成为律制分析的重要手段。黄翔鹏先生结合曾钟测音数据,提出了“复合律制”①黄翔鹏:《音乐考古学在民族音乐型态研究中的作用》,《人民音乐》,1983年,第8期,第39页。“钟律音系网”②黄翔鹏:《中国传统音调的数理逻辑关系问题》,《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期,第9–10页。以及“‘钟律’就是‘琴律’”③黄翔鹏:《均钟考—曾侯乙墓五弦器研究(下)》,《黄钟》,1989年,第2期,第86页。等观点。
较多学者对从测音数据分析曾钟律制的做法表示了质疑和否定,比如陈应时先生认为“黄先生提出‘折衷律制’‘复合律制’的依据主要是曾侯乙编钟的测音数据。”“面对这套编钟充满误差的音律……就目前所得的测音数据来看,因其中无规律可循,故还是难以从中找出它的律制归属来的。”④陈应时:《评“复合律制”》,《音乐艺术》,1996年,第2期,第8页。王洪军先生认为:根据测音数据对各律的音高作出精密的规定是非常困难的,因而根据测音数据对编钟进行律制研究的可信度是很弱的。”“对照钟律研究,显然运用测音数据难以或无法开展编钟的律制研究。”⑤王洪军:《测音数据在编钟律制研究中的可信度分析》,《音乐艺术》,2005年,第2期,第53–60页。
既然在“以耳齐其声”的条件下,编钟本身就调不准,那么从测音数据分析曾钟律制的做法确实是值得怀疑的。调不准,但是否在往某种律制上调呢?测音数据能否体现出某种律制倾向⑨“即使我们充分估计到青铜钟调律的实际困难,和它的误差,也仍可从全套编钟调律情况的总的倾向中看出先秦钟律并非单一的律制”(参阅黄翔鹏:《音乐考古学在民族音乐型态研究中的作用》,《人民音乐》,1983年,第8期,第39页。)“作为活的音乐,作为乐器的调律,尤其青铜编钟的调音困难,且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而铜绿斑驳,测音数据只能提供一个总的倾向。”参见李成渝:《如何认识传统音乐中的“纯律”音程》,《中国音乐学》,1998年,第3期,第21页。或“可能性”呢?最近王友华先生在《也谈曾侯乙编钟的生律法》中把音准较好的中层甬钟“基-角”音程测音数据所反映的音程值,与纯律、五度相生律大三度比较;把“曾-基”音程测音数据所反映的音程值,与纯律减四度、纯律大三度比较,观察接近哪种“三度”音程的多,从而判断倾向哪种律制,认为曾钟“基的产生采用五度相生律,角和曾应该都源于纯律,曾为基下方的纯律大三度音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为角上方纯律大三度音可能性”⑩王友华:《也谈曾侯乙编钟的生律法》,《音乐研究》,2019年,第2期,第39页。。
相对而言,通过观察“基-角”“曾-基”三度音程测音数据体现的音程值与纯律、五度相生律相应音程的接近程度,从而判断律制倾向或“可能性”,无疑比直接从测音数据解读铭文并进行律制归属判断,要可行得多。因为在同一次测音数据条件下,比较相同音关系(大三度音程),而不是单个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测音数据误差造成的解读主观性。应该说王友华先生为从测音数据客观分析曾钟律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角,推进了曾钟律制研究进程。
但是通过这种比较,是否会得到曾侯乙编钟“角和曾应该都源于纯律”的结论呢?鉴于曾钟律制研究在中国音乐理论上的至关重要性,本文从测音数据进一步探讨。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接近曾侯乙编钟律制归属的答案。
一、中层甬钟“基-角”“曾-基”音程测音数据没有反映出明确的律制倾向
“四角”为“四基”上方大三度音,学界没有异议。
关于“四曾”,一种认为是“四角”上方的大三度音,即“四基”上方两层大三度叠置;一种认为是“四基”下方的大三度音。⑫如冯光生先生说:“四声下方的大三度音,则以四个阶名后缀‘曾’字,被分别名为:徵曾、羽曾、宫曾、商曾。”参阅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两者都把“曾”字解读为“增”,只不过前者理解为音高的叠增,而后者理解为“生律法上的弦长之增加”。⑬黄翔鹏:《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第39页。设宫音为C,先不考虑律制,前者实际得到增五度音#G,“宫曾-宫”大三度由增五度音与基音构成的“减四度”音程(#G-C)替代而成;后者直接得到大三度音程“bA-C”。
在我国规划体系中规划一般分为“三级”,即国家级、省级、市县级。不同层次级别的规划因所覆盖的区域范围大小存在很大差异,即规划的尺度和精度不同,水资源论证的深度不同;不同管理部门的职能不同,所涉及的规划主题不同,则规划功能、规划方法与规划表现形式都有很大不同,这直接关系规划水资源论证的重点,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目前水利部开展规划水资源论证的重点范围主要有: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专项规划,②城市总体规划及其专项规划,③重大建设项目布局规划,④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⑤行业专项规划。
我在《十二音位的五度相生—曾侯乙编钟上层一组钮钟的乐学内涵》一文,认同上层一组钮钟“四曾”在律学意义上,是从宫下五度反生(“三倍”生律)而得(即“四基”下方的大三度音),而不是“宫的基础上连续五度相生十一次”⑭宋克宾:《十二音位的五度相生—曾侯乙编钟上层一组钮钟的乐学内涵》,《音乐研究》,2019年,第2期,第34;86、89、90页。。这反映在文中的图3和图11。尤其是附1“曾侯乙编钟十二音五度相生的现代音名说明”,“四曾”(宫曾bA、徵曾bE、商曾bB、羽曾F)明确为“四基”(宫C、徵G、商D、羽A)下方大三度音,不是上方增五度音(#G、#D、#A、#F)。⑮宋克宾:《十二音位的五度相生—曾侯乙编钟上层一组钮钟的乐学内涵》,《音乐研究》,2019年,第2期,第34;86、89、90页。
认同曾钟基础十二音中“曾”为“基”的下方大三度,是因为在同一律制内,无论是纯律或五度相生律,两个大三度叠置所得到的增五度数比复杂,远不及“基”下方生得的大三度音(或上方小六度音)简单,协和程度高。以宫曾为例,设宫(C)的相对波长为1,⑯关于“相对波长”,参见赵宋光:《中华律学传统的复兴与开拓》,《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期,第4–8页;赵宋光:《一笔恼人遗产的松快清理》,《音乐研究》,1993年,第3期,第57–68页,92页。纯律增五度音的相对波长为,而纯律下方大三度音的相对波长为;五度相生律增五度音(#G)的相对波长为,而五度相生律下方大三度音(bA)的相对波长为
需要注意的是,在同一律制内,可以判断曾钟优先选择生律过程简单或协和程度高的音。但是面对不同的律制,就不能只从生律复杂度来判断曾钟的选择了。“四角”“四曾”作为一对概念,到底是“四基”的上、下方纯律大三度音,还是五度相生律大三度音?这可以通过王友华先生所提出的方法,即统计测音数据体现的“曾-基”“基-角”音程值,是接近于纯律的多,还是五度相生律的多,进行“可能性”判断。
在进行测音数据分析之前,还需要交代一个前提,即曾侯乙编钟铭文里“角”和“”的意义是否等同?⑰黄翔鹏先生说:“显然‘’字是来源于钟上大三度的鼓帝音。钟铭行文常作‘’,而标音字一般作‘角’字,说明‘’与‘角’的音程意义可以互换,这也是‘宫’相当角音之故,写作角,从其易解了。”(参见黄翔鹏:《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第39页。)这是需要商榷的。本文只讨论曾钟标音铭文所呈现的“四曾”“四基”“四角”十二音,不涉及带附助词“”的音。
(一)测音数据反映的“基-角”音程与两种律制大三度的再比较
纯律大三度音程为386音分,五度相生律大三度音程为408音分,两者中间值为397音分(408+386=794,794÷2=397)。由于王友华先生在《也谈曾侯乙编钟的生律法》比较时,有几例与官方发布不符合的测音数据⑱王先生的测音数据以“京测”为依据。参照1989年出版的《曾侯乙墓》公布的曾侯乙编钟“京测”数据(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10–114页)。中一5钟正鼓音(下角)的测音数据为“E5-63”,王先生的为“E5-64”;中二11钟正鼓音(商角)的测音数据为“#F4-22”(365.3HZ),王先生的为“#F4-70”(316.57HZ)。此外,与中二11钟正鼓音(商角)构成“基-角”大三度的“基”应为中二12钟正鼓音(商),测音数据为“D4-55”,而不是测音数据为“D5-48”的中二6钟正鼓音(商)。否则不在一个八度之内。这个“商-商角”大三度音程本应为433音分,不是378音分。,而且设置了5音分的中区间不作判断,减少了2个接近五度相生律大三度的“基-角”音程。因此,本文重新比较,并且在表中直接标示出“基-角”大三度音程对两种律制理论音高的偏离程度,如下表(见表1):

表1 中层组“基-角”大三度音程测音数据分析表
统计结果,6个接近纯律大三度,7个接近五度相生律大三度,相互比例为6︰7。接近五度相生律的多一个。
三组甬钟的形制均不相同,还应该在每一组中来具体分析。中层一组无枚甬钟“基-角”大三度偏向纯律与五度相生律的比例为1︰3,可以判断为偏向五度相生律;中层二组短枚甬钟(2︰2)和中层三组长枚甬钟(3︰2),双方都没有明确优势,无法判断。
从偏离程度来讲,以纯律为标准,最高偏离47音分,最低偏离11音分;以五度相生律为标准,最高偏离25音分,最低偏离33音分。本来就是模糊的倾向性或“可能性”分析,既然两边不设边界,中间也不应该设限。
(二)测音数据反映的“曾-基”音程与两种律制大三度的比较
无论是纯律还是五度相生律,小六度(下方大三度)显然比增五度要协和得多,基础十二音中“四曾”适合选择“四基”下方大三度音,构成“曾-基”大三度音程。因此,需要比较的是:“四曾”究竟是倾向“四基”下方的纯律大三度,还是下方的五度律大三度。比较如下表(见表2):

表2 中层组“曾-基”大三度音程测音数据分析表
统计起来,9个近纯律大三度,5个近五度相生律大三度,接近纯律大三度的确实多4个。但是具体到每一组,中层一组无枚甬钟纯律与五度相生律大三度的比值为3︰2,中层二组短枚甬钟的比值为3︰3,中层三组长枚甬钟的比值为3︰0。结论只能是,中层三组“曾-基”大三度音程倾向纯律,而中层一组与二组还不能判断。
从偏离度来讲,以纯律为标准,最高偏离46音分,最低偏离37音分;以五度相生律为标准,最高24音分,最低偏离59音分。既然两边不设边界,中间也不应设限。
二、上层二、三组钮钟“基-角”“曾-基”音程测音数据更倾向于五度相生律
由于只是分析模糊的律制“可能性”,除了中层甬钟外,同出其他编钟也应该在讨论范畴之内。出土下层甬钟㉑把下一3钟(徵-徵曾)摆到原来挂在下层二组的位置,下层一组甬钟只剩2件,讨论意义不大。下层二组甬钟的“基-角”大三度,共有5个,其中下二8钟正鼓音(徵,G2+8)与侧鼓音徵角(bB2-15)构成的大三度音程才277音分,下一3钟正鼓徵(bB2-20)构成的大三度音程才272音分,音高偏离均超过了100音分,完全是另外一个音程。剩下4个音程倾向纯律与五度律的比例为2︰2,无法判断律制可能性。由于“京测”没有下一1、下一3、下二9、下二10钟侧鼓音的测音数据,使得4个“曾-角”大三度无法进行比较。以及上层一组钮钟音准不佳,有的测音数据与标音偏差太大,分析意义不大。
出土上层二、三组钮钟形制相同,原来应有14件合编,挂在出土中层一组的位置㉒维四、冯光生:《关于曾侯乙墓编钟钮钟音乐性能的浅见—兼与王湘同志的商榷》,《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第83页。。这两组钟有完整的测音数据,并且相邻钟正鼓音之间、侧鼓音之间都是大三度音程,适合进行比较。其“基-角”音程共有8个,与两种律制的大三度关系如下表(见表3):

表3 上层二、三组的“基-角”大三度音程测音数据分析表
统计起来,1个偏向纯律大三度,7个偏向五度相生律大三度,后者占绝对优势。偏向纯律的那个大三度(徵-徵角)只偏高纯律6音分,偏低五度相生律16音分,应该说偏离幅度也并不大。单从测音数据来看,上层二、三组钮钟“基-角”大三度音程倾向五度相生律的可能性更大。
上层二、三组钮钟有7个“曾-基”音程,与两种律制的大三度关系如下表(见表4):

表4 上层二、三组钮钟“曾-基”大三度音程测音数据分析表
2个偏向纯律大三度,5个偏向五度律大三度,后者也占绝对优势。单从测音数据来看,无疑偏向五度相生律的可能性更大。
讨论与结论
在进行结论之前,还有一问题还需要讨论,就是曾侯乙编钟一共存在四次测音,分别为:1978年7月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考察小组,用闪光音准仪(即频闪观察仪,原名Stroboconn)的测定(简称京测);1979年7月,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与复旦大学物理系用示波器与PB-2频率仪的测定(简称沪测);1980年10月哈尔滨科技技术大学二系用示波器、PB-2频率仪和XFD-7A型低频信号发生器的测定(简称哈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视听技术实验室的测定数据(由韩宝强主持,可简称韩测)㉓韩宝强、刘一青、赵文娟:《曾侯乙编钟音高再测量及测音工作规范问题》,《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第108–109页。。
四次测音的音高数据都有不同。音高数据变化,音程大小也随着变化。那么,只以“京测”数据来探讨,结论是否具有说服力?如果不同次测音数据反映“基-角”“曾-基”音程接近纯律或五度相生律的结果很不相同,只用一次测音数据来探讨显然是存在较大问题的。因此,笔者对中层甬钟“基-角”“曾-曾”音程其他三次测音数据也进行分析。限于篇幅,本文只呈现统计结果。关于“基-角”音程,其他三次测音数据反映的接近纯律与五度相生律大三度比例均为6︰7,三组各自比例分别为:1︰3(中层一组)、2︰2(中层二组)、3︰2(中层三组)。关于“曾-基”音程,稍有不同:沪测与韩测总比为10︰4,三组分别为3︰2、4︰2、3︰0;哈测总比为9︰5,三组分别为:2︰3、4︰2、3︰0。
总的来看,四次测音反映的“基-角”“曾-基”音程接近纯律、五度相生律的比例整体变化很小,因此只以“京测”数据来分析也是可以的。这也说明以这两种“大三度”音程来探讨曾钟律制倾向,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测音数据与标音铭文所呈现理论音高之间的误差,也避免了同一音在不同次测音中的音高误差,得到的比例结论是客观的。
通过本文的以上讨论,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第一、依据测音数据,不能明确判断出中层甬钟的律制倾向。关于“基-角”音程,中层一组、二组、三组甬钟测音数据所体现接近纯律与五度相生律的比例分别为:1︰3、2︰2、3︰2,总比为6比7。除了中层一组(1︰3)可判断倾向五度相生律外,另两组没有明确优劣势,无法判断。关于“曾-基”音程,中层一组、二组、三组甬钟测音数据所体现接近纯律与五度相生律的比例分别为:3︰2、3︰3、3︰0。总比为9比5。虽然接近纯律大三度的多4个,但主要由中层三组甬钟造成,只能得到中层三组“曾-基”音程倾向于纯律的结论,而不能得到中层甬钟“曾-基”音程整体倾向纯律的结论。
第二、单从测音数据看,上层二、三组钮钟“基-角”“曾-基”倾向于五度相生律的可能性更大。8个“基-角”音程,7个偏向五度相生律大三度,1个偏向纯律大三度;7个“曾-基”音程,5个偏向五度相生律大三度,2个偏向纯律大三度。整体来看,15个音程,接近纯律大三度与五度相生律大三度的比例为3︰12。事实上,即使这样的绝对优势,也不能必然得到其律制就是五度相生律的结论。因为作为论证材料的测音数据,背后有太多不确定性因素,不能排除这种比例是巧合,无法保证能够真实反映编钟设计者观念上的律制。曾钟律制归属的确定性,还需要建立在更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上。
第三、以上众多“基-角”“曾-基”音程的客观数值,再一次证明从测音数据去分析曾钟律制归属,确定“角”“”“曾”“下角”等概念的律学意义,是不太可能的。这应该成为曾钟律制研究的一个共识。中层甬钟以及上层二、三组钮钟,一共42个“曾-基”“基-角”大三度音程,最小318音分,最大503音分,相差185音分!从小到大依次为:318、338、349、367、375、378(2个)、379、380、381、382、383(2个)、385、390(2个)、392、395、398、399、401、405、410、412、413、415、417、420、425、426、429、430、432(2个)、433、434、438、448、468、490、491、503。众多数据中,只有4对相同的大三度音程:378音分、383音分、390音分、432音分,其它均不相同。这离律制研究要求的精确数值相隔甚远,也无法反映出某种律制倾向。
第四、既然从测音数据分析曾钟律制是不太可能的,测音数据的“误差”也“与律制无关”,那么是否曾钟就没有了律制的存在呢?曾钟设计者是否没有考虑过律制问题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正如韩宝强先生所说:“任何律制被应用到具体乐器时都会存在误差,但这并不能否定律制在乐器上的存在。”㉔同注⑧。测音数据无法分析曾钟律制归属,再一次呼吁回到曾钟律制研究的第一手材料:铭文原典。事实上,测音数据、琴律等手段,起初都是为了帮助或辅助解读曾钟铭文所呈现的乐律内涵。可是在研究的学术历程中,由于乐律铭文内涵的理解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性突破,解读视线就渐渐离开了铭文,变得其他手段更为更重要了。曾钟研究应该回到起点,延续黄翔鹏先生最初从铭文解读乐学体系的思路,深入下去,分析出曾钟曾磬乐律铭文所呈现设计者观念上的理论律制。
最后,曾侯乙编钟音律体系存在纯律因素,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除了本文解读的代表曾钟生律基础的“角-曾”十二音外,铭文还有不同于“角”的“”类音位存在,包括徵、商、羽,以及徵下角和羽下角。曾钟究竟是否为“复合律制”?代表生律基础的中层甬钟“角-曾”十二音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关键要看曾钟音律体系里纯律与五度相生律是如何结合的。厘清“基”“角”“曾”“”“变”的音律术语关系,分清哪些是五度相生律的?哪些是纯律的?这都需要通过对乐律铭文的透彻分析才能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