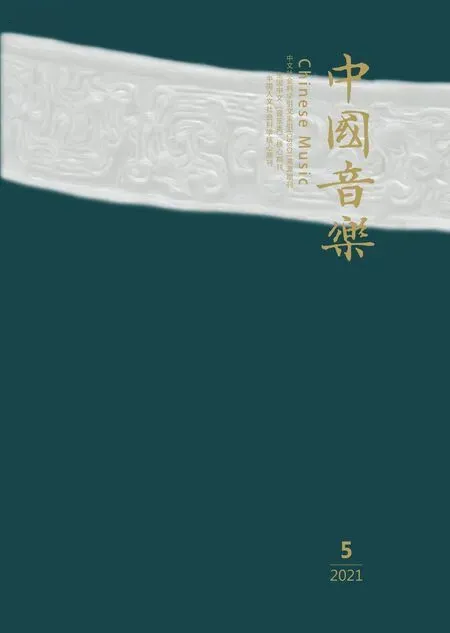彝族诺苏火把节和祭祖送灵仪式体系的衍变关系
○ 路菊芳
一、两类仪式在诺苏文化系统中的分层格局
(一)从节日体系看两类仪式的对立与协调关系
根据民俗学界研究,中国现代节日体系呈现明显的官方与民间二元对立的特征。其实这种二元结构自古就有萌芽,只是古代中国官方节日大多依据民间传统习俗而拟定,传统节日就是官方假日,如“唐代以前主要还是以民间传统节日这一单一结构为主,官府将一些传统节日予以确定,供职于官府的大小官吏们也参与对那些节日的庆贺”①魏华仙:《官方节日:唐宋节日文化的新特点》,《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8页。等。但从节日的体系而言,官与民又统一于一个节日结构中,即使唐代新兴的很多节日,如唐朝统治者有意建构的中和节、诞节、降圣节,以及唐人民间发明的清明、八月十五等,②参见张宏梅:《唐代的节日与风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页。学者们认为仍不能以官方和民间来划分,因为唐朝节日民俗的流变发展是官方和民间共同在发挥作用。③同注②,第8页。由此说明,在中国古代节日系统中,官方与民间一直在共同建构节日,协调二元结构的关系;同时也佐证了节日建构并非今日之新题。而官方节日(官定节日、官办节日)与传统节日真正出现分野,源自20世纪20年代官方推行公历(西历),要求所有节假日根据公历拟定,废除夏历(旧历、老百姓用的农历)。但公历节日对于老百姓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官方用公历假期,老百姓依然用旧历祭祀过节,无奈之下,官方只能取消对旧历的限制,而采用公历(官方)和夏历(民间)并行的两套历法格局。④参见高丙中:《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中国节假日制度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第76页。由此,也形成了现在节日体系中官方与民间的二元结构关系。
彝族文化中,节日往往体现为宗教仪式活动,火把节就是民间祭祀火神和祖先、庆祝丰收的传统节日。现代官方将火把节作为法定节假日,是遵循了传统节日的时间结构和祭祀主题。虽然官方火把节中包含了诸多现代音乐文化信息,官方参与是其主要标志行为,但在节日的时间框架内依然体现着官与民的和谐统一。如阿都地区官方火把节,无论仪式时间安排,还是仪式内容主体,均具有明显的传统节日特征。而祭祖送灵自古即为古代彝族统治者为祭祀祖先创制的仪式结构,传承至今体现的仍是民间传统,是属于家支范围内人群的节日。那么,再从节日仪式的音乐文化内容看,官方火把节是在民间火把节祭祀娱乐音乐活动基础上的再造或建构。因为传统音乐文化仍是其固定内容,加之毕摩诵唱的纳入,又增添了官方火把节与诺苏传统宗教信仰的亲缘关系。当然官方火把节也吸收了现代通俗音乐文化,只是这些都是不稳定的流动性因素。所以官方火把节在仪式内容上体现了继承传统信仰,容纳族性音乐,又展现当代节庆仪式文化认同的复合性特征。但祭祖送灵仪式是以毕摩诵唱为主要音声,特定场合应用世俗音乐的民间传统节日。
由此,两类仪式均归属为彝族诺苏现代节日体系,体现着官方与民间、现代与传统、民族与族群文化的二元特征。
(二)从民族和族群层看两类仪式的主文化、亚文化关系
“亚文化、交互文化、主文化”是1992年美国马克·斯洛宾针对音乐文化空间提出的基本描写方式及词汇组。⑤马克·斯洛宾在其《西方微观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1992年)一文中认为,主文化有区域、跨区域、单一民族国家的特征;具有主宰性,也可看成一种支配性的主流意识,兼具有形性和无形性,且无所不在的特征;是复合、矛盾的结合物。亚文化具有地域性特征,主要涉及文化层面有家庭、邻里、组织委员会、族群、性别和阶层。转引自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年,第203页。若从民族层和族群层⑥关于国族、民族和族群的内涵和关系,参看笔者论文《彝族诺苏人的现代火把节仪式音乐与国族文化认同》,《中国音乐》,2020年,第6期。看两类仪式,同样存在着主文化和亚文化的交错关系。
1.从民族层看两类仪式的主、亚文化关系
自1987年凉山州政府将火把节做为法定节日,到1994年第一届国际火把节举行,火把节逐渐从地域性亚文化向区域性主文化发展。2016年义诺区马边政府突破传统,举办官方火把节,火把节自此成为了凉山彝族诺苏人各土语区共有的节日⑦凉山除了义诺土语区没有民间火把节祭祀,其他土语区大多有此传统,至于何因也是众说纷纭,所以义诺土区的马边官方才建构火把节。,并且在不同地区呈现以官方为主导的主文化特色,代表的是民族文化认同。如火把节开幕式中领导致辞、参与点火等官方行为,昭示了火把节仪式隐含的政治性色彩,也由此注定了火把节与祭祖送灵仪式不同文化风格和仪式属性的特征。
相对而言,祭祖送灵仪式尼姆撮毕是彝族远古时期已存在,备受当时统治阶层重视的传统仪式活动。传承至今,仪式规模和时长虽然有所缩减,但鉴于此仪式是彝族人死后灵魂归祖的重要通道,仪式内容涉及彝族天文历法、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和教育生产等各方面经典文献,故其在诺苏族群文化观念中仍占据至高位置。彝族谚语“父养子娶妻生子,子养父送祖归灵”就是对前述言论的重要论证。而至当下社会,祭祖送灵仪式已无任何政治色彩,更多作为诺苏族群一项古老宗教习俗自然传承。因此,从民族层次分析祭祖送灵仪式,即处在与火把节并峙的亚文化层,代表的是族群文化认同。
2.从族群层次看两类仪式的主、亚文化关系
鉴于现代凉山的义诺土语区民间无火把节传统习惯,所以从族群层看火把节,它只是处于亚文化层。当然义诺土语区民间传说中曾有过此类习俗,只是未找到确切的文献记载。而祭祖送灵仪式却是既有地域性传承因素,又有跨地域性传播的区域文化特征;它不仅流传在诺苏族群中,在云南、贵州的彝族支系中同样存在。因此,相对火把节而言,祭祖送灵仪式又是非常复杂和庞大的祭祀体系。由此看,祭祖送灵仪式又占据主文化层位置。
3.从仪式音乐文化看两类仪式的对比和模仿关系
根据近几年考察可知,火把节中主要存在四种音乐文化元素:当代政治音乐文化、宗教音乐文化、民间音乐文化、通俗音乐文化。其中政治音乐文化并非直接呈现,而是通过隐喻的手段和途径,借用其他音乐表现形式来展示。由此,单独从音乐类型看各地火把节仪式音乐,主要包含三种基本元素:毕摩仪式音乐、民间音乐和通俗音乐。民间音乐如民间歌曲朵乐嗬、丫,器乐音乐如马布、口弦等。其中朵乐嗬是传统火把节中固有音乐形式,现全部被移入官方火把节,而丫作为诺苏人山歌,在阿都火把节中也是固定出现。最有意思的是宗教仪式中的毕摩诵唱,尤以改编祭祖送灵仪式中《指路经》(见谱例1)的模式性音调为盛,在不同地区火把节中广为传播(见谱例2)。两首谱例中标记Ⅰ、Ⅱ型旋律及其变化形式,可知两类仪式音乐形态之间的模式与变体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火把节中毕摩诵唱不再是单纯传统祭祖仪式中诵唱,而是表演诵唱;专设的毕摩点圣火仪式也成为近几年各地官方火把节中的共性特征。
谱例1 祭祖送灵仪式中的毕摩诵唱《指路经》片段;采录时间、地点:2017年10月、西昌太和农村;诵者:曲比拉伙(美姑毕摩);采录、记谱:阿余铁日、路菊芳

谱例2 火把节中改编的毕摩诵唱片段;采录时间、地点:2017年7月20日、布拖火把场;采录、记谱:路菊芳

由此,舞台上的毕摩表演唱具有了艺术性和舞台效果,并改变了最初的仪式功能,更多作为一种传统宗教文化符号象征而存在,同时隐喻着火把节与诺苏传统宗教信仰的一脉相承。
而祭祖送灵仪式在过去时期,也是神圣与世俗结合的狂欢。《西南夷族考察记》载“是日亲友毕至,男女老幼,各穿新服……惟赛马必赌输赢,大哭不下泪。音乐、口琴、大号、枪声,震动一时。以红黄黑白布千条万缕悬于竹顶,随风飘舞,此时虽为丧礼,但一般青年男女,借此男女错综的大好机会,实行初步的恋爱工作,真是悲喜之剧合演,可谓盛极一时。”⑧曲目藏尧:《西南夷族考察记》,转引自马玉华主编:《西南边疆卷三—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五种)》,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03页。说明早期的祭祖送灵仪式也发挥着民间音乐传播的功能,神圣祭奠的外围包裹着世俗的娱乐。现代祭祖送灵仪式同样如此,如“火角”仪式中,人们为烘托热闹的仪式气氛或为凸显本家族势力,用各种混响造势,鞭炮声、烟火声混杂着人们的喊叫声,年轻人手提音箱播放很大声响的通俗歌曲,或者敲锣打鼓助威入场,也有人弹奏月琴或吹奏克西觉尔等民间乐器,场面壮观,沸沸扬扬。但是,祭祀送灵仪式的核心—毕摩诵经场域一直以来都是相对严肃和神圣的空间。
由此两类仪式的音乐来源、音乐侧重可证,在诺苏族群文化发展的不同时期,两类仪式曾发挥过相同的作用。发展至当下,现代火把节偏重于世俗,祭祖送灵仪式着重神圣。故而可认为,当下火把节是对过去祭祖送灵仪式在某种程度上的模仿。
(三)两类仪式在诺苏文化中的分层一体格局关系
笔者根据对祭祖送灵仪式多年的考察,结合火把节发展现状得出:在凉山地区,祭祖送灵仪式流传范围和仪式规模由东北向西南逐渐缩小;反之,火把节却从东北向西南逐渐扩大。在祭祖送灵仪式广泛传播的义诺土语区,火把节虽是官方主办节日,但该地区凸显的族群文化是祭祖送灵仪式,火把节处于次要地位。其他有火把节传统的土语区,火把节是最隆重和流行的节庆仪式,占据主文化位置,而祭祖送灵仪式却日渐式微。所以,从当下彝族区域文化视角分析,火把节作为凉山彝族法定节日,被各地官方广为传播,具有强烈的主文化意识特征。
那么综合上述论证,将诺苏文化系统作为纵轴,地域和区域性地点作为横轴,中间向右延伸的斜线为时间轴,两类仪式体系的文化关系图(见图1)为:左纵栏为族群文化层,右纵栏为民族文化层。立于左栏族群文化层的祭祖送灵仪式即为主文化,具有地域性和跨区域性双重属性;当时的火把节仅是地域性传承的民间祭祀。而随着“彝族”概念的出现,民间火把节逐渐升级为官方火把节进入民族文化层,并从地域性到跨区域传播,占据彝族民族区域主导文化的地位;而与之并列,承袭古代彝族的祭祖送灵仪式依然存在,且代表着诺苏族群传统文化特征,只是已经处于亚文化层中。

图1 火把节与祭祖送灵仪式的文化关系图
由此,火把节以开放性的仪式特征既吸纳民间音乐、毕摩文化,又展现当下通俗音乐风格,成为现代彝族诺苏音乐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祭祖送灵仪式作为族群文化的典型代表,与火把节互有对比,又有联系地共存于诺苏信仰文化系统内。
二、两类仪式体系结构要素的比较
(一)两类仪式属性的对比关系
1.仪式类型—复合型和聚合型
火把节原为彝族民间一种较零散的仪式活动,即以地域性的家庭祭祀祖先为主,结合部落或村寨为单位自愿组织而成的欢聚活动。现由官方出面,在民间祭祀仪式基础上进行了规范、加工和改造,朔造出一种新型的彝族节日。即使无火把节传统的土语区,也从传统中吸取经验“发明新的传统”,形成定时定点的聚合型仪式。故可认为现代火把节是一种复合型节日体系,以官方为显性特征。而祭祖送灵尼姆撮毕从远古时代起就是彝族先祖统治、联络各种势力的重大宗教活动,传承至今流传区域虽日渐缩小,但在诺苏的不同土语区,依然是其普遍信仰,代表诺苏人的族群文化认同。
由此,火把节从地域性到区域性的传播发展,也使其仪式属性从离散型发展到聚合型。但祭祖送灵仪式一直是定时定点的聚合型仪式,以地域性传承和跨区域性传播相互结合的方式存在。所以,两类仪式在彝族宗教信仰文化中的地位,以及火把节仪式属性的变迁,正是族群文化和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也是本文将两类大型仪式进行对比研究的初衷。
2.仪式功能属性—官方与民间
火把节也是祭祖,只是相对于祭祖送灵仪式,为小型的家庭祭祖。官方介入后,仪式属性开始转变,其原初的仪式功能被扩大化,出现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的仪式功能是祭祀火神,围绕火展开祛除污秽的象征行为;隐性的仪式功能即为发展区域经济文化。⑨该部分笔者另文讨论,此不赘述。但是祭祖送灵仪式不同于火把节,它不会为了适应社会时代发展而改变其送灵魂归祖先的仪式功能,只是其送灵归祖的表面隐含着微妙的家支间礼尚往来、相互炫耀家族势力的意义。由此,整体观察两类仪式,火把节担负着既要体现传统仪式功能,又不能失去当下政治意识形态赋予的功能意义,否则火把节就失去了官方扶持的根本价值。那么进一步推论,火把节本身携带的政治性特征,也使其从族群文化特征脱颖而出,升入民族文化层,代表民族文化认同。与祭祖送灵仪式的族群性特征正好形成对比:一个政治层面(官方),一个文化层面(民间);一个是现代节庆仪式,一个为传统节庆仪式。同时,火把节中纳入毕摩诵唱元素,又从音乐和宗教信仰上将两类仪式连接一起。
3.社会认同属性—民族性和族群性
从仪式参与群体分析,早期的火把节是家庭式小型祭祖,结合村寨规模的聚集活动;现转型为以县、区为单位的大型节庆活动,仪式参与群体已超越以往族群范畴。而祭祖送灵仪式的参与者仅限于族群范围内家族之间,不具备当下政治性特征,但涉及不同家族间利益和权势往来,是当下诺苏家族团结互助的仪式实践活动。
从社会认同角度分析,仪式参与群体范畴限定了其社会认同度的大小。火把节从村寨规模的聚集,发展为人人都可参与的当代节庆仪式活动,使其得到民族层,甚或超越民族层更广范围的社会认同度。而祭祖送灵仪式本身属性和参与人群的限定,使其只能在族群文化层传承。甚至某些传统地区的仪式程序禁止外族,尤其女性观看,所以在社会认同度上祭祖送灵仪式很难进入民族文化层。笔者认为这也是官方之所以选择火把节作为法定节日,象征彝族文化认同的根本。
总之,火把节以开放性、较强的社会属性和人为建构的政治性特征得到民族内外认同,并以民间和官方两种形式相互协调,并处于同一节日体系代表着民族文化。而祭祖送灵仪式以半封闭型、较强的族群性认同和宗教性特征只能处于族群认同层面。随着火把节中毕摩诵唱符号的纳入,使原来火把节家庭式的小型祭祖,成为更广泛意义上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演祭祖—祭火。诺苏人在无意中完成了传统文化到现代认同的交接,并通过族性音乐的衍变、发展,建构着当下的音乐文化认同。
(二)两类仪式构成要素的模式与变体
根据官方、民间火把节仪式的区分,其仪式场域也分两种:民间家庭祭祀的仪式场域和火把节舞台上人为创造的仪式场域。另外,从仪式属性的比较可知,祭祖送灵仪式对仪式场域和仪式结构都有严格限制。火把节在官方介入后也成为定时定地点的聚合型仪式。下表(见表1)是针对两类仪式要素的述略和比较。若将民间火把祭祀和官方火把节合在一起与祭祖送灵仪式对比,可观之两类体系在仪式时间、仪式场域上的相互对应,以及仪式主题、仪式表演对象等方面殊途同归的相似之处。如仪式主题中,祭祖送灵仪式围绕祭祖、送祖,同时也有祈祷后代子孙兴旺和吉祥的意涵。而民间火把节家庭仪式主题为祭祀祖先和祈祷丰收、家人平安;但官方火把节仪式主题较复杂,除了祭火,展示传统文化,也隐含着发展旅游,为地方带来经济利润的驱动力。尤其《指路经》的改编诵唱、毕摩点圣火仪式的纳入,使两类仪式体系在宗教文化发展上存在必然关联。

表1 火把节和祭祖送灵仪式构成要素比较表
其次,两类仪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仪式类型、社会属性和仪式范畴方面。政府介入后使火把节具有了不同于祭祖仪式的政治性色彩,从原来零散的聚集仪式发展为大型的开放性仪式活动;从祈祷家庭平安到民族文化层,为民族区域带来更大经济利润的节日。而祭祖仪式停留于族群文化层面,其半封闭型仪式很难超越族群文化层。由此,两类仪式的仪式类型和社会属性,使火把节和祭祖送灵仪式一个处于民族文化层,一个处于族群文化层,两者互相呼应,又各自平行发展。
总之,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待,火把节和祭祖送灵仪式都是彝族诺苏文化在不同时期,展现不同风格特色的仪式实践活动。而火把节是当下社会认同语境中,彝族诺苏文化与当代社会政治接合的最佳产物。
(三)两类仪式结构和音乐布局的扩大或缩减
祭祖送灵仪式虽普遍承袭于彝族不同地区,但其仪式程序、仪式风格等都有差异。这种差异除了土语间的不同,也有“视家族祭祀先人身份、亡故原因、玛都(亡魂)多寡和财力决定仪式内容和规模”⑩路菊芳:《马边彝族尼姆撮毕仪式音乐的多声形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75页。的区分。因此,根据凉山彝族不同土语区火把节仪式结构和音乐布局的共性因素,结合义诺土语区多个祭祖仪式个案中仪式结构的固定因素和音声布局进行对比(见表2和表3),可知毕摩诵唱是两类仪式中共有音乐元素;其实民间器乐和《达体舞》也会在祭祖送灵仪式必要场合出现,如火角仪式,但非固定因素;而火把节中广泛改编的毕摩诵唱和祭火仪式,成为彝族各地火把节连接为一个宗教系统的纽带;此外,仪式结构中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即祭祖送灵仪式中频繁出现的“木古此”[mu33ku33tshɿ55]⑪“木古此”指点火,通知天神或曰祭祀天神;诺苏的祭祖送灵仪式汇集了所有大小型仪式程序,日常仪式的很多经文诵唱均可在祭祖送灵仪式中找到原型。而木古此在这里也频繁出现。(该仪式规模小表格中并未显示,但其重要性高于其他任何程序),它与“尔察苏”[lʉ33tsha33su33]⑫“尔察苏”指净化仪式。是诺苏毕摩做任何仪式的前奏曲,笔者推测官方火把节中的点圣火仪式,很大程度就是在祭祖送灵仪式“木古此”基础上的模仿或者扩大化。

表2 火把节的仪式结构和音乐布局

表3 祭祖仪式结构和音乐布局的固定性因素
三、两类仪式表演情景化的比较
“所有的表演,像所有的交流一样,都是情景性的、被展演的(enacted),并在由社会所界定的情景性语境中呈现为有意义的。”⑬〔美〕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1页。那么,通过上文的论证,火把节和祭祖送灵仪式都可界定为一场具有情景化的文化表演,都在彝族传统文化系统中发挥着一定的意义,阐述着共同的族群信仰。由于两者产生于不同时空,应用于不同表演场域,运用不同的表述语辞和文本,所以在表演形式上塑造了不同风格的诺苏文化。“自反性”⑭贝克认为“自反性”“这个概念并不是(如其形容词‘reflexive’所暗示的那样)指反思(reflection),而是(首先)指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转引自〔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 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页。吉登斯认为“自反性这个概念并不是指反思(reflection),而是首先指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拉什则认为自反性主要指“首先是结构性自反性(structural reflexivity),在这种自反性中,从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社会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其次是自我自反性(self-reflexivity),在这种自反性中,能动作用反作用于其自身。”转引自李银兵、李丹:《自反性、主体间性与现代性:民族志书写特征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121–129页。概念主要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英国人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美国学者芭芭拉·巴伯考克将其同表演民族志结合,谈道“‘自反性’一词表明了表演具有的两种相关的能力,它们都植根于任何意义系统所具有的成为其自身的对象以及指涉自身(to refer to itself)的能力”⑮转引自〔美〕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2页。,同理,火把节和祭祖送灵仪式作为文化表演,分别拥有对不同时期社会的自反性特征。
(一)两类仪式表演语境的自反性
自反性主要指表演本身对于其源出文化的反映,也可理解为文化意义的意义,即情景的再情景化。火把节和祭祖送灵仪式具有不同的仪式属性,代表不同的文化认同,由此也限定了两类仪式音乐不同的表演语境。首先,火把节属于开放性仪式,其表演语境就必须以多元化形式呈现。如毕摩在舞台上挥舞法扇祭祀天地或舞蹈,均是对传统仪式情景的模仿和扩大化。再如丫的比赛,每个选手都是走上舞台手拿话筒歌唱,与其原本山野之外个人感情抒发的歌唱完全不同;这时的丫更多是为了表演,获得奖项心理的驱动。另外,祭祖送灵仪式属于半封闭传统仪式,音乐表演语境相对单一;但每一个仪式语境又都是对古代彝族迁徙历史、自然万物之源的情景追溯。其次,火把节处于民族文化层,为官方组织参与,由此火把节中就有体现政治色彩的语境,如领导开幕式致辞,以及丫歌手对当下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歌颂等,都是火把节政治最好的反射。⑯笔者博士论文实录中有歌词翻译,此不赘述。而祭祖送灵仪式处于族群文化层,是各家族的相聚,无任何当下政治痕迹,只是暗含着不同家族势力、财力展示的竞争,当然这也是备受诺苏人看重之处。
总之,火把节以多元共生的表演语境,既能容纳族群宗教文化,又能自反当下政策变化,而成为各区域竭力扶持建构的节庆仪式活动。
(二)两类仪式表演形式的自反性
火把节处于民族文化层,其开放的仪式特征致使音乐表演者与观众分离。如朵乐嗬原本是女孩子们围着篝火自由歌舞,观众、演员兼于一身;现在转换为演员表演和观众欣赏分离。再如火把节家庭祭祀中,毕摩蹲在门口面对牲品为祖先诵唱;现转换为火把节舞台上毕摩手持经书、舞动法扇,跟随音乐声音模仿或仅是营造神圣气氛,唱、演分离的诵唱,等等均是对原来仪式表演形式的再创造。
此外,祭祖送灵仪式归属族群文化,其所有表演形式均停留在族群原初文化层面。如毕摩诵唱姿势的传统性,毕摩诵唱、表演、声音和情感的融为一体等等。正如涂尔干所言,“宗教是一种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⑰〔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页。
由此,在表演形式上传统宗教和当下节庆仪式表演尚存在很大差异。火把节中毕摩诵唱和表演,既是对诺苏宗教传统文化的建构,又是对当下社会信息的自反。因为仪式主持者、参与者和观众不再是宗教信仰的践行者,毕摩诵唱和表演行为只是在为不同族群身份的观众塑造宗教信仰的氛围,是对火把节源自传统宗教而建构的符号象征。而祭祖送灵仪式是对诺苏宗教信仰的自反,仪式主持者、参与者和观众就是诺苏宗教仪式的实践者,无需任何外力干涉就完成了诺苏宗教的传承。
(三)两类仪式社会—心理上的自反性
表演的自反性除了体现在表演语境和表演形式上,也体现在社会和人们的心理认同上。美国社会哲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认为,“‘自我建构’的过程中,表演的展示方式将表演中的自我(舞台上的演员、火炉前的故事讲述人、乡村广场上的节日舞蹈者)建构为自我的对象和他人的对象,在扮演成他者的角色并从该视角反观自身方面。表演是一个尤其有效的、升华的方式”。⑱同注⑮,第74–75页。因此,自反性在两类仪式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自我心理上的自反性。火把节作为彝族对外展示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的仪式实践活动,对于每一位彝族人都是一种自豪。作为舞台演员为能够展示自我,同时又歌唱自己民族歌曲而感到自豪;而作为台下观众,当看到舞台上歌者或选美比赛获奖者就和自己出自同一家族或来自同一地区时,那种兴奋和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是通过他者表现激发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自反性表现,是观众与表演者一起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从心理认识上强化本族群音乐文化的认知。所以,火把节中以比赛的形式展示传统音乐,倒也有一种激发本族群人们主动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动力。而祭祖送灵,只有仪式现场倾听毕摩诵唱的人们,才能感受到彝族历史文化的精深和祖先的智慧。因此,两类仪式,一个是对自我当下身份的自反性确证,一个是对过去族群历史文化的自反性认同。
其二、社会认同的自反性。前文已述火把节包含了当下政治、宗教文化、民间音乐和通俗音乐四种音乐文化元素。相比祭祖送灵,火把节更多是面对当下社会,瞻仰未来,加之其开放性仪式特征,有着比祭祖送灵仪式更广的社会认同度。而祭祖送灵仪式是对古代彝族宇宙观、自然观、历史文化、生产教育等知识的集体回顾,每参加一次祭祖仪式就是对自我族群身份的一次强化和建构,这种根深蒂固的族群认同在当下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所以毕摩文化符号才会成为各地火把节中的共性特征,因为这是火把节得到族群宗教文化认同的最大自反性行为。
总之,无论民族文化层的火把节,还是族群文化层的祭祖送灵仪式,表演者同观众的互动产生共鸣,是作为一场仪式或者文化表演最成功的展示。火把节作为代表民族文化认同的表演语境,既要与传统信仰保持联系,具有一定神圣感,又要与时代接轨,体现当下社会时代的自反性特征。故,火把节在对参与者身份认同建构上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和难度,也是其音乐文化之所以多元共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祭祖送灵仪式是诺苏宗教信仰的核心,其以不断的仪式重复强化族群身份认同,巩固宗教信仰。
结 语
综上所述,从现代节日体系呈现的二元特征、人类学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关系得出:在诺苏文化系统生成的时空维度中,火把节和祭祖送灵仪式共处同一节日体系。只是所处不同文化地位,拥有不同的音乐文化侧重点,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认同建构,具有着官方与民间的二元对立关系。
那么,从彝族传统宗教文化发展历程视之,火把节和祭祖送灵仪式是诺苏传统文化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社会制度接合的产物,两者具有前后承递的关系。从仪式音乐形态特征、音乐类型和仪式表演情景观察,火把节和祭祖送灵仪式分别是其产生于不同时期文化语境的自反性体现,同时火把节又是祭祖送灵仪式在古代彝族社会中的自反性表现。最后,再从两类仪式此消彼长的传承现状分析,火把节本身具有的,不同于祭祖送灵仪式的开放性仪式特征,为其带来先天的便利条件,使其能够立足于当下彝族社会作为诺苏文化代言人,以及诺苏本土文化对外展示的窗口。而祭祖送灵仪式在古代彝族社会作为主文化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只能与火把节并峙对望:一个外在,一个内化;一个位居民族认同,一个位居族群认同。
“梅尔耶夫(Myerhoff)写道:‘仪式借助永恒不变的和潜藏着的形式,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从而消除了历史和时间。……即使人们发明了新的仪式,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已有的象征素材库,新仪式的出现并不依凭于发明者的心血来潮,而是取决于那些参与在新仪式之中的人们所存在的社会环境。”⑲〔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因此,这种并峙非偶然的相遇,偶然的接合,而是同仪式相关的社会物质资源、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所以,诺苏的音乐文化认同建构必须以族群信仰系统为基础,否则为无根之茎,生命持续力缺失,终有一天被另一种新的形式取代。而真正实现这种传统文化延续的方式就是族性音乐文化在当下节日中的承传。
附言:文章内容源自本人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得到导师杨民康老师的辛勤指导,特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