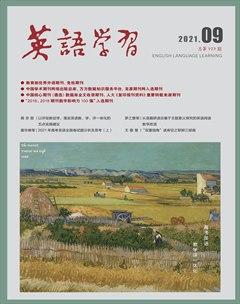欲解其中意,还须数秋冬
姚斌 李长栓
编者按:2019年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前身联合国译员训练班(部)成立40周年。2019年8月,笔者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笔译司中文处工作期间,有幸访谈了译训班第6期校友赵兴民老师。赵老师1988年赴日内瓦工作,从事联合国文件翻译30余载。他对待翻译工作“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态度,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赵老师不但精于翻译实践,还不断总结经验,为学习者提供指导。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合著)有《联合国文件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联合国文件翻译案例讲评》(外文出版社,2011)和《商务翻译译·注·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等。在访谈中,赵老师侃侃而谈,回顾了他学习翻译和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并对有志成为译员的学子提出了宝贵建议。2021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迎来80周年华诞,我们期待这篇访谈能为校庆献上一份礼物。
姚斌:赵老师,在联合国译员训练班(部)(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前身,以下简称“译训班”)成立40周年之际,很高兴能有机会与老校友聊一聊,回顾一下当年在译训班学习的情况。请问您是从哪里考入译训班的?
赵兴民:我于1980年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我上大一的时候,有两位老师考上了译训班,一位是崔永禄老师,一位是淮清涛老师(注:均为第二期学员)。我大一时,淮老师一直教我英文精读课。他考上译训班之后给我介绍过联合国考试,对我帮助很大。崔老师、淮老师都先后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工作过。
姚斌:您第一次参加联合国考试是在什么时候呢?
赵兴民:我第一次参加考试实际上是在大三,而当时水平不够,就没考上。第二次考试在大四,大概是在1983年年底,幸运地考上了,1984年9月就入学了。
姚斌:您还记得当时的考试内容吗?
赵兴民:我记得有英译汉、汉译英、中文,还有时事政治,即综合考试。大概有四门吧。
姚斌:那时候有二外考试吗?比如法语?
赵兴民:我不记得是否有二外考试了。
姚斌:当时的英译汉、汉译英考试的内容是关于联合国的吗?
赵兴民:英译汉考试好像和联合国有关系,考试内容涉及国际政治和时事。汉译英考试是翻译一段文学作品——一位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所以还是很有难度的。中文考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综合考试就是考当时的时事政治。
姚斌:您这个是笔试吧?后面还有面试吗?
赵兴民:我不记得是否有正规的面试,但我记得外交部干部司曾派了两位女同志专程到南开了解情况,我还到学校行政楼与她们见了一面,这大概就算是面试吧。我当时既兴奋又紧张,同宿舍的一位热心同学借了一件西装上衣给我,让我大胆地去会面,并祝我好运。面试的结果很顺利。我一直不忘那位老同学借给我西装上衣的情景。
姚斌:您考入译训班以后,当时的任教老师都是谁呢?
赵兴民:有张载梁老师、王若瑾老师等。张载梁老师教的视译是第一门翻译课,我印象非常深刻。王若瑾老师教交替传译。周育强老师除了教交替传译,还开了一门国际法知识课。夏祖煃老师、吴嘉水老师教笔译。还有一位俞天民老师,教的是一门经济学课,用的课本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俞老师用英语讲经济学,讲得很有趣,课堂里经常有开心的笑声。当时负责行政和后勤的有鲁人老师和万里老师,资料室有董黎老师。
姚斌:当时你们学习的情况大概是怎样的?
赵兴民:第一年我们的学习不分口译和笔译,第二年译训班才根据大家的成绩和特长区分了口译方向和笔译方向。
姚斌:您第一年是学同传还是交传?
赵兴民:第一年大家都需要学视译和交传,还有笔译。其他课程有国际法、经济学、语言学等。第一年课程比较多。第二年将口、笔译分开教学后,我们的课程少了,但练习多了。学口译的同学大部分时间在同传练习室里做练习。学笔译的同学稍微轻松一些,他们的练习内容主要是联合国文件,我记得文件中有安理会的逐字记录。
姚斌:你们毕业的时候,毕业考试是联合国考试团来考试,还是自己的老师组织考试?
赵兴民:联合国派遣的考官,与译训班老师组成一个考试团。老师这边有张载梁老师和其他一两位老师,大概共有四五人吧。考试团要对每一位考生进行面试。面试是重要的一关,大家都知道以往有面试不过关而拿不到证书的,所以大家都很重视。
姚斌:当时大家学习的劲头足吗?学习勤奋吗?
趙兴民:非常勤奋。首先入学考试的难度就很大,参加考试的人来自几个大城市,竞争很激烈。那一届参加考试的据说至少有300人,但最后只录取20人。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的内容大家也都觉得很有挑战性。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练习,都是非常贴近联合国实战的。第一年就有因上课紧张而睡不好觉的同学,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记得在一次模拟演讲活动中,我们曾幽默地以联合国大会辩论的方式来讨论如何遵守作息制度,如何做到相互尊重,互不影响。
姚斌:您觉得在译训班学习这两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赵兴民:首先,无论是口译老师还是笔译老师,他们的水平都很高。他们都有联合国翻译的经验,这些翻译经验特别宝贵。其次,联合国的文件有难度,学习本身的挑战性就能激起大家强烈的兴趣。同学们的外语水平和知识水平也普遍很高,能起到相互促进、相互激励的作用。大家相互讨论的气氛也很浓厚。北外在学习语言、翻译方面具有特别的优势。一些选修课是高水平的教授来讲的。我记得讲语言学的是一位外籍教授,他教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讲得十分清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讲座也很有意思,学校请尤金·奈达来开过一个系列讲座,介绍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我有幸通过这些讲座开阔了眼界。奈达的讲座对于学习笔译的人非常有启发,让我意识到翻译还有这么多的学问。译训班注重实战的特点,加上学校浓厚的学术氛围,都非常令人怀念,这为我们后来的口译或笔译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姚斌:从译训班毕业后您就去了外交部吗?
赵兴民:一毕业我就去了,我的大部分同学也都进了外交部,分配到新闻司、条法司、国际司、翻译室等部门。我去了新闻司新闻发布处。当时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刚刚建立。我们在新闻发布处协助拟定发言口径,做一些新闻发布稿的翻译,还会参加一些新闻发布会。我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两年,也就是从1986年8月到1988年6月。1987上半年我由外交部借调到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中文科,做了半年的临时笔译。严格地说,在新闻司实际工作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尤其是从工作多年的外交部前辈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以1988年到日内瓦去工作为起点,到现在已有三十一年。
姚斌:您在联合国工作这么多年,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未来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学?
赵兴民:首先,大学阶段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打基础阶段。学翻译的同学如果在大学的时候扩大知识面,同时全面提高英文和中文的使用能力,这对以后做翻译就非常有帮助。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都是如此。我在大学的时候接触过一些社会科学知识,比如心理学。我曾在一位老师的带领下参与翻译一本社会心理学著作。这些知识都很有用。我对文学也很感兴趣,听过一些文学讲座,比如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讲座。我也看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这些对提高文学素养和中文表达能力都有帮助。我觉得,要真正做好笔译,强化英文和中文功底,拓宽知识面,是最基本的要求。
姚斌:在这么多年的笔译经验中,您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平常在书里看不到的心得?您提到了语言能力和知识,但在联合国这样的机构里做翻译,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赵兴民:联合国是目前最大、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语文部门对于这个组织完成其使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的笔译工作具有机构翻译的特点。翻译所涉领域广泛,既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又要不断迎接新的挑战。对于译员个人来说,我的一个很深的感受是,虽然使用的翻译工具有变化,但工作性质常年不变,甚至连续几十年不变。翻译工具方面,比如技术手段,现在大家每天都在使用互联网,获得参考资料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去翻阅纸质工具书的情况越来越少,但基本的工作性质没有变,仍然是要把一种外语(比如英语)变成汉语,而且要变成尽可能准确、通顺的汉语,这一点基本没变。所以在联合国做职业翻译,如果说有特殊的要求,那就是需要对翻译工作本身有持久的喜爱和热情。这样才可能做好这份工作。
具体说来,要做好翻译工作,就要永远怀着学习的愿望。任何领域的翻译都充满学问。联合国翻译更是如此。译员很难一下子达到很高的水平,需要钻研和积累,坚持五年、十年,就不一样了。我从进入联合国开始,就怀着一种学习的愿望,而且想把这件事做好。我内心始终保持这样的追求。所以,一开始我就多向老同事学习,多请教、多琢磨。这样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对翻译的体悟也越来越多。随着我对背景知识越来越了解,对联合国会议和文件的了解越来越系统,对这些文件所用语言的历史、变化以及相应译法的变化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便有了足够的信心。遇到新的词语,进行一番研究之后,我一般都能够敲定译法。这就是多年学习和积累的结果。
我想对年轻的同学说,如果选择做笔译工作,就需要对这份工作有热情,要真心喜欢,要有探索未知的愿望、有追求完美的精神、有持久的耐力。持久的、认真的努力一定会带来较大的收获。除了职业上的成功,另一种收获便是知识和学问上的收获。翻译的学问不是抽象的,是跟实践密切相关的。在过去十多年里,我在业余时间里不断地总结自己的和集体的工作经验,单独或与朋友合作编写了几本与翻译有关的书,例如《联合国文件翻译》(与曹菡艾合著)、《联合国文件翻译案例讲评》和《商务翻译译·注·评》(与蔡力坚合著)等。这些翻译经验总结会对以后的学生有帮助,它们也反映了联合国翻译的普遍经验,具有相通性。实际上,做任何翻译,基本道理都是相通的。一个优秀的联合国翻译人员,不单单是能胜任联合国翻译,也应该能够胜任大多数其他机构、组织、企业所需要的翻译工作。从事联合国翻译,收获的也不仅是这些。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意见、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都会汇集在联合国进行交流,这给译员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精神视野。还有,联合国会议的讨论成果会直接影响世界。虽然作为笔译是在幕后工作,但是我们同样有很强的参与感。因为你翻译的文件会直接由代表们使用,他们的讨论成果会变成决定、决议、宣言甚至公约,会影响各国的行为。比如我和这里的多位同事参与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巴黎气候协定》等文件的翻译。这些文件含有复杂的技术内容,又涉及各国敏感的安全、环境、经济利益。这些文件的翻译、修改、完善也往往伴随着大量讨论、协调和交流,故最后的定本凝聚着众多译员、与会代表和有关专家的贡献。这一工作的意义不言而喻。
姚斌:最后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做笔译要有热情,而且是长久的热情,但现在学习翻译的同学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总觉得笔译挣不到钱,所以都愿意学口译,不愿意学笔译。从您的角度来看,长期坚持做笔译最大的魅力在哪里,值得人们去追求的是什么?
赵兴民:国内笔译报酬低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不正常的,有待于将来逐步得到纠正。在国际组织里,口译和笔译的地位是一样的,都是语文部门的专业人员。实际上,据我所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包括在各个国际组织内,都普遍缺乏高水平的笔译人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联合国给笔译设定了很高的门槛,必须经过考试才能进来,但高水平笔译人员仍然不足。能够考到联合国,不直接等于高水平。动力不足,学习精神不够,水平也会停滞。实际情况表明,遇到比较重要的、紧急的或者复杂的任务,就特别需要工作认真、水平较高的译员来完成。
姚斌:国内也是一样,真正高水平的笔译人员很缺乏。
赵兴民:对,这一点毫无疑问。笔译本身既是一个专业,一个职业,同时它也包含着许多学问。这些学问是与实践高度相关的学问。这种学问涉及很多学科,比如语言学、经济学、法律以及各种科学技术领域。总的来说,要做好笔译需要不断学习,积累各个学科的知识。我觉得有志于笔译的同学应该满怀信心地来学习笔译,不用担心将来的工作前景。机器翻译会越来越普遍,但是机器翻译难以真正替代高水平的翻译,所有重要的翻译都离不开人,不可能靠机器翻译来定稿。除了作为职业所具有的意义以外,翻译(我主要指笔译)带给人的智力挑战和满足,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会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对翻译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成为许多人终生喜爱和钻研的事业。说到这里,我也在此提醒有志于笔译的同学,笔译与其他需要长时间使用电脑的工作一样,是一项艰苦的职业,需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作基础。为此,你们需要加强体育锻炼,需要培养一两种持久的体育爱好,这样才能防止或减少长期坐在电脑前工作引起的职业病,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精神。我自己现在也比较重视锻炼身体,希望保持良好的状态,在今后几年以及退休之后多做点有益的事情。我期望做的一件事是继续整理自己的翻译经验,尤其是在国际法翻譯方面的经验。我负责国际法文件的翻译已经有十几年,平时与同事们经常进行讨论和互动,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和资料。将国际法的翻译经验整理出来,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最后,我分享几句打油诗。这是我三十多年前刚到日内瓦后写的。在纪念译训班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这几句打油诗或可表达我自己继续学习翻译和探讨翻译的愿望:日观窗前景, 清晰又朦胧。欲解其中意,还须数秋冬。
姚斌,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副院长,入选201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卓越人才支持计划。
李长栓,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