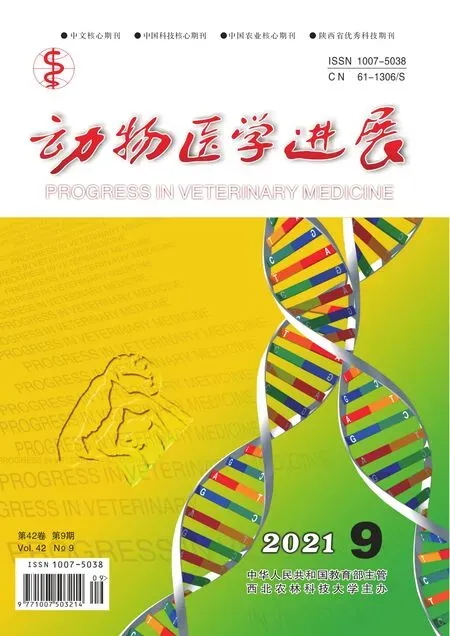牛呼吸道疾病两种细菌性病原研究进展
陶乔孝慈,马 雪,张丽媛 ,操义恒 ,李 劼,周 霞,张星星,黄 新,吴桐忠*,韩猛立*,钟发刚
(1.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新疆石河子 832003;2.新疆农垦科学院/省部共建绵羊遗传改良与健康养殖国家重点实验室,新疆石河子 832000)
牛呼吸道疾病(Bovine respiratory disease,BRD)是一种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综合征,包括环境和管理相关的应激源以及多种病毒和细菌病原体,给北美和世界养牛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仍然是影响北美地区肉牛最常见和损失最大的疾病,也是引起奶牛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1]。我国目前尚未研制防控BRD的相关疫苗,防控措施较为单一,建议深入开展致病机理及防控技术研究,开发有效的诊断试剂与疫苗,对高效防控该类疾病,保障养牛业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3]。Dubrovsky S A等[4]报道美国加州的饲养场中BRD的发病率约为75%和病死率接近50%;育肥场的发病率更高,初步估计发病率和病死率约为90%。而在奶牛养殖场中,断奶犊牛BRD的发病率约为22%和病死率约20%,也是导致断奶前犊牛死亡的主要原因。
BRD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引起并最终导致受感染牛表现临床症状,但引起发病的细菌性病原体主要是溶血性曼氏杆菌(Mannheimiahaemolytica,Mh)和多杀性巴氏杆菌(Pasteurellamultocida,Pm)[5]。这些病原体已经适应并定植于呼吸道黏膜表面,从而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适应机制包括表达黏附素、产生和分泌毒素与蛋白酶以及形成生物膜。耐药性是BRD病原菌中的一个新问题,而Mh广泛耐药(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XDR)菌株的分离越来越普遍[6-7]。本文对引起BRD的两种主要细菌性病原体的生物学特性、免疫逃避和致病机制、耐药性与耐药现状及多重耐药的遗传机制,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对此类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疗效等进行简要概述,以期为我国防控该病提供参考。
1 Mh与Pm概述
Mh和Pm是巴斯德菌科的革兰氏阴性兼性厌氧菌,通常定植于临床健康牛的口咽部黏膜上。一般来说,这些微生物引起牛的临床疾病是由应激、免疫抑制和病毒感染的共同作用导致的,最终导致其在下呼吸道的过度生长。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具有传染性,至少Mh可在种群内传播[8-9]。
多杀性巴氏杆菌由5种荚膜血清型(A、B、D、E、F)和16种菌体血清型(1-16)。相比之下,溶血性曼氏杆菌至少由12种荚膜血清型(1、2、5-9、12-14、16和17)组成。对于两种病原体,荚膜血清型是引起宿主特异性和致病性的原因。尽管存在不同的血清型,但临床疾病多集中在荚膜血清A1型Mh(>75%的病例)和荚膜血清A3型Pm(肉牛>30%和奶牛>60%的病例)。Cozens D等[10]的研究表明,A1型Mh的特异性毒力因子促进了其在牛呼吸道上皮细胞的侵袭,使其能够进行不受控制的复制并扩散到邻近的细胞;一旦进入细胞,能对受感染的组织造成广泛的损害,同样的现象没有在呼吸道共栖的血清型中发现[10]。
除了荚膜型外,这两种微生物都是革兰氏阴性菌,其特征是细胞外壁存在脂多糖(LPS)。内毒素是一种强有力的促炎介质,可触发细胞因子的释放,并刺激炎症细胞的涌入,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此外,内毒素与白细胞毒素协同作用可以增强Mh的致病性。
2 Mh与Pm的免疫逃避和致病机理
许多革兰氏阴性病原体已经进化出在黏膜表面定植并增强细菌与宿主相互作用的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强毒株的详细研究使得各种影响因素为人所知,这些因素使Mh和Pm在逃避宿主免疫反应或增强临床疾病方面没有差异(表1)[5]。这种能力是很重要的,因为了解致病的不同毒力因子可能有助于开发出以增强对这些化合物的免疫力为中心的控制策略。

表1 溶血性曼氏杆菌和多杀性巴氏杆菌的免疫逃避机制和毒力因子
Mh和Pm都能产生一系列黏附素,这些黏附素允许上皮细胞附着并防止吞噬作用[5]。例如,荚膜 A型Pm的荚膜由透明质酸组成,这种荚膜增强了与呼吸道上皮细胞的结合和在下呼吸道的定植。此外,Mh产生一种纤维蛋白原结合蛋白,该蛋白包裹在细菌细胞表面,阻止补体结合,从而降低调理作用[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病原微生物的其他血清型的荚膜是由与宿主组织成分非常相似的物质(如肝素、软骨素)组成的,这可能导致它们的抗原性较差。
这些病原体还有其他几种逃避和操纵宿主免疫系统的方法。例如,免疫球蛋白(Ig)A-特异性蛋白酶系列可以裂解IgA并阻止其与病原体结合[11]。这些蛋白酶的最终作用是防止调理作用或补体介导的杀伤。此外,Mh具有在呼吸道中形成生物膜的能力,生物膜是一种由多糖、蛋白质和DNA组成的聚合物包裹的有组织的细菌群落,是细菌适应生活在潜在的恶劣环境中的一种手段[11]。在健康的宿主中,大多数Mh可能存在于口咽和扁桃体隐窝的生物膜中。在生物膜内,细菌可以免受抗菌药物和宿主免疫反应的影响。当病原微生物处于生物膜而非浮游状态时,许多抗菌药物对Mh的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倍增[12]。此外,研究表明,宿主产生的应激性化学物质(P物质、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可以促进生物膜扩散,生物膜是一种能够从上呼吸道向下呼吸道运动的因子,并将应激与临床BRD联系起来[13]。
白细胞毒素是一种由Mh产生的与临床疾病相关的重要毒力因子,这种毒素的重要性与Mh致病性直接相关。因此,在设计Mh的控制方案时,必须首先考虑白细胞毒素的影响。白细胞毒素是毒素(repeat in toxin,RTX)家族中的重复序列,在细菌的对数生长期所有Mh均可产生[6]。白细胞毒素可特异性地与牛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血小板和淋巴细胞表面的分化簇(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CD)18相互作用,一旦与之接触,中性粒细胞就会脱颗粒并释放有效的消化酶进入周围组织。此外,白细胞毒素刺激组织肥大细胞的脱颗粒和血管活性介质的释放。如前所述,内毒素和白细胞毒素具有协同作用,内毒素是一种有效的趋化剂,可使中性粒细胞和其他炎症细胞进入呼吸道。此外,内毒素的释放有助于CD18在炎性细胞表面的上调表达。因此,更多的细胞对白细胞毒素具有更高亲和力,其存在可导致严重的临床疾病发生[5],如Mh经常与典型的纤维蛋白性胸膜肺炎的发生相关。
3 Mh与Pm的耐药性
兽医最关心的是细菌的临床抗药性,他们感兴趣的是某种特定抗菌药物能有效治疗被某种特定病原体感染而导致某种疾病的动物[14]。临床耐药的概念是基于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CLSI)——兽医抗菌药物敏感性测试委员会制定的药敏结果解释标准,具体如下:一是特定细菌病原体代表性群体的抗菌药物的体外最小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范围;二是通过药物浓度与微生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建立的药代动力学/药效学(PK/PD)的参数;三是在目标物种中进行临床试验的结果[15]。
对于BRD病原体,CLSI批准了针对青霉素(仅限于肉汤稀释法)、头孢噻呋、达氟沙星(danofloxacin)、恩诺沙星、氟苯尼考、硫酸大观霉素、拖拉霉素(tulathromycin)、加米霉素(gamithromycin)、泰地罗新(tildipirosin)和替米考星(tilmicosin)的药敏结果解释标准[16];对于这些抗菌药物,敏感性结果表明治疗成功的可能性明显大于耐药性结果。这些药敏结果仅适用于按照抗菌药物使用说明进行,且药敏试验采用CLSI批准的方法和解释标准的情况下,然而药敏试验与临床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善。同样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认识到抗菌药物药敏试验不能保证在单个动物身上得到特定的临床结果。试图通过体外测试获得的药敏结果来推断体内反应,疾病结果通常受到诸如宿主免疫状态、个体药代动力学参数变化或疾病严重程度增加/病程延长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没有CLSI批准的药敏结果解释标准的抗菌药物,已从其他物种的血浆和组织液中推断获得,例如青霉素G(纸片扩散法)、四环素(纸片扩散法)、强化磺胺类药物、氨基糖苷类药物和红霉素等药物[17]。对于这些抗菌药物而言敏感结果优于耐药性结果,但是目前尚无相关数据可将敏感性测试结果与牛BRD的预期结果相关联。
第二种耐药性是根据监测细菌野生型种群中药物敏感性分布特征变化的数据进行定义的[18]。这些流行病学临界值没有提供与临床结果相关的数据,而是代表了MIC与原始细菌种群的偏差,可以用来指示耐药性决定因素的出现。因此,流行病学临界值可能表明MIC的耐药性与临床药敏结果解释标准有所不同(通常更低)。此外,尽管文中提到的许多研究可能涉及多种抗菌药物,但仅讨论CLSI已建立敏感性结果解释标准的药物;病原体为Mh、Pm和睡眠嗜血杆菌(Histopilussomni,Hs),抗菌药物为头孢噻呋、达氟沙星、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加米霉素、青霉素、大观霉素、四环素、泰地罗新、拖拉菌素、替米考星(仅适用于Mh)。
4 Mh与Pm的流行率与耐药模式
最早建立的Mh与Pm的MIC分布是利用现代实验室诊断方法和CLSI批准的药敏结果解释标准,通过对1988年至1992年期间死于BRD的动物调查得出的[19];在这项研究中,对美国和加拿大20多个州的461株Mh和318株Pm菌株进行MIC测定,结果表明Mh和Pm分离菌株100%对头孢噻呋敏感,83.5%和83.3%对大观霉素敏感,57% 和70.5%对四环素敏感,69.1%和未测试对替米考星敏感。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使用的替米考星的解释标准在Mh与Pm上均未通过验证;按照目前公认的标准,使用该药物的耐药性将显著降低(>90%敏感)。对1994年至2002年俄克拉荷马州死于BRD的肉牛肺中分离获得的390株Mh和292株Pm耐药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四环素和大观霉素的敏感性各不相同且较低,氟苯尼考和替米考星与头孢噻呋和恩诺沙星的结果正好相反,敏感性很高且相对稳定[20]。对2000年至2009年间美国和加拿大收集的Mh(n=2 977)和Pm(n=3 291)分离株进行药物敏感性评估,结果显示头孢噻呋对两种病原体均保持高度敏感且一致(100%敏感),对达氟沙星、恩诺沙星和氟苯尼考的敏感性随时间的推移保持稳定,而对替米考星和拖拉菌素的敏感性均下降[21]。一项来自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对细菌多重耐药性和共同耐药模式的研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该研究评估了2009年至2011年期间从患有BRD的牛肺部分离的Mh分离菌株;研究结果表明分离株对5种或5种以上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比例从5%增加到35%,对土霉素或替米考星耐药的菌株,至少对另外1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明显更高[22]。
研究人员对到达和离开育肥场的牛就抗菌药物的耐药性进行了多项研究。Klima C L等[23]对阿尔伯塔省南部2个饲养场,在进入时和离开前30 d内选取30%圈舍采集10%的动物鼻拭子样本,用于Mh的分离和药敏试验,获得了409株Mh,药敏结果显示对所有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从0.2%到3.9%不等且都很低,其中对土霉素普遍耐药;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中许多被评估的抗菌药物,CLSI没有明确由Mh引起的BRD的药敏结果解释标准,这使得研究中的一些结论难以解释。Noyes N R等[16]对加拿大4个饲养场按照到达时和离开前的一个时间点,采集深部鼻咽(deep nasopharyngeal,DNP)拭子,获得2 989株Mh,评估21种不同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耐药性很少见,87%的菌株对所有抗菌药物都敏感。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与Klima的相似,许多被评估的抗菌药物, CLSI没有解释标准。一项来自加拿大的研究评估了从健康和患有BRD的牛身上分离出Mh的耐药模式, 18%的分离菌株具有耐药性[17]。总的来说,收集于BRD牛的分离株(32%)比健康牛 (2%)更容易产生耐药性。分离菌株普遍对四环素耐药,一般来说,如果分离株对一种药物耐药,它也至少对一种其他的抗菌药物耐药[17]。
Snyder E等[7]评估了使用长效大环内酯类药物拖拉霉素预防Mh耐药性的流行情况,取得了令人惊讶的结果。犊牛在进入育肥场之前被给予拖拉霉素以防止BRD发生,在抵达当天采集DNP拭子,10 d~14 d后再采集1次。结果表明与在抵达时相比,对于除头孢噻呋外的所有抗菌药物,第二次被划分为中介或耐药的分离株比例显著增加。第二次药敏结果显示0.8%表现为敏感, 24.4%对2种抗菌药物(氟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中介或耐药, 74.8%对3种抗菌药物(氟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以及酚类或头孢菌素类)表现为中介或耐药[7]。评估恩诺沙星和拖拉菌素在治疗和预防犊牛BRD中的疗效和耐药性时得出了与Snyder类似的结果。Woolums A R等[18]进行的相关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使用大剂量泰地罗新进行药物治疗后采集DNP拭子,分离鉴定的Mh分离株几乎对除头孢噻呋外的所有药物均具有耐药性,且100%属于多重耐药(multidrug resistance,MDR)。
综上所述,许多有关BRD主要细菌性病原体耐药性的研究工作都来自饲养场和育肥场。而在养殖场中,关于耐药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来自瑞士的Pipoz F等[19]收集了来自52个奶牛群的中犊牛临床样本,对样本中Mh和Pm分离菌株的耐药流行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Mh(n=8)分离菌株对四环素、恩诺沙星、青霉素、头孢噻呋、大观霉素和氟苯尼考敏感;相比之下,Pm(n=37)分离菌株对恩诺沙星、头孢噻呋、大观霉素和氟苯尼考敏感,但对替米考星呈现中介,对四环素呈现耐药。Owen J R等[20]评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育肥场和饲养场采集的犊牛鼻拭子中分离出的Mh和Pm菌株耐药性的流行情况,结果显示Mh和Pm分离株对头孢噻呋和恩诺沙星敏感,其中大多数Pm分离株对青霉素和托拉菌素敏感,超过50%对达氟沙星耐药,30%对氟苯尼考耐药,90%以上的对四环素和替米考星耐药;所有的Mh分离株均对大观霉素敏感,20%对达氟沙星、拖拉菌素和氟苯尼考耐药,30%对替米考星耐药,有60%对青霉素耐药。一项来自Snyder E等[5]的最新研究,收集了加利福尼亚一个牧场的100头诊断为BRD的奶牛样本(经鼻腔清洗、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的DNP拭子),对样本中分离的Mh(n=53)和Pm(n=175) 进行了药物敏感性评估,结果显示多数Pm(>90%)分离菌株对氨苄西林、头孢噻呋、青霉素、大观霉素和托拉菌素敏感,但对恩诺沙星和氟苯尼考耐药;相比之下,大多数Mh (>90%)对氨苄西林、头孢噻呋、青霉素和氟苯尼考敏感,对恩诺沙星和大观霉素中介,对拖拉菌素耐药。
5 多重耐药的遗传机制
上述表明BRD是主要细菌性病原体,特别是Mh的耐药性正在增加,广泛耐药(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XDR)Mh的分离也越来越普通。所以,问题是只接触一种药物后,如何产生对多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通常是水平基因转移导致了抗药性的迅速增加。水平基因转移有3种不同的方式:(1)通过转化从环境中所谓的外源DNA中获取基因;(2)通过转导由噬菌体转移遗传物质;(3)通过获取可移动的遗传元素[21-22]。虽然这3种机制都可以在获得耐药性中发挥作用,但在Mh和Pm中,多重耐药(multidrug resistance,MDR)菌株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似乎是获得一种称为整合共轭因子(integrative conjugative element,ICE)的移动遗传元件[23]。ICE是整合到宿主染色体中的移动遗传元件,然后可以将它们繁殖并传给后代,但也可以自我切割,以环状中间体的形式复制,并通过Ⅳ型分泌系统转移到其他邻近细胞,最终整合到新宿主的染色体中[22]。ICE中通常还带有其他载体基因包括抗药性基因,受体细胞正是随着ICE转移的这种方式迅速获得了多种抗药性基因[24]。
Mh和其他与BRD相关的巴氏杆菌科中已记录了大量不同的ICEs。Pm(ICE-Pmu1)中鉴定出第一个携带四环素、氟苯尼考、磺酰胺、大观霉素、恩诺沙星、替米考星和拖拉霉素抗性的ICE基因。 Eidam C等[25]在Mh 菌株42548中发现鉴定出第一个ICE基因是ICEMh1,该ICE基因比ICEPmu1长但缺少一些基因,这些基因赋予了ICEPmu1对相同数量的抗药性基因。
2014年Klima C L等[23]对来自Mh、Pm和Hs的25个ICEs进行了鉴定。在采集自乔治亚州肉牛育肥场的Mh分离菌株中发现了3个ICEs(命名为UGA1,UGA2,UGA3),这些ICEs的长度各不相同,但与ICEMh1和ICEPmu1具有同源性;ICEMh-UGA1和ICEMhUGA2的前1/4与ICEMh1相似,而其余3/4与ICEPmu1相似。此外,这些ICEs携带的所有抗性基因与存在于ICEPmu1中的相同,但ICEMh-UGA2中不含有floR基因(对氯霉素类药物具有抗性的基因);与鉴定出的其他两种ICE不同,ICEMh-UGA3仅携带tetH/R抗性基因复合体(该复合体编码对四环素类抗生素的抗性基因)。
ICEs中存在的耐药基因将对多种类型、具有抗菌作用的大量抗菌药物产生抗性。在Mh分离株携带的β-内酰胺抗性基因中,最常见的是blaOXA-2,其次是blaROB-1(尽管该基因携带在不依赖于ICE的质粒上的可能性较大,就像最近发现的blaROB-2基因)[8,23,26-27]。所有这些编码超广谱β-内酰胺酶的基因,不仅对经典的青霉素类药物,而且对较新的广谱头孢菌素类药物都具有抗性[27]。已知所有这些基因均可传递对氨苄青霉素和青霉素的耐药性,并可能增加头孢噻呋的MIC[23,28]。不过,这些基因的存在可能不会自动导致抗性,因为已知这些基因会产生导致基因失活的点突变[29]。
Mh和Pm对氯霉素类抗生素的耐药性通常是由floR基因的存在引起的[23]。该基因编码一种药物外排转运蛋白,它能主动地将氯霉素类抗生素泵出细胞。然而在某些情况下,floR并不能使Mh和Pm产生完全的抗性而是将MIC调整到中间范围,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微生物中基因的活性降低。tet类基因是编码四环素的最常见抗性基因,这些基因可调控外排泵将四环素主动泵出细菌细胞。在Mh和Pm中,tetH、tetB、tetL和tetG是编码这种泵的最常见基因,它们可以在质粒和细菌染色体中找到[30]。但是在Mh和Pm的ICEs中仅发现并记录了tetH基因[23,25]。在这些ICEs中通常还存在一个tetR基因(有时是重复的),它充当tet基因对四环素浓度敏感的转录调节因子[23,25,31]。
大环内酯类药物广泛应用处于高风险的BRD牛身上[32]。erm42、msrE和mphE基因是Mh和Pm ICE中最常见的大环内酯类耐药基因,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这类抗菌药物产生耐药性。研究表明erm42基因编码一个单甲基转移酶,该转移酶在23S核糖体亚基上的A2058核苷酸处添加了一个甲基基团,从而导致对林可酰胺类药物的耐药性,以及对低浓度大环内酯类和链霉素类抗生素具有耐药性。msrE基因编码大环内酯类外排泵,对14元和15元环大环内酯类药物如红霉素、拖拉菌素和加米霉素产生耐药性;然而,它不产生对16元环大环内酯类药物的耐药性,如泰乐菌素、替米考星和泰地罗新。mphE基因是一种大环内酯类磷酸转移酶,在传递抗菌药物耐药性的方面与msrE具有相似的作用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磺胺类药物在治疗牛病上的疗效逐渐下降,伴随着新抗菌药物的出现其使用量越来越少。sul1和sul2基因是革兰氏阴性菌对磺胺类药物的主要耐药基因,它们是通过编码一种耐药的二氢叶酸合成酶来起作用的。到目前为止,在Mh和Pm中仅发现sul2基因和ICE相关。ICE中存在的其他基因有aadA25、aadB、strA和strB以及aphA1,这些基因编码对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抗性。aadA25(ant3〃)通过编码氨基糖苷类O-核苷酸转移酶促进对氨基糖苷大观霉素和氨基糖苷链霉素的耐药性。aadB(ant2〃)也编码氨基糖苷O-核苷酸转移酶,但对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地贝卡星(Dibekacin)、西索米星(Sisomicin)和卡那霉素产生耐药性。strA(aph3〃)、strB(aph6)和aphA1(aph3′)是抗性基因,其编码修饰和使氨基糖苷失活的氨基糖苷O-磷酸转移酶。strA和strB均对链霉素产生耐药性,而aphA1则对卡那霉素、新霉素、巴龙霉素(paromomycin)、核糖霉素和利维霉素(lividomycin)产生耐药性。
导致Mh分离菌株XDR株流行率上升的因素可能是携带多种基因,这些基因对目前用于预防和治疗BRD的大多数抗菌药物产生耐药性。重要的是由于牛呼吸道病原体具有XDR的性质,接触一种抗菌药物不再仅仅是选择对这一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耐药性现在是一种多药现象,接触一种抗菌药物中会选择对其他多种相关和不相关的抗菌药物产生耐药性。关于BRD病原体耐药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耐药性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众多MhXDR菌株所携带的ICE导致的[8]。抗菌药物导致XDR菌株的扩增和繁殖,以及随后该菌株基因组中携带的所有基因和突变。因此,如果动物被诊断出患有BRD并接受了一种特定的抗菌药物治疗,那么该动物随后不仅会携带对该抗菌药物具有耐药性的分离株,而且会对该动物分离株ICE所携带的其他所有抗菌药物具有抗性,因为不同的基因之间存在联系[7,9]。此外,由于XDR Mh菌株也含有对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产生耐药性的突变,尽管该基因/突变未携带在ICE上,但对此类抗菌药物的仍将呈现耐药表型[8,18]。重要的是,有新的证据表明这些菌株可能通过牛犊之间的接触以及暴露于受污染的环境,在具有感染风险的牛群中传播[8-9,16]。因此,了解XDR,重要的是不要仅仅局限于治疗过的动物;相反,有可能会在与治疗动物使用但从未接触过抗菌药物的动物身上发现XDR克隆[16]。
6 抗菌药物耐药性对治疗结果的影响
首次治疗成功的定义是在第一次应用抗菌药物治疗效果显著的动物比例。在大多数育肥牛饲养场中首次治疗成功的比例都很高。通常,大于80%的首次治疗成功比例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Avra T D等[33]对引起治疗失败的风险因素进行评估和回顾性研究发现,超过30%的牛对首次治疗没有反应,而且暴露于高风险感染状态比低风险状态的犊牛首次治疗失败的可能性大。但是关于耐药性对患BRD牛临床预后的影响很少有人评估,Mcclary研究表明处于易受Mh分离株感染中的牛群 62%(n=688)对替米考星治疗有反应,但是38%(n=6)的牛携带耐药菌株。
7 结语
在临床治疗中必须认识到毒力因子和抗菌药物耐药性,并在制定以这些病原微生物为中心的治疗和控制方案时考虑这些因素。尽管BRD对北美乃至世界养牛业具有重要意义,养牛业发达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研究人员很少有经过精心设计的研究来评估引起BRD重要细菌性病原体的抗药性。现在发表的多数文献均是来自于经过多次不同抗菌药物治疗的病死牛样本中获得实验诊断报告,且这些动物已经用多种不同的抗菌药物进行了多次治疗。以Mh为例,总体趋势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敏感性降低了,临床耐药菌株在逐渐增加。近年的研究表明,某些牛场中常见的抗菌药物使用方法可能是促使耐药克隆增加的主要因素。在科研人员做好流行病学、病原分离鉴定、致病机理、耐药性与免疫防控研究的基础上,广大从事具体养殖的牧场主和从业人员,应将重点放在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控、减少应激、增强免疫功能和抗菌药物管理上,将有助于成功控制由这些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综合征,减少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促进养殖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