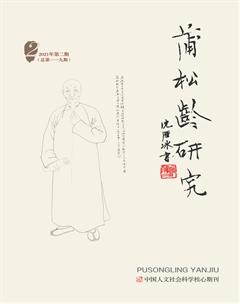试析《画皮》文本与电影改编的有效互设作用
王璟

摘要:《聊斋志异》的名篇《画皮》在20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多次被改编搬上银幕。综观《画皮》系列电影改编历程,其在原著基础上对接不同时代热点及审美需求结构故事,借助日益精进的电影制作技术拓展文本改编空间,并渐趋弱化劝诫警示主旨而凸显爱情主题。本文希冀结合不同时代的审美需求、技术特色及受众的价值观,探讨《画皮》文本与电影改编的有效互设作用。
关键词:画皮;电影改编;时代热点;电影制作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21)02-0143-11
《聊斋志异》作为我国优秀文言短篇小说集的代表,因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典型鲜明的人物形象、奇崛精彩的文学想象、细致精到的人物描写让众多读者手不释卷,同时也为多种艺术形式改编提供了广泛的空间。20世纪中期至今,伴随着我国电影领域的拓宽、电影技术的日益精进,电影界编导掀起了“聊斋IP”的改编热潮。《画皮》《聂小倩》《辛十四娘》《小翠》等名篇被赋予时代印记及前沿影视技术手法,在多次翻拍、改编中对我国古典文学的当代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名篇《画皮》因离奇的故事情节、清晰的人物关系、开放性的角色设置、劝诫警示的小说主旨及“变幻之状,如在目前” [1] 第九卷209般高超的鬼怪形象描写,一直受到电影界的青睐,成为被改编次数最多的篇目。据笔者统计,自1966年至2020年,《画皮》故事多次被搬上荧幕,成为经典电影IP,详见下表:
通过对《画皮》系列电影中主人公角色设置及人物间关系综合评析可知,电影改编一方面遵循小说故事主线,将或妖或鬼或机器人的异化者角色植入正常夫妻(恋人)关系之中,在此期间异化者通过“借皮成人”的特异手段以期达到某种目的,最终均借助正义使者将其制服,有效发挥了小说原著惩恶扬善的劝诫警示作用;另一方面,《画皮》系列电影在日新月异的电影科技推动下,将文学想象转化为华丽、精彩的视觉盛宴,“借皮成人”的特异手段,“两女爱一夫”的三角恋爱故事,降妖除魔的故事主旨被历任编剧,导演置于不同时代背景中,帮助观众有效获取时代信息,再次认知经典形象。在以往关于小说《画皮》到电影拍摄的研究中,研究者或关注中国商业电影的运作模式,或立足于电影改编的魔幻视觉效果,或探讨影片对传统文化的承袭,或择取两部雷同影片进行纵向比较;其中,部分研究者在把握电影改编所带类的科技特效展示、人物情节突破性的同时,往往忽略了《画皮》系列电影改编近六十年的历程中,如何在原著基础上结合不同时代审美需求有效增删故事情节、丰富人物形象,如何借助日益精进的电影制作技术创新性拓展“《画皮》IP”改编空间,又如何一步步在影片中弱化小说劝诫警示的主旨而改为凸显人间真爱的爱情主题。在此,本文立足《画皮》系列电影近六十年的改编历程,结合不同时代的审美需求、技术特色及受众的价值观,探讨《画皮》文本与电影改编的有效互设作用。
一、“皮”之变:对接时代热点结构故事
关于电影对小说的改编,有研究者称为“旧瓶装新酒”或者“新瓶装旧酒”,即改编结果一方面要有小说文本“旧”的故事结构或人物关系,方能依随小说母题进行合理的二度创作并对接小说认知群体;另一方面则将发力点集中于“新酒”或“新瓶”中,依托同时期审美需求、电影特效技术及时代潮流创新故事情节或丰富人物关系,方能在多次改编中跨越雷同误区,成功寻求鲜活的、对接时代的改编热点。《画皮》系列电影能够在近六十年的改编历程中多次引發观影热潮,其成功要素之一便是有效地改编而非拟古翻拍,恰如美国著名戏剧与电影理论家劳逊所言:“如果一成不变地把一部小说改编为电影,那就不可避免成为名副其实乏味的东西。” [2]253《画皮》系列电影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90年代四版改编之后,至21世纪初的三版改编仍然吸引了大量观众观看并引发了一次次观感讨论热潮。《画皮》系列电影作为《聊斋志异》诸多短篇故事中改编较多且颇为成功的一部,关键得益于跨越近六十年的多版电影改编在保持原有“人鬼对峙”、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内核基础上,均能够实时对接观众时代感极强的审美需求,恰如小说《画皮》中女鬼斑斓的外衣,通过多变之“皮”有效地完成了一次次故事结构的创新。
1966年版《画皮》,虽然是历次《画皮》改编中最忠于原著的一部,但是导演鲍方仍在原著故事内核的基础上对接同时期社会文化心理,对主人公人设进行了部分改编。此版《画皮》突出了男主人公王崇文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第的人生发展低谷之身份设置,通过求签拜佛及谄媚考官女儿(即女鬼)的行为反映了古代书生渴望学而优则仕的普遍心态。1993年版《画皮之阴阳法王》,则依托20世纪90年代电影制作中魔幻、枪战、赌场等热门题材,延续1987版《倩女幽魂》的制作模式,在传统小说IP中融入幻象、武侠、搞笑、妖魔横行、善恶对峙等时代热点。影片在男主人公身份设置层面彻底摒弃了原著小说男主人公渴望功名、加官晋爵的相关描述,将其塑造成贪财好色、游手好闲之徒,有意通过电影改编折射出批判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因素。同时,影片中女鬼角色出场时白衣飘飘的场景,仍由饰演1987年版《倩女幽魂》的女主角扮演者王祖贤演绎,加之影片中升腾的烟雾、快退的镜头、飞檐对打的场景,人为地将其改编为当时颇为流行的武侠剧。
至21世纪,三版《画皮》电影相较原著故事改编更大,仅保留了小说文本中异化者“画皮嗜血”的核心故事情节,大篇幅地改造了时代背景、男女主人公身份设置,更将小说中女鬼杀人嗜血的邪恶目的转化为狐妖、机器人渴望人间真爱的情爱意图,旨在借助《画皮》故事关注青年男女的婚恋实况。
2008版《画皮》将原著故事时代背景上移千年至汉朝,影片中王生由一介柔弱书生转化为驰骋大漠、剿匪除恶的将军形象,原著及前几版影片中邪恶化身的女鬼则被演绎成“九霄美狐”,“人鬼对峙”演变为“人妖之恋”,“杀人嗜血”的故事桥段转化为隐匿于婚姻背景下的人妖之恋。影片中的异化者狐妖小唯娇小、可人、妩媚,她与人类亲近并非单纯的出于嗜血夺命之目的,而是渴望得到人间真爱。为了寻求人间真爱,狐妖为自己打造了娇羞的体态、我见犹怜的人设,并不惜出卖色相一次次潜入军营。狐妖小唯在这期间虽带有明显的“猎狐”式动机,企图接近不同男子以达到嗜血续命的最终目的,但故事却戏剧性的偏离了狐妖杀戮的直接目的,转向一场飞蛾扑火的人妖之恋。在一场刻意为之的英雄救美场景下,非但男主人公王生借助两次梦境隐晦地表现出对婚姻之外“美色+艳羡”桥段的无法自持,即使最初抱有杀人嗜血目的的狐妖小唯,在这场人妖博弈中也不由自主地爱上了面前英姿飒爽的将军。当狐妖身份被众人揭穿时,此版《画皮》仍旧背离了小说文本中对女鬼“立而切齿”、剖人腹、掏人心的暴力描写,则是沿用1993版《画皮》对女鬼的秉性设置,为了成全爱恋者王生对婚姻的忠诚、对妻子的守护,不惜牺牲自我以成全人间婚恋。影片中“王生—狐妖—王妻”之间的关系突破了原著劝诫警示的社会性寓意,通过狐妖目的性极强的谄媚之态唤起观众对审美无意识欲望的追求,借助“一张人皮面具”放大了人类婚恋生活中隐藏于角落的复杂情愫,成功映射了21世纪以来部分家庭关系的真实状态,进而引发了观者对婚姻、爱恋态度的多重思索。
2020年6月,通过网络播放平台上映的科幻电影《机械画皮》时隔多年重拾《画皮》IP,再次借助异化者“换脸成人”的小说经典桥段,并突破性地将叙事空间下移至21世纪20年代的白领阶层。《机械画皮》以机器人寻找爱情为主线,实则揭示了当下青年一代渴望丰裕的物质享受与经济匮乏的生活逆差,反映了热恋情侣在职场打拼多年仍囊中羞涩难购婚房的无奈,直面当今职场、婚恋现状,一时间引起众多90后观众的广泛共鸣。在《机械画皮》中,影片的情感主线围绕智能机器人寻找爱情铺设。机器人在升级皮肤自主生成系统后,已然具备行为自主的实力。因此它不甘沦落为男性宣泄的工具,更加渴望人间真爱。为了“寻爱”,它不惜杀人、换脸,只为取悦其制造者即假想恋爱对象,并不断询问对方“你爱我吗”,却在一次次努力中得到“你需要爱吗”之类的质疑。为了寻求其所缺憾的真爱,机器人努力搜索“爱情”与“钱”是否具有必然性关联,认真对街边人群作出系统客观的“人物关系状况分析”,在换皮成人后尽心满足男友的一切需求。在机器人苏辛与男友王生的相处中我们不难发现,机器人对爱一味迁就又迷失自我,这其中除了电脑程序所设定的“我是苏辛,我爱王生”之命令因素,更主要的体现了异化者在最爱之路上的迷茫。当机器人将爱情等同于顺从及陪伴时,它便会出现在男友生活的各个角落,殊不知人间真爱绝非“问”与“答”这般单一。因此,机器人闯入男友公务宴会导致了各方尴尬,每天更换一束鲜花并烹制价格昂贵的进口雪花牛小排,却换来男友对生计的担忧,私自拿出买房积蓄拍的古董花瓶直接引发二人激烈的冲突……当自己权倾付出之后仍被否定,机器人陷入了困惑与伤感中。当机器人卸掉人类伪装,恢复机器人形态,蜷蹲在废旧厂房的角落里,抚摸着自己强壮的机械手臂,独自为爱困惑忧伤时,它永远不会明白:人类的感情并非一味付出、全力迎合那般简单,更不能简单套用任何公式或程序。人间真爱需要承载双方家庭关系、物质压力,除了付出还有彼此的信任与包容。而《机械画皮》中的机器人作为《画皮》系列电影中异化者的代表,虽真诚地追求真爱却始终缺乏对人间真情的实际化感悟。即便每一版本在结尾处均为异化者打造了舍己救人的美好人设,却仍旧无法改变其“缺爱”“失情”“追梦而不得”的悲情结局。
综上可知,《画皮》系列电影对经典IP的改编已突破了传统电影翻拍小说文本的时代局限性,它们在遵循小说原著“换脸成人”“两女爭夫”等故事情节的基础上,高度浓缩不同时期“大众心理中最常见的情结” [3]107,实时对接社会热点及受众审美需求,“自然地作用在观众的无意识层面,对观众的身心二元产生改变” [4]43,理性地引导观众踏进“入片状态”。可以说,《画皮》系列电影能够多次被搬上银屏并引起广泛关注,得益于编导对社会热点的准确捕捉,观众既能在观影过程中对照《画皮》故事突破思维定势、自觉生成银幕幻象,更能够在“换皮”“嗜血”等视觉刺激中迅速游离于幻象之外并直观自身。
二、“技”之变:渐趋成熟的电影制作技术拓宽改编之路
据朱一玄先生考证,蒲松龄的《画皮》故事最早脱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刘义庆的《异苑》卷三《女子变虎》 [5]32,在经历了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明清小说传播之后,创造性地将“化身形虎”的故事母题、“虎变人”的经典故事情节转化为“妖变人”的故事桥段。其中,蒲松龄不但加入“秽物救命”的故事桥段使之更加完整,更简练、生动、精确地描绘了女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 [6]178的独特面容及“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 [6]178的画皮桥段。关于“画皮”之情节,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小说“虎变人”“妖变人”的必要技能成为同类型故事发展的核心“利器”;另一方面,蒲松龄在《画皮》中凭借精炼、生动、传神的文学描述之“技”突破了以往同类型故事的语言描写,为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文学想象空间。三百多年之后,蒲松龄的“画皮之技”在20世纪中后期至今多版《画皮》系列电影改编中得以有效彰显。历任编导无论如何改编故事情节、创新人物关系,均保留了原著中异化者“换皮成人”的经典桥段,借助日益精进的电影制作之“技”,一次次将“《画皮》IP”推向广阔的影视改编新领域。那么,作为《画皮》历次改编中最具猎奇性的声画场景,如何通过电影镜头语言、科幻特效展现小说中女鬼“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 [6]178的生动文学性描述,又如何借助电影的特殊剪辑方式、技术特效祛除小说文本中对女鬼诸如“面翠色,齿巉巉如锯” [6]178的惊骇性特写描述,从而达到寓真实于审美、创新而不失真的观影效果,这成为《画皮》系列电影成功与否的亮点之一。
1966 版《画皮》遵循原著如实再现了女鬼绿面锯齿、弓腰画皮的角色形象,并设置了阴森的音乐背景,这无疑增添了影片“画皮”桥段的惊悚效果。同时,该版《画皮》抹去女鬼脱皮的全过程仅保留脸部特写镜头,巧妙运用了“叠化法”镜头设置方式,以窗户为投射点,借助窥视者王氏兄弟二人的折射视角表现影片“女鬼+画皮=人”的经典镜头,既如实再现了小说文本令人恐惧的文字描述,更有效祛除了大银幕特写镜头所带来的恐怖预设,展现了电影镜头对小说描述的二度创造。电影镜头的“叠化法”同样在1993版《画皮之阴阳法王》中进行了运用,影片将1966版的窗户转换为镜子,女鬼的面部特写摒弃了原著中“翠色”描述改为缺失五官的脸部轮廓设置,以七窍镂空的造型彰显女鬼惊悚之态。
进入21世纪之后拍摄的三版《画皮》更是借助精湛的电影制作技术将“换皮成人”的经典桥段一次次推向视觉高峰。2008年版《画皮》将中国古典文学中妖魔鬼魅的经典情节融入当代数字化影像,以“东方新魔幻” [7]风格示人,成为《画皮》系列电影中改编最为成功的一部。该版《画皮》除借助高科技电影制作技术将狐妖换皮、嗜心等视觉冲击力极强的镜头画面推至观众眼前、使用3D制作技术增强画面的真实感之外,最突出的便是突破了小说文本及前几版电影改编中老生常谈的劝诫警示之主题,并将小说中女鬼“画皮嗜血”的邪恶行为“进行了重新的解构和编排……赋予了《画皮》这个故事一种新的理解、意义、道德与美学价值” [8]29。该版《画皮》直接摒弃了以往电影改编中人鬼同构的镜头设置,再次突破观众的视觉预设,运用数字化电脑技术、动画特效制作,创造性地将狐妖脱皮之态描述成浑身布满千万条扭动蛆虫的腐尸。当风情万种的狐妖在大银屏前公然褪去人皮,皮肉撕扯背景声音,搭配女妖裸露出类似女性肌肉骨骼轮廓下蠕动的万千蛆虫,再加之女性动作展示,其惊悚之状已然超越先前各版本,一经上映便引发受众讨论热潮。2012版《画皮Ⅱ》作为一部拥有1200多个特效镜头、800余个高难度效果镜头的全新视觉特效魔幻电影,通过电影3D、IMAX、CG技术将更为真实的声画场景直接诉诸观众面前,“追求一种物理写实的质感和画面的逻辑感” [9]136,将特效镜头与《画皮》故事完美结合,再次将“《画皮》IP”搬上银幕,上映四天便收获3亿元票房,获得业界普遍认可,成为2012年中国商业电影的领军之作。在影片筹备期,制作团队借助不同的概念设计图勾勒出爱慕、误解、成全等迥然不同的情景氛围,引入动画电影制作的动态分镜,力求拉近大银屏与观众的亲密感,满足新时代观影效果。《画皮Ⅱ》制作团队利用CG技术,将替身身体与狐妖小唯的饰演者周迅的头部进行翻模、拼接、裂变造型,并借助硅胶、发泡乳胶、玻璃钢等人工材料完成假体的特效化妆工作,彻底颠覆了以往版本女鬼揭皮瞬间狰狞的视觉效果,实现了特效与东方审美的结合。影片不但保留了以往《画皮》系列电影揭皮的经典镜头,更挑战性地增加了水下揭皮、人妖换皮的故事情节。两位饰演者在水下通过“揭皮、脱皮、套皮”等连续镜头,需要摄影、特效、化妆、灯光、CG多部门协同配合方能自然展现人、妖迥异的皮肤状态,真实还原皮肤组织的柔软性、粘度及弹性,借助“换皮”的电影情节实现了可与好莱坞相媲美的视觉唯美效果。至2020年,《机械画皮》对人机换脸这一经典桥段的描绘已不再选用惊悚的特效镜头以满足观众的猎奇欲望,并有意弱化视觉冲击力极强的银屏特效,而改用当代科技感十足的电脑皮肤自主生成系统,完美切换眼球与机械瞳孔形态、食指与机械切割机形态,在高科技技术背景下完成了人机转化模式。
三、“旨”之变:弱化劝诫主题,揭示婚恋真谛
小说《画皮》引出故事人物矛盾关系的导火索便是王生的淫欲邪念:路遇貌美女子便“心想爱乐” [10]177并“导与同归” [10]177,在不明女子身份的情况下仍“与之寝和” [10]177,对他人的忠告置若罔闻并妄加揣测。恰恰是王生贪欲好色的致命弱点继而引发了被女鬼裂腹掏心、命丧黄泉的后果。作为对比,小说《画皮》将其所扬之善倾注在王生妻子身上,通过王生妻子“伏地不起”跪求道士救夫、忍痛承受乞丐“杖击”、“强啖”乞丐“痰唾”、怀抱丈夫“哭极声嘶”等形象生动的文学描述赞颂了不惜一切勇救丈夫的、坚贞不渝的中国女性形象,更与丈夫王生得知女鬼身份后“不敢入斋”“不敢窥”“不敢进”等胆小懦弱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蒲松龄表面描绘了女鬼所画之皮,实则通过描写男子被艳丽外表迷惑之悲剧达到劝诫说教的目的。在《聊斋志异》成书三百多年之后,电影改编倘若再沿用原著劝诫警示的故事主旨,显然已无法在现今社会引起观众的观影欲望并获得情感共鸣。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先后多版《画皮》电影改编通过对情节背景的位移、人物关系的改变、角色设置的创新有意弱化甚至摒弃了男主人公王生贪恋美色的讽喻主题,转向对人类婚姻观、爱情观及人之本性问题的多方位探究。尤其是21世纪以后的《画皮》《画皮Ⅱ》《机械画皮》三部电影,不再围绕惊悚的镜头、阴森的音效、昏暗的布景结构故事,吸引观众。影片虽立足不同时代展开人妖之恋、人机之情,却直指当代婚恋观,有“混浊”更有“净化”,一方面表现了婚姻之外禁忌的灵肉情欲;另一方面则通过异化者追求幻灭、人类婚恋圆满的结局,解读人类爱情构建正确的打开方式。
三版《画皮》借小说原著一张“皮”,通过异化者介入人类婚恋展开故事情节。狐妖小唯(2008版、2012版)和机器人在情感缺失的背景下渴望获得人间真爱,它们对爱情的追求如同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的“本我”层面,不受人类伦理道德、纲常法纪的约束,全凭欲望本能驱使耍心机、行诱惑。2008版《画皮》的狐妖在将军王生面前以娇媚柔弱之态极尽博取沙场英雄的爱怜,不惜使用卑劣的手段挑拨王生和妻子佩蓉之间的情感信任。2012版《画皮Ⅱ》在2008版的基础上让重生的狐妖再次魅惑将军霍心并骗取靖公主信任交换身份,以期享受人间真爱、获得化妖成人的机会。两版《画皮》虽为姐妹篇,凭借相同的饰演者、“两女争一夫”的近似桥段合力打造了中国电影IP的“东方新魔幻”风格。但剔除饰演者带给观众同一爱情故事正在延续的错觉,两版《画皮》唯一不变的仅有狐妖小唯这一角色,而它对人类爱情的追求只有强烈的目的性及占有欲。狐妖施计代替二人心爱女子获得男女之情仅凭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体性行为,无论王生亦或霍心在狐妖面前权且是一张张贴有被征服标签的男性代码,以满足异化者对英勇男子的艳羡、占有欲望。2012版《画皮Ⅱ》中的狐妖为了冲破魔咒化妖成人,再次带着强烈的目的性投入到另外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漩涡中。当它深深爱上将军霍心时,早已忘却了千年之外那位曾经沧海桑田的将军王生。殊不知人间真爱除了彼此吸引的人格魅力之外,还有互为包容、相互成全的一生坚守及期盼来生的永恒性期许。无独有偶,2020版《机械画皮》中的机器人形象对人间真爱的关键词界定同为“占有”和“取代”。当机器人发现即使自己套取女性的皮肤升级成真人形态也无法获取恋人林博士的真爱时,它不似人类那般念及旧情、感恩生命之赋予,其自我程序设置给出的第一顺位反应便是杀戮及替代。同理,当机器人置换苏辛的皮肤希望博得与男子王生的真爱未果时,它的程序设置仍旧将“放弃苏辛、取代女上司蔡嘉钰”作为拥有男子之爱的唯一砝码。
在《画皮》系列电影中,异化者无论如何装扮,怎样进行形象改造,以何种手段侵入人类婚恋体系,均逃不出失败的困局。而一次次打败鬼、妖、机器人的并非各类除魔降妖的道符神器,而是永恒不变的人间真情。《画皮之阴阳法王》中的书生在初遇女鬼时,十分期待这场艳遇会带给自己身心愉悦并达成传宗接代的目的,但当女鬼露出真容时,书生第一反应便是将曾经厌弃的妻子搂入怀中。这一下意识的举动恰恰反映了人间夫妻在患难时相互关爱的情感本能。这一点在2008版《画皮》中得到了更有渲染力的表现,影片结尾处王生、佩蓉夫妻与狐妖小唯的相互成全的情感桥段,至今仍被奉为经典。该版《画皮》中妻子佩蓉一直扮演着中国传统贤妻的角色:面对丈夫的情感“出轨”她隐忍不发,面对情敌狐妖的威胁她甘饮毒酒。当妻子步步妥协退让时,丈夫王生选择视而不见,仍旧在梦境中编织着与小唯的美妙交合场景。王生一再暗示自己这仅是男性荷尔蒙被激发下的潜意识行为,实则这只不过是人类对其跨界(婚姻)行为的一种托词。只有当时刻呵护自己的妻子饮毒酒即将逝去生命时,丈夫此时才幡然醒悟,认清狐妖占有欲极强、残害妻友的恶毒行为本质,并不惜舍己救妻。在一路伪装身份魅惑王生的过程中,狐妖凌厉地表现出异化者对人类既定婚姻的破坏欲:它不顾人间道德伦理,公然介入他人家庭并妄图取而代之;它不畏妖孽身份只想在化妖成人的道路中暂时停滞,获取与威武将帅的唯美爱恋;它不惧除妖者的步步追击,表现出在爱情面前飞蛾扑火般的疯狂行径。最终,阻止小唯妖孽行径的人类盾牌依然回扣小说《画皮》及多版影视改编的思想主旨,即人间真情、夫妻真爱。看到心爱之人王生舍命救妻时小唯先前编织的唯美爱恋之梦瞬间破灭,目睹了王氏夫妻在生死面前执子之手、舍命救夫(妻)的人间挚爱后,狐妖企图破坏人类婚恋的行为彻底破灭了。影片结尾处,伴随着婉转舒缓的背景乐,小唯用自己的生命挽回王氏夫妻的性命,以唯美化的自我终结方式成就了人间爱恋。同理,在《机械画皮》最后,机器人目睹了恋爱双方在逆境中的坚守与信任,终于承认自己对人类情感真谛的缺失。
综上,《画皮》系列电影以异化者肆意介入人间婚恋开局,以介入者的最终失败结束故事,在当代物欲横流、消费享乐的时代因素下,引导观众直面复杂人性并引发深刻地思考和讨论。异化者美艳的外表、娇羞的体态、凄惨的身世共同构成了一个虚拟空间,恰好迎合了部分人群对压力的纾解及欲求的宣泄。《画皮》文本及电影中的异化者作为人类本性中欲望、贪婪、邪恶的化身,形成了有效的互设,在一场场与人类正义、善良、奉献的对峙中实则巧妙地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及人类在面对诱惑时所表现出的迷惑与痛苦。而这种对于异化者的精准刻画与深刻定位,正是蒲松龄作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如炬目光和创作初心所在。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约翰·霍华德·劳逊.电影的创作过程[M].齐宇,齐宙,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3]安东尼奥·梅内盖蒂.电影本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M].艾敏,刘儒庭,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4]周清平.电影审美:理论与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5]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6]蒲松龄.聊斋志异[M].济南:齐鲁书社,2000.
[7]陈嘉上.《画皮》是中国魔幻大片的新“起点”[N].中國电影报,2008-8-28(7).
[8]陈利辉.论电影《画皮》对同名小说的解构[J].电影文学,2010,(3).
[9]魏俊宏,冯妍.华语魔幻片的新视觉——与许安、肖进谈《画皮Ⅱ》的数字特效和特效化妆[J].电影艺术,2012,(5).
[10]蒲松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M].任笃行,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