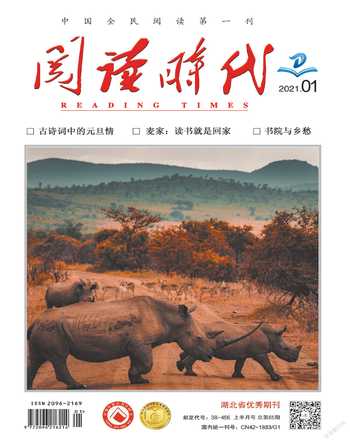读书能否“不求甚解”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的确说过:“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虽然这里说的是五柳先生,但其实是在抒写自己的胸臆,说这是作者本人的读书态度,自无不可。只是把“不求甚解”解释成读书马虎,囫囵吞枣,却似有不妥。因为陶渊明这里所说,是有针对性的。他针对的是汉儒的章句之学,烦琐的考据之风。
在读书时,弄清字句的解释,当然是必要的。如果连字句也读不通,要领会文章的意思是不可能的。所以陈寅恪有读书先识字之说。但若只是停留在识字上,而不能进一步领会文章的意思,那也等于不读,谈不上治学。所以陶渊明强调“会意”,就显得很要紧了。
其实,陶渊明的“会意”说,也并非他的发明,而是老庄思想的继承。《庄子·外物篇》云:“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看庄子的感叹,可见得意忘言之人甚为难得也。陶渊明有诗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更明显地表现出其思想与庄子的关系。
以我看来,陶渊明强调“会意”的读书方法,不是降低了阅读要求,而是在“识字”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倒是提高了閱读要求。因为毕竟“会意”比“识字”更难,“识字”只要下死功夫还可以做到,而“会意”则需要有更多的文化知识与社会阅历。鲁迅就曾说过:“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1936年4月2日复颜黎民信)盖亦此意也。而事实上,他的有些文章,恐怕三十岁也未必全能读懂——不是字句上的懂,而是意思上的懂。诗人绿原就说过,鲁迅的《隔膜》一文,他是有了相应的经历之后,回过味来才懂得其中的含意,可惜为时已晚。那时他已是中年之后。
此外,儒道两家,对于读物的要求也大有不同。孔子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所以汉儒是非圣贤之书不读,不同观点者即不屑顾之,这样局限性必然很大,脑子难免僵化;而道家则只要有“真意”之书都愿读,还能在提取出“真意”之后,把语言的外壳扬弃掉,当然把不实的东西也扬弃掉,即所谓“得意忘言”。
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在《思想·山水·人物》一书的《题记》中谈他翻译的取材之道,说:“我的译述和绍介,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
(吴中杰:作家,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