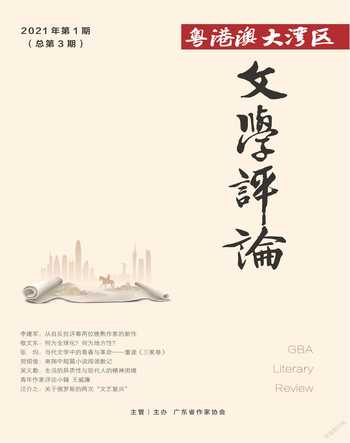反重力写作与思想爆破
邵部 孟繁华
摘要:作家王威廉的小说具有冷峻的语调和冷静的叙事,在日常生活的敘述中寻找思想爆破。他的小说充满了反抗的精神,聚焦于社会的“异人”,从中呈现出独异个人如何被社会秩序规训,成为其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王威廉不仅试图剖析城市 / 城市文学的肌理,甚至寄寓了从中发现当代中国的总体性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无疑在迫近当下时代的“核心知识”。
关键词:王威廉;小说;日常生活;思想爆破;核心知识
面对王威廉,“80 后作家”的标签是多余的。王威廉便是王威廉,他是那种不需要依赖“群”而独自生长的作家。他依然年青,然而早已成熟。处女作《非法入住》(《大家》2007 年第 1 期)出手即不凡,俨然一副老练的小说家手笔,为他的文学生涯定下一个很高的起点。这是一篇“沉降”式的小说,记录了蜗居在九平米房间的“你”如何在侵占者的紧逼下,从最初的反抗,到最终丧失“精神的自我”,退化成又一个“非法”之人。处女作在此被刻意提及,是因为它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王威廉小说中“冷” 与“热”这两个相反互成的特质。冷,自然是冷峻的语调和冷静的叙事,这为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注入了现代主义的质素。在这篇“放纵”之作后,王威廉走上一条更为沉稳和内敛的路子, 他的小说可贵的一点,是懂得点到即止的节制和收束;热,既是作者自述的“生活对生命的灼伤”,更含有催生创作活动的倾述的热望:将对当下生活广博的观察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冷的笔和热的心,在小说里碰撞、混溶,形成了兼具可读性和思想性的文学质地。“习作期” 的关隘近乎一跃而过,《非法入住》之后,王威廉“忽然就懂得叙事了,开始不间断地写小说, 把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困惑统统写进小说里”[1]。 “困惑”表示的是作家与生活遭遇时的内心体验,构成了王威廉写作的动力之源。如果我们继续追问这种“困惑”聚焦于何处,亦即为王威廉的小说寻找一条主线,我想答案应该是人的社会性存在及困境。
一、“反重力”的“异人”
巡阅王威廉已发表的数十篇中短篇小说, 我们大致可以发现,他不是一位本着根据地意识刻意经营一方文学地理的作家。他的写作似乎是情之所起、兴之所至,无所谓聚焦,全然随了个人的观察和体验着笔。一如李健吾对文学创作的分析:“根据各自的禀赋,他去观察; 一个富有个性的观察,是全部身体灵魂的活动,不容一丝偷懒。从观察到选择,从选择到写作,这一长串的精神作用,完成一部想象的作品的产生……”[2]因为视点的不断偏移,王威廉对当下生活的摄取主要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完成。如若对一个集中的话题感兴趣,他也会以续作的形式接续意犹未尽之处。《非法入住》之后有《合法生活》,又有《无法无天》,“它们全都和一种生命的界限相关联”[3],因此有“ 法三部曲”之称。《内脸》背后的作者化身为现实中的落魄小说家,成为《第二人》中的二号主人公,作为引子勾起鬼脸大山的故事,以延续前作对于脸的社会功能的讨论。甚至于《潜居》和《野未来》也有某种内在的对话性,无论是执迷于在现实寻找科幻感(赵栋,《野未来》)、还是做科幻世界中的怀旧人(“我”和敬亭,《野未来》),他们与身处的时代充满张力。
转移与关联不断发生,渐渐勾勒出一幅明晰的文学图谱。我们因此得以在小说人物身上嗅出某种共通的气息,即异质性。王威廉提供给当代文学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异人形象系列。他们是丧失了表情的虞岑(《内脸》)、鬼脸大山(《第二人》)、灵魂出窍的小孙(《合法生活》)、“矮乐鸡”以及从捉弄他到扮演他的“我” 和小宋(《无法无天》)、没有指纹的人(《没有指纹的人》)、写信成癖的信男(《信男》)、醉酒时身体内仿佛有两个人的“我”(《听盐生长的声音》)、深锁庭院而以空调洞口保持外部联系的人(《我的世界连通器》)、得了应声虫病的人(《书鱼》)、在实验室与鳄鱼交换了大脑的人(《市场街的鳄鱼肉》)……如小说中人的自白,“我是人中异类”(《没有指纹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身上的“异”,并非源自作家对人物的减损(设置某种生理上的缺陷)或增益(赋予人物超出常人的能力),更多地是在日常生活的逻辑中展开。也就是说,王威廉着意刻画的,不是传奇性而是日常性,他关注的是那些“对日常生活有些障碍的人”(《我的世界连通器》),捕捉他们身上那种与生活无法和解的东西。“荒诞”是学界评论王威廉创作时的一个关键词。在我看来,无论是以现代主义的文学传统还是以信息膨胀的现实社会为参照,变形记式的超现实描写所带来的荒诞感已然在题材复写和新闻传奇的覆盖中,消耗了它的大部分文学势能和冲击力。作为读者,我们的知识与体验显然足以支撑我们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接受这样的写作。我们在王威廉小说中察觉到的荒诞,语言试验或技巧探索提供的只是形式层面的观感,深层次的来源还是在内容上,来自个人的自由遭遇社会的秩序而发生碰撞的一霎那,来自王威廉对这种“障碍”的呈现和放大。独异个人如何被社会秩序规训,是王威廉小说的一个主题。
《没有指纹的人》(《山花》2011 年第 11期)中,生来没有指纹是“我”的人生魔咒。按照科学的定义,指纹是比 DNA 更加独特的人类表征,本意原是人的个体性的表现。然而在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使指纹变成了对人的辨识和界定,衍化成无处不在的区隔的标志物, 进而成为监督模式中的重要环节。童年时,母亲隐约感觉到“这太不符合人的特征了……”, 她的忧虑在“我”未来的生活中被证实——指纹成为“我”的人生悲剧的起点。随着指纹识别技术的发展,先是单位考勤推行打卡制度,迫使“我”从一个没有指纹的人,变成一个偷指纹的人。再是活体指纹技术的出现,“我”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殆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说的结尾,恰恰是因为指纹证据确凿,一个没有指纹的人却要面临一场无妄之灾。科学之于“我”变成了一种强权,变成了对于异类的压制。叙述至此,我们不难看出王威廉小说中游荡着福柯的身影。
小说的核心情节是“我”与妻子游览城市公园里的指纹主题展,一边是妻子念读的科普文字,一边是“我”对这种知识 / 准则愤慨的抗辩:“现代社会就是监控无所不在甚至变得歇斯底里的牢狱。不止像我这样没有指纹的人是囚犯,你们这些有指纹的人更是囚犯!当所有的人都被关进监狱的时候,监狱外边便成了更加孤独的监狱。”现代社会对个体的控制与管理, 不再主要地诉诸于暴力形式,而是将个体纳入到技术—政治领域进行精密的控制。规训进行得如此隐蔽,以至只有如“我”这般被惩罚的异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温情脉脉的暴政。
《合法生活》(《大家》2008 年第 5 期) 是这类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哲学系毕业生小孙和舍友史博,一个是保健品推销员,一个整日沉迷于网络游戏,从社会的定义来说, 他们是当代生活的失败者。“父亲”突然要来探望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让他们怀疑现在的生活是否具有合法性。父亲俨然是秩序的化身。等待父亲的到来,就像是等待社会对个人的检查和认定,迎接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为此,他们开始试图“找到一条成为正常人的途径”。小孙因为无法解决如何葆有内在尊严地活着这个问题,在一次醉酒后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小孙的灵魂”与“小孙的肉体” 分裂,在夜晚的城市上空孤独地飞翔,成了审视现实世界的超然物外的观众。叙述的视点由此随着“小孙的灵魂”挪动,变成了洞察“秩序”的目光。“小孙的灵魂”看到,小孙的肉体持续受到外在的观察和评估。“他的生活方式有问题”,“改邪归正”的好友如是评价他;父亲得知他的不成器,按捺不住对病床上的儿子一通殴打。小孙的肉体终于启悟:“由千百万人构成的生活规则,你不去参与,你想推翻千百万人吗?千百万人都错,就你是对的?”他苏醒过来,考上机关单位的公务员,获得了世俗的认可。小孙的灵魂用所有的精力去观察他的肉体,最终发现二者根本不是一个人。从某种程度上讲,王威廉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技术—政治领域的发现者。他的很多小说处理的都是社会如何用文明的合理的手段使身体就范的问题。王威廉对于“异人”的描绘,即是从边缘的角度重估主流,实际上是在有意拆解被他名之为“法”的界限和秩序。
如果要为这种拆解做一个命名,我想可以借用《倒立生活》(《青年文学》2011 年第 9 期) 中的一个词汇:“反重力情结”。“重力”是神女的悲伤之源。一次毫无因由的流产,被荒诞地归罪到“重力”上,她由此生发出反重力的心结。她不再写诗,把精力放在创造意象的事业上——画画。长在天空中的向日葵、悬挂在天花板上的椅子,所有的画作都是绚烂的色彩和倒立的意象。从设想到实践,我们在现实中真的把家具固定到天花板上,开始倒立生活。“毁坏一种本质的秩序,反过来说也是建造”,小说中的这句话或可视为王威廉写作的隐喻。
二、日常生活的思想爆破
反重力的写作,即是对日常生活的审视和反思。作家能否把这种写作落在实处,关键是能否找到一个坚实的支点。我们谈论先锋文学,常会引用剥洋葱的比喻,形式一片一片剥落,最后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王威廉的小说有先锋文学的余韵,他甚至有新世纪的先锋派之称。只是,那种纯粹的形式探索已经完成了它的文学史使命。王威廉与之最大的区别,在于他的作品是实心的,有一个坚实的内核。有可能是一个观念,一个意象,甚至于一个词汇, 便足以成为王威廉撬动现实世界的支点。
这个支点,在《没有指纹的人》中,是那句“指纹识别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管理个人的一种精密技术”,在《野未来》中是“我”对赵栋的质问,如何看待一个与自己没有关系的未来。在《父亲的报复》中是结尾断壁残垣中父亲打出的“羊城河山可埋骨,岭南夜雨独丧神”的条幅,道尽外乡人的城市认同。是“倒立”之于《倒立生活》,“怀旧”之于《潜居》。尽管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王威廉的小说依然可以带给读者“好读”的观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结构上的经营和对主题的把握。按他的话说,是“把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进行爆破”:写短篇小说的时候,作家对于自己将要写出的故事虽然不能做到全然在胸,但是某个重要的点必然是已经领会到了的。这样说似乎有些神秘,但的确如此,那个重要的点是写这篇小说的根本冲动之所在,比如可以是主题上的,关于新技术,还是性别观念;可以是手法上的,比如第二人称的使用;可以是情感上的,比如一种莫可名状的怅惘……不一而足, 那么就是将这个点视为一个完完全全的目标, 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之做到极致。[4]
扎米亚京在《新俄罗斯散文》中写道,“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狂人、隐遁者、異端者、幻视者、怀疑家、反抗者产生出来”[5]。王威廉和他笔下的异人,都带有与此类似的精神气质。他为文本投注一束思想的光,以完成小说对现实的爆破。如评论家注意到的,小说对于他是一种“思想历险的方式”。他笔下的人物多少有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气质,是那种思考和探索崇高的“思考型人物”。[6]
这一面在《归息》(《十月》2016 年第 6 期) 中展露无遗。这篇小说情节很淡,坦率地讲, 进入它的过程甚至有些“失望”——它实在不是一篇“精彩”的小说。前半部分,“我”与管苧从心生爱慕到步入婚姻,一切都太顺畅,缺少虚构故事必不可少的曲折。小说用力之处是后半段,岁月静好的生活之下,思想的暗流涌动。这一任务主要由“我”与岳父的对话完成。岳父是在大历史中应运而生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用思想穿透日常生活,与庸常角力。比如谈到亲自下厨与青年人点外卖的区别,他再次征引“监狱”的意象:“实际上你们把自己和这个世界隔开了,你们更加陷入到了自己的小圈子里,似乎万事万物都可以安排和归结到你们的小逻辑里边,这是非常虚妄的事情。因此, 这种表面的方便,仔细想想,反而是束缚,像是一座名叫‘自由’的监牢。你们是在坐自己设置的牢。”对于岳父这一代启蒙知识分子而言, “我们这代人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气质,影响也就格外深远,你们以及你们以后的人们,都生活在我们这代人造就的格局里。”他的身上凝结了理想主义的余绪和知识分子的崇高感。他平静地以自杀的方式走向死亡,是对信仰的拯救也是对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时代的告别:“你和小曹好好地生活下去,属于你们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你们要尽力融进那个新时代,而我,并不属于那个时代,我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更糟糕也更恢弘、更单纯也更复杂的时代。”
在这里,王威廉试图在认同和拒绝之外,通过两代人之间的沟通,找到一种理解父辈的方式。岳父在对话中谈到,“思想一定要和生命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被真正理解”。理解父辈的思想,就是在理解他们的生命。历史的密道由此向王威廉敞开——这实则也是一种具有历史意识的写作。
在凝重的思想者面前,“我”的形象温和, 声音微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只是一个听众和受众。面对父一辈的心灵,“我”试图接近, 却又不曾遗忘个人的立场:“我厌倦了非此即彼的选择了,我觉得历史与每代人的亲密关系应该是不一样的,我其实已经很少用‘一代人’这样的思维去考虑问题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称这篇小说是两代知识人的对话而不是一代人的宣教,它形成了思想 / 声音上的复调性。
如同《听盐生长的声音》(《文学界》2013 年第 12 期)里,在地下挖煤的小汀受够了把人憋死的黑,如涸辙之鲋一般把颜料视作水,用最鲜艳的色彩作画,并对“我”身处的盐湖充满期待。然而,“我”的盐场却是一个过分光明的世界,只有旷古的荒凉。“我”、金静、小汀、夏玲,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各自画地为牢,初始把希望寄托在另外的人事上,最终都要以各自的方式寻找精神出路。我们大概可以发现王威廉不是一个进化论者也不是一个怀旧的人。他是一个时刻对二元论保持警惕的怀疑论者, 或者说,一个相对主义的文化批判者。城市比之农村,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未来之于当下,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空间与时间,都不过是人的外部环境。然而,只要有人,只要由人联系成社会,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制度性矛盾就不会消失。总有少数被时代的列车所甩下的人,作为知识理性的弃儿被文学安慰。
三、从“上游”理解作家
哲思、深度、现代、荒诞、科技……无论我们命名王威廉的写作时,在现实主义前面加上怎样的定语,不可否认,他的根底还是现实主义。他终归是在用虚构的方式模仿和复制现实,只不过,呈现出来的不再是平面的镜像, 而是如哈哈镜一般,杂入了对事物的变形。他不是将文学视作生活的仿真术,而是致力在文本中展示“生活性”,呈现“被最高的艺术带往不同可能的生活”[7]。这种“变形”既是自然的,又是自觉的,隐含了我们在理解当下文学创作时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恩格斯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还能否恰切地表达我们对时代的感受和认知?这个问题在九十年代已经被晚生代作家群意识到,他们提供的改良方案是用“个人”置换“典型人物”,用“日常生活”置换“典型环境”。从晚生代到王威廉,社会平稳而高速的运行以及学院知识的普及和积累,无一不在推动文学创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在当下文学创作中感受到的小说艺术的变革,实则是作家在寻找与个人的知识结构和时代的生活结构相调谐的文学结构。
在王威廉的文学结构里,与其说是“经验”,倒不如说是“体验”构成了创作的根基。九十年代以后,“智性”是文学创作的大趋向。到了王威廉这代作家,他们普遍表现出以“知识”表达“体验”的特点。面对这种情况,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愈来愈显得疲于应对。或许, 文学批评的关键词更新已经是一个可以提上议程的任务了。
在这样的理解中,我想着重强调“上游” 这个词汇。“当代文学研究必须对周边和上游的所有学问都要有所了解甚至深入研究”[8], 这大概是我们学科内部的一个共识。对于“50 后”及其前辈作家而言,只有掌握了作家作品的“周边”信息——人生经验、人事关系、创作过程、出版波折、文学制度甚至于大的社会历史氛围,我们的文学研究才能做到合宜,不会流于妄断。在他们身上,从周边进入文本的路径是打通的。他们没写作一部重要作品,总是习惯配上一个情境化的、叙事性的序跋文谈。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年轻作家的创作谈几乎不会从人生经验的角度展开。作家讲述故事,他们自身却变成了王威廉自述的“没有故事的人”。王威廉的数本小说集,所录序跋都是对话或阐释性的,充满专业术语。作为读者,我们已经很难在文本内外捕捉到事件性“材料”。可以说,从“周边”进入文本的路径越来越窄,与之对应,作家作品的“上游”却越来越多地向我们敞开。“上游”不同于“传统”。后者强调作家受到的直接影响,试图将后来者放置在某个前置的序列里面。前者则要宽泛得多,指向的是总体结构解体之后,碎片化知识甚至于异质性知识的混溶共同构成了对作家的滋养。王威廉的身上,有古典文学的遗风,有对鲁迅、郁达夫的追慕,有先锋探索的接续, 有向卡夫卡、加缪、契诃夫的致敬,更有福柯、马尔库赛等理论家的刻痕。翻一翻王威廉的创作谈或批评文章,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名单列得更长。“上游”如支流汇入主河道一般, 共同塑造了我们所面对的作家,然后在相互作用中消融,直至隐藏起来。这形成了王威廉文学谱系的混杂性。评论者很难看清他所有的来路,然而,探明的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启发对作品的解读。
另一方面,更为宏阔也更为根本的“上游”,是王威廉的现代性经验。“现代性”之于前代作家是问题,之于王威廉则是起源。对于他这代作家而言,“现代性经验已经内在于我们的生活了,因而这种‘现代主义’就不仅是一种技巧,而是已经成为了我们自发性的本土经验。”[9]“现代性经验”具体指的是对“城市” 的体验。广义地说,王威廉的所有写作都是城市文学,因为无论题材如何,它们都是在城市的文化空间中展开。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当代的城市文学一直存在着知识滞后于经验的尴尬境地。当城市的物象及其背后的新的生活方式扑面而来时,我们总是手足无措或反应过激。无论是在革命年代将其作为腐蚀心灵的香风毒雾予以压制,还是在八十年代以现代主义手法的表现人的“变形”,固有的生命体验与城市短兵相接之时,总会在心灵内部引发一场看不见的战争。王威廉这代作家终于调和了知识与经验的矛盾。且看王威廉对于城市文学的论述:现代城市不再仅仅意味着地理学意义上的闭合空间,而是成为了一种开放的、没有边界的文化空间,它依靠更加精密的技术手段不断地将自身的一部分镜像传播出去,以复制、模仿等手段使得文化基因得到再生。成熟的城市文学无疑是要努力去呈现出这样一种流动的空间,以内在的精神关联塑造出当代中国的整体景观。这样的写作是有难度的写作,也应当是城市文学的书写方向以及创造契机。[10]
全球化的经验、城镇化的趋向以及科技在生活中的全方位渗透,只有在“开放的、没有边界的文化空间”中才有可能被涓滴不漏地容纳和吸收。王威廉不仅试图剖析城市 / 城市文学的肌理,甚至寄寓了从中发现当代中国的总体性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无疑在迫近当下时代的“核心知识”:对时代“核心知识”的提供,是现实主义小说未被言说的另一要义。没有一个时代的核心知识,小说的时代性和标志性就难以凸显。在当代中国,尤其是都市文学,之所以还没有成功的作品,没有足以表达这个时代本质特征的作品,与作家对这个时代“核心知识”的稀缺,有密切关系。诸如对金融、人工智能、信息等知识的不甚了了,严重阻碍了作家对这个时代都市生活的表达。“核心知识”不仅科幻作家应该了解,传统小说作家也应该了解。另一方面,高科技给现代生活带来了极大便捷,但潜在的危机几乎无时无处不在。没有危机意识是当下小说创作最大的危机。因此,将时代的“核心知识”合理地植入小说中,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将有极大的改观。[11]
提供时代“核心知识”的文学作品,必然能够与时代构成共名关系。我们不能断言这种表征性的著作能否在王威廉及其同代作家中横空出世,但我们对此心怀期待。
[注釋]
[1]王威廉:《又记》,《非法入住》,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81 页。
[2]李健吾:《咀华集 咀华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1 页。
[3]王威廉:《隐秘的神圣——有关〈“法”三部曲〉的随笔》,《大家》2009 年第 3 期。
[4]王威廉:《迷途之中,岂有捷径——短篇小说艺术散论》,《青年文学》2020 年第 7 期。
[5]张大春:《小说稗类》,天地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85 页。
[6]李德南:《作为思想历险方式的书写——论王威廉小说的叙事美学》,《百家评论》,2013 年第 1 期。
[7][英]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8 页。
[8] 孟繁华:《史识、史料与文学史的写作实践——从洪子诚钩沉的两则文学史料说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 年第 2 期。
[9]舒晋瑜:《王威廉:走向历史化的个人写作》,《中华读书报》,2015 年 4 月 15 日。
[10]王威廉:《发现一种新的中国经验——论中国当代城市文学发展的新趋向》,《百家评论》2016 年第 4 期
[11]孟繁华:《现实主义:方法与气度》,《文艺报》,2018 年 7 月 27 日。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