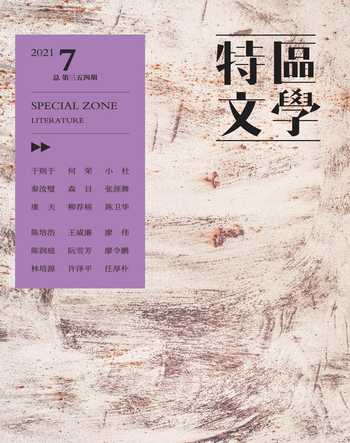历史、文学与记忆
任厚朴,男,获武汉大学第37届樱花诗赛优秀奖,作品见于各文学期刊,参与编选广东省重点专业建设项目《云山文萃》。
长久以来,每每提及王十月,批评家一直都着力于谈论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工文学、他的底层叙事和草根性等叙事特征。这种对于文本的评论不失准确,但放到现在太过老生常谈。若让目光超越文本,凝聚在王十月本身,批评者难免会将他与胡万春等作家进行类比,讨论如当代工人作家的培养等制度性的问题。
对于王十月的讨论,大多聚焦于故事本身和作者的身份,以讨论文本的内容和意义为核心,而对其技法和叙事选择等内容选择性地忽略。王十月是我十分喜欢的作家,因此我必须很谨慎地对他进行谈论,以避免主观的喜爱太过强烈,影响了批评逻辑和理性。本文试图沿袭旧路,从叙事特征入手,佐以文本分析,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批评王十月早期作品,并发掘作品的历史文学意义。这种试图以客观角度进行论述或许过于匠气,但希望得出的结果能足够公允。
王十月是一个具有历史叙事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历史的意义。作为走在时代浪潮前面的人,打工的经历和所处的身份让王十月更加敏感,更加注重那些社会底层的声音。作家的身份和他的过往赋予了他独特的使命,让他必须要倾听那些来自人民的声音,并让那些声音超越人民的局限和偏见。
王十月很早就注意到了人民的失语。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虽然数量庞大、众声喧哗,但在历史上却鲜能发声,只能保持着痛苦的沉默。这个描述看上去是个悖论,但是却真真实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尽管人民有说不完的话,但可悲的是,他们却只能“沉默不语”,发不出任何声音。
王十月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并为此感到焦虑。他对历史叙事和话语权的焦虑主要反映在他的小说《不断说话》之中。
《不断说话》的开场白中引用了加缪对克尔凯郭尔论断的转述:“真正的无言并非沉默,而是不断说话。”王十月的引用赋予了克尔凯郭尔的论断新的含义,将言说与沉默同话语权力相挂钩,通过悖论的形式着重强调了底层人民在历史环境下的失语以及对叙述本身的强烈渴望。
“那么,好吧,你听我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南方……”
《不断说话》以上述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开始,以“我”自己的口吻喋喋不休地讲述着“我”的历史、过往、城市、态度、情感……急促地交代着“我”的小镇、小镇上的河流、河上的大桥、我那喜欢摄影的朋友还有那些爬上桥寻死的人们。
倾诉的欲望透过大段大段的文字的堆叠展现了出来,通过叙述语境的构建,将真实的身份内在地赋予了“我”这个叙述者,文字堆叠在一起,传递着“我”的焦虑。
虽然《不断说话》并没有标明叙事的时代背景,但是通过文本细节可以判断,时间线大概是定位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在这个经济不是非常景气的年代,“我”虽然摆脱了厂弟厂妹那种流水线作业的工作,从蓝领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搞广告文艺的白领,但是“我”从未摆脱“我”的阶级,也从未摆脱社会大环境下的重压。那些焦虑一直未曾离我远去。“我”迫切地想要言说,但是却无人诉说。
全文节奏急促,第一人称的口语叙事在事件和意象之间不断切换。“我”固然是叙述的核心,但是把这些事件在逻辑上串联起来的,却是一种作为个体的压抑和孤独的情感。王十月虽然只字不提“我”的感受和心理活动,但在读者倾听“我”的声音时,所有“我”的每一个想法和念头都以“我”所见的那些人物外部动作作为躯壳,逐一呈现了出来。这种由社会关系撕裂所带来的孤独和压抑贯穿全文,如影随形,如附骨之疽般挥之不去,为那些碎片化的描述之间的衔接确立了亲近感的连续性。
在叙述的意象方面,桥的意象贯穿全文,具有象征意义,是全文得以构建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不断说话》中,忘川大桥反复出现,是确立不同情节之间因果关系逻辑的中介,是那些人们命运交叉的节点。
如果将“我”定义为叙述者,那在《不断说话》中,故事的真正主角则是这座忘川大桥,这桥不只是一个故事推进的背景,它的存在更决定了人物的活动,界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在桥的周围形成了某种力场,支撑起故事进行的空间。桥作为一种外在的、可见的表征,揭示了人与人、事与事之间的联系,它具有一种叙事的功能。
忘川这个名字来源于王十月故土—楚地好巫鬼的传统,赋予了这部作品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桥这个意象则别有深意。桥是架设在江河湖海、山川险峻中的建筑物,作用在于使车辆和行人得以通行。桥的本义进一步引申,发展为连接和中介的含义。比如语言,就时常被比作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桥梁。“桥”这个意象的使用十分精妙,放置在该小说的特定语境之下,所指和能指被无限地拉开了,具有深意。桥是叙述的开始,也是叙述的结束。“我”无数次经过“桥”这个意象本身和它的实体,与同事、“小鱼儿”和守桥人等站在那座桥梁上夜谈,尽管“我们”并不能理解彼此。还有那无数决定跳桥的人,他们爬到在桥上,面对这警察和围观的群众—那些拥有同一身份的人们诉说,可他们又如何能够倾听呢?人们就像两难的豪猪一样,试图拥抱,却不断刺伤彼此。桥一直横跨在这条忘川之上,尽管人来人往,却彼此孤立。物理的桥只能连通物理的距离,内心的隔阂和孤立又该用何等办法来连通呢?王十月类似的表述和隐喻太多了,这让我想起了他在《梅雨》里面描写的马广田老人、老人的天眼还有那连绵不断的雨。在人们内心中,那场大雨一直在下,很少有人能像“我”一样从他人的心中真正感受到雨,很多人只是被社会的那一份痛苦给淋湿了。
业已死去的红衣打工仔在桥上不断出现,诱惑着“我”上桥;小鱼儿和守桥人的姐姐这两个面目相同的人在我的面前反复出现;攝影、莫奈的画、印象、色调和那些模糊的面孔……王十月用着浓烈的魔幻现实主义笔调来书写着《不断说话》的剧情。那些错觉与幻觉、生命中的幽灵幻影对于“我”来说是虚假的,也是真实的,它们是“我”内心中渴望倾诉和被倾听的欲望之具象。也正是在这样的撕裂和孤独下,那些“默不作声”的人们才相约登上忘川大桥,仿佛被什么驱使着一样。
小说结尾,“我”站在大桥上。在小鱼儿的指点下将目光投向远方。顺着忘川大桥绵延的铁轨,“我”仿佛灵魂出窍般看见“我”沿着铁轨在向着自己走来,时光飞快地作用在自身。小鱼儿悄然消失,一朵莲花在钢铁横梁上悄然绽放。我看着桥下聚集的人—熟悉的、陌生的人:哭喊的妻子、举起镜头的摄影师朋友、维护秩序的守桥人……最后,我看着喊话的警察,张开口,开始了我的叙述:“那么,好吧,你听我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南方……”
这个精妙的结尾让故事形成了闭环,如莫比乌斯之环一样打破了叙事时空的界限。在衔环之蛇的结构中,结尾即是开头,过去即是将来。王十月很喜欢这种故事首尾衔接的闭环叙述,在很多的小说里都引用了这个叙事方式,让故事通过这个巧妙的叙事结构得以超越预设的背景,拥有更加深刻的含义。
王十月对于话语的焦虑一直存在,他就是从那些人里面走出来的,他或许是吃够了那种拼命说话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的苦,因此他试图通过文学之口为那些只能保持“沉默”之人言说。王十月的现实关怀和时代性让他的小说具备了历史叙事的意义。
文学的历史意义根源于两者之间的渊源。文史不分家,两者在诞生之初不可避免地会纠缠在一起,无论是孔老夫子删的《春秋》亦或者是修昔底德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两者兼具文学和历史的身份,是话语权的一种体现。
政治权力与话语权的关系天然地密切交织在一起。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两者之间正反馈的关联:掌握了权力就意味着掌握了话语权,因为语言和知识能为巩固权力服务。反之亦然,知识亦能产生权力,因为认知决定了行为。
为了满足统治的需要,历史叙事与权力捆绑在了一起,作为政治权力的话语表达。古今中外,都是由官方来行使历史叙事的权力。正是他们利用掌握的话语权,将曾经客观存在的往事“确定”为历史。
作为社会中大多数的底层,普罗大众也有自己的历史记忆,也想讲述自己的历史故事,以此表达对历史的独特理解。但是由于话语的缺失,在过去的千年,总的来说普罗大众还是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他们就像《不断说话》里的那些小人物:小保安、红衣打工仔、守桥人的姐姐甚至是“我”,无论多么大声,他们的言说总是被历史和这个社会被忽视,他们的诉求无人问津,鲜能得到答复。
但历史不应该仅是编年史,不应该仅由时间表组成,不应该只是观察者所编写的一堆关于日期的目录。克罗齐认为,政治历史必须通过思考和情感与作为个体的受众联系起来,只有思考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
随着人民当家作主,教育和识字率逐渐提升,人民逐渐摸索出了一个新的方式去介入历史—通俗文学。因此通俗文学发展成了普罗大众进行历史叙事与历史接受的一种有效方式。王十月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用通俗文学介入历史叙事的人。通俗文学的介入让原本那种钦定历史的单声道霸权叙述,逐渐演变成了巴赫金所言的“复调”叙事。原本由官方确定的历史,成为了如今多声调的众声喧哗。
王十月的小说就是这样一种历史言说的方式。作为打工人,一个没有文化话语权的平头百姓,王十月通过小说这种通俗文学样式讲述了那些属于外来务工者的历史。小说的题材决定了这种方式的历史叙事始终是故事,充满虚构。它们不像编年史一样,不能够将每一件事情都按照时间轴“对号入座”。但这些故事本身是真实的,客观发生的。王十月的故事都是先在的,那些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事件虽然被王十月按照因果顺序编排交织在一起,但是那些故事和事件所承载着一种真实并没有被破坏,反而在强烈的冲突下更加鲜明地凸显了出来。
编年史被认作是过去的历史,只是历史的干枯骨架(克罗齐语)。而真正的历史必然是当代史,是现在的、在场的历史。历史的文本必须通过思考和情感与作为个体的受众切实地联系起来。王十月的小说就是这样一种在场的历史叙事,它虽然无法反应事件和数据,但是可以记载另一种编年体无法承担的、个体的客观事实。王十月的打工文学和乡土故事可以视为那些乡村内陆的升斗小民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下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事物所进行的一种观察,是一种集体记忆、一种思想情感乃至愿望的表达。
集体记忆和情感的表达需要媒介和形式。承载这些内容的故事有其生成的逻辑。齐泽克偏爱借用《猫和老鼠》的经典镜头来向读者阐述,故事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在追逐老鼠的过程中,汤姆猫丢失了他的杰瑞鼠,但汤姆猫没有办法停下来,而是凭借惯性,盲目地加速,向前冲锋。汤姆猫冲出悬崖,在毫无依凭的虚空中奔跑着。直到汤姆猫注意到脚下的虚无时,他才感觉到惊恐,在恐惧中坠落。
这个被齐泽克偏爱的镜头,描绘了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的割裂,和王十月的小说叙述策略不谋而合。《开冲床的人》里的李想、小广西;《国家订单》里的李想、小老板、张怀恩;《寻根团》里的马有贵、王六一、王中秋;《梅雨》里的马广田……在王十月小说里,那些人物默不作声,在追赶着什么,又好像在被什么驅逐着一样。他们如汤姆猫一样,咬着牙,追赶着他们自己的老鼠,机缘巧合中与初心不断错位,生活的驱赶和积重难返的惯性让他们不得不加速冲向未知的前方,如赴约般奔赴时代的断崖。
相比《如果末日无期》等新作,我更喜欢王十月的早期立足于乡土和打工题材的成名作。为了避免误会,我觉得有必要进行解释:这并不是说《如果末日无期》就没有《国家订单》好,我上述的表述不是一个对作品优劣下定义的事实判断,而仅仅是一种个人对于作品喜爱程度的价值判断。这种偏好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审美疲劳的问题,因为科幻题材的泛滥,加之卡尔维诺等作家珠玉在前,因此我对于王十月新作那种故事模式和题材不再具有首次接触那般惊艳的感觉;其二源于我的个人经历。我生在广州,王十月的早期作品总能唤起我对于童年的记忆。王十月的描述是如此简洁,如此真实,每每看到这个情节桥段,我就会想起孙志刚,想起很多和他们一样的人。那些被我亲眼见证的、早已被遗忘的童年记忆会再一次浮现脑海。
王十月在叙事语言方面的选择和努力,时常被评论家忽略。我认为这是不公允的。王十月的叙事语言赋予了早期作品独特的魅力,对于那些曾经身处同一时空的人们更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在那些成名作品里面,王十月的叙述从技法上而言并不繁复,甚至可以说有些稚拙。很多评论家将其成因归咎于打工人的文学储备低,潜意识地认为这是一种语言上的路径依赖,这种看法是肤浅的。
我们可以看到,王十月在讲述小说故事时所使用的技法来源于民间文学的叙事传统,很简单,也很有效,像是无数次权衡之后的大道至简。王十月在叙事上的简化使得叙述的文本更贴近叙事内容的核心,使文字能着力于刻画场景,以对群体记忆进行呈现。我将对王十月小说进行浅要分析,归纳出其叙事的特征,并分析王十月对语言和节奏选择的原因以及其对于集体记忆的呈现和传承的作用:
快,明晰的叙事节奏。
王十月偏爱节奏明快的叙事。在小说里面,呈现故事的叙述都是外部的、直观的,以描绘行为和语言等客观方面的动作为主。王十月很少花笔墨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主观方面的心理描写。但是他没有忽略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性。王十月对人物内心的描写不是通过独白,而是通过动作和神情对内心进行刻画。人物心中那些必须呈现到读者眼前的想法,王十月则会以全知的第三人称口吻告知你,那些人物的内心究竟怀着什么想法,而不是通过复杂的心理活动和独白进行展示。这是一个避免小说失真的简化,也是一个给小说节奏提速的技巧。
在《国家订单》中,王十月以李想辞职—这个冲突的高潮径直开始了故事的叙述,奠定了这个故事快节奏的基调。上述的一切特征都呈现在短短的三段当中:
“终于,李想这一天对小老板提出了辞呈。小老板坐在租屋的旧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里吴小莉那职业的微笑,沉默许久。他想说什么来着,想说一说李想的诺言?说一说让李想再帮帮他?可他终究什么也没有说。他理解李想,并不责怪他。李想有自己的生活,没有理由被绑死在他这辆眼看就要倾覆的破车上。
小老板说,工资的事,过几天好吗,赖查理……
小老板说到赖查理,说不下去了。”
叙事的本质就是对于时间的把握,每一个故事都是由一个个客观占据若干时间的事件组合而成。要想将那些事件串联成为故事,就必须按照表达的需要,使用语言,对于呈现的事件进行缩短或延长。
辞职需要多长时间?漫长的思想斗争,默契而许久的沉默。那乔伊斯可能要用上万字才能表述的想法,被王十月浓缩到短短百余字。
情节有长有短,叙事的时间可以轻逸明快,也可以是凝滞沉重、缺乏动感的。在王十月的小说中,快慢两种速度都被很好的驾驭。两者的选用,全凭表达的需要。但总的而言,王十月小说的风格是偏向明快的,这种明晰快捷的叙述节奏本身对于对于通俗文学来说就是一种可贵的价值。
这种对于时间的压缩就是民间口头叙述的传统,例如说书讲古里的转场推进所用的词语“话说”,或者“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是时间压缩或加速的表征,旨在跳过中间环节那些时间流逝,通过删去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来强调叙事的核心内容。清晰明快的节奏会让叙事简洁,将叙述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汇聚在一起。
在《国家订单》的开头,王十月压缩了故事。没有接受,只是接连不断地抛出矛盾和情节。小老板遇到了什么困境?赖查理究竟是谁?李想的诺言是什么?出租屋是什么样子?对于这些细节,后面在情节的推动中或许会有解释,或许没有,但不管怎么说,王十月在这里都只字不提。被压缩的时间和内容是故事的肌理,尽管抱有疑惑,那些提及的事物在情节中都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构建起了冲突的框架和引人入胜的悬念。
那些明快的情节围绕着一个叙事核心构建,王十月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能够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的骨架。这个骨架在《国家订单》里是钱—小老板迟迟发不出的工资;是《寻根团》里的根—王六一魂牵梦萦却物是人非的故土;是《开冲床的人》里的声音—打工仔李想一直追求回复的听力;是《梅雨》里的往昔—马广田开天眼之后看见的景象……这些确立不同情节之间因果关系逻辑的意象将事件编织起来,贯穿整个叙事的始终。
王十月不喜欢用直接引语,他的对白是直接放置在人物述说的动作之后,用逗号隔开,不加任何修饰。人物的对白不再被引用般呈现出来,而是作为一种客观的叙述罗列。这种提速的小技巧让本来就急促的情节进一步加快了,提高了叙事的节奏。
快是九十年代的群体记忆,这和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不无关系。随着改革开放,大片的厂房设立,奔向南方的打工仔、还有那些心怀淘金梦的大小老板,都将效益放在第一位上。打工仔要日以继夜地加班,多赚钱;老板要四处奔波去跑生意,让资本快速周转,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这种被资本体系加速的生活是集体记忆的一个方面。小说叙事的节奏本身就是对集体记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目不暇接的叙述和接踵而至的冲突,或许是王十月的下意识选择,或许是王十月精心设计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叙事形式从表现上来看,对于当时那种快生活的集体记忆是一种很好的呈現。
慢,沉重的文字质感。
现实主义所面临的对象决定了现实主义作品的沉重。王十月作为一个着力于描写底层的现实主义写作者,他的作品也十分沉重。
楚地巫鬼带来的魔幻色彩并没能消解他作品中的沉重,反而增添了奇诡的质感,使得个体化的经验与群体、社会和命运相联系起来,构建了一种不可回避之重,使得小说本身的质感更加沉重。
王十月运用的急促明快的叙述节奏并不能让文字摆脱现实的重力、超越局限、飞翔起来,以获得卡尔维诺最为推崇的轻逸质感。相反,快节奏的叙述让那些冲突聚集,接连不断地集中爆发,如机枪攒射,无法回避,无可奈何。
王十月叙述所使用的,是一种压缩的语言。在同样的篇幅下,压缩的语言能让文章有更大的密度,更沉重的质感。就好像同等体积下,铁远比棉花沉重。只有压缩了一切不必要的因素,语言才能超越文字叙述的时空局限、穿过那些繁复的背景、渡过浩如烟海的知识以还原现场—那可怕的喑哑沉默、死亡的恐惧和历史本身的重量。
王十月的小说借由压缩的过程构建起了故事的真。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无数次的具体事件,被王十月提炼成小说里的一个分镜、一段情境或场景,通过文字为我们所亲历。借着凝练的情境或场景,读者得以体验那些人生活的艰辛,体现出一种现场感和亲历感。
《开冲床的人》是王十月写的一个短小精悍的小短篇,结构简单,只有主角李想和小广西韦超的两条交织主线。开篇刚交代完两个人物之间的联系,马上就带来了第一个冲突的高潮:“有一天,小广西的一只手掌被冲床砸成了肉泥,连血带肉溅了李想一脸。”
紧接着王十月一反常态地着重描写人物的内部世界。通过告知读者李想的想法,将“小广西的一只手掌被冲床砸成了肉泥”这一个沉重的场景无限拉长。我们可以看到,王十月不只有明快,叙事中的时间也有可能是拖延的、周期性的、缺乏动感的。
李想的思绪回到了过去,刚进厂子里的日子,天津大麻花、母亲炸的油饼、雪地、野兔子、水坑、高烧、失去声音的最后一个晚上还有父母亲招魂的声音……
抹了抹脸上的血,李想才意识到小廣西出事了。血肉让李想联想到王水,又进入到了思绪的凝滞时空:
“王水没有吃到他的肉,冲床没有咬着他的手。给他写下‘王水’二字的工友,那只写字的手早已被冲床吃掉了,就像小广西的手一样。失去了手不久,小广西失踪了。十年来,李想习惯了这样的失踪。他知道,用不了几天,甚至是几个小时,就会有人来填补小广西留下的空位。这硕大的车间,能坚持做满两年的人已不多,能全身而退者更是少之又少。李想已记不清这车间吞噬了多少根手指,李想时常会想:他们做事何以马虎若此?李想就不ー样了,他在这位置一坐就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可能还会坐下去。李想觉得冲床很温柔,很安全,也很听话。脚尖轻点一下控制,床的大铁掌呼地抬起,放下要冲的料片,脚尖再轻点控制,冲床呼地冲下。一切都是那么简单。看着小广西那血肉模糊的断掌,李想木然地想,好好的人,脑子又没毛病,为何把手放进冲床口,手在冲床口里,为何又要踩控制开关?若只一个人如此尚可以理解,为何每年都有人会犯同样的错误?李想喜欢他的这台冲床,和冲床有感情。仿佛这冲床是他的恋人。”
这是一段非常可怕的描述,通过对车间历史和李想过往经验的刻画描绘了车间的危险。王十月借着李想之口,以抱怨的口吻轻描淡写地呈现出来。这一段描述李想满不在乎的口吻和读者局外人的定位和语气产生了重合,表面上显得有些轻佻。但是如果注意到前面母亲炸油饼时所说的那如同预言般的抱怨,你已经知道后续结局了。母亲的谶语预示了李想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李想对自己所言的谶语就像命运一般,在向读者昭示,他将会和小广西一样,被他最心爱的、如同恋人般的冲床把手给碾碎。
这个注定的命运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李想的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而李想自己却毫不自知,沉迷在被物化的错觉之中,还觉得他和冲床是一个整体,他就像熟悉自己手指一样熟悉着冲床。未来在李想看来,是如此的光明,他很快就能攒够做人工耳蜗的手术钱,然后恢复听力。
第一节就是李想的一个念头,可短暂的一瞬间被王十月延长,压力顺着文字传递到读者的身上。
第二节跳到了李想和小广西认识之前的时空,是一个意识流般的转换。通过回忆开始交代小广西的人物主线。王十月刻意放慢的叙述的节奏,通过阅读,我们知道了小广西的身份、他的情绪、他的爱恋、他的调皮与自卑。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小广西逐渐丰满起来,他不再是一个代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最为沉重的就是,我们先知道了小广西悲剧的下场,才进一步了解到他的存在。就像古希腊悲剧中,阿尔刻提斯为了丈夫不得不奔赴她的死亡一样,她越是美丽、善良、圣洁,我们就越对这个故事感到悲剧、痛苦和绝望。读者对小广西越是了解,就越能感到文字所透露出的沉重。
但这还不是结局。小广西的命运比断了一条手更糟。在第三节,讨要工伤赔偿的小广西被拿着钢管的保安猫抓老鼠似的、戏弄般地围攻。小广西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赔偿要不得,还得被暴打一顿。因此小广西迫不得已,只能挟持了他爱慕的小玲子—一个管仓库的女工,仅为了脱身。后来李想的上铺换了工友,但李想已经不想再交朋友了。李想好不容易攒够了十万块钱,植入了人工耳蜗。可是当恢复听力的他再一次回到冲车前,他却被那恐怖的噪音给吓坏了。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将铁皮放到冲床的铁掌上,啪的一下,铁掌结结实实地砸到了他的右手上。
看到结尾,我们再回望开头。我们可以发现,这仍然是王十月最喜欢使用的闭环结构。开头和结尾的两个场景中,小广西和李想两者的形象发生了重合,叙事的时空被打乱了。仿佛昔日的小广西,就是今日的李想。
这个暧昧的结尾给了这个故事多元的解读。我们既可以把《开冲床的人》理解成是开头小广西的手被冲床碾碎到结尾李想的手被冲床碾碎线性叙事的时空;也可以理解成是李想的手被冲床砸碎之后,回光返照般想起了那些往事。那两段线性时空或许只是发生在李想心头,作为对过去回忆的意识流—前文那些李想的回忆,或许是在回忆中回忆的套娃结构。
冲床落下来那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和被王十月刻意延长的意识流,这个转换让我一下分不清究竟现实和叙事,何者呈现出来的时间才是真实的。这种似快实慢的叙述给了故事充足的张力,当李想因为疼痛扭成麻花状时,我们读者才意识到,开头就预示的命运,在须臾间已经实现。就好像刽子手手起刀落,那脑袋落地的时刻,才想起了要喊痛。
李想的悲剧包含着更深的隐喻。要向在钢铁的丛林中生存,你必须自我物化,放弃那些你所珍视的东西,放弃作为一个人应当拥有的听力或胡思乱想的情感。你必须自我物化成机器,放弃一切人的需求,反复按着冲床,重复机械的劳动。当你没用的时候,你就会如机械零件一样被替换、被遗弃。
王十月的慢,将悲剧中那些不可回避的痛苦放大,如照片,让不易察觉的电光火石定格,让一个人的个体经验放大成为所有人共同“亲历”的体验,以唤起读者共情。看着那些工厂门口聚集的、因工伤残、尘肺、癌症而讨赔偿无门的前辈,工人们就像看到了自己命定的明天。他们看不到出路,却无力改变、无力反抗那不公的待遇。打工,或许会受伤,会失去健康和劳动能力;但是不打工,就无法在这冰冷的城市活下去。对故乡的思念、再也回不去的家园、痛苦的权衡、无法回避的命运和对未来的恐惧成为了工人们外出务工时难以逃避的集体记忆。
王十月将其凝练,用沉重的语言将那些惊惧惶恐的瞬间固化成一个个情节和片段,将记忆连同过往的质感完全地呈现在读者们的心中。这沉重的文字质感唤起了打工者对于工厂压抑的集体记忆。通过阅读文字的途径,那些农民、工人的后代会传承延续父辈对于城市的那些集体记忆,记得那些工厂里曾经流过的血汗。
王十月的快与慢,就好像太极的阴与阳,首尾相连,唤起了人们对千禧年前后的集体记忆。快是时间的流逝,是都市资本的快节奏,是工作量,是月底要赶的订单;慢是重复机械劳动的枯燥,是压抑的厂房,是痛苦难耐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未来,是看不见出路的明天。快与慢的矛盾包含在他们的集体记忆当中,源于他们亲历的那些生活,正是那些他们所体验到的撕裂。
文学作品就像是代替社会言说的口,每每合上,必然要咬住某些坚实的东西。这叙事的基础,可以是业已发生的客观事实、永恒存在的爱恨情仇、周而复始的历史规律抑或者是不变的正义……对于王十月而言,集体记忆就是他所呈现的重要基础之一。王十月的作品一方面呈现了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又塑造了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人们立足于当下对过去意象的重构。集体记忆涉及到过去和现在两个维度的结合,要求我们的叙事要是现在的、在场的历史,而非罗列时间与事件的编年史—那是过去的历史,只是历史的干枯骨架。王十月的小说就是这样一种在场的历史叙事,能够让人们立足于当下,对过去的意象进行重构。通过阅读王十月的小说,当我们随着历史的叙事回忆过去时,我们不是通过如罗列时间和事件并让它们一一对应对的方式去完全客观地重现过去,而是对记忆有选择地挑选与重组之后的再现。这正是王十月的作品所存在的意义。它虽然无法反映事件和数据,但是可以记载另一种编年体无法承担的、个体的客观事实,以及属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王十月的写作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叙事策略或模式,给我们打开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王十月的写作模糊了虚构、非虚构与历史纪实三者的界限,产生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新叙事角度,营造了一种特殊的张力结构—是超越历史的真实、集体记忆的真实和客观存在的真实三者的结合。
文学,就是通过文字构建读者(主体)与世界(客体)的联系。王十月的写作既有通过“虚构”抽象凝练出文学与世界的普遍性的特质;也具有历史纪实那种对于虚构的逆向写作,用以构建读者与真实事件的联系。这种似非虚构而非非虚构的写作开辟了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
对于王十月作品的阐述,限于篇幅,仅能略谈。这是坏事,也是一件好事。对于王十月,我有太多的话想说,因为他有太多的好作品值得讨论和分析。但我必须在这里停下,就像诺齐克所言:“对于主题要保留余地,而不是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希望这个留白能够唤起读者对于王十月作品的探索。王十月的字里行间还有很多精妙的地方,等待讀者去一一发现。
(责编:朱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