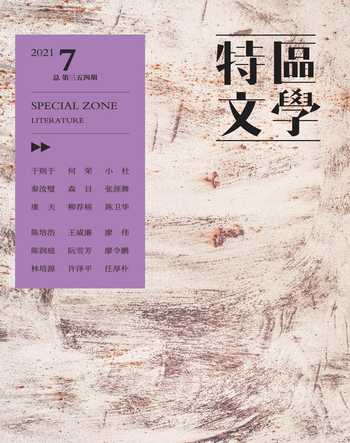西南高速
张涯舞,外科医生,业余写小说,作品散见于各文学期刊及网络平台。
绮陌,我喜欢这个名字。
有点绮丽,又有点疏离。从窗户可以看到村子,白墙灰瓦、收割后的田野、叶子红黄斑驳的树木,我想应该是枫香。焚烧秸秆的烟雾被细雨润湿,缓慢地上升。看不到一个人,也听不到犬吠。
就用这个扫一下条形码,机器上会有价格。老吴又拉开收银抽屉,这里面有两百块零钱,尽量让他们扫支付宝或微信。
行了,你走吧,我知道。
老吴出了门,我坐在电脑前,把收费界面最小化,新建一个文档,刚打完名字,门上挂着的维尼熊的搞笑的口音又响起,欢迎光临。
老吴探进头和半边身体,啤酒可以喝,仓库里还有十件,反正司机不喝酒。
意思那些我都可以喝,我指着货架的一排,有小瓶的白酒、黑糯米酒、预调鸡尾酒、五六种听装啤酒,没搞懂他弄这么多酒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做什么。
这些你自己扫码后付钱买。老吴也就口气凶点,半个月后我就算把它们全干光,他也最多哀叹两声。
维尼熊再次欢迎光临,我从屏幕上抬起头,瞪着他,还有什么遗言?
没事别去那边逛。
哪边?
村子那头,靠国道那条街。
干嘛?
前几天发生一起凶杀案,一个发廊妹被割喉了,警察一大堆,没事别去凑热闹。
还有这么可怕的事?说说看。
具体也不清楚。
人抓到了么?
没有,前天还组织搜山呢。反正你就别去凑热闹。
他终于走了,我站在门口,看见他的车拐进服务区出口匝道,进屋时,维尼熊又说了句欢迎光临,我敲了它头一下,它又出来一声,声音嘶哑。
我坐在柜台后面,看着屏幕上的小说名字:西南高速。
半个小时过去,电脑屏幕上还是那四个字。
进来母女俩,维尼熊好像受了委屈,不再欢迎光临,只是叮咚作响。小女孩直接拉着她妈妈去找方便面。两盒方便面,微信收款20元,第一单生意,开张大吉。
整个上午,卖了两瓶红牛,三瓶矿泉水,一盒饼干,总共进账32元。最后进来一个男的,看了一圈出去了,什么也没买。他审视货物的时候弓着背,动作太猥琐。下午进来的也就十多个人,卖出去的东西不到一百元,我只好安心写小说。
绮陌是321国道旁的一个村子,因为来来往往的车辆而繁荣起来。
早些时候村里人喜欢做长途班车的生意,车一停,陆陆续续下来几十人,很快就洪水般涌进店里,带来喧嚣和长时间坐车的汗酸味。乘客们围着柜台,蛋炒饭两份,一份加蛋不加糟辣椒,另一份不加蛋加糟辣椒。牛肉粉来一碗,黄焖的,酸粉。啊,没有酸粉,细粉也行。老板,炒个怪噜饭,来三份酸菜肉末炒饭。有条理的老板,会专门安排一个人开票收钱,然后叫号领餐;没条理的老板会一下子忙得不可开交。你的不是蛋炒饭加饭?没加饭,加蛋,而且我不要糟辣椒。那怎么办,炒都炒出来了。顾客骂骂咧咧接过炒饭,端到旁边桌子去吃。如果桌子不够,只好到外面蹲在路边,再顺便吃点灰。也有的老板天生好记性,能从餐台前的茫茫人海中认清楚客人。司机一般是不用去挤到人群中点餐的,会由老板娘亲自把他迎接到角落里单独的桌上,给他端来喜欢的饭菜,把茶水杯加满热水。
司机就在那慢慢吃着,没查酒驾那几年,还可以来一瓶啤酒或者一小杯枸杞酒。等乘客们都吃完了,老板娘会按人头把回扣塞给他,然后捏着他胳膊,下次来啊。司机回头,看见老板正埋着头在灶台后作忙碌状,趁机拍一下老板娘的屁股。
每一个大客司机都会有自己常去的店,和自己熟悉的老板娘。也有的嫌老板炒的菜盐放得太多,一路老是喝水,水喝多了又要上厕所。或者给的回扣不够大方,老板娘脸蛋不好看,屁股手感还不好,于是下次换一家。
这种店我们货车司机一般不去,嫌吵,老板娘也不愿做我们这些孤家寡人的生意。
我们常去的店要往前开两百米,都是三四层的水泥房,贴着艳红色的瓷砖,一楼餐厅,二三四楼可以住下。其实吃饭算小事,吃完洗个澡,美美睡一觉才是舒服。
十多年过去,G75高速从绮陌中间穿过,把村子分成两半,一半是完全的農村,另一半就是衰败下去的饭店区。
做客车生意的饭店慢慢衰败了,做货车生意的饭店依然红火。总有货车司机喜欢在国道上学习漂移,也有开那种大挂车的司机,把车停在高速服务区,自己从加油站旁一条小路穿过树林再从高速路下面一个涵洞走过来,花上十几分钟到店里。
我是七点半才去吃的晚饭,老吴说六七点是高峰期,领了人家工资,好歹还是贡献点产值。
老吴算是帮了我个忙,他得知我又辞职回家后也和其他人一样絮絮叨叨,你够折腾,好好的大学老师不当了,出来开货车;好好的又不跑车了,不知道你想什么。写小说? 这样吧,正好有个高速服务区便利店,原来是我表妹看,现在有事,你能不能将就一下帮我看店,顺便写你的小说?
老吴说也可以自己做饭,便利店后面有个小厨房,里面锅瓢碗筷米油盐煤气罐都齐全。可是六七点的时候,叮咚声此起彼伏,方便面、火腿肠、饼干、矿泉水、红牛、口香糖……销售额估计有五百。忙完这一段,我也饥肠辘辘,跑到隔壁要了碗牛肉面,花了15元。端着回来,又开了一瓶酒。
九点后就没什么人了。老吴说大概十一点就可以关门,晚上没什么生意。你要是睡不着,也可以晚点关门,生意能有一单是一单,蚂蚱也是肉。
叮咚。我从电脑屏幕上抬起头,没看见人进来。维尼就挂在门把手上傻笑,它的裤腰上插了个纸鹤。
我确定没有见到过,从上午到晚上,它应该不在这儿。粉红色的纸,好像写了字。我拆开它。
你是小说家吗?你小说的地名就是这里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字迹娟秀,应该是年轻女孩子的。
她是谁呢?隔壁小吃店有一个大妈、两个年轻的服务员。煮面的那位身材矮胖,抓起一把面条扔进沸水里,拎起一个碗,把面条抄出来。右手快速地把葱花、味精、牛肉片、香菜、撒进面碗,再浇上一勺辣椒油,还不忘抬起来用手背搽下鼻涕。她的手指短粗,应当写不出这么秀气的字体。我拿起纸凑到鼻子前,有一股清香,柑橘的味道,还混着点玫瑰,没有牛肉味。另一个身体消瘦,站在手抓饼摊前,神情冷淡,右手时不时从兜里拣出一颗瓜子,用嘴嗑了,皮就吐地上。
她们估计也没作案时间,我离开便利店最长的时间也就是去买晚餐。等待煮面时,我顺便看了看她们模样。
或者是加油站那位,今天来买过东西,拿着一包卫生巾,回头看见我坐在收银柜台,扭捏着又把卫生巾放回去。电脑屏幕上四个摄像头,四幅画面。她在其中一个摄像头下拿起一包饼干,又在另一个摄像头拿上卫生巾。
从加油站走到便利店有两百米,走过来,看了我的小说回去,怎么也得十分钟,她的作案时间也不够。
我想来想去没头绪,于是在纸上写上一句话:我写的是鬼故事。然后按照原来的折痕,把它复原成纸鹤的样子。我把它插回维尼裤腰,退后一步看,脖子和脑袋似乎大了一点,不像鹤,像鹅。
我又写了一段小说,期间来了五个顾客。
十二点半关门,我把收银柜里的三张百元大钞收起,锁进柜台下的一个抽屉里。关门时我看了看维尼,纸鹤还在那,张开翅膀,似乎想飞向远方。
我是早晨六点一刻起床的,洗漱完毕,出门跑步。既然要写小说,就要有个小说家的姿态,跑步那是不能少的。晚上也不能喝啤酒了,要改成威士忌。
夜里睡得很好,枕头和被子还有一种带有洗发水混合润肤露的味道,成分里面应该有薰衣草,以及若有若无的女性体味,我想这就是小玲的味道。又想像着她的模样,身材婀娜、皮肤白皙,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我围着服务区跑了半个小时,手机显示有五公里。罗鸿雁不在加油站,我还没弄清楚他们上班的规律。
早餐自己煮面,煎了个鸡蛋。
七点半开门迎客,老吴说,有些在服务区过夜的长途货车司机会早晨来买东西,你也跑过车,肯定知道,他的意思是让我不要起得太晚。
维尼熊叮咚一声,我没有看见纸鹤,也许真的自己飞走了。
我看了昨天自己的小说,开始修改,将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据说海明威就这样,每天先改昨天的,然后才开始写新的。
那天,他把斯太尔靠边停在绮陌。多拉了二十五吨,怕高速被查车,只好走国道。路边烧秸秆的烟和暮色混合,一个艰难上升,一个缓缓下降。看到那家熟悉的饭店,招牌又换了,变成了 “枫林晚”,搞得很有文化的样子。
几个月没来,除了提供餐饮的旅馆,或者提供住宿的饭店,路两边还开了一排发廊,粉红色的灯光,穿裙子的女子坐在里面。一阵突如其来的饥饿,像锋利的爪子一般抓住他的胃,在那揉搓。他看到路边有家面馆,便停车吃了碗鸡蛋面。出了一头汗,胃里热烘烘的舒服多了。他本来计划开到下一个镇子吃点宵夜再住下的。
他减慢速度,侧着脸看路两边,有女子向他招手。后视镜里突然出现一个穿黄色毛衣裙的女子,长发卷曲。毛衣裙下光着的两条腿,走在路中间,踏着节奏去踩白色分道线。暮色中依旧明艳的黄色、来回交替的腿,像鼓槌敲打着他的心。他从后视镜看着她走进右边第三家发廊的粉红灯光中。
在五十米外的宽阔处停好车,他从驾驶室跳下来,去寻找那家发廊。两边发廊的外观都一样,简陋的水泥平房,玻璃落地门,没有招牌,一样的粉色灯光。一时间他有点迷惑。镜子里是反的,过了路口,左边第三间。
叮咚。发廊玻璃门把手居然挂了只玩具熊,他进门时被吓了一跳。
一整天生意马马虎虎,大概卖了八九百块钱的东西。
小说写得磕磕碰碰,我大多时间在发呆,靠在椅子上,把脚抬起来架在柜台上,望着天花板,那里有一片污渍,形状像非洲地图。北边是地中海,穿过苏伊士运河便是红海,沿着海岸线,从北往南,红海狭长,与海平行的是尼罗河。从下游的三角洲到上游的埃塞俄比亚,然后东非大裂谷,人类起源的地方。继续往南,印度洋波澜壮阔,陆地上的高地是肯尼亚,走出非洲。库切的青春夏日,内陆深处和幽暗之地。然后是好望角,绕过便是大西洋。天花板上,污渍组成的非洲大陸如小岛一般孤独,那些刺眼的白色,是一望无涯孤寂的海。
便利店离高速公路的直线距离至少两百米,那些呼啸而过的车辆,带来空气的颤动,以每秒340米的速度传导而来。我的便利店就是一座孤岛,那些声音就像海浪涌向我,拍打、破碎、回溯、泡沫……飞驰的车辆,会把一部分波浪带向远方。我喜欢分辨被拉长的警笛,救护车的声调较长,就像哀嚎,疼痛后要停顿一下,抽一口气才发出声音;警车就欢快得多,哇啦哇啦一路而去。
维尼熊发出叮咚的声音,我会抬起头,看进来的顾客,大部分司机来去匆匆,也有不少气质颇佳的女子,墨镜后的眼影应该像三月的桃花。时不时我也会看一下维尼,他的裤腰处空空如也,没有粉红色的纸鹤。我懒得去猜想那是谁。那样秀美的字迹,和服务区这样无聊的地方并不符合。
晚餐自己煮饭,炒蛋炒饭。今天开了瓶500ml的二锅头,每天二两,至少够喝五天。
做饭时听到叮咚一声,粉红色的纸鹤又飞到维尼的裤腰那里。
还是那种清香,混着淡淡的柑橘和玫瑰,只有十一个字:
我觉得你有个地方弄错了。
他也是事后才发现自己的错误。
事后他也曾想,路边两排一样的建筑,一样的玻璃门,一样的粉红色灯光,每一扇门都是一个选择,都可以通往一个不同的平行世界。
他走进左边第三间,进门时被叮咚声吓了一跳,门把手上挂着一只玩具熊,正咧着嘴傻笑。一个短发的女孩子正站在镜子前忙碌,镜子前坐着一个胖男人,已经睡着了,任凭女孩的手在他头上忙碌。女孩不时要把他的脑袋扶正,看着镜子。镜子中的女孩神情专注,染了暗红色的头发。
女孩回过头,先生你先坐着休息一下,这里马上就好。
看着镜中女孩的面容,她穿的是一件高腰棕色皮夹克,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下面是牛仔裤。他一阵恍惚,刚才明明看见那个黄毛衣女孩走进的这家店。他没想到这家居然是真的理发店,屋子中间有道横拉门,里面还有间屋子,也许她就在里面。
理发的胖子已经醒来,注视着镜子中的自己,从罩衣下伸出一只手,把嘴角的口水擦掉。
短發女孩离开她的顾客,端来一杯冒着热气的茶,先生先喝杯水,马上就好。她转身时衣角扫过,有柑橘的气味,混合着玫瑰,应该是香水。他端起茶,蒸汽中升腾出茉莉花的气味。
他也不好问,找个椅子坐下,镜中的自己面色晦暗,头发油腻,鬓角已经遮挡住半边耳朵,头发的确长了。
胖子理完发,还要修面,短发女孩去烧水热毛巾。她走过来说还要等一会儿,不好意思。
女孩黑毛衣下的胸脯高耸,笑容很甜,声音也很好听。他靠在椅子上,松弛下来。
女孩拿来热毛巾,用脚踩了一下理发椅下的一个脚踏,椅子向后倾斜,胖子的身体随着椅子后仰,似乎又要睡着了。
理发椅还是那种铸铁基座,以前国营理发店才见过的那种。踏脚被磨得光滑,发出幽微的铁器之光。女孩拿起一把剃刀,在椅子后面的长皮片上来回磨了磨,刀锋闪过,又是一道刺眼的光。
他的目光从涂满肥皂泡的胖子脸上移开。他看着面前的镜子,镜框是胡桃木的,顶部一个圆拱,两边是欧式的纹饰,镜框外还有墨绿色的绸缎装饰。镜子前也有一把剃刀,一个电动推子,两把剪刀,一个电吹风。剃刀下压着一本杂志。
他拿起剃刀,把杂志抽出来。
杂志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应该是故事书。他随便翻到一页:
高健走进一家理发店,发现这家店的装修风格复古,镜框是欧式的圆拱形胡桃木,周边还装饰着墨绿色的绸缎,绸缎在圆拱处打了个结,看上去就像一只停在鲜花上的蝴蝶。
最让人惊奇的是理发椅,居然是七八十年代国营理发店的那种,铸铁基座,脚踏已经被磨得光滑。
理发师穿着棕色皮夹克,深蓝色牛仔裤,高领黑色毛衣,身材前凸后翘,短发染成暗红色,就像凝固的血迹。
他躺在理发椅上,从镜子中看到红发女孩拿起剃刀,在牛皮磨刀布上来回刮擦,声音刺耳,他的意识渐渐模糊,也许是刚才的那杯茶,茉莉花的气味很好闻,但喝到嘴里总觉得有点苦。镜中的女孩一丝冷笑,剃刀发出寒光……
杂志在这中断了,不知道有没有后继。他抬起杯子,又喝了一口茶。
睡到七点半才被闹钟吵醒,其实六点半它已经折腾过一回,我爬起来,把时间调后一个小时,继续睡。什么早起,什么跑步,都滚蛋。
早餐连方便面都懒得泡,撕了包萨其马,吃了三块,甜得汪心,又开了罐百威,也许味蕾一直在甜味中昏昏欲睡,此刻啤酒的苦无疑能让人清醒。我知道自己心情糟糕的原因,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小说写不下去时,我会出门,戴着耳机,跟随摇滚的节奏,围着小区的人工湖走上几圈。
我把门锁了,戴上耳机,走到这栋房子背后,越过围墙,可以看到村子。高速公路这一段是东西走向,村子被分割成南北两边。北边的房子是灰色的歇山顶,墙被刷成白色,几年前每户都拿到一两万的补贴,把房子统一翻修成这个样式。即便这样,这部分村子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在初冬的细雨中,成为一团团氤氲的色块,灰色、白色、枯黄色。看不到一个人,也听不到犬吠。
村子的另一边,我现在看不到,在双向四车道高速路的另一边,老国道上来来往往的货车,带来了柴油燃烧不完全的黑烟,刹车片不堪重负的焦臭,屋顶落下的灰,顺着窗户玻璃留下来,像一条条细长的蛞蝓。路面永远是湿的,现在是雨,不下雨时是路边店面为了防尘泼出的水。泥泞里混着揉成一团的烟盒、瘪的易拉罐,以及被汽车轮胎降维打击成薄片的死老鼠。那些驾驶喘着粗气的大货车的司机,在路边的发廊,轻易就把钱花出去。出了门,一想自己辛辛苦苦跑几百公里,也就换来几分钟的欢愉,于是恶狠狠把一口痰吐到泥地里。可也就十几天后,再次经过此地,又忍不住减慢速度,往两边落地窗里张望,直到把车停下来。
这条高速从最东边的海边开始,一路向西,一路爬升,房子越来越少,树越来越多,天空越来越蓝,这种想象出来的诗意或许是我开货车的缘由吧。暴烈的音乐回荡在驾驶室,在鼓膜和车窗玻璃间产生共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玫瑰色的早晨到淡青色的黄昏。大半年的时间,我基本都睡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吃完东西,到厕所洗漱,然后回到车上,拿一本小说,直到睡意袭来。
大概晚上八点半,叮咚声后我醒来,抬头看见纸鹤如期而至:
结局值得期待。
我昨天并没有回复她,今天也不打算回复。
我不去纠结到底是谁把这个纸鹤放在这,她又是什么时候看我写的小说的,我没有心情去做侦探。对于无法理解的事情,就当它理所当然。我又读了一遍昨天写的,开始修改。把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改变了视角,但仅仅一个“他”又显得刻意。我需要一个名字,这样看上去会更真实。我在心中默念字与字的组合,用替换键,把“他”替换成:高健。
好了,让你久等了,坐过来吧。女孩拿起白色罩袍给他披上,她收紧脖子系带时高健感觉像被套上绞索。
罩袍上还有些细碎的花白的短发梢,从织物纤维中探出来,高健看着觉得就像喉咙里有根鱼刺。也许是刚才胖子的,也许是前一个客人的,还可以闻到香烟和发油混合的气味。屁股下的温热可以确定是胖子的体温。
先生,想理个什么发型?
也就……修一下吧。高健的右手从罩袍下伸出来,摸着鬓角说。
电动推子发出呜呜的声音,头发如被收割的稻谷。
刚才有个穿黄毛衣的女孩进来了吗?
谁呀,这里就我一个人呀。女孩的左手四根手指轻轻把高健向左倾斜的头扶正。她的左手,指头纤细,在镜子中,在她身体的右边。
高健突然想明白,倒车镜的左边还是事实上的左边,不用在镜像中认为是她的右边而去纠正,他下车后往回走,应该是过路口后右边第三间。
高健突然转向门一侧,呀,收割机在稻田中开出一条深沟。女孩连忙道歉,高健反而不好意思,没事没事,你再理短点就行了。女孩的右手把高健脑袋扶正。
收割机的嗡嗡声,梳子划过,纤细的手指不时敲打在头皮上,柑橘混合玫瑰的气味,迷迷糊糊很舒服的感覺。
修个面吧,女孩把理发椅向后放下。
高健努力抬起头,从镜子中看到红发女孩拿起剃刀,在牛皮磨刀布上来回刮擦,声音刺耳,他的意识渐渐模糊,也许是刚才的那杯茶,总觉得味道有点苦。余光里的剃刀发出寒光……
我是被敲门声吵醒的,拿起手机一看,八点半。
谁啊?
有咖啡吗?
我披起衣服,下楼开门,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穿一件灰色夹克,鸡心领红色毛衣,露出深蓝色圆领内衣。兄弟,吵你睡觉了,今天要赶路,昨天没睡好,他们说你这里有咖啡卖。他穿着条黑色西裤,面料上有一些刮痕起球,左边裤腿有很多鬼针草,右边裤腿有几粒苍耳子,裤脚很多泥,棕色皮鞋上也全是泥。
那边自己去选。我把电脑电源打开。
他转身,似乎带着一股风,柑橘混合玫瑰的气味。我站起来,走到他身后,这种特浓的提神一点,我用力闻了闻,好像又没有那种气味。
不想吃早餐,也不想吃午餐,我看了昨天写的小说,改了几个字,今天不知道如何发展。我靠在椅子上,把左脚搭在收银台上,右脚搭左脚上,头顶上的非洲,一只苍蝇停留在撒哈拉,我对着它吹口哨,它无动于衷。我的手中有一包鱼皮花生,我把它作为炮弹,手指弹射出去,第一发,弹着点偏右,修正射击诸元,第二发。它飞起来,在大陆上空盘旋后又降落,这次它的脚下,马拉河在流淌,河流右岸,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斑马、角马、羚羊。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中曾经猎捕过它们,而现在等待它们的,是河对面越野车上架着长焦镜头的游客,以及埋伏在昏黄河水的尼罗鳄。
或许大多数人,都和食草动物一样,整日为了食物奔波,随时警惕捕猎者,在黄昏的片刻闲暇,它们会不会抬起头来看一下风中的落日?
对于食肉者,稀树草原和水泥森林不过是换了形式的狩猎场。
我的那些小说,主人公经常死于非命,车祸、疾病、凶杀、坠崖,我似乎在书写死亡中获得满足,获得自己造物主般的虚幻感。
老吴是少数看过我的小说并认为不错的,他说你还是写小说吧,他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情,你不写小说,可能会成为变态杀人狂。
整个下午,一个字都没写。傍晚时生意异常好,原因是停了大半天水,隔壁小吃店没做吃的,很多人来买干粮。忙完那一阵,觉得胃就像被两只铁爪拧在一起。赶紧去厨房烧水,泡方便面。
欢迎光临。听到声音,我出来,没有人,维尼那里有只纸鹤,翅膀似乎还在微微颤动。
你编不下去了吧。
粉色的纸上黑色的字在冷笑。
一连三天,我一个字没写。我在想要不要让高健走进对面那家发廊,去寻找那个黄毛衣女孩,就像进入另外一个平行世界。他现在还躺在铸铁理发椅上,椅子被放倒,就像躺在行刑床上。
我躺在床上,右手伸进裤裆。枕巾上还有残存的小玲的味道。这也许就只是某种激素效应,我的行为和草原上求偶的食草动物并没有太大区别。
一晚上都是乱七八糟的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套着一个。先是开着车回家,盘算着要在楼下买点菜,晚饭后还要去接女儿。进入小区后是连续的S形下坡,我的速度很快,向心力带来的倾斜,以及失重感,让我有飘浮在半空俯视自己的错觉。恍惚间觉得自己其实已经死去,就在这坡道,车子冲出弯道,翻落山崖。先前那些想法,不过是我的执念。我和她走在街上,借过马路的时机,我拉起她的手。她没有躲开,我们牵着手漫步在街头的灯影中。我不时紧张地侧过头看她,她直视前方。一辆公交车路过,车窗里有人在看着我们,那是一双巨大的红色眼睛。我的鞋不知怎么掉了,路上全是鞋,而且和我的鞋都很像。终于找到了,坐在马路边把鞋穿好,一抬头,她却不见了。来回寻找,都没有她的身影,摸出手机,却发现找不到她的电话号码。我坐在办公室盯着电脑屏幕发呆,屏保是城市车水马龙的街头,霓虹闪烁,屏幕上映射出我的脸,头发油腻,从额前垂下一缕,双眼发红。转过目光,望着窗外,亚热带灼热的阳光落在建筑上不真切地散射,就像骤雨的匆匆脚步掠过屋顶泛起的白雾,或许有一只蝴蝶,它的翅膀刚掀起了一场亚马逊的风暴。走进领导办公室,他让我先坐,然后在办公桌那忙这忙那。我坐着无聊,看了看窗外,昨天的那朵灰色的云变成了兔子模样,把一场显而易见的雨隐藏在肚子里,风在屋檐那徘徊,一只白鸽的尾羽。等他表演完忙碌,靠在椅子上,端起茶杯,我已经记不起要说些什么了。
这半年,我去了很多城市,最北方的呼伦贝尔,最南方的海口。但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晃而过。和我最初的想象一点也不一样,闻不到草原的青草味道,也吹不到南海的海风。开车时喧嚣的摇滚也无法让我思考。
所以现在的生活,不过是既往的延伸和变异。高速公路,只有远处,而没有远方。
便利店生意每天差不多,八九百,好的时候上千。今天中午,我懒得泡面,又去隔壁吃了碗牛肉面。吃完后回到便利店,半个小时没有人,百无聊赖,便把门关了。从旁边小路,穿过小树林,是一片杨树,几天时间,叶子几乎掉光了,徒劳地向天空伸出枯瘦的手臂,灰色云层中似乎有一点阳光。
在涵道前,我掏出手机,打开电筒。地面潮湿,电筒光只能照射一小片,走着走着,会觉得黑暗中有什么在那张着嘴等着。远处的出口就像时光隧道的另一头,能回到过去或者抵达未来,或者是去往另一个世界。我走出去,会看到一片蔚蓝,白色沙滩,椰树,海浪涌来,回溯、破碎、淹没,永不停息。
维尼那没有纸鹤飞来,我想她也厌倦了。
中午在绮陌那条道上走了一圈,路边只停了几辆货车,两个司机模样的在一家饭店里坐着。那两排发廊有一半开着,透过落地玻璃门的灰尘和污渍,可以看见屋里面目不清的年轻女子。左手边接连好几间都拉下了卷帘门,其中一间被贴了白色封条,就像一个巨大的X,上面的红印像唇印,又像血痕。街上没几个人,偶尔路过的灰白色的狗拖着舌头,姿势松松垮垮,也没看到警察模样的。呲的一声,一辆红色斯太尔越过前面路口,很急迫地在一辆面包车前停下,排气管吐出一团浊气。我曾经开过这种车,熟悉它停下时发出的叹气声,就像一个得了肺病的老人的喘息,无比沉重。司机跳下车,拉了拉夹克下摆,往回走来。我们擦肩而过,我觉得他似曾相识。我忍住没有回头,此时停在路边的面包车的后视镜里正好出现他的身影。我从镜中看见他走进右边第三家发廊。蓦地,我突然意识到不对劲。于是回头,走过路口,开始计数,没错,右边第三间,正好是被叉掉的那间。我回头再次确认,的确是第三间。前后两间的玻璃门后都坐着几个年轻女子,其中一个还对我招了招手。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镜子中是镜像,右边应该是左边,或者,当时我和他相向而行,我记住的是我自己的方向……我走到马路对面,推开落地玻璃门,一张椅子转过来,一个穿黑色紧身毛衣,牛仔裤的短发女子站起来,她把搭在椅子扶手上的棕色夹克提起,披在身上。先生,理发吗?
镜框是欧式的圆拱形胡桃木,周边装饰着墨绿色的绸缎,镜子中的男人面色晦暗,头发油腻,头顶上还有一缕像根鸡毛般翘起。我抬起右手去拂平那一缕头发,镜中男人也抬起手,那只手明明在他左边……
整个下午浑浑噩噩,晚饭吃的方便面,喝了一小瓶二锅头。关门时已是零点十分,又是新的一天,回到阁楼,睡不着,左右搜寻,屋子里小玲的气息已经所剩无几。床头靠墙的角落有一摞书,我曾经粗略扫视过,最上面一本是《乖,摸摸头》,然后是《第13个小时》《罗杰疑案》《悬崖山庄奇案》。我不记得有这几本侦探小说,要不前几天也不至于那么无聊。但此时我已经失去了探索和推理的欲望。我继续翻看,剩下的几本,都是我没兴趣读的。书下面还有一摞杂志。我把书抱开,一叠《知音》,几本《读者》,最下面是一本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的杂志。16开本,5号宋体字,颜色居然不是黑色,而是蓝色的,那种蓝色,就像蓝黑墨水的颜色,而且仿佛时光久远,褪色般如远山淡影。杂志没有封面和封底,估计只有半本,我拿起来。
高健努力抬起头,咬自己的舌头,一股血腥味,驱散了那种令人昏昏欲睡的柑橘混合玫瑰的气味。
镜中红发女孩左手中的剃刀闪着寒光。
高健下意识伸出右手,抓住她拿剃刀的手腕。
啊……她伸出左手去掰。高健用力,她失去重心,扑倒过来,手里仍握着剃刀。
推子、剪刀、梳子落在地上,被墨绿色帷幔装饰的镜子裂开,如蛛网,如雨后干涸的大地,如火烧后的龟甲兽骨。
天鵝般的脖子,雪白的肌肤,一道口子,血珠如日全食后的贝利珠,一颗,两颗,三颗,突然暂放的鲜艳花朵……
咚咚咚,卷帘门被敲响,声音急骤,如鼓点,如心跳。
(责任编辑:廖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