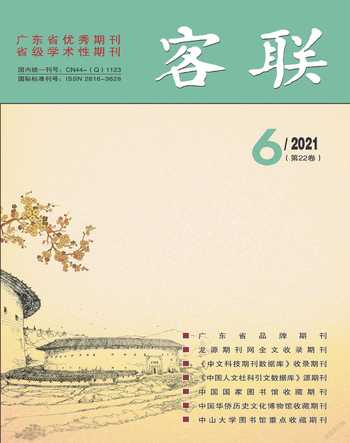他我之异、寻根之同:《走向花山》与《花山壁画》
何永艳
摘 要:1984年杨克对花山岩画进行了主动融入式的激情歌唱;1990年黄神彪对花山岩画进行了“灵魂归属”式的民族写作。《走向花山》与《花山壁画》体现了杨克与黄神彪在“他者”与“我者”不同视角下的花山文学创作之异:激情抒怀与民族史诗的风格之异、血脉相融与突破疏离的身份之异、由外而内与由内而外的影响之异。但二人对花山岩画的文化定位殊途同归,都认为花山岩画是广西文化的摇篮和文化之元,是他们文学创作的缪斯和根脉。
关键词:花山岩画;杨克;黄神彪;他者;我者
花山岩画是广西文学的文化动力来源之一,书写花山岩画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当属1984年杨克的组诗《走向花山》和1990年黄神彪的《花山壁画》。杨克对花山岩画“主动融入”式的激情歌唱,引动了广西文坛“百越境界”的文化自觉;黄神彪对花山岩画“灵魂归属”式的民族写作,成为推动广西文学的一束“精神圣火”。
一、1984:杨克《走向花山》——主动融入的激情高歌
1984年杨克主动走向花山,率先写出了组诗《走向花山》,成为第一个走向花山、寻找文化之根的诗人。这一场花山岩画文化之旅演变成一场文化精神的追寻,进而演变为一场“百越境界”的文化自觉。
首先,从诗歌题记可以看出杨克对花山文化的主动融入。杨克在诗歌开头有一段题记,在这段题记中作者对花山岩画进行了简练而准确的定位,岩画所处的位置、颜色、图像等,最后一句以一个“元”字对花山岩画文化价值进行定位,元即为始、首、大之意,点明了花山岩画的初始性、原始性。
其次,诗歌A部分句式内容突出了“走向”花山、融入花山文化场域的意义内涵。杨克对花山岩画图像的选用不是随意而为而是配合诗歌内容进行精心选择,体现了花山岩画图像与文字的互文诗美。A部分选择的是三个蹲踞式人像,中间者身佩环首刀,这是花山岩画最多、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图像因子,与之相配的文字内容是对花山岩画的整体赞颂,火与血的激情、猛虎、饿狼等猛兽的野性来凸显岩画的野性狞厉之美,“从野猪凶狠的獠牙上来/从雉鸡发抖的羽翎中来/从神秘的图腾和饰佩的兽骨上来……我们举剑而来,击鼓而来,鸣金而来/——尼罗!//从小米醉人的穗子上来/从苞谷灿烂的缨子中来/从山弄垌场和斗笠就能盖住的田坝上来/……我们唱欢而来,雀跃而来,舞蹈而来/——尼罗!//绣球跟着轻抛而来/红蛋跟着相碰而来/金竹毛竹斑竹刺竹搭成的麻栏接踵而来/……我们匍匐而来扬幡而来顶礼而来/尼罗——尼罗”[1]209-215,“从……来”的系列句式与题目之“走向”二字吻合,表明了一种主动寻求花山岩画为诗歌的图腾、文化的根脉,将自我“内置嵌入”花山岩画的文化场域之中的态度。
再次,从诗歌结构和词汇意象的安排上可以看出诗人对花山文化的主动嵌入。在诗歌结构内容的总体安排上,诗人受到花山岩画火、血、美的诱惑走向花山、来到花山,继而深入了解花山,试图融入花山,因此在诗歌的B部分诗人选择的是人与兽图像的组合作为诗歌内容,想象了先民使用箭簇狩猎的情形;C部分选用铜鼓图像为诗歌内容试图在花山岩画中穿越2600多年想象先民从野蛮向文明过渡,在鲜血和尸骸中穿越死亡的民族历程;D部分诗人选用三位怀孕的长发女子的图像为描写内容试图解释花山岩画与民族血脉延续的关联。总之,该诗四个部分分别与花山岩画的四种图像相对应,形成一种动势一致、图文对照、互相增益的诗美效果,表现出对花山岩画天马行空的神秘想象,所选用的诗歌意象较为广泛多样、五彩斑斓:血、火、野猪、雉鸡、猛虎、饿狼、小米、苞谷绣球、红蛋、糍粑、五色糯饭……。既然是主动的嵌入,在诗人所使用的形容词、动词中可以见到诗人与花山岩画间的文化互动,如礼赞、膜拜、震慑、匍匐、抡着、咆哮、呻吟、沸腾、崛起、奉献,以及神秘、斑斓、狞厉、崇高、亘古、神圣、纷乱、残忍、冷酷、孤独、温柔、炽热、青春等,在诗人的笔下意象流动如此之迅速,如万花筒般绚烂多姿,是接触花山文化后受到强烈震撼后的冲突、碰撞的表现。
杨克离开花山岩画文化场域后,诗歌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元。但是80年代他与花山岩画的邂逅,以及对其文化场域的嵌入,的确使他受到了他的“诗歌缪斯”——花山岩画的洗礼,不知不觉熏染和滋养了他的生命,抚慰了他孤独的灵魂,激发了他的潜意识的灵感顿悟,让他的诗歌智性从沉睡中苏醒,找到诗歌的图腾以及贯注其图腾的血液之河,创作出了一批代表着他诗歌历程正式起航的优秀诗篇,正如他自己所说:“尽管零零星星发过作品, 我以为我真正的创作始于1985年”[2]16。以《走向花山》为突破口,他继而创作了一系列以花山岩画文化圈为文化场域的“红色”作品,悲壮热烈的红色基调为他的诗歌增添了力量。在他后来创作的诗歌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花山岩画滋养后的一些写作的惯性和延续,如《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天河城广场》、《野生动物园》等作品中依然表现出一种生态的关怀和隐秘的愿望,花山岩画的确有力地推动了杨克的诗歌创作,赋予他的诗歌一种醒悟了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辅之以他强烈而敏锐的个体意识,进而塑造了他诗歌风格中凝重、粗犷的浑厚气质。
二、1990:黄神彪《花山壁画》——灵魂归属的民族写作
黄神彪,生于秀丽的明江河畔,与花山有长达三十年的创作姻缘:“我写花山岩画我写了近三十年,回过头来想写花山壁画并没有后悔,我没想到它今天在世界文化史上能够占据这样的位置。” [3]
(一)民族灵魂的召唤与回应
首先,黄神彪对花山岩画的理解是从岩画创作民族主体的视角出发的,体现了民族内部文化的情感对应与灵魂相通,这是《花山壁画》创作的基础。黄神彪对岩画所处的每一片河湾都情义深厚,他认为:“有山有水有绿地,河湾是最美的地方,也是最富有诗意的地方。” [4]
其次,《花山壁画》的诗歌内容是诗人对花山岩画的民族灵魂的互动与回应。在序诗中诗人即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将花山岩画与整个壮民族紧紧相连,肯定了花山岩画“民族文化摇篮”的地位,点明了全诗“生命与诞生,诞生与希望”的主题,诗人的思绪飞扬,将花山岩画与埃及金字塔等进行等量齐观,热切呼唤:“魂兮,归来我的民族魂”;第一章宇宙洪荒,詩人从史前文明、米洛甲诞生写起,突显沉重的历史感、责任感与沧桑感;第二章《编年永乐》是以神话具象书写的历史。将花山喻为伏羲兄妹寻找到的美丽的“斯奥斯波家园”;第三章《皇天叩问》,诗人点出了花山岩画的终极主题:生命;在第四章《世纪幽灵》中, 诗人触及到壮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血泪沧桑;第五章伟大梦想,诗人对全诗进行归结与升华,壮民族历经风雨苦难,从遥远的过去走来,而“花山故乡,从遥远的昨天已成为了我们民族文化圣地和文化乐园”[5]85-102,花山从遥远的过去就已经作为壮民族的家园、故乡、圣地,它的身上包蕴着民族最初、未来的伟大梦想,凝结着民族的生命与希望。
诗歌的后部,诗人运用了三个象征性地意象来对花山岩画的文化精神进行归结:千年歌墟、族徽和绿色摇篮。诗歌结尾诗人对花山岩画的未来进行展望。
(二)民族文脉的梳理与界定
黄神彪的《花山壁画》对花山岩画进行了文化地位的立体界定,准确把握住了花山岩画的精神内涵。花山岩画是壮民族的斯奧斯波家园;它是先民留给后代子孙的绿色摇篮。这一文化地位的界定明显是将花山岩画置于历史文化中,诗人把神话、传说、民族历史溶入诗篇,时间跨度大昨天、今天、明天,从远古洪荒到改革开放、到更遥远的未来,视野广阔:从花山到世界、从世界到宇宙,从小我到大我,从微观到宏观,从具象到抽象,从个人情感到民族精神,从神话到哲学,将花山岩画与世界各文化景观并列展现。综合、全面、整体地,具有前瞻性地对花山岩画的文化地位进行了立体界定,具有诗性之美、理性智慧和思想深度。
黄神彪在世界文化的宏阔视野内对花山岩画进行了文化脉络的梳理,由此发现了“花山文脉”(不单指文学)与广西文脉的关联、与中华文化的吻合。同时,黄神彪认为“散文诗应摆脱浅小,走向宏深”[6]40-44。因此,诗人将花山岩画与历史、文化紧密联结,在对花山岩画的哲学叩问中,逐渐揭示出花山岩画的终极主题和终极功能:生命,对新生命的花神迎接,对亡魂的祭祀,是生命的神圣宫殿,凝结着壮民族的生命意识,象征着壮民族的生命愿望,昭示着生命的崇高、永恒、不朽,它联结着壮民族生命的源头、伸展至生命的历史、延续到生命的未来,诗人认为这是花山岩画深刻的终极主题。
(三)民族写作的初衷与延续
黄神彪对《花山壁画》的创作并非一时的诗情爆发,而是一位民族诗人深厚积淀、长期思考、目标明确、持续跟进的民族写作。
首先,诗人创作《花山壁画》的初衷即是作为民族诗人对民族文学创作的继承与突破,黄神彪关于花山岩画的写作一直在延续和跟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以青年民族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1992他在北京专门举办了作品讨论会,将的《花山壁画》被认为是“具有民族风格的史诗性作品,是一束民族的精神圣火”。
其次,基于民族诗人的身份定位,黄神彪对《花山壁画》的创作具有民族文学的特别追求。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花山人,“生存的大自然背景,就是在中国左江流域秀丽明江河畔那举世闻名的花山壁画的氛围中”[7]123,他对花山岩画的探索是由内而发的,具有文化的自觉和创作的深层冲动。后来他“大面积、全方位地联系民族文化、世界民族文化以及发展史与现当代意识确定了立足民族放眼世界的视野”[7]127-128。在确立了《花山壁画》写作的立足点之后,他还确立了“三感三度”(历史感、民族感、现代感;深度、广度、厚度)的创作原则,将花山壁画作为本民族的艺术瑰宝来写,又将其置入世界艺术史之中,确定了作品雄浑高昂的基调,这就是诗人为何纳入大量的神话、生物进化史、社会发展史、大量民族图腾崇拜物以及民风民俗,从民族和人类起源对花山岩画进行文化意识追溯的原因。
总之,黄神彪的《花山壁画》具有民族文学创作方面的创新性和拓荒性,其诗歌风格体现了民族性统领下的地域性,具有民族历史的长度、民族精神的高度、民族意志的深度、民族文化知识的广度。黄神彪创作《花山壁画》有深厚的文化积累、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知识积累,有着明确的身份角色定位,具备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是在做了充分的写作准备,确立了明确的写作目标和原则,在清晰的写作思路指导下才开始进行创作的,这一过程历时久远,可以说融于其生活、贯穿其生命历程之中。
三、风格、身份、影响三重创作之异
杨克的《走向花山》与黄神彪《花山壁画》有诸多差异,从中我们可以辨识出“我者”与“他者”对花山岩画进行文学创作时不同的文化诉求。
(一)激情抒怀与民族史诗的风格之异
《走向花山》与《花山壁画》在诗歌体式风格方面差异很大,从诗歌形式上可以看出前者为较短的现代新诗组诗,在形式上大胆开拓创新,在诗歌内容上大开大合、跨越古今,在诗歌语言上简练、跳跃,对于壮民族文化、民俗、神话传说等意象大量使用了简笔勾勒,色彩以浓烈的血红色浓墨重彩;在诗歌情感表达上激烈、野性、洒脱、一泻千里。而黄神彪的《花山壁画》是一首近8万字的散文长诗,虽然采用了散文诗的体裁,但在诗歌内容、风格上又呈现出史诗般的雄浑、稳健、大气磅礴。杨克激情迸发,以抒情为主,想象丰富、豪迈奔放,黄神彪则在历史中冷静的思考,夹杂大量的叙述和议论,语言繁复、华丽、节奏感强,饱含浓郁的民族情感。
黄神彪的《花山壁画》将民族与历史、人类和整个世界融合沟通,将诗意升华到民族魂、民族精神的哲学高度,呈现出庞大崇高的史诗境界,他站在民族、人类的起点上关心自己的民族家园。其《花山壁画》等诗作是其血液中流淌的民族魂、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基因的自然展现,充满了对本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细腻描画。他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习俗等了如指掌,对以花山岩画为典范的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充满自豪与骄傲,对本民族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的历程充满清晰深刻的认识,并将诗歌情感的抒泄上升到庞大崇高的史诗境界。
比较而言,杨克与花山岩画的初次相遇也是在寻根文学、现代诗歌浪潮的影响下的偶然相遇,这种猝不及防的相遇给予他们的震撼和情感刺激一定是比土生土长、久经熏陶的当地族人更加迅猛和激烈的,对岩画产生的神秘感、好奇心和巨大的兴趣一定是急促深切的,这也是他迅速写就《走向花山》,随之发出“百越境界”宣言的重要原因。他在《那一年,我们走向花山》一文中,对当时遇见花山岩画的情感状态作了详细描绘:“租了蚊帐、薄被、席子。到了江边,乘船而下,水之湄,看见了那一仞绝壁。热血贲张!” [8]在强烈的情感刺激下诗人和同行的作家们收获了巨大的灵感大爆发,1985年,杨克率先写出了《走向花山》组诗,诗的名字来看“走向”二字值得推敲,代表了一种外来者对花山岩画文化场域的自觉接近的态度,寻求精神文化的滋养。
(二)血脉相融与突破疏离的身份之异
从杨克所写的一系列与花山岩画文化场域有关的诗作《走向花山》、《图腾》、《深谷流火》等来看,这种他者的视角是明显的,“我”作为观察者的个体意识是时时存在的。如《图腾》这首诗中诗人将自我与各种文化事象一一对应,柳江人、桂林甄皮岩的化石、壮锦花纹、印纹陶片、悬棺、岩石山歌、羽人夢、唱着祈雨歌跳起蚂拐舞、从花山石壁周氏兄弟画作中的红人“是我”,表现出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根脉的巨大认同和皈依,但欲将自己皈依于花山文化场域的诗人又是与本土乡民差异毕现的,他与自己广阔的现实场域又无法剥离,“博物馆”、航天研究所、洛杉矶这样的生活场域与花山文化圈内左江流域边地古老的文化地理迥然有别;同时,他也难以与自己现代化的现实生活相剥离,诗歌中“宣读论文”、扭迪斯科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多元生活状态与宁明县城里慢节奏、随时与花山岩画对话的生活状态还是有不同的;当然,作为一名生活在广西的汉族诗人,与花山子民隔阂最大,最难以跨越的还是语言的障碍,说着“英国话日本话广东话普通话”的“我”在向着花山迈进的路途中,语言交流的困难一定是突破文化隔阂最明显的阻力所在。
全诗总共使用了数十个“我”字,如此多的“我”恰好反映了自我身份的身份的无所皈依,为此他主动融入花山岩画民族文化场域之中,将情感最大化地代入其中,取得了非常好的诗歌效果,契合其文化寻根的主题;另一方面,诗人也意识到了文化壁垒的存在,这种内置型的皈依又不能彻底地完成,尚有文化的、语言的、地理的、血脉的诸多的屏障存在,因此,杨克对花山文化的家园皈依和书写是一种以“他者”为主意欲超越“他者”的状态,虽避免不了“他者”的疏离,又达不到“我者”的距离,但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少数民族创作的“临界点”。
比较而言,黄神彪在《花山壁画》当中的民族身份是非常确定的,八万字的长篇现代散文史诗《花山壁画》的创作是诗人一次深层次的精神之旅,在写作过程中他实现了与花山岩画生命的交融,黄神彪现如今依然生活在花山岩画文化场域之中,其创作有从民族文化中的营养吸收,有从自我探索中的开拓,有在时间的长河中长久的文化层累、积淀和传承,有对“我者”文化的自信自觉及责任使命担当。
(三)由外而内与由内而外的影响之异
花山岩画对杨克的影响是由外而内的,具有偶然性、碰撞性和情感性,花山岩画开启了杨克的诗性智慧。偶然性是指杨克“走向花山”的行为是受到各种外在因素机缘巧合的作用,是具有偶然性的;碰撞性是指他在欣赏了花山岩画后剧烈的文化碰撞激发了他的诗性智慧,带给他极大的灵感刺激,形成一种文化上的碰撞和补充。情感性是指花山岩画对杨克的影响主要是视觉上的和情感上的,远未进入到民族意识和精神灵魂的内核,因此,他的诗歌表现是激情喷发的浪漫主义式的。对于杨克本人来说,以这首诗歌为发轫和契机他“走向花山”,主动融入花山文化圈获取艺术的滋养,寻求到灵魂的抚慰与归宿,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动向,一种主动的身份上的靠拢,呈现了对花山文化的独特理解,大胆使用花山岩画图像,与诗歌文字互文对应,其诗歌语言充满激情、野性和古拙之美,在诗性思维方面新颖而超前,以此为始进而开拓出红水河系列诗歌,找到自己诗歌的图腾,为后来的诗歌写作奠定下浑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以此诗实践了“百越境界”的理论构想,唤起了广西文学的理论自觉。
花山岩画对黄神彪的影响是由内而外的,具有原生性、层累性和深层性,体现了“我者”的使命。原生性是指花山岩画对他的影响是持续的、渗透的、根深蒂固的;层累性是指他继承了世代祖先的集体文化记忆;深层性是指花山岩画对他的影响是直接作用于精神和灵魂的深处,这种影响由来已久,当主体产生要创作花山岩画史诗作品的文化自觉时,这种文化因子被激活继而产生了由内而外的诗歌表现,因此,他将花山岩画与历史文化进行全面、深层、立体的而非泛泛、表层、单一的关联。
从杨克的《走向花山》中我们能感受到情感的激荡,从黄神彪的《花山壁画》中我们能感受到精神求索的艰辛。《花山壁画》发表后,黄神彪在北京召开的黄神彪作品讨论会,著名壮学家梁庭望认为:“诗人没有一味地追溯历史, 而是把历史与现实结合在一起, 表现了壮民族对现代化的呼唤”。[9]20
四、结语
综上所述,杨克的《走向花山》与黄神彪的《花山壁画》在“他者”与“我者”不同的身份视角下具有内容、写作方法、诗歌风格、文化远近、影响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杨克主动融入式的写作是尝试为广西文学找寻文化之根,为广西文学代言,他主动把自己融入了广西、融入花山,他的《走向花山》充满文化碰撞下的激情高昂,具有民族地域文化因素;黄神彪创作《花山壁画》是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充满民族历史的沉重与自豪,可以称之为壮民族散文史诗。二者都认为花山岩画对于广西民族文学具有“文化之根”的意义,是对花山岩画文化意义的肯定,同时也是对花山岩画核心精神的开掘和传承,对后申遗时期的花山文学创作具有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克.杨克诗歌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2] 温远辉.涉过红河到达人生的大水边写意—记青年诗人杨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3).
[3] 陆艳梅,陆观荣.花山圆梦 文学归乡——2016·第二届花山文学论坛实录[OL].http://www.huashanzimin.com/article-19-1.html,2016-7-27/2017-10-23.
[4] 2017年12月13日在南宁市对散文诗《花山壁画》作者黄神彪进行访谈的记录.
[5] 黄神彪.花山壁画[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
[6] 黄神彪.面对光芒禁果——献给我的桑妮[M].散文诗,2002(01).
[7] 黄神彪.花山壁画[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17.
[8] 杨克.那一年,我们走向花山[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30cd80102wjp9.html,2016-03-30 /2017-10-23.
[9] 晓赫.黄神彪作品讨论会在京召开[J].民族文学研究,19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