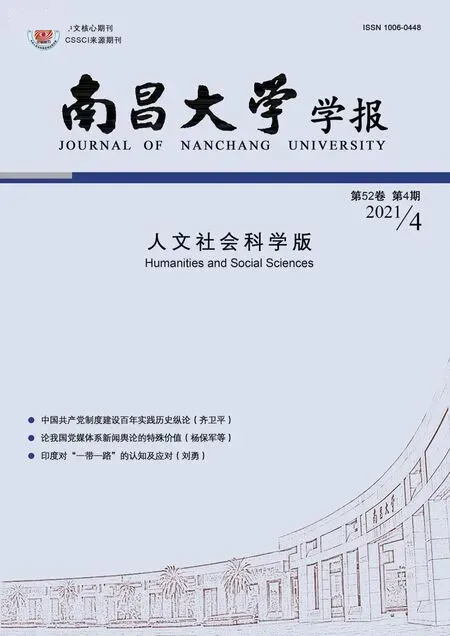行权:儒家执经的最高境界
——公羊学视野中“权”的字源考辨与意义阐发
唐 艳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经权观念是公羊家哲学的重要话题,自孔子开始,儒家对经、权问题的讨论就从没间断过。从先秦至明清,“权”始终伴随着“经”而被赋予各种各样的伦理规定与道德涵义,今人已逐渐读丢了“权”最初的文字本义与精神指归。纵览《说文》《玉篇》《广雅》《广韵》《集韵》等字书,“权”字之训释几乎不离“称锤”“反常”“反经”等字眼,追溯其形、音、义,权本为一种名为黄花或黄英的木属植物,进而由木引申为称锤,由称锤演变为“反经”“反常”,再被诠释出“反经为善”“反经合道”等学说,其从生物科学概念转化为哲学范畴必然经历极其微妙的发展流变过程。再细究先秦儒家经典及其历代注疏,“权”字亦多取称锤、反经、反常等引申意,而不常显露其本义。以董仲舒、何休、陈立等为代表的公羊家尤其关注儒家之权变观念。鲁桓公十一年,《春秋》经曰“宋人执祭仲”,《公羊传》曰“反经而后有善”,权虽违背经之规定,但最终以善为归宿。“行权有道”[1](P63),经有经道,权有权道,掌握了权的特质、原理、法则、规定才有行权的资格。有学者讥公羊家为“诈权”,陈柱批评此为“不善读书之过”[2](P115)。忽略了权由木衍生出的一系列涵义及其内在关联,造成了“权”的字源本义被悬置、架空,致使后人解读文本时偏离权之原初意旨,对于经权问题的义理讨论也不彻底、不深刻,缺乏充实饱满的学理养分。即便我们掌握了经、权的“形式意义”,仍然无法阐明儒家经、权之“实质意义”[3](P8)。宋代陈淳认为权字取义于称锤,因“权轻重以取平”[4](P51)而得名。张岱年提出儒家权变之权是“衡量轻重而随机应变”[5](P209)。至于为何权取称之名,二者之间有什么关联,还有待论证,弄清“称”与“权”之间的关联性、过渡性的意义转换有利于填补二者在语用学上存在的鸿沟。林义正提出“善统经权”[6](P170)的观点,而行权与儒家的道、善、仁、义之间还有丰富、复杂、多元的解释向度与发挥空间,仍值得进一步研判和探讨。
一、权从木如何引申出称锤?

权从一种普通的木属植物升格为量器,并且权与称二字并无明显形、声、义方面之字源关联,欲澄清二者关系,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方面,以“权”之木性特点加以想象推断。权很可能是一种木性较为特殊的植物,具有材质坚硬,结构致密,木性稳定,不易变形,光滑耐磨,韧性强等特征,古人用其制作称杆、锤柄、拄杖、农具等,或者雕刻工艺之类。其中,作为衡器使用的情况最为普遍、常见,久而久之,权的其他功能逐渐淡化,权木便演变为称的代名词或专有词,后再被引申为衡器、称量、轻重,便也不足为奇。《孟子·梁惠王上》曰:“权,然后知轻重。”赵岐注曰:“权,铨衡也。”[13](P23)荀子曰“欲恶取舍之权”[14](P51),“不权轻重”[14](P74),即权乃得知物体轻重之前提与基础,若不以器物或人心去权量,物体本身只是它自身,无所谓轻重可言。故尹知章注《管子》“权修”曰:“权,所以知轻重也。”[15](P1165)程颐甚至说:“权只是称锤,称量轻重。”[16](P234)可见轻重乃权之内在属性与核心规定,分清轻重是行权的基本要求,故《墨子·大取》曰:“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孙诒让引《文选·运命论》李善注引《尸子》曰:“圣人权福则取重,权祸则取轻。”[17](P404)权之祸福取决于事情的轻重,取重者能抓住重点、紧扣要害,而取轻者则舍本逐末、因小失大,二者的行为后果自然不同。另一方面,从“称”之本意出发,称以平衡原理量物体之轻重,那么,权、称互训,意味着权作为一种木,不仅符合称在功能上的操作需求,还具有某种因称而引申出来的一系列表现特征。古人擅长以物达义、借物显道,这种极富中国性情特征的认知方式将称的平衡、轻重、权量等特征又反向赋予了权字,进而充实和丰富权之义界。
权自从有了称之属性与功能,便衍生出了一系列与称相关的涵义,其中最有趣的是,以权指代称之重要组件“锤”。《宋本玉篇》《全韵玉篇》中,权皆作“称锤”。《孟子·离娄上》曰:“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朱熹将“权”直接解为“称锤”[18](P265)。权从称演变为“锤”,其内涵更加概括、具体、分化。在诸多典籍中,权与锤甚至可以互训,如《广雅·释器》曰“锤谓之权”,《吕氏春秋·仲春纪》曰“角斗桶,正权概”,高诱注曰“称锤曰权”[19](P28),权、锤二字在特定的语境中可相互替代使用。

可见,平衡是锤与权在涵义上之共通点,以“称”“称锤”衍生出的相关概念为基点,权之内涵又进一步扩大。如“平”“衡”“重”“量”“正”均能直接或间接与权字相关,且无论从何种角度诠释,均能说得通。在实际称物过程中,权也被视作具体的重量单位,《汉书·律历志上》曰:“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权者,铢、两、斤、钧、石。”[23](P900-901)权主轻重,衡主均平,无权不衡,无衡不权,二者相互作用。颜师古注曰:“权谓斤两也。量,斗斛也。”[23](P890)孟康曰:“权、衡、量,三等为参。”[23](P901)《礼记·月令》中也有“同度量,平权衡”[24](P327)的说法。可见,权、衡、量之间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三者只有保持高度同步、统一、谐和,称物之事方可圆满成功。
二、权有变,尊经而不乱
权无论作为称或锤,在称量过程中都必须时刻进行调节变化,否则权就无法完成衡量物体轻重的实践活动,更不可能实现其自身的真正价值,故权最重要的特征是因事、因物、因时、因情、因地而变化。《周易》较早提出行权之说,《系辞下》曰“巽以行权”,高亨注曰“《巽》是退让”,“退让者称而隐,乃行其一时之计也”[25](P438-439)。《巽》卦有根据具体情境而灵活调节的品质。《说卦传》曰“巽为风”,“为不果”,来知德解曰:“气之善入者莫如风,故无物不被。”“风行无常,故进退。风或东或西,或不果。”[26](P363)《巽》卦取象风之灵动、柔和、轻盈的易变特性,有巽德之人自然不会固执己见、死守教条。《孟氏逸象》中巽“为进”“为退”[27](P22),即个体面对事情时进退有度、收放自如,能够把握好现实情境与社会法则之间的张力。《彖》辞曰“柔皆顺乎刚”,《象》辞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26](P262)可见,在特殊情境中能顺势而为、以柔为贵、通时达变是君子行事的一种高尚美德与超凡境界。
在诸多典籍中,以“变”释“权”的现象极为常见。《后汉书·崔寔传》曰“故圣人执权”,李贤注曰:“权,谓变也。”[28](P1 726-1 727)权可直训为变,二者涵义相通。鲍彪、朱右曾、阮逸等在校释、注解中皆以“变”训“权”。但这并非就意味着权、变二字无所区分。变,指变易、变动、变更,是描述事物运动状态之词。《说文》曰:“变,更也。”《小尔雅》曰:“变,易也。”《礼记·檀弓上》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郑玄注曰:“变,动也。”[24](P117)变可指“现象学上事物存在的非正常状态、突发事件或异常情况”,亦可指“方法论上能够引起物事情形发生更改或变易的行为活动”[29](P273)。而权特指非常情况下所采取的特殊对策或临时性、应急性的措施,旨在因时制宜、因情制宜。孔颖达《周易正义》曰:“能顺时合宜,故可以权行也,若不顺时制变,不可以行权也。”[30](P173)无变不行权,变是行权的前提与基础,二者基本内涵有重合交叉之处,但不能完全等同。
权以变为特征,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度、无节制、无底线地变,而是有原则、有境界、有高度、有追求地变。权,从操作层面而言,是以进退之变以衡量物之轻重;而对具体事件而言,则抽象为变通以别轻重、缓急、利弊之分,旨在解决社会情境中的矛盾与冲突。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九》曰“权现”,注引贾逵注《国语》曰“通变以应时曰权”[15](P1 165),权并非是一种既定的规范或要求,而是一种灵活变通的智慧。北齐刘昼在《刘子》中说:“循理守常曰道,临危制变曰权,权之为称,譬犹权衡也,衡者测邪正之形,权者揆轻重之势,量有轻重,则形之于衡。”[31](P52)权是在紧急关头使用的应急之策,行权需多视角、多纬度考量得失,这与称量物体时进退变化的道理是相通的,不可过多,不可过少,两端平衡方可为正。这就需要行权者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应变能力、评估能力、统筹能力,顾此失彼,取小舍大,必然会不平衡、不和谐,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在儒家看来,行权的首要原则仍然是经,遵经而行权,有经才有权,若无视经、背离经,权连存在的理由都没有,更不可能有行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春秋繁露·玉英》将权解为“谲也”[32](P21),《经义述闻》中谲也可训为权(3)《说文》曰:“谲,诈也。”谲训“诈”则为恶德,训“权”则为美德。参见王引之撰,虞万里主编:《经义述闻·通说上·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 880页。。《文选·张衡〈东京赋〉》曰“合二九而成谲”,薛综注曰:“谲,变也。”[15](P2 149)谲、权皆以变通为要。但相比谲,权之内涵与外延更为具体、专一、明确,这是由权之衡量轻重、平衡得失之本义所决定的。权之变化最终要“归之以奉钜经”,苏舆注曰:“权虽谲,仍以正归之,取其不失大经耳。”[33](P77)钜经、大经仍是经,权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搏斗、矛盾抵触、道德权衡之后的更高级的经,其是处于常经之上而超越常经的一种具有灵活性、挑战性、创新性的经。常经与变经最根本的道德要求与精神旨归是一致的。权所变的只不过是外在的形式和方法,而不可能动摇儒家伦理纲常与礼乐教化的宗旨大道,故而有“变而反道”[33](P265)“前枉而后义”[33](P57)之说。经与权都是行为选择时的思考活动,经者只看其一,而权者必须综合考量。若将执经视为文明向善之平坦大道,则行权好比遇阻而绕路行走的必然抉择,换条路走,心中要有定力、有方向、有信念、有勇气,兜一圈还必须回到大道上来,人心才能安定,行为才能有着落,否则越跑越远,迷失方向,便会违背或扭曲做人之正道,行权毋宁是尊经的一种高级方式。
无论行权如何变化,均不可能脱离权字“称”“锤”“衡量”的原初本意。当权解为“称”或“称锤”时,无论它称量何物,标准都是轻重,而不可能是大小、高矮、胖瘦或其他。称大象得大象之重,称石头得石头之重,称树木得树木之重。权考试得考试之重;权人品得人品之重;权人生得人生之重,等等。无论是权之本义或引申义,其内涵都十分简单纯粹,即辨别、衡量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问题。随着权在人们生活与精神世界中的价值发挥与意义赋予,其逐渐被注入了政治、历史、文化、道德、伦理等丰富的精神内涵,但其最为根本的“平衡”特质却从未丢失,也不能丢失。《汉书·律历志上》曰:“权与物均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23](P900)万事万物均离不开权衡之道,有权才有衡,有衡才有正,有正才有道。《荀子·礼论》曰:“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悬矣,则不可欺以轻重”“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14](P347)有绳墨则曲直自明,有平衡则轻重自明,绳不畏直,衡不忧平,此乃颠覆不破之定律。权若不平衡,则不可以谓之权,而平、衡本身就昭示了经所强调的中庸之道。权以衡为贵,故需左右进退而求其均和,万物至衡,和谐有序,则与天地共美而不殆;衡以权为媒,无权则轻重不明,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厚或薄,难以成其中和,故权、衡须臾不离。
三、权反经的限度与追求
称物有标准,权变有限度,权而有衡,衡而有平,平而有和,和而有善。按此逻辑推理,权是由一系列互相交融的概念共同作用而构成的复杂范畴,但任何一个行权者都不能满足并停止于这些概念本身。行权者必须抓住权之原初含义,将自己想象成“一杆称”,称从失衡调整到平衡,总有多少、进退、尺度的来回变化,人欲走出两难困境,必然要经历各方取舍、考量、判断等一系列复杂的理性审视与行为选择,方可达到平衡。这是权字的第一要义,也是我们解读经权问题的初心。而行权坚守的“平衡”与执经是否统一?其所追求的道德底线与精神归宿是什么?
权之义界多为“反经”“反常”。《全韵玉篇》作“反经”,《说文》作“反常”,《后汉书·周章传》曰:“权也者,反常者也。”[28](P1158)从字面上看,权与经、常之间似乎是一种对立、矛盾、相背的关系。因而欲进一步理解权,还得清楚经的涵义。《说文》曰:“经,织也。”《玉篇》曰:“经纬以成缯帛也。”经,原指织物纵向之线,引申为绝对、普遍之规定、法则。《广雅·释诂》曰:“经,常也。”[20](P38)常,《玉篇》曰“恒也”,《正韵》曰“久也”,恒久不变即为常,反常即为变,权、变互通,故又以“反常”训“权”。对于权“反经”之解释,学界或解为“归返”,或解为“背反”,而就经、常与权、变的内在关联而言,还不足以构成相反或对立的关系,甚至经、权之间并无本质性的差别。但是,在没有更好的说法出现之前,也只能通过“反经(常)”来解释权。否则要么陷入陆贽的“狭隘论”(4)陆贽《论替换李·楚琳状》曰:“以反道为权,以任数为智,君上行之必失众,臣下用之必陷身,历代之所以多丧乱而长奸邪,由此误也。”陆贽把权与经直接对立起来,并将其解读为祸乱之术,看到了经、权的差异性,却忽略了二者的统一性。,要么陷入程朱的“同一论”(5)程朱往往消解了经权之区别。程子曰:“权只是经所不及者,权量轻重,使之合义,才合义,便是经也。今人说权不是经,便是经也。”见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4页。程子把权直接解为经,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了。相比程颐“权即是经”的观念,朱熹看到了经、权之间的差异,认为经、权中央应有个界线,主张“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并视经为“道之常”,权为“道之变”,这也是朱熹“理一分殊”思想在经权问题上的投射。引文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884-885页。。故孟子将“执一”“执中无权”均视为“贼道”(6)《孟子·尽心上》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杨子过于利己,无天下情怀;墨子太过无我,忽视人欲;子莫执中而不知权变,与“执一”无异,此皆为不知权,权不该被教条化、刻板化、极端化。引文见十三经注疏,赵岐,孙奭:《重刊宋本孟子注疏附校勘记·尽心章句上》(影印本),台北:艺文印书馆,2013年,第239页上。。“权”乃活泼泼之变术,人用心量衡,取义审度,通时达变,切不可死守一端。从方法论上看,权可能走出与经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路子,确实有反经倾向。但从根本上讲,权不脱离经,经也离不开权,二者之目的皆在尽可能减少事情所产生的伤害、矛盾或冲突,使事件朝着更加符合人之为人的良好道德方向上发展。
首先,反经有善。权虽不服从于经,甚至超越经之规定,但其行为结果却是向善的。桓公十一年,《公羊传》曰:“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宋庄公诱迫祭仲“出忽立突”,祭仲若不从其言,则可能国灭君亡,性命难保;若从其言,则可保国存君。祭仲最终选择以存国之大局为重,暂从宋公之言“出忽而立突”,公羊家嘉美其有权贤。“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当实施权变是避免死亡的唯一选择时,就必须背经行权,否则人亡国灭,何以言善?何休《解诂》将祭仲与伊尹放逐太甲于桐宫而终成大业之权变相媲美,“前虽有逐君之负,后有安天下之功”[34](P174-175),祭仲存郑之功大于忠君之功。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考虑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一国之利必然大于一人之利,祭仲宁愿自己背负逐君之恶,也要先保国,舍身救郑,牺牲小我以救大我,故谓之有善。《孟子·离娄上》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赵岐注曰:“权者,反经而善也。”在危及生命的紧急关头,根本来不及、也顾不上那一套男女有别的礼法规定,面对嫂溺的突发情景,人人皆当猝然相救,急不暇虑,保护生命最重要。“嫂溺不援,是豺狼也”[13](P134-135),嫂溺即亡,刻不容缓,还继续死守人伦、纠缠礼法之人,岂不是狼心狗肺、见死不救,与禽兽何异?故受本能的“不忍人之心”所驱动而行权亦可为善。面对“嫂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13](P65)的紧急关头,必先以救人为大。礼法在特殊危难时刻之效能是缺失的、空白的,此时不得不由人心来定夺。在此刹那间,人自然发动“恻隐之心”,根本来不及思虑合不合法、背不背礼、丢不丢人等问题。而行为结果是不是善,则取决于人之为人的内在良心与本能善性。
其次,反经合道。“许多哲学家都承认‘道’是居于最高地位的、独立无对的哲学范畴。”[35](P107)《春秋公羊传》作者、董仲舒、何晏、《刘子》作者等人均提倡“反经合道”之说[36](P23)。《周易·系辞下》曰:“巽以行权。”韩康伯注曰:“权,反经而合道。”[30](P173)权违背经,但最终却能够返回到儒家的基本要求与根本宗旨。儒家的经就是道,道就是经,在不同的权变案例当中,道又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面向与伦理品质,如祭仲执权存国有义;嫂溺援之以手是有“不忍人之心”;鲁宣公十五年,楚国司马子反闻宋国已“易子而食之,析骸以炊之”[34](676)的惨状而劝楚庄王停战是有仁。除此之外,忠、恕、孝、信等都可能是儒家道的体现。故“反经合道”只有放在具体的道德情景与伦理冲突当中才能彰显出其理论意义。
最后,反经取义。在孔门儒学看来,当义、利发生冲突时,个体当毫不犹豫选择义、舍去利,故《论语·宪问》曰:“义,然后取。”[11](P125)义是一切道德动机与行为实践的出发点、根本点。《孟子·公孙丑上》曰“配义与道”[13](P55),“义”是做人的底线和原则,行权必须合于义才能有道。日本重泽俊郎引《春秋繁露·竹林》曰:“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37](P13)凡事以“义”贯之,虽刚开始违背义,但最终能回归义,把义作为长远标目、终极收口而行权,即使失败,《春秋》亦会嘉善之。祭仲与逄丑父同样都是舍身救君,逄丑父以“李代桃僵”之计欺骗晋人,保住了齐顷公的性命,背信无义,使国君蒙辱,“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32](P17),虽然开始的行为动机是保护国君,但却目光短浅,不够睿智,缺乏义气,以诈得生,行为本身就不能善终,背离了权变之本,故《春秋》不美。权变之策最终以义为支撑才能有底气、经得起考验,从而站得高、走得稳、行得正。
权虽“反经”“反常”,但却不离善、道、仁、义,甚至在本质上就没有背叛过经,而是执经以行权。“反经—行权—反经”是行权的基本运作模式,权始终在经的域限当中发挥自身的变通价值与灵动特性,第二个经比第一个经更深刻、更内在、更根本、更高尚,进一步凸显了权之所以“反经”的重要意义。“权实际上保证了经之宗旨的真正落实”[21](P48),个体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行权,最终都是在追求一种向善的、美好的、平衡的生存状态,努力在不同情景中实现把人当人、把物当物、把事当事的道德理想,形成一种谐和、宁静、自然、融洽的关系结构与伦理秩序,这也是“权”之本意所在。
四、行权最难与“圣人之大用”
权与经在儒家的道德诉求与精神归宿上有内在可通约性与一致性,但无论从技术上、道德上,还是风险上,行权都比执经困难、复杂、危险得多。传世文献《春秋繁露·玉英》中认为,经礼可让人“安性平心”,执行起来有据可依,相对简单直接。而变礼则“无以易之”[32](P20),没有固定法则可循,必须全面统筹,综合判断,考验个体的应变能力。苏舆引《礼记·丧服四制》曰:“有恩有礼,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礼、节,经也。权,制则变也。”[33](P72)而相对于恩、礼、节之经,权所占之比例虽少,但却非常重要。人之生活情境变化无常,社会纷繁复杂,无奇不有,经不可能全尽,必须通过行权去解决那些突发的、特殊的、涉及多方利益考量的伦理冲突与道德困境。因而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简单、安全、高效的经礼,而不愿去突破、挑战变礼。成功行权之人,都有着高尚的道德修养和高瞻远瞩的处世智慧。《孟子·尽心下》曰:“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13](P263)对于治理庶民,经礼最有效。而真正的君子能够超越经礼、跳出固定思维,引发内心的道德自觉与人性光辉,不拘泥于礼法教条,随心所向而不越矩,这才是行权的魅力所在。
经、权在形成过程与工夫修炼上大不相同,其内在的发生机理为:经,事件—经—谐和—中庸—善(仁义)—道—事件;权,事件—经—权—平衡(轻重、缓急、大小)—和谐—中庸—善(仁义)—道—事件。根据经先权后、经易权难的原则,人们遇到问题往往首先从经出发予以解决,若经行不通则返回事件本身再考虑行权。执经、行权都以某一事件为出发点,其共同目标皆是使事件能够在具体情景中被妥善处置,因而“和谐”是二者的第一个交汇点。只不过行权要考虑事情的轻重缓急、平衡各方因素,而执经按部就班即可。通过执经或行权使得事情保持和谐的状态,在儒家看来就是遵守中庸之道,使事情得其所宜,进而选择一种向善的生存方式,最终归于儒家的仁道大本。从事物的内在发展关系上看,经、权皆以“事件”为出发点,以“道”归宿点,二者均属于事件的处理范畴,经本身就是原则、常规,其与道的要求相统一,执经就是守道而为;权则是灵活应对,其与道的基本规范不一致,行权是变化,是归道而行。无论是执经还是行权,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不违背儒家的道,而道本身就是经。故朱熹将“经”“权”与“道”形象地比喻为“称得平,不可增加些子,是‘经’;到得物重衡昂,移退是‘权’;依旧得平,便是‘合道’。故反经亦须合道也”[38](P988)。经乃斤两准确而平衡,权乃斤两不准确而通过移动称砣而达到平衡,此平衡与彼平衡难道有本质上的背离之义吗?
权比经的路径更复杂,考虑的因素更多,且难度大,风险大,要求严,境界高。行权必须从一定的社会情境中抽离出诸多因素进行全方位考虑、分析、判断和比对,如从大小、缓急、轻重、得失、优劣、利弊等不同维度来衡量执经与行权的代价与结果,以一种创新灵活的方式来平衡当下的道德困境或伦理冲突,尽可能减少其对生命的伤害、对道义的破坏、对良心的背叛。行权者必须有大视野、大格局、大智慧,在反经的同时又能巧妙地回归到经。因而,在实际生活中行权比守经要难。《论语·子罕》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知识学问、实践大道、人格建树,皆率礼法而为之,而权却无特定内容可依,必须及时跳出条条框框的约束,迎接挑战,敢于突破,一般人很难做到。邢昺疏曰:“人虽能有所立,未必能随时变通权量其轻重之极。”[11](P81)权之所以难,因其没有统一的参照标准和先例示范,全靠个体的主观自觉与道德修养,常人行权极易出现走极端、舍本逐末、惜指失掌等问题。《春秋繁露·玉英》曰:“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董天工《笺》曰:“适权,应变权衡。”[39](P46)无论面对何种情境,人都要分清轻重缓急,掂量利弊得失,保持通透、理性、应变之心境,不被复杂情势、困境所迷惑、误导,游刃有余,拿得起放得下,方可真正做到“适权”。“如果固守已成的见解而不进行积极的探索,就会陷于‘昏昧’的困境”[40](P19),人自然也难以通时达变以行权。相比于执经,行权虽十分困难,但其所得到善、道、义一定要更多、更大、更深刻,否则行权将毫无意义。
基于经、权的发生机理,执经与行权的第一个交合点是和谐,而和谐只是一种状态,将其上升到道德与精神层面则为更高层级的中庸、善、道。“中庸”是儒家最理想的道德法则与人格要求,故权与经皆守中庸之道。而权之中庸源自其本意(称或称锤)中的平衡之道,称不中则不平,不平则不衡,不衡则不权,故保持中庸之道也是权的应有之意。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11](P55),中庸之道以德为本,德行越高,就越接近中庸,越有能力行权。能够主动行权之人,必定善于用中庸之道去调节任何复杂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作出明智的抉择。《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本身就是一种生生的、活泼的、发展的、持续的、美好的、向善的生命势态,行权亦当选择更有利于长远进步或更大利益的方向。“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行权到底是善还是恶,无法以确切的道德准则来衡量,儒家便以一种内在的、抽象的、高尚的中庸之道来引导、鼓励和强化人们,中庸则善,反中庸则不善。朱熹曰:“此行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18](P20-22)即事情做得合乎其宜、恰到好处就是合乎中庸,符合中庸之道,便是选择了一种趋善的生活方式,最终必将归于儒家的仁道理想。“为了法则的必然性,当然需要以理性作为关注重心”[41](P27),经、权皆起于事件、归于事件,而以经、权处理过的人、事、物,已从一种矛盾的现实状态转变为一种美好的理性诉求,其被注入了儒家的人伦精神与道德养分。事件本身也从一种现象描述升格为了一种人道诉求,其一定是比原来未有经、权介入的状态更接近于儒家对人的要求与规定,否则经、权一定是失败的或无效的。
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权都不曾与经分离,而且行权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透,做得更妙,可以说是执经的最高境界。明代高拱在《问辨录》中以“圆”“通”来形容行权之道:“夫权也者,圆而通者也。是圣人之事,而学之仪的也。圣人圆,而学圣人者以方,始而方可也,终而愈方焉,则遂失其圆也。圣人通,而学圣人者以一隅,始而一隅可也,终而止一隅焉,则遂失其通也。夫学不至于圣人,非成也;不能权,非圣人也;非圆非通,不可以与权也。”[42](P151)“圆”“通”都是极其高尚、灵活、通透、精深的处事境界,只有圣人才能够掌握这种通时达变、巧妙脱俗的处事智慧。行权毋宁是一种处世哲学、政治智慧、审美情操,有谋略,有格局,有边际,有境界,非常人所能为之。《论语·子罕》曰:“可与立,未可与权。”朱熹引洪氏曰:“权者,圣人之大用。”[18](P110)权立足于经又高于经,乃做人之高超境界,堪比一门艺术,若无一番修炼工夫,难以有此觉悟。
五、结语
权字从一个木属植物的生物学概念延伸至伦理学、社会学、哲学范畴,最终成为个体为人处事的一种生存法则与道德境界。人们不断地将自身的意志、想法赋予权,因而才催生出一系列本不属于权自身的价值观念与人伦诉求,使得权越来越脱离它自身的内在规定性而异化为一种无根无据的语词概念。人们使用权时必须先弄清楚它的原初本义,而后推而广之,使其根基牢固,原理充实,不至于牵强附会。古人对权字的诠释与发挥不可能抛开其文字源头,任何一种附加于权身上的观念,都有与其相对应的事物原型或实践根据。权能反经因其变化之性,权守中庸因其平衡之本,权可为善因其中和之理,权之有道因其不离自性。因而追溯字源的解读思路,不仅澄清了权之本真面貌,又挖掘了权背后的历史文化蕴意。但是,从哲学角度分析,“权”字本身就不真实,不存在,对其进行的一系列意义建构,只不过是用其来满足人们在现象世界中生存的精神文化需求,即便回归到权最初的原生态含义,也不可能完全把权的社会意义消解掉,只能在适应人伦诉求的基础上尽可能存留或接近权之本真,净化文字本源,保护文化初心。
——基于SZH的案例研究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