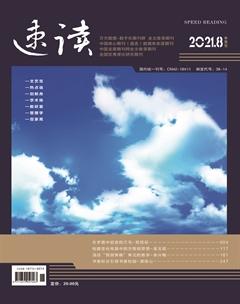同是“悄悄”与“轻轻”各有滋味在心头
《再别康桥》与《荷塘月色》都是作者的代表性篇目,都以极其细腻的手法再现了作者的内心情感,有趣的是这两篇诗文都以“轻轻”“悄悄”为开头或结尾来结构全篇,用惊人的相似的形式再现了各自细腻的心理。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第一节连用三个“轻轻”,实写只身来到和离开康桥时的情景,并且以轻微跳跃的节奏,衬托出缓步飘然而去的形象,给全诗定下了抒情的基调。由于诗人对康桥的无限依恋,百般珍惜,不愿其心目中完美的形象受到人为的损伤,不愿其纯洁受半点污染,不愿这种独自享用的心境和氛围被破坏,故诗人先以“轻轻的我走了”开篇,后写“悄悄的我走了”告别。“轻轻”“悄悄”,透露出诗人对康桥难分难舍的离情。在节奏上,“轻轻”与“悄悄”的反复使用,增强了诗歌节奏的轻盈感,同时又用看似轻松的词语将那股热烈的情绪包孕在诗的内层,首尾同中有异,遥相呼应。更显柔美婉约。
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即景抒情,借那輕纱般薄雾掩笼罩下的荷塘景色,反映他当时微妙的心思。他要无牵无挂独自受用无边的荷塘月色,就是要摆脱“心里颇不宁静”的现状,而追求难得的片刻安宁。因为有这种情绪和心理要求,开头作者“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在荷塘里作者所看到的景色全是一派宁谧:“花是零星的,香是缕缕的,风是微微的,月是淡淡的”,作者一路写景也一路抒情,随着景象描写的展开,全文描绘了一幅宁静的荷塘月色图,即使是畅游荷塘结束了,那份独特的清静氛围作者也依然不忍怕破坏,故而“轻轻地推门进去”轻轻与悄悄既写出了作者的心境也透露出作者为创设宁静环境而刻意做出的努力。
轻轻与悄悄既相近又不同,相近在都表现出了一种“静”的状态。不同在“轻轻”即“轻手轻脚”,指动作行为很轻,是人的主观努力的结果,即尽量不弄出声响;而“悄悄”指没有声音或声音很低。可见,“轻轻”重点指人的动作,而“悄悄”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环境状态。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徐志摩在《再别康桥》里使用这两个词所表现的心理状态了。1920年9月,徐志摩由美国前往英国,想成为罗素的弟子,但徐志摩到达时,罗素因思想激进已被剑桥的三一学院解聘,离开了康桥,徐志摩寻梦不成,于是在康桥当了一年的自由自在的旁听生,度过一年美好的时光,匆匆离别时也不愿惊动别人,甚至是康桥这个“故人”。以“轻轻”开头,既可理解为不愿把寻梦之事说出,也可理解为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处境和复杂的心情。而结尾诗人变“轻轻”为“悄悄”则写出了诗人情绪的变化,“悄悄”满含寂寞之意, 体现诗人由写主观对动作的控制,转而从客观环境方面来创设意境。诗人将自己多年对母校的感情,浓缩在凝练的诗句中,几声淡淡哀愁的笙箫,反衬出了的环境的寂静,而沉默的夏虫,沉默的康桥,更与“悄悄”相应,共同塑造了一个梦幻般的惆怅氛围。可见《再别康桥》这首诗以“轻轻”开头以“悄悄”结尾前后呼应妙合无痕地表现了诗人欲离不舍、欲留不能的留恋与怅惘。
朱自清在写作《荷塘月色》时心境可以说是复杂的,他的夫人陈竹隐在《忆佩弦》一文中说,“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统治了全国佩弦当时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四顾茫然,‘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他又在苦闷彷徨了。他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在当时,他两条路都没有走,而是采取了逃避的办法……”
以上是陈竹隐的对朱自清的解读,陈是不是自己丈夫的知音?这恐怕要打个问号的。按理说,一个人的苦闷应找自己最亲的人排遣,但朱自清却没有,相反,他以悄悄的动作出去,以轻轻的动作进来,他的来没有惊动他妻子的睡眠。因此,作者以“悄悄”开篇以“轻轻”结尾也反映了他内心的苦闷无以排遣的状况,也是连亲人都无法理解,也许是不愿给亲人添堵,总之,他只一个人。
“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听不见了,妻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这三句交待了当时夜深人静的环境,“眠歌”用的是以有声衬无声的手法来塑造安静的氛围的,因此这里用“悄悄”恰与这个静的氛围相适应。正是这“悄悄”的氛围勾起作者希望能寻得片刻的安宁,释放长久积压在心头郁闷的想法。于是作者悄悄成行,走幽径、赏月色、闻荷香,神凝其间,魂染清爽,朦胧的月色、清淡的荷香、幽远的歌声无处不体现了他暂得的淡淡喜悦。这是与现实的苦恼截然不同的两个境界,他多么希望自己能长处其中远离尘嚣。然而超脱毕竟是短暂的,猛一抬头之间恍若隔世,已回到了现实,但这余韵犹在的超脱怎能让他割舍!连他自己也不忍心打破这让人心醉的幽静,故而推门也是“轻轻”的。
可见这里“悄悄地出”“轻轻地进”正体现了作者由现实到超脱,由超脱到回归的过程,其深深的忧愁,其努力想去营造的放松,都在这悄悄与轻轻的动作中不经意间尽情流出:“现实是永远的现实,超脱是超不了的刻意之为。”行文前后呼应,回味悠长。
作者简介
张长松,男,汉族,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正高级教师,教育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