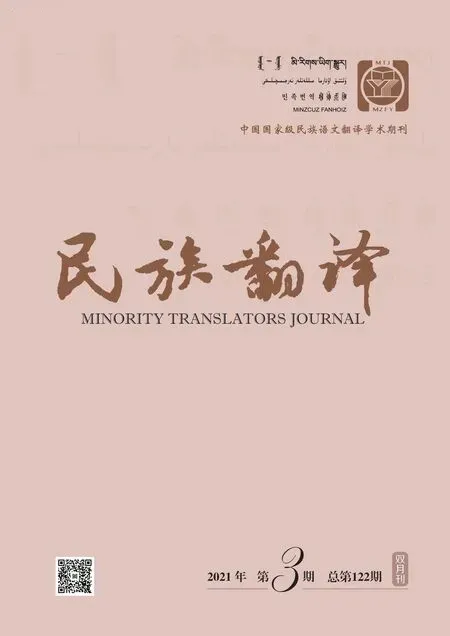民族志翻译的分类与距离刍议
——以黑格尔翻译中的中国形象为例
⊙ 孔艳坤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目前,将不同文化或民族的跨语际书写或翻译视为民族志翻译的研究已不鲜见,不少中国学者将苗族、彝族、羌族、壮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学翻译作品看作是民族志翻译来进行研究。比如,段峰以羌族文学为例研究民族志翻译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王治国以阿库乌雾的《凯欧蒂神迹》为例研究彝族诗歌的跨语际书写与民族志翻译。不过,中国学者中将他者对中国的描写视为民族志翻译的不多,但有不少将此类没有原文文本的书写回译视为“无本回译”。黑格尔关于中国的翻译并没有原文文本,是根据德文译文及之后的英文译文进行的一种民族志翻译,再被翻译为汉语就是一种回译。虽说有可参考的文本,但只能追根溯源到最初的德语文本,所以其实没有源语文本。目前,民族志翻译中这一类特殊现象尚未被关注。本文首先厘清民族志翻译的定义,对其进行初步分类,并基于此探讨各类民族志翻译中所涉及不同文化现象与实际情形之间的距离等问题。通过分析黑格尔翻译中关于中国的描写,探讨黑格尔眼中与中国行政体制、伦理规范、文化艺术和科学有关的中国形象,以及翻译中反映的误读、美化与丑化等问题。
一、关于民族志翻译的几个再定义:一种与无本回译的结合
民族志翻译概念衍生自民族志与翻译间的内在一致性,1954年由Casagrande首次提出。Casagrande强调民族志翻译将源语文化挪移至译语中,因而亦为文化翻译。[1]民族志翻译兼具翻译与民族志双重性,其实并不是一个独属于翻译研究的说法。民族志研究也留意民族志与翻译的内在关联。Robinson认为民族志自身将不同民族文化以其他语言展现的过程与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对照翻译虽不完全相同,但其内在具有翻译属性,只不过民族志的原文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文本,而是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2]这种文化即文本的观点之前也被Asad提出过。[3]
黑格尔的翻译依赖于西方传教士的资料,是基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进行的民族志翻译,或者说是在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固定原文情况下进行的翻译,其文本更多为西方传教士将所见或所感受到的中国文化相关内容翻译之后带回欧洲的关于中国的一些记载。由于没有固定原文文本,这样的翻译也就可以称作“无本翻译”,而“无本”指的就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源文本。这个说法受王宏印教授的“无本回译”概念启发而提出。
“无本回译”概念是从“无根回译”演变而来的。王宏印教授认为“无论是作为‘缺乏原译的回译’,还是作为‘异语写作的回译’,都不是绝对的‘无根回译’,毋宁说是‘无本回译’,即不是完全空无依傍、无中生有的回译过程。换言之,所谓‘无本回译’,充其量是缺乏文本根据的回译,但仍然有文化之根作为根基,而不是完全失去其根”。[4]2当“无本翻译”发生在记录或描写其他民族文化时,由于这种记录本身所具有与人类学中民族志类似的形式及内在属性,也就是一个外来的观察者对某种其他民族文化现象的见解及记录,则又可以看做是一种“无本民族志翻译”。
笔者认为,黑格尔所读到的西方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记载属于一种“无本民族志翻译”。因此,黑格尔首先是“无本民族志翻译”的读者,其阅读的是西方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记录和描写,所以黑格尔的翻译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编译。由于黑格尔的编译加入了很多个人阐释,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一种民族志翻译。但它又与其他民族志翻译不同,将西方传教士的“无本民族志翻译”视为原文文本的一部分,因而成了一种“有本民族志翻译”。这种“有本民族志翻译”中对其他民族文化现象的描写,距离实际情形隔了一层“无本民族志翻译”,是对“无本民族志翻译”的编译或者说再翻译,甚至因为又隔了一层可以看做是“民族志二次翻译”,或者说“民族志再翻译”。也就是说,西方传教士的“无本民族志翻译”,相当于是记录中国的一手资料。因此,黑格尔在其基础上进行的“民族志二次翻译”对于读者来讲也就是二手资料。如果黑格尔翻译作品的读者根据其译文内容再次对中国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和翻译,那么这就算是民族志二次翻译的再翻译,可以称为“民族志三次翻译”。这样的数字介入虽然能够清晰地标明所看到的民族志翻译是在第几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但并不利于将其界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因而建议在提及于“无本民族志翻译”基础之上进行的民族志翻译时,不管参考一手资料,还是参考二手资料,都无法界定为是在单一的第几手资料基础之上完成,因而也就无法单一地定义为“民族志二次翻译”或“民族志三次翻译”。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民族志再翻译”无疑是更加适合将其定义为“有本民族志翻译”基础之上进行的民族志翻译。同样,“有本民族志翻译”在参考“无本民族志翻译”之外,可能还参考了其他的“有本民族志翻译”。因此,不妨直接将“无本民族志翻译”以外的民族志翻译统称为“民族志再翻译”。虽然在定义上仅保留“无本民族志翻译”和“民族志再翻译”,但这并非否定“有本民族志翻译”“民族志二次翻译”等说法存在的必要性。在具体的讨论中,依然可以对后者的多种概念进行分析。本文为了引入回译的情景,首先对其他民族文化观察者的民族志翻译大致进行了分类,具体如下图1所示。虚线表示部分“民族志再翻译”可能没有直接参考其他民族文化的实际情形,而仅以“无本民族志翻译”为基础。

图1 关于民族志翻译的分类
二、各类民族志翻译涉及的距离问题
不难想象,“无本民族志翻译”中的描述与实际情形存在一定的距离,难以完全呈现原貌。依照常理推理,之后进行的“民族志再翻译”自然也与实际情形距离更远,其翻译与阐释可能与实际情形更加脱钩。不过,这种脱钩是不是必然会出现?民族志再翻译就一定比“无本民族志翻译”更加不真实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把情形设置得更加复杂一些,再引入到上述的回译情景之中。“民族志再翻译”已经离实际情形很远,源文化国家的译者用源语言再进行翻译时,就成为了“民族志再翻译”的回译。单从逻辑上来讲,这种与“无本民族志翻译”的译者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形已经隔了三层。那么,“民族志再翻译回译”所包含的内容应该与源文化的实际情形会相差更多。然而,果真如此吗?另外,通过对比“民族志再翻译”的回译与源文化国家当时的实际情形又会发现哪些异同呢?这些异同点又能否为文化翻译带来某种启示呢?
如图2所示,直观上来讲,经由三次翻译的传递,“民族志再翻译的回译”之前的过程中每进行一次翻译都会让其与实际情形的距离更加遥远。所以分别用图2中的L1、L2和L3表示“无本民族志翻译”“民族志再翻译”“民族志再翻译”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实际情形之间存在的距离,应当是L1 图2 各类民族志翻译的距离图示 黑格尔的民族志再翻译回译中的中国形象主要涉及中国的行政体制、伦理规范、文化艺术和科学4个方面。由于黑格尔对中国没有直接了解,民族志再翻译回译与中国文化的实际情形之间所隔着的距离就不能通过黑格尔对中国的了解被有效缩短,黑格尔眼中的中国形象在上述4个方面存在很多或是丑化,或是美化中国情形的地方。下文将分析黑格尔眼中具体的中国形象是什么,以及民族志再翻译中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 黑格尔在对比东方世界的中国、印度、蒙古与波斯帝国等国家时指出,从各国的国运来看,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中国的国运持久与其当时的行政体制有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么,中国的行政体制,特别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经由黑格尔翻译之后是怎样的一副面貌呢?同中国历史上的实际情形相比,会有哪些异同之处呢?黑格尔是否能算得上是一名合格的翻译家呢? 黑格尔直言,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记载,中国确实是最古老的国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极古,以伏羲氏为文化的散播者、开化中国的鼻祖。他在《历史哲学》第一部《东方世界》中指出历史开始于中国和蒙古,两者都是神权专制政体的地方,把“大家长宪法”作为原则[5]119,而中国的皇帝就像地位最高的大家长。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黑格尔的眼中一是具备更多的神权色彩,二是他将皇帝比作大家长,突出皇帝在中国地位最高、一统天下而至高无上的特征。具体来讲,黑格尔认为中国社会纯粹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其国家的特性便是讲求“家庭孝敬”[5]119,因此中国人不仅在自身的家庭中秉持忠孝的品格,同时又是报效国家的儿女。时至今日,这一观点仍然适用于如今的中国。中华儿女弘扬尊老爱幼的道德风气,将国家称为祖国母亲的爱国热情更是经久不变。黑格尔把中国的皇帝比作大家长的说法虽说不常见,但也是基本符合中国当时行政体制的实际情形。 此外,黑格尔之所以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含诗意的帝国,是因为形式无限性、理想性的对峙在中国还没有发展。他认为中国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很早就已经发展到今日的情状,但因为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只能任由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代替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换句话说,在黑格尔看来中国的历史缺少所谓的“真正的历史的东西”,由于自身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之间缺少一种对峙而不能经历任何变化。具体来看,这种对峙由于客观性和主观自由的统一而全然消弭,导致物质无从取得主观性,而“实体的东西”以道德的身份出现,进而使得中国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黑格尔指出,中国这样的东方帝国具有实现理性的自由。只可惜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进展成为主观的自由。[5]111-112抛开何为这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和主观的自由,从上述中的民族志再翻译回译也不难看到,黑格尔认为中国皇帝如同一个大家长,他对中国的这种政体把握得基本正确,但又认为中国的历史停滞不前,是一个不含诗意的帝国。可见其翻译的中国形象必然与真实的情形有差别,实质上是基于其本人历史观的一种对中国形象的想象和解读。 译者与文化之间距离上的遥远使得“民族志再翻译”中可能出现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美化的现象。由于缺乏对中国官场的近距离观察,黑格尔将中国官场从上到下美化成一种理想的执政状态。他认为由于中国的天子接受严格的教育,所以中国能培养出最伟大、最优秀的执政者,从而实现自芬乃龙所著的《太里马格》行世以来,关于君主和君主教育的理想。黑格尔认为中国唯一一种孤立的自我意识便是皇帝这个实体,也就是“威权”。[5]137中国历朝历代中的确出现过不少优秀的执政者,但并不是每一位都是黑格尔口中的明君。他将中国的皇帝以及官场过于理想化了。 此外,黑格尔认为在中国只有有才能的人才可以当行政官吏,因此国家公职都由最有才智和学问的人担任。正因如此,其他国家往往将中国当做一种理想的标准,视作模范。[5]130他对中国官场缺乏全貌的了解导致片面,和其他人一起纷纷将中国的行政体制视为模范,只看到中国科举制能够积极选拔人才的一面,却因遥距万里而无从知晓中国古代官场中存在的并不尽如人意的另一面。“民族志再翻译”中出现美化其他民族文化的现象与“无本民族志翻译”中的美化是脱不了干系的。“无本民族志翻译”的译者来过中国,却并不能概览中国古代官场的全貌,可见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志式考察和了解需要深入细致全面,仅凭片面的观察和印象所进行的“无本民族志翻译”将无法真实地反映其他民族文化的实际情形。 黑格尔对中国古代行政管理的美化,基于对当时中国的人与人之间地位的美化。黑格尔认为在中国人与人之间是绝对平等的,不过因为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必然是专制主义。由于他误认为中国人之间是绝对的平等关系,所以错误地认为中国古人只要具有才能便可以谋得一官半职。由此可见,“民族志再翻译回译”中出现的美化现象也可能是互相有关联的,一种美化现象可能会促使另一种美化现象的产生。 黑格尔对中国古代行政体制的美化,也反映出“民族志再翻译”中存在将其他民族文化现象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黑格尔认为中国的行政机构古往今来大致相仿,但是皇帝却要担任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5]132-133因此,如果皇帝的个性不是最佳理想状态,整个机制都将废弛,政府也就会解体。为了说明皇帝个性对国运的影响,黑格尔更是以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为例,指出因为他的个性柔性温和,所以导致政府纲纪废弛,以至于带来暴乱,最终明朝灭亡。实际上,王朝的兴衰不管是明清之际,还是其他朝代都有着较为复杂的多重因素。黑格尔将明朝的灭亡简单绝对地归因于末代皇帝朱由检个性的柔和,就把错综复杂的政权更迭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将王朝灭亡归罪于一人的性格也有失公允。 除了上述的行政体制之外,黑格尔对中国的伦理规范也具有一定的的认识。基于对中国家国关系的考察,黑格尔发现中国有5种义务或者说是根本关系,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历史哲学》一书的王造时译本中将这5种关系注为“五常”。根据《历史哲学》一书内容可知,王造时译本是根据J.Sibree的英译本而转译,并由译者托付友人依照德文原本进行校阅。J.Sibree英译本中对“五伦”相关的对应段落这样写道“Five duties are stated in theShu-Kingas involving grave and unchangeable fundamental relations,1.The mutual one of the Emperor and people.2.Of the Fathers and Children.3.Of an elder and younger brother.4.Of Husband and Wife.5.Of Friend and Friend”。[6]由此可见,王造时译本中所出现的“五常”并不是黑格尔本人所叙述,也不是英译本中J.Sibree添加的。J.Sibree将其译为“Five duties”,而王造时翻译这部分时增加了注释。因此,王造时在“民族志再翻译回译”中将中国文化中的“五常”翻译得更加生动、清晰。在“民族志再翻译回译”中,较为熟悉该文化的回译译者可以让文本更加明晰地彰显出实际情形。因此,一方面要求“民族志再翻译回译”译者在对待自身文化时应当更加严谨认真,不要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比本土文化的译者更加熟悉他们的文化;另一方面当“民族志再翻译回译”中出现不够具体的文化现象,回译的译者应考虑对其进行补充说明。 不过,黑格尔还认为中国人在家庭中和国家内都缺少独立的人格。皇帝如同严父一般关心臣民的精神,引导他们遵守家族的伦理原则,但他们也不能自行取得独立的人格和公民的自由。中国人全体也便成为一个帝国,同时使得中国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约法具有强调道德的特点,同时又是完全不含诗意的——也就是理智的、没有自由的“理性”和“想象”。[5]129道德在中国社会一度发挥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若说这样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约法完全不含诗意,仅有理智,而没有自由的“理性”和“想象”就有待商榷。 基于将其他民族文化现象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除了美化之外,“民族志再翻译回译”中也可以窥见“民族志再翻译”和“无本民族志翻译”中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丑化。黑格尔认为中国人以说谎著名,使得欧洲人与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不得不提心吊胆。而中国人在道德上的放任还能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中得到证明。[5]136这样以偏概全的说法不能不令人觉得黑格尔关于中国人人性的看法过于绝对和简单化。在黑格尔看来,佛教中最高的和绝对的“上帝”是虚无的存在,鄙视个性和弃绝人生才是最完美的成就。[5]136由此可见,黑格尔对佛教的评价很低,认为佛教一无是处,这显然也有失偏颇。 此外,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性中最显著的特色是远离属于“精神”的一切,也就是实际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5]143另外,他称中国人不会因出生背景而存在不平等,但中国人的平等却足以证明中国人没有对内在的个人或者说精神作胜利的拥护,而只有顺服听命,还没有发达成熟到足以分清各种差别的意识。[5]143这种观点在精神层面上将中国人贬低成没有精神的生物,结合其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带有种族偏见的色彩。由于没有保持客观的立场,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与描述又存在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其民族志再翻译难以客观真实地反映其他民族文化也就不足为奇。 黑格尔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所以对中国文化也缺乏透彻清晰的认知。虽然黑格尔的翻译中提及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有《书经》《易经》《诗经》《礼记》和《春秋》等,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似乎没有深入的了解,只是笼统地认为中国人把所有文书都称为“经”,而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实际上有经史子集等分类。不过,黑格尔提到中国古代有官吏负责采集所辖地区的歌咏,并带去参加祭礼供天子评判。他对典籍中的文字内容可能并没有多深的了解,甚至可能根本没有读过这些典籍,但却知道中国曾有采诗官这样的专职人员存在。黑格尔对待中国典籍的态度更像是一个民族志的撰写者,而不是对文本内容本身的细读与分析,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具备一定的好奇心,能注意到采诗官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对采诗官所收集的诗歌,即对具体文化对象与内涵的了解又不那么深入。因此,黑格尔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了解最多只能算是一个走马观花的游客,他从中国典籍所获得的文化知识并不具体入微,只是泛泛而谈的印象。 如果黑格尔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只是一种粗浅的概括也无伤大雅,问题在于黑格尔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不熟悉直接导致他对这些典籍存在误读。黑格尔误以为《礼经》后面的附录是《乐经》,但实际上《乐经》与《礼经》一样都是“六经”中的一种。与之直接相关的另一个误读就是认为《礼记》又叫《礼经》,而两者实际上是两本不同的书籍,或者说《礼记》是对《礼经》的注解。黑格尔对中国的了解依赖于西方传教士带到欧洲的记录,而正是这些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解读也直接影响了黑格尔的翻译。可以说,黑格尔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了解不全面,与他接触的相关资料缺乏准确度直接相关。由此可见,“无本民族志翻译”与实际情形之间本身存在一定的的距离,经过“民族志再翻译”译者对“无本民族志翻译”的挪用与吸收之后,这个距离在“民族志再翻译”之中依然存在。 此外,由于上述的五伦的存在,黑格尔认为在古代中国“五”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这和西方人将“三”视为一个重要数字是一样的。除了五伦之外,黑格尔还注意到中国有金木水火土即五行这五种天然的元素,以及中国人承认的天有四方和一个中心的特点,进而使得凡是建筑祭坛场所的四角有四个坛,然后正中间有一个坛。由于天坛等祭祀场所并没有采用这种建筑结构,所以这种说法未免说得言过其实、以偏概全。黑格尔提到的五个坛说法极有可能是根据西方传教士的“无本民族志翻译”以讹传讹而得。如若缺乏对中国的正确了解,那么黑格尔所进行的民族志再翻译极其容易被“无本民族志翻译”的记载所影响,延续其中错误的见解和看法。 笔者认为,“民族志再翻译”的译者与“无本民族志翻译”的译者以他者身份去看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时,或多或少会有一种寻找与自身不同之处的猎奇心态。通过王造时回译本可以看出,黑格尔格外关注中国的各种礼制,大幅描述中国皇帝和百官朝贺,还有葬礼及家族祭祀扫墓的场景。不过,这种猎奇心态可以帮助译者通过其作品反映其他民族文化的某些特殊社会现象。比如,黑格尔提到中国有因复仇而自杀、遗弃婴孩等现象,映射出当时的中国人把自己和人类看得轻微。根据《儿童权利一般理论研究》,明清期间中国的确存在异常严峻的弃婴现象,不过为此也开始推行育婴堂和保婴会等救助婴幼儿的专门机构。[7]黑格尔对弃婴这一社会现象也没有言过其实。 另外要提到的是黑格尔在探讨中国神灵塑像问题时对中国艺术的一点看法。黑格尔观察到中国的宗教含有以人事影响天然的巫术成分,各个神灵受特殊的敬礼,并有一定的塑像。但是,他认为中国神灵的塑像与艺术的尊严无法相比,并不能代表崇高的精神,只是令人讨厌的恐怖、可怕的雕像。黑格尔并未亲眼见过中国的神灵塑像,最多见过西方传教士的“无本民族志翻译”中关于中国神灵塑像的绘图,却敢对这些塑像做出如此负面的评价,太过于信任“无本民族志翻译”中的内容。如果只是单纯地在审美上贬低中国宗教的艺术呈现形式还情有可原,但是黑格尔却将中国人的精神性也贬低到极点。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用木头降落方式决定凶吉的方式是巫术,常常将偶然的事件认作与天然有联系,因此认为中国人没有精神性。中国云南地区彝族的确有用木头占卜的风俗。[8]不过,仅仅因为占卜方式的存在就将中国宗教统统归为带有原始性质的自然宗教,还认为中国人没有精神性的观点,体现出黑格尔在评价中国宗教问题上的草率与偏颇,因而这部分的“民族志再翻译”也与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去甚远。 至于中国的绘画艺术,黑格尔对其持一种不认可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很普通,亦即在日常生活,甚至艺术方面的模仿技术高明。不过,由于中国绘画中没有远近光影的分别,在黑格尔看来中国人不能够表现出美之为美,中国人的艺术和技巧的领域中体现不出那种崇高、理想的美丽。[5]142黑格尔对中国绘画艺术的贬低带有极大的主观色彩,他纯粹从西方的绘画透视方法去评论中国的绘画艺术,并没有走出自己的固有思维和视野中,体现了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科学虽然似乎极受尊重和提倡,但是缺少主观性的自由园地和将科学当做理论研究的兴趣。中国在他的眼中是一种没有自由、理想、精神的王国,能够称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范畴,绝对地以国家或个人的“实用”需要为服务对象。[5]139纵览中国清代以前的科学发展情形,黑格尔的“民族志再翻译”也并不失真。像中国的四大发明这种科学成果,大多都是以实用为导向,或者说更多是隶属于经验科学,而没有发展出具备严密分析的推理体系。 在黑格尔看来,中国科学发展受阻的一个原因同汉字有关,他甚至将汉字视为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黑格尔直指与德文这种表音文字不同,汉字除了发音还有文字,必须要用符号来表示观念本身。第一,汉字字符本身不能用字母和音节来代表清晰的发音,单音字又常常包含不止一种意义,因此只能靠重读和发音等方式明确其意义表白分明;第二,汉字字符相比于德语只有二十五个符号,高达几千种,极不实用。实际上,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很难站得住脚。汉字乃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一大体现,说其阻碍科学发展实在过于牵强。中国近些年来在科技上的突飞猛进,使用的文字依然是汉字,这足以证明黑格尔对汉字的评价是错误的。 黑格尔还指出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但却和科学研究并没有联系。中国人虽然对于许多科学事物早已知晓,但却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比如,中国人发明火药,但其第一尊大炮却是耶稣会士所制造。颇为有趣的是,黑格尔在《中国》篇中还提到中国人过于自大,不屑于从欧洲人那里学到东西。[5]142 从“民族志再翻译回译”的内容可以看出,像黑格尔这样的“民族志再翻译”译者往往更像是一个民族志的撰写者,对其他民族文化具备一定的好奇心,能注意到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对具体的文化对象与内涵又缺乏深入的了解。由于“民族志再翻译”的译者可能直接挪用与吸收“无本民族志翻译”中的内容,“无本民族志翻译”与实际情形之间的距离可能会在“民族志再翻译”之中保持原样。因此,“民族志再翻译回译”译者应当要更加谨慎对待回译。从心态上来看,“民族志再翻译”的译者与“无本民族志翻译”的译者以一个外人的眼光看待其他民族文化时,或多或少会有一种寻找与自身不同之处的猎奇心态,进而去关注其他民族文化中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从而反映某些特殊的社会现象。距离上的遥远使得“民族志再翻译”中可能出现美化其他民族文化的现象。这与“无本民族志翻译”中的美化现象脱不了干系。而黑格尔“民族志再翻译回译”中同样也存在对中国的丑化。“无本民族志翻译”的译者来过中国,这一点说明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志式了解和考察需要深入细致而全面,仅凭片面的观察和印象,必然无法真实反映其他民族文化。从回译中的美化和丑化等现象也可以看出,“民族志再翻译”存在对其他民族文化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又使得“民族志再翻译”与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去甚远,甚至引发极大的贬低其他民族文化的弊端。
三、黑格尔民族志再翻译回译中的中国形象
(一)关于中国的行政体制
(二)关于中国的伦理规范
(三)关于中国的文化艺术
(四)关于中国的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