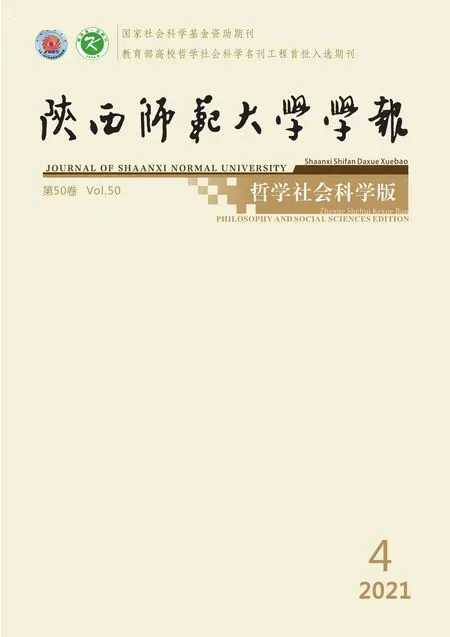让我们重新认识汉语、定位汉语
——兼论“中心论”和“扩展说”
张 振 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一、 关于汉语的类型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23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说:“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1]对此,他进一步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对于中国应该建设怎样的考古学,他用了3个词来形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言语中传递着满满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中国语言学,尤其是中国的汉语语言学,在学科性质上是最接近考古学的人文社会学科之一。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之一,是中国最具重要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中华文化之根,华夏民族之魂。因此也应该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准,来建设现代中国语言学,建设现代中国汉语学。
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汉语,重新定位汉语。以往的很多语言学教科书都认为,在语言类型研究方面有较大贡献的是德国的W.F.洪堡特(Wilhelm Freiherr von Humboldt,1767—1835)、美国的E.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R.雅柯布逊(Jakobson,Roman1896—1982)和J.H.格林伯格(Joseph Harold Greenberg,1915—2001),此外还有英国的S.乌尔曼、德国的F.von.施列格尔(1772—1829)等人。远在19世纪初期,他们就把世界语言分为3大类型:孤立型、黏着型和屈折型。后来洪堡特又增加了编插语(或称多式综合语),成为4个类型。并且把汉语、壮语等汉藏系语言以及越南语等其他一些语言归入孤立语[2]。与此同时,完全从语言语法的角度,定位孤立语为词根语,是词的形态变化比较少的语言,就是构成词的语素中表示词的语法意义的附加语素比较少。这样的词在组织句子的时候主要靠词序和虚词来表达语法关系。因此,词在句子里是孤零零的,没有一点形态变化。孤立语以外的屈折语、黏着语、多式综合语可以是有形态变化的,所以可以总称叫作形态语。更有甚者,很多西方学者把这种笼统的语言分类逐渐演变为语言进化的理论。例如洪堡特根据语法形式4个阶段产生和发展的假设,认为人类语言是沿着一条由低向高呈阶梯式发展的道路向前发展的。按阶梯式发展之说,处在第一至第四阶段的分别是:初民语言、孤立语言、黏着语言和屈折语言。这就是西方学者著名的“语言演化类型说”。
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汉语研究的某些内容是笼罩在西方学者这套理论的阴影之下的。在这套理论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危害现象。例如:(1) 盲目跟随西方理论,人为地规定人类语言发展的唯一道路,从而否定了人类语言发展演变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否定了汉语发展演变的自身规律,否定了汉语的重要性,并一定程度地遏制了中国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固有发展势头;(2) 忽视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辉煌成就,把19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笼统地称之为中国语文学,是前语言学研究阶段,进而切断了中国语言学发展的传统联系,使中国语言学部分地沦落为西方语言学的附庸;(3) 一味地模仿西方,不适当地夸大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性,用西方语言学的规范方式研究汉语语法,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些不良文风:大量引进西方理论原文,追求术语“创新”,行文佶屈聱牙。其实,我们略为仔细地审视“语言演化类型说”,很容易发现其致命的弊端。关于孤立语的定义完全不符合汉语。汉语存在大量的变音或音变现象,包括大量的调变或连读变调现象,这是一种突出的形态变化,一种屈折现象,只不过是跟英语等其他语言的屈折变化在表现形式上不一样而已。
我的学长和师友贺巍教授,2011年7月在桂林举办的一次“汉语方言学教学科研骨干高级研修班”讲学中针对“语言演化类型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汉语是属于“立体型”的语言,不同于英语等“线性型”语言。[3]他只是说汉语和英语等语言是不同类型的,但并不是把世界语言分别为只有这两类语言,也没有说到除了汉语以外,还有哪些语言是属于“立体型”的;除了英语等以外,还有哪些语言是属于“线性型”的。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学者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的态度。我非常赞同贺巍教授的主张。这是从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对汉语提出的全新的语言类型理论。从语言结构和语言形式来看,“立体型”的汉语具有以下重要的语言类型特征。
语音上一般都是音节性的,音节的数量是有限的;每个音节都是拼合的,都有声母、韵母、声调三者的组合,声韵调的数量是有限的、少数的;音节的核心是少数的主要元音,可以有零声母、零声调(轻声),但一般不可以零元音;具备声调的要素是一个重要条件,在一个固定的音节里,声调跟元音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词汇拥有多种分类,并且拥有庞大的数量;单音节词具有完整的语义因素,是词汇系统的基础和核心,它们通过前扩和后扩的有效机制,形成一个巨大的词汇库。在这个词汇库里,动词是一个最主要的部分,量词、虚词也非常重要。
语法规则是重要的,但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也不一定是最有规则的。语序相对固定,但不是绝对不变的,在口语里尤其如此。非常有意思的是,语法规则跟语音、词汇规则往往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语法和语音在构造上具有某种相似性。这种构造特点突出地显示出在汉语里,语音、词汇和语法是一个整体。
在“立体型”的汉语里,文字和语言高度一致。汉字也是立体的,基本上是上下结构或左右结构,甚至是品字结构。所以汉语和汉字可以上下读,左右读,可以实现“倒背如流”的境界。这在“线性型”的语言里是不可想象的。
二、 中心论和扩展说
上面说的都非常简单,只是“略说”而已。从方法论来说,“立体型”的汉语,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其中可以说到建立在层次分析基础上的“中心论”和“扩展说”。下面以闽语方言的词汇为例,简单说一说。
(一) 方言词汇的层次分析
方言的语音有层次问题,尤其像闽语这样的方言,需要进行语音的多层次分析,这已经是方言语音研究的常识,无须多说。方言的语法按照传统的层次分析法,当然也算是一种层次。这对于语法学界来说早已不是新鲜事。不过语音讲的是历史重叠层次,语法讲的是平面分析层次。两者不是一回事。从现在已知的语言事实来说,方言语法也是有历史重叠层次的。
方言的词汇跟语音一样,也有历史重叠层次。完全没有语义差别的同义、等义词汇就是历史重叠层次造成的。 简单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有的方言:
太阳日头月亮月头
日光 月光
日爷 月娘
就这个方言来说,“日头、月头”是一个层次,“日光、月光;日爷、月娘”是另一个层次。由邢向东、王临惠、张维佳等所著的《秦晋两省沿河方言比较研究》[4]是一本写得很好的方言学专著 ,值得一读。此书在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中,系统地提出“底层词”和“上层词”的比较概念。此书指出,底层词的标准依次是:分布的普遍性、土俗性、古老性。普遍性是必须条件,土俗性和古老性是伴随特征。例如:
底层词上层词底层词上层词
早烧“烧”去声早霞 葱头 洋葱
晚烧 晚霞 蛾儿 蝴蝶
木植 木头 胰子 香皂
肥指人胖 洋碱 肥皂
藏 抬 把式 内行
老汉 男人 烧酒 白酒
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两个层次的词汇分析法,比起其他方言著作里一般性的讨论方言词汇,有了重要的进步。我由此得到启发,用来分析福建漳平(永福)方言,好像两个层次不够,应该用“底层”“上层”和“表层”3个层次才能满足需要。举例来说:
底层上层表层
做风tso21hoŋ24,起风k‘i31hoŋ24刮风kua55hoŋ24
凝冰gan22pan24冰pin24
天时ti‘24si22,天色t‘i22sit5天气t‘i24k‘i21
落时缝lo53si22p‘aŋ21,赴时hu21si22准时tsun31si22
年科ni22k‘o24冬情taŋ24ts‘in22,冬成taŋ24sin22
铰剪ka24tsian31,铰刀ka24to24剪刀tsian31to24
位祖ui53tsou31乡里hiŋ24li31


灰hue24涂粉t‘ou22hun31,飏埃gioŋ24gia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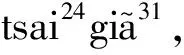
以上3个层次里,“底层”是本方言的远期固有词;“上层”是本方言的后起衍生词或早期周边方言借用词;“表层”是近期通语借用词(有的经过适当改造)。
跟语音的层次一样,方言的每一个词语都可以归纳进入这3个层次。在我的方言里,词汇的层次划分是跟语音层次的划分大致上是相对应的。
一般来说,3个层次的词语在数量上应该形成枣核型:中间大,两头小。方言词汇是由这3个部分组成的。
因此,底层词只能见于早期文献,或根本无文献可查,方言的通行范围相对小,方言特征词往往见于底层词;上层词是后来衍生的,文献可见性大,方言通行范围也相对大;表层词一般汉语词典几乎都能见到。
(二) 整理词语的中心词和扩展词
语言的词语是由中心词扩展构成的,中心词是基础,要分析出中心词和它们的前后扩展形式。
就汉语来说,中心词大多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多音节的;扩展可以是一次扩展,也可以多次扩展。多次扩展就成为词组,有的也成为短句。广而言之,汉语的句子都是词语扩展形成的。还以漳平永福方言为例:

前扩:好天 □bai31天天气不好日头天晴天反天变天落雨天 乌暗天
后扩:天气 天色 天时 天地 天顶 天舷天边天晴 天星 天虹

前扩:项物 无物看伊~:瞧他不起有物看伊~:瞧得起他
后扩:物件 物空物品
路lou22
前扩:上路 下路 大路 细路小道山路仔 公路 火车路 水路
后扩:路途 路头 路尾 路岭山岭路当央 路街街道路口 路后
墟hi24
前扩:赴墟去集市上墟 落墟 出墟 去墟 下墟下一个集市日寻墟上一个集市日
后扩:墟坂市场墟市 墟场 墟里 墟日 墟头日集市的前一天墟了日集市的后一天
日头lit5t‘au22
前扩:大日头 出日头 无日头 曝日头晒太阳
后扩:日头鬼 日头影 日头天晴天
睏k‘un21
前扩:爱睏 大堆睏长时间睡坦直睏仰着睡坦横睏横着睡伏落睏俯着睡
后扩:睏眠睡觉睏床 睏椅躺椅睏[勿会]去睡不着睏醒睡醒了
以上的例子中,“天、物、路、墟、日头、睏”等都是中心词。离析方言的中心词也是词语研究的基础。没有中心词就谈不上扩展的问题。
要特别推荐一本书,就是陆志韦编纂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5]。 陆志韦是音韵学家,他的音韵研究也许还有瑕疵,但这本著作却是难得一见的学术精品,它基本上采用“同形替代”的办法来确定“词”,例如:
我吃饭 我吃饭
他吃面 我盛饭
猴儿吃花生 我煮饭
……… ………
在左边的那些同形式的句子里,我们把“吃”从它的环境“我……饭”里提出来,又把它搁到同形式的环境里,“他……面”“猴儿……花生”里。
在右边的句子里,又用别的成分把“我……饭”的空隙补上,可以补上“盛”“煮”等。 “吃”是一个独立的成分,就是一个“词”。这个词可以是单音的,也可以是双音的或多音的。如果是双音的或多音的,就要看看有没有办法再分离出单音词。
这个办法当然很复杂,很多情况下要跟语法因素,如词类、虚词、成语分析等等联系起来考察。这本书就是通过这么一些办法,分析出北京话的单音词,主要是名词、变化词(动词)、形容词等。大约1 000来个,每个词都附上了口语的例句。 这些单音词是北京话词语和句子的基础。单音词的前后扩展形成多音词或词组,多音词或词组的前后扩展形成句子。
(三) “中心论”和“扩展说”
上面我们举了简单的例子,说说方言词汇研究中的层次和中心词问题,只是提起话题而已,大多语焉不详。借着这些简单的例子多处提到“中心”和“扩展”的字眼。这个也是受到贺巍教授的启发的。上文提到他在一篇《汉语语法语音构造的相似性及其差别》的重要文章里,提出汉语语音和语法的相似性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独到的见解,用时髦的话来说,应该是一种理论创新吧!
我于是加进词汇的讨论。在汉语里大体上可以这么说,以主要元音为中心,前后扩展而成音节;以单音词为中心,前后扩展而成词汇或词语;以动词为中心,前后扩展而成句子。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音节是由主要元音扩展来的,词汇或词语是由单音词扩展来的,句子是由动词扩展来的。
可以把这个意思概括成“中心论”和“扩展说”。用这个说法可以把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一个系统,可以有效解释汉语的整体性,证实汉语是一种“立体型”的语言,相对的是“线性型”语言或其他类型的语言。
三、 余 论
我们从批评西方学者的“语言演化类型说”开始,主张重新认识汉语,重新定位汉语,进而说及“中心论”和“扩展说”,多少有点挑战现有理论的味道。一种理论的形成,并且为学界很多人所接受,自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有的理论还是可以挑战的。
例如很多语言学家认为人类语言最早起源于非洲,然后再由今阿拉伯半岛向东到亚洲腹地一直到东北亚、向西到欧洲大陆扩散。这是语言起源一元论的观点。但2015年10月15日,中国科学院多位研究员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宣布在湖南道县乐福堂乡福岩洞古人类遗址发现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表明8—12万年前,现代人在该地区已经出现,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这对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提出了挑战,当然也就对人类语言的起源提出了挑战!人类语言起源多元论的理论,更容易解释人类语言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又例如中国科学家2019年11月29日在距离地球约1.5万光年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巨型黑洞LB-1,其质量是太阳的70倍。根据目前大多数恒星演化模型,这种质量的黑洞甚至不应该存在于我们的星系中。这个黑洞的发现,使得相关理论家们不得不接受挑战,要去解释一下这个巨型黑洞是怎么形成的,这就需要突破原有理论的底线了。自然科学界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界也是如此。
语言类型的分类,至今为止还都是西方一些语言学家的专利。其实,就汉语而言,中国语言学家对之具有更多、更深刻的了解。我们需要放开固有的语言理论束缚,逐步建立中国的语言观。并不是欧美的就是先进的,语言学的接轨应该是双向的,不是只能向西方接轨。要实事求是,尊重语言事实。汉语研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征,摆脱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束缚。汉语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对汉语的认识和研究,本来就走着自己的道路,我们现在只是主张继续走自己的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