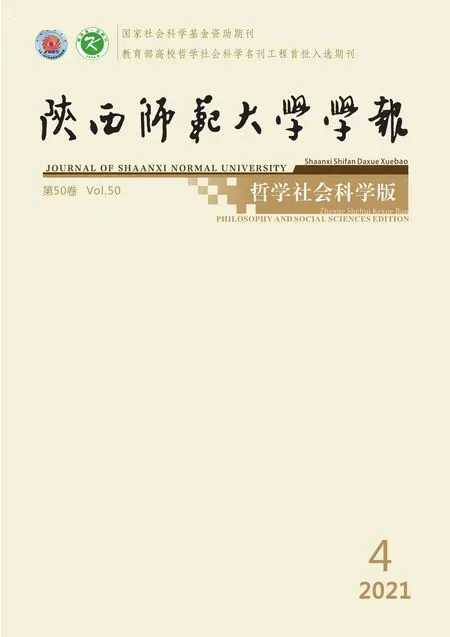论加略利汉语辞书编纂的基本特征
王倩茹, 胡范铸
(1 上海体育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上海 200438; 2 华东师范大学 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传教士双语辞书的编纂和出版始于明末而盛于晚清,19世纪以传教士为主体或主导编纂了70多部中外双语辞书[1]。这些传教士的辞书,采用不同于中国传统辞书的编纂理念, 不但促进了中西辞书编纂的互动交融,更构建了一种与中国自身传统知识体系迥然不同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其中,加略利的《字声总目》(SystemaPhoneticumScripturaeSinicae)[2]和《汉文总书》(DictionnaireEncyclopédiquedelaLangueChinoise)[3]可以说是重要的代表著作。
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1810—1862)是意大利—法国汉学家,1835 年离开法国被派往中国和朝鲜传教,1836 年到达澳门。加略利作为新教第2次入华的先行者,像大多数传教士编写汉语辞书的经历一样,编写辞书也正是其学习和整合汉语的过程。历经七、八年后, 他于 1841 年编纂汉语—拉丁语字书《字声总目》,1842年编纂汉语—法语《汉文总书》, 旨在驳斥当时欧洲“中国文字落后论”的观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之的研究和认识还较少。本文试图探索早期传教士在汉语知识学习、查阅、搜集、整理、运用上的特点,思考该文献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 以声符、义符系统识记汉字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辞书编纂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编什么和怎么编;但对传教士来说,识记数量庞大、陌生的“汉字”是西方传教士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内容。怎样找到汉字的规律,把大量看似毫无联系的汉字知识块快速地纳入他们已有的知识体系当中,并能迅速识记大量的汉字,这对以字母为文字的西方人来说是必须思考的问题。为解决汉字的识读问题,早期耶稣会士利玛窦创制了“拉丁字母注音方案”,其对在中国生活的汉字初学者效果显著,有利于传教士记音、查阅字义。但是,这种方法还存在一定的识读困难。一方面,由于早期传教士来自西方不同母语国家,他们记音和读音的方式略有不同,即使使用拉丁字母拼读法,也需要专业化的拉丁语知识才能顺利检字。如果遇到同音字,他们还是无法准确地获知字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部首检字法,在同一部首下的汉字太多,其字与字之间的形义关联性小,对传教士群体来说,也不是识记汉字的有效方法。
为了找寻识读汉字的有效方法,加略利从汉字的可拆分性入手进行探索。一方面,他受其老师——葡萄牙传教士江沙维(Joaquim Afonso Gonalves,1780—1841)和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的启发,又接受了“埃及学之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ois Champollion,1790—1832)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结构的一些做法,综合影响了他对汉字结构的认识。另一方面,宗教传播需要解决《圣经》的翻译和印刷问题,而当时印刷使用的木字模具有易损性和不易拆分的缺点,这直接引发人们对于金属活字模的开发。再加上金属字模造价比较高,需要提高金属字模的可利用率,综上情况进一步引发了西方学者对汉字可拆分性的研究,加略利便是其中的研究者之一。加略利在江沙维老师的帮助下,挑选当时常用的汉字,归纳出其声符。1841 年他在老师江沙维的帮助下编纂完成书籍《汉语发音书写系统》(SystemaPhoneticumScripturSinic)[4],从书名就表明“发音”和“书写”是该字书的两大目标。随后该书在澳门印刷出版时命名为《字声总目》,其定位的目标群体是不同国籍的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学生。该辞书的编撰体例和特点如下:


3. 区别不同字体、列出汉字笔画便于识字和书写。汉字有不同的字体,且同一个字存在几种不同的异体形式,这些都是传教士识读汉字的难点。加略利在字书《字声总目》的前言和《汉文总书》的宣传册中曾道:“目前我们不仅要识汉字的隶书(Modernam Classicam), 还要识汉字的传统字体小篆(Antiquam Classicam),尤其要认识草书(Modernam Cursivam), 因为草书是世人和商人唯一使用的字体。”[3]Ⅳ因此,《字声总目》的 TRIPLICEM SCRIBENDI MODUM 部分列出了每个声符的 3 种字体。在汉字基本笔画方面,加略利使用了其汉语教师江沙维的 9 个基本汉字笔画,作为其字书排序和检字的依据,见表 1。

表1 江沙维的9个基本汉字笔画
他把发音相近,字形相近的汉字汇总起来并按笔画由少到多排列,便于传教士识记。
可以说,加略利编撰的字书打破了中国传统字书按韵或者按部首分类的标准,探索了新的编排体例,即依声符而分,同声符下的字又按 9 个基本笔画为检字顺序,满足了当时传教士群体对字书查检和教学的功能需求,建构了以声符和义符为属性的汉字知识块,有效地帮助初学汉语的传教士解决了汉字发音和书写识记的问题。虽然他的学术主张没有得到巴黎主流汉学界的认同和支持,但他得到了在中国本土的传教士群体以及域外传教士汉语学习群体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促成了《字声总目》“笔记式字典”的出版。(1)此书的出版由喜欢中国文字的商人颠地(Lancelot Dent,1799—1853)赞助出版,而不是巴黎官方汉学界出资出版的。由此可见,这部字典是以市场需求和受欢迎程度为导向的。
二、 以核心词素建立词汇网络
加略利的《字声总目》基本解决了汉字的语音、识记和书写的问题。随着学习的深入和表达上更高的需求,他体会到单个汉字在汉语表达中的制约性,意识到词和词组才是汉语使用的关键问题。于是他萌生了依照《佩文韵府》为底本,出版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汉语词典的设想,由此诞生了《汉文总书》,该书原计划编辑 20 卷,每卷 600 页,但由于市场受限, 只出版了1卷便戛然而止。
如果把词典单纯当成查找汉字形音义的工具,遵循“词典工具论”,就会割裂字与字、词与词之间的联系[5]。中国传统的字典编排体例虽然便于快速地检索汉字的音义形,但同时也割裂了词与词之间的联系,把每个词都孤立了起来,造成了词语体系的碎片化。但对于西方人来说,除声调外,汉语字、词和短语的切分一直是他们学习汉语的难点之一。加略利意识到词和词组,以及词组背后隐藏的中国文化典故才是理解汉语和深入了解中国的最佳途径。所以,他尝试解决词和词组的认知和表达问题,试图有序分组并建立字、词和词组之间的关系网。他在《汉文总书》英、法文宣传册指出:“汉语比起任何一种东方语言更像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的语言。如果汉语学习者不完全了解这些语言事实、风俗习惯和修辞原理是不可能理解汉语的。”[3]Ⅳ加略利在宣传手册中列出 3 个声符作为样例:“妻”“军”“童”。如“妻” 的编撰体例如下:
首先,用法语介绍“妻”的词源意义,标出“妻”做声符的读音,并标出以妻为构件的汉字和词语数量。“妻”声符下的汉字不多,只有3个汉字“妻、淒、悽”;其次,列举出“妻”声符的 3 种传统字体:楷书、小篆和草书字体,并在下边用欧式标音法标注:官话、广州话和福州话3种发音;再次,解释“妻”在汉语文化中的意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特殊文化现象。
在中国古代“一夫多妻”的制度下,妻子是以丈夫个人财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媒人”在婚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男子纳妾及买卖小妾的价格由其年龄、相貌、脚的尺码、育有多少子嗣等来决定,等等。如上他大量列举这些特殊的、易于引起目标使用群体兴趣的文化现象。接着,他还列举出以“妻”为核心词素的词和词组,并说明三字格或者四字格“妻”的词或词组,其中169 个词或者词组中,1—50为二字格,如“女妻、归妻、寡妻、令妻、两妻”;51—162为三字格,如“负羁妻、伯宗妻、舌示妻、买臣妻、糟糠妻”;163—169为四字格, 如“柳下惠妻、百里奚妻、四十九妻”等。且列举后以脚注的形式解释每个词的具体意义和典故出处。由此,辞书学习和使用者便能建构一个以“妻”为中心的字网、词和词组网络、中华典故网络[6]4。
加略利《汉文总书》词条的编纂方式与“逆序词典”有相似之处。“据有关材料介绍, 逆序词典的始祖是中世纪13—14世纪阿拉伯的古典词典……我国清代编写的《佩文韵府》, 就排列方法来说,与逆序词典颇有相近之处。”[7]逆序词典,顾名思义是词目的尾部按一定顺序的编排,拼音文字为最后一个字母,汉语以词或词组的末字为音序或者形序来编排。逆序词典有助于查阅同词尾的词,对于学习构词方式和词汇的教学意义显著。加略利结合音序和形序两者,构建声符“妻”的同音和类义网络,对二语学习、课堂教学以及教材生词的编排都有一定的启发。
加略利的《汉文总书》试图给学习者梳理和总结现行通用的大量常用词汇,便于学生分组记忆查阅或者演绎推理,掌握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而推测、理解新词语的含义。在加略利的汉语词典中,汉字不再是孤立的存在,每个汉字不仅构成了同音字、类义词网络,还形成了字、词、词组、句子、文化典故的网络系统。这些理念在纸质辞书时代的确比较难以实现,加略利的《汉文总书》原计划为 20卷,最后只编写和出版了 1 卷。但是,这些理念为电子网络时代的辞书编纂提供了可能,为外向学习型汉语辞书或者对外汉语教材提供了编纂理念和方向。如欧美汉语学习者常使用手机 APP 中的 PLECO,该词典的开发者是来自美国纽约的汉语学习者——程序员麦克莱武(Mike Love), 他的电子词典的编纂理念同 19 世纪的加略利不谋而合。尽管 PLECO 义项排序层级缺乏科学性,词汇难易度混乱,语言知识有错误等,但该词典依旧受到欧美学生的青睐。因为该词典是以学习者的角度出发来编纂的学习型词典。
三、 以口语手抄本描绘民众日常生活
马礼逊的《华英字典》首次在释义中使用汉语中的成语和谚语,改变了在字典中仅引经据典的传统,开辟了在字典中使用白话文的先河。自此以后,使用这些辞书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无论他们是否在中国生活过,都能接触到大量中国民间流传的日常用语。在西方传教史上,传教路线中的“上层路线”与“下层路线”始终并存:“基要派”主张采取传统的“直接布道”方式,直接面对下层民众宣讲教义,分发宗教印刷品,以教徒和教堂的数量为衡量传教工作的标准;“自由派”主张“间接布道”,重视文字的工作,创办报刊、杂志, 翻译编纂汉语书籍,建立西医医院和西式学校,希望逐渐使中国的统治阶层意识到西方的先进性,实现基督教自上而下扩展,即从统治阶层到一般民众。19 世纪 90 年代前,“自下而上”的传教路线占领主导地位。19 世纪初新教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国土后面临的是目不识丁的寻常百姓即传统社会的底层民众,直接布道的传教方式促使了民众口头领域知识体系的文本化。大量宣讲教义的小册子出现,被印刷和分发给普通民众。《圣经》的口语体译本包括白话文译本和方言译本就是为了适应“自下而上”传教政策的需求应运而生。有学者认为“自上而下” 的传教路线主要是采取文化和科技传教,针对的受众是士大夫文人群体;“自下而上”的传教路线主要是采取药理和奇物等基础科学知识的普及,针对的是下层民众。然而,不论何种传教政策,都生产出了大量的文本材料。由于书籍是传教士最便捷高效、影响深远的传教方式,因此,推动了新闻报纸、杂志、辞书、翻译等行业的发展。诚然,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面对和使用的文本完全不同[8]277。
与社会底层民众直接面对面交流的需要,使当地口语学习的需求产生了。传教士作为当时西方的知识分子阶层,把这些口语语料记录成文本的形式成为可能。一些学者认为可以通过明代的日用类书或者明清曲本来考察中国民间知识和生活系统。我们认为,任何知识群体在把口语转写成文本时,都会带有该群体的烙印。明代的日用类书、清曲文本、口语手抄本与传教士记录和翻译的口语材料都是民间知识和生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可以彼此形成互文。《汉文总书》英、法文宣传册在陈述辞书的改进和创新部分第 9 条中有言:“尽管现存汉语辞书具有完整性和覆盖面广的特点,但是在中国日常生活的语言是不受尊重和绝不入册的。然而,每个到中国的人都发现口语的需求先于书写,口语的习得大大有助于书本的理解。我们认为实用性应该战胜偏见,因此,我们在辞书中加入了大量的日用表达。”[3]Ⅻ早在加略利的字书《字声总目》中就已经有了这样先进的理念,第 9 章题目为“各种职业口语手抄本附欧语翻译”描绘出了民间日常生活的文本,例如:
(1) 大人上了山。/(2) 工人下了山。/(3) 今日干戈止了。/(4) 幼子生了半个月。/(5) 交互合同了。/(6) 吾兄弟考中了秀才。(7) 幸妻子有生育,免了立妾。(8) 知府可以上本言民生之事。(8) 那个卷文字重复不少。/(9) 疾了多时,不能乘马。(10) 阿兄失了阿弟金子,兄弟两个去告官府。(摘自加略利《字声总目》)
显然,随着交往的深入和交际的新需求,字、词、词组的认知和学习无法达到直接与民众当面交流的需求。编者把这些语料如实地记录了下来,为研究当时的民间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语料。无疑第 9 章的各种职业口语手抄本记录下了民间生活的鲜活图景。随后的《汉文总书》典故文献引用目录中也涉及了大量包含口语语料的作品。例如,字书类有东汉末年服虔所撰的《通俗文》,保留了当时大量的口语、俗语成分。“《通俗文》所收语词很多上承《说文》、下启《现代汉语词典》,属常俗用语。”[9]儿童启蒙教材类有《急就篇》,分为姓氏、言物、职官3部分7字一句,朗朗上口;《名贤集》作为古代社会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教材, 取材大部分来自社会民间,反映了当时社会民众的人生经验和心理愿望;西汉王褒《僮约》又名《责髯奴文》是用古代白话文写的一位叫“便了奴”的卖身契,反映出当时民间社会上买卖奴婢的情况和西汉的经济状况;《岁华纪丽》《风俗通》等类别的记录民间节日文化风俗的书籍,记载了民众多姿多彩的岁时民俗生活。此外,还有大量笔记体小说、志怪传奇、人物传记、接近口语的诗歌等等,涉及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建构了立体鲜活的民间生活图景。“虽然在现代学术语境中,‘民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民间’本身是现代意识的产物,因此,从历史的维度看,‘民间’的存在方式,包括民间公共知识体系的建立并非依赖文本,而是通过宗族、语言、信仰、服饰、建筑、游戏、习俗等等非文本形式为载体传承的,这就使得在做相关研究时,首先需要解决文献资料的问题。”[10]民间知识体系主要以代代相传为主要方式,以口语为载体,以文献资料和民间日用类书为代表。加略利记录或者引用的口语语料或者文献材料无疑丰富了现存的民间知识的总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民间社会的特殊视角。
四、 以引用文本的目录建立中国文化全景图
加略利曾经在《汉文总书》的前言中提到:“当他认为词组和短语无法理解深刻内容的时候, 他就从最优秀的作品中选择例子,以解释意思和支持译文。挑选引用时,尽量给出不同的文体。让学习者体会到汉语写作的方式以及汉语历时发生的变化。”[11]Ⅲ-Ⅵ这些“优秀的作品” 便是以加略利为代表的传教士眼中的中华文化的总汇和缩影。
作者引用的汉语文本以汉语文献作品和作者的姓名编成目录,以独特的双字母大小写排列组合的编排方式(1.AA,2.Aa,3.aA,4.aa,5.aa)标明引用典故的位置。不同于《佩文韵府》,该词典的使用者可以依据双字母标注找到典故的源头,了解每个词或者词组产生和使用的年代和文本。“双字母标注法”是加略利历时两年研究并实现的。所选汉语文献文体包括:乐府诗、歌行、绝句、檃括、联句、问答体、小令、隐括词、骚体赋、七体、问对、连珠、叙记、制书、檄文、表文、启文、对策、札子(劄子)、露布、尺牍、帖、笺、颂体、赞体、题跋、座右铭、家训、碑记、诔文、小品文、语录体、笔记体、神话、志怪、唐传奇等等。除传统的诗词选编外,作者注重刻意尽量选取同一作者的不同文体,如编者选取了柳宗元 22 种文体之多。选取文献的作者身份阶层包括:皇帝、宰相、女性文人、传教士,僧人、少数民族作家等等。加略利的文献篇目的选择则有以下特点:第一,除去词没有细分以外,加略利把乐府、歌、行、联句、谣、曲、隐栝、鼓吹、问答体,联句等从大的诗类中列出,与诗的地位平行。第二,选取辞赋类包括骚体赋、大赋、小赋、七体赋、九体赋、难体赋、问对、连珠、骈赋、律赋。且极力推崇七体赋。第三,散文中除选取常见的论体文外,还注重上行、下行公文和日常应用文的选取,其中涉及制书、敕书、教令、檄文、表文、启文、对策、札子、尺牍等。第四,包括大量碑文、书信、史料笔记、笔记体小说,志怪小说等,并把其作为与诗词歌赋同等重要的文体列入文献目录。第五,选编了大量的书法、绘画、中药学、植物学、地理类和谱录类著作。
加略利编写辞书的第一目的是为来华传教士服务,必然在辞书中涉及一定数量的天主教词语,加略利自己也曾提到他在《佩文韵府》的基础上添加了白话和天主教的词语。不过, 与此同时,加略利的辞书中还选编了大量佛教著作。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佛教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是加略利所代表的传教士群体的重点学习和模仿对象。从引用典籍的书目表来看,佛教部分涉及的书籍篇目有:佛教得道高僧的传记《莲社高贤传》, 大乘佛教论书《中论》,佛经《图觉经》,佛教禅宗理论著作《宗镜录》,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佛经《法华经》,佛典《净住子净行法门》,佛教著作《洛阳伽蓝记》,佛教史书《高僧传》,佛典注疏《心经注》,佛教禅宗史书《五灯会元》,佛教经典《楞严经》,佛教经典《譬喻经》,佛法的根本《阿含经》,佛教辞书《翻译名义》,佛教禅宗史书《景德传灯录》,佛教地志《佛国记》,佛教大乘经典《维摩诘经》,佛僧传记《指月录》。此外, 还有大量的佛僧诗歌和碑铭文等文献。佛教著作涵盖佛经、高僧传记、佛经序文、佛典注疏、佛教辞书、佛教地志,高僧创作的诗歌、记录寺庙佛像的铭文、记体文等等。
除佛教各类书籍外,道家和道教思想的书目也遍布于文献目录。加略利尝试把辞书编纂的理念与百科全书的理念相结合,因而未完成的《汉文总书》又命名为《汉语百科全书》。这为我们研究早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全景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加略利的《汉文总书》所引典故的文献目录隐藏着试图构建一个融合东方与西方、贯通传统与现代的知识分类体系。
中国传统的文献分类体系“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以书目设类别。“知识决定行动,行动生产知识。”[12]加略利的文献分类法并没有否认中国古代“依人立类”和“依文献体裁分类”的原则,除借鉴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以外,还引用了现代西方的知识体系,“经部”“史部”和“子部”的书籍在地位上集体降低,成为与诗歌、小说和戏曲地位等同的文献。这样的目录呈现方式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献秩序,弱化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因素造成的分类结果。他尝试从知识总体高度,把宗教学、植物学、药物学、书法学、绘画学、历史地理学、养生学、谱录类书籍、围棋论著等著述从传统分类结构中分离出来,用西方知识体系融合和重组他记录的汉语文献,这对中国社会的知识现代化的萌芽和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加略利的《字声总目》和《汉文总书》第 1 卷作为 19 世纪传教士汉语辞书编撰的一件历史“事实”,更是中西语言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而其之所以实现“从事实向事件的转化”[13],就在于他充分关注汉语的基本特点和中国知识的整体风貌,把辞书作为字书,以声符、义符系统记忆汉字;把辞书作为词典,以核心词素建立词汇网络;把辞书作为口语语料库,以口语手抄本描绘民众日常生活;把辞书作为中国知识总汇,以引用典故文献的目录建立中国文化全景图。与此同时,还在标注汉语语音系统的读音时,列表标出每个声符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和英国6个不同欧语国家的发音,以尽可能适应不同国家来华传教士的需要;而对具体汉字标注时,又不但会列举楷书、小篆和草书 3 种字体,并在下边用欧式标音法标注了官话、广州话和福州话 3 种发音;以尽可能适应传教士面向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沟通的需要。由此,体现出别具一格的加略利式“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词典编撰思想, 时至今日,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建立编纂外向学习型汉语辞书或者对外汉语教材的理念和原则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